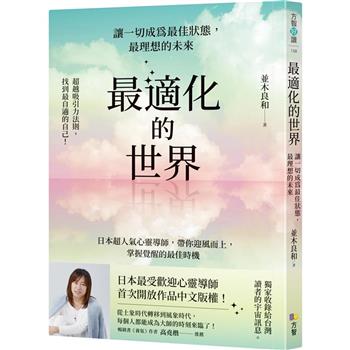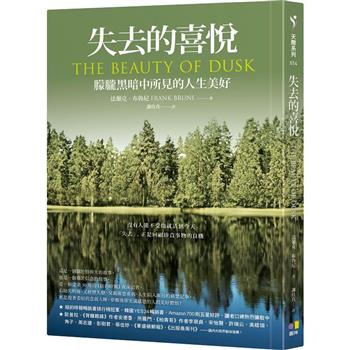●迷失在字裡行間
公眾語言(public language)至關緊要。文字免費供應,政客、記者、市民取之不竭。卻有論述者發現自己必須決定未來走向,用字必須精審的關鍵時刻。長久以來,領導者、評論者、行動家,或者理帶同情,或者能言善辯,不僅從人民的情緒中汲取養分,甚或影響情緒的形成。結果呢?和平、繁榮、進步、不平等、偏見、迫害、戰爭,不一而足。公眾語言,因此,至關緊要。
這當然也是個公眾語言的時代。尤有甚者,我們正歷經一場無與倫比、尚待開展、猶未定型的公眾語言蛻變。在我們考量、辯論現代政治與媒體的實況——政策與價值如何被討論、決策如何成形——依舊傾向認為公眾語言或修辭,只需順帶一提、只是某種興趣,頂多能協助我們了解旁枝、釐清基礎概念。而這本書的論點是,公眾語言——我們討論政治與政策的語言、在法庭上辯論,或者在公眾領域裡,試著說服他人——本身就值得檢視。修辭,有關公眾語言的理論與實務,一度被認為最重要的人文學科。如今,它養尊處優,卻是面目模糊;而我即將要把它重新推上王座。
二○○九年七月十六日,前紐約州副州長貝希.麥考伊博士(Dr. Betsy McCaughey),出現在佛雷德.湯普森(Fred Thompson)的廣播節目中,評論當年夏天最熱門的政治議題: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引發爭議的美國健保改革計畫。這個計畫試圖納入成千上萬沒有健保的老百姓。
這其實不是麥考伊擅長的議題。她是哥倫比亞的歷史學博士(讓她得到了Dr.頭銜,聽起來好像跟醫學界有關),靠著非凡的智慧,從匹茲堡的平民家庭出發,成為美國右翼重要的公眾人物,被認為是健保政策的專家。一九九○年代,民主黨嘗試改革健保,出師不利,她猛烈抨擊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健保,展現法庭辯論的凶悍氣勢。歐巴馬健保卻是迥然不同的提議——基礎原則反而接近共和黨的設計,或者曾經施行過的政策。更尷尬的是,歐巴馬健保跟密特.羅姆尼(Mitt Romney)擔任麻塞諸塞州州長期間的做法,異常相似。麥考伊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羅姆尼已經開始爭取總統提名,準備在二○一二年迎戰歐巴馬。
但是,麥考伊卻悍然不顧歐巴馬健保跟共和黨的主張,有思維上的血統關聯,仍然墨守意識形態的立場。在接受由律師轉任電台主持人的專訪時,她也不曾面對嚴謹的交叉檢驗。早在歐巴馬進入白宮之前,美國的政治已經向兩極分化,媒體議論政治,各有立場,選邊站。秉持反對意見的人,恕不邀請——但他們可能集結在另一邊的演播室,把自己帶進意識形態的舒適圈,作繭自縛,減輕面對衝突的危險。
就表面來看,這種遭遇戰也沒什麼——政治氛圍、名嘴、特定偏好與討論取向——罕見之處。但是在那一天,麥考伊卻發表了前所未聞的說詞。當時,歐巴馬健保計畫正送交國會審議,但她竟在草案的深處,找到了沒人注意卻暗藏凶險的提議:
草案爭議,不一而足,但我認為最駭人聽聞的規畫,出現在第四二五頁,其中規定,國會有強制權力……每五年,要求健保參與者接受諮詢會議,告訴他們如何提早結束生命、如何斷絕營養與水分、如何接受收容照顧⋯⋯這是生死攸關的神聖議題。政府不應該介入。
這段談話有兩個地方必須說明。第一,指控不實。麥考伊說的法案,應該指的是一二三三條,並不是召開諮詢會議,強制「終結生命」。諮詢會議必須由投保人主動要求才能召開。草案設計的目的是把諮詢會議納入健保,由聯邦保險項目支付相關費用。
雖然麥考伊的評論純屬虛構——事實上也招來立即與果決的否認——卻無法阻止它搜刮眼下的現實利益。這牽連到第二個更有趣的重點。終結生命諮詢條款,在先前,曾經短暫獲得兩黨的初步支持。但在麥考伊語出驚人之後,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保守派評論者與諸多共和黨知名政客,包括眾議院少數黨領袖約翰.貝納(John Boehner),便尾隨在她身後,展開一輪猛攻。論述開始膨脹。電台主持人蘿拉.英葛翰(Laura Ingraham)引用她八十三歲老父親的反應,宣稱「我不想讓任何一個政府官僚告訴他,想當個好公民,就得接受怎樣的治療。越想越恐怖。」當部分右派評論者與政客,大肆嘲笑、揶揄一二三三條中的「神話」或是「騙局」成分——MSNBC的「早安,老周」(Morning Joe)談話節目——周.史卡波洛(Joe Scarborough)開始追進,將一二三三條說成「死神條款」——在政治光譜這一端的保守陣營,自然不認為麥考伊的說法是神話,一口咬定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八月七日,裴林在臉書上,貼文加入戰局,其中包括了這樣的敘述:
我所知道與深愛的美國,不會讓我罹患唐氏綜合症(Down Syndrome)的父母或子女,站在歐巴馬的「死亡陪審團」(death panel)前,讓他的官僚根據主觀的判斷,決定他們在「社會中的生產水平」是否值得接受健康照顧。這種健保系統根本就是造孽。
接下來的發展眾所皆知。隔沒幾天,這個新鮮炮製出來的「死亡陪審團」,立刻滲入美國的每個角落;狂熱的敵對陣營大力駁斥,卻在無意中造就了難以避免的結果,導致這個名詞更加流行。八月中,皮尤(Pew)民意調查顯示,有不少於86%的美國人聽過這個名詞,30%的人相信確有其事——其中共和黨人占了47%,另外20%的受訪者無法確定真假。
儘管一再否認,卻有越來越多的人執意相信,接受歐巴馬健保,等於接受強制性的「死亡陪審團」,蔓延趨勢難以遏止。幾個月之後,民主黨放棄了這項基本原則。二○一二年,歐巴馬政府再度觸及由健保支付「生命終結諮詢」的可能性,污名化的標籤頓時蠢蠢欲動,迫使提議迅速作罷。二○一五年夏天,當局宣布,經過深入的研究與諮商,健保傾向支付「生命終結諮詢」。可想而知的是:麥考伊立刻在《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上宣稱:「『死亡陪審團』捲土重來。」
一個誇大不實、極盡扭曲的名詞,完全與歐巴馬健保的核心理念沒有任何關係,卻改變了政治的軌跡。事實上,這是許多美國人在憶及健保辯論時,唯一有印象的焦點。老牌的保守派評論者派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評論裴林的表現時,不減煽風點火本色:「這女士總是知道如何創造議題。」
在這齣政治鬧劇中,且把我們對於主角的觀點放在一邊,也暫且不管健保與政治,單從修辭學的角度來考慮「死亡陪審團」。什麼原因讓這個詞瞬間爆紅?為什麼這個名詞成功的形塑了健保辯論?更重要的是,這個現象能不能告訴我們,我們的公眾語言究竟怎麼了?
●我們失去事物真正的名字了
無論落在政治光譜的哪一點,都有越來越多的人發現:我們的政治以及政治議題的辯論與決策方式,已經走上歧路。從美國、英國到其他西方國家,無一倖免。批評民主粗糙喧鬧,已經是老生常談了——從柏拉圖(Plato)到湯瑪士.霍布斯(Thomas Hobbes)都一再論及。現在卻有充足的證據,證明憂慮並非空穴來風。
我站在BBC與《紐約時報》的制高點上,看著全球金融危機逐步開展。我很訝異的發現,每個人——政客、記者、學者——都在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某些人受到的衝擊特別嚴重?解決方案是提出來了,政客或者促銷,或者排拒。每個月都有經濟數據發布。在各種媒體上,充斥著過量的新聞、評論與辯論。
林林總總的措施與訊息,很明顯的跟公眾脫節。不僅僅是一般老百姓難以測量這次危機的幅度——多數的政治與媒體菁英也是霧裡看花。許多人索性放棄了解現況的努力。菁英之間的討論,充斥著華麗的學術用語,即便他們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越來越多的人懷疑政客、商業領袖以及自認是專家嘴裡冒出來的每一個字。
遇險訊號層出不窮、形式各異。在許多民主政體,無論是現任領導者或執政黨,無論政策或政治取向紛紛中箭落馬。有的國家,民粹主義、仇外與種族主義趁勢崛起。在某些歐洲國家,全國罷工、民眾騷亂,司空見慣。幾乎到處都聽得到——討論政治現況時,總免不了的背景聲音日益喧囂、黑暗的冷言冷語——全面滲透。
在這本書裡,我要設法澄清:問題不是出在任何一組演員太過脆弱,真正核心的關鍵是語言本身。我當然不是說,修辭學是策動政治與文化變遷的主要推手。但我們將會發現,勤奮的偵探早已鎖住導致政治僵局的力量,而修辭正是這些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不過,我不會把修辭當作底層因素的副產品,而是把它放在因果連結的樞紐。跟我們共享公民結構、體制與組織,同等重要的是活生生的公眾語言;修辭一旦改變,公眾語言也會跟著變動。政治的危機,就是政治語言的危機。
這些趨勢也未必僅限於文字。除了書寫、敘述的語言被無限上綱之外,新聞與政治的影像修辭,也被壓縮進精心拍攝與編輯的畫面中,不斷重複、技巧嫻熟,且有特定傾向。我們可以把九一一大型攻擊事件,看成一件修辭的案例。在這個個案裡,飛機衝進摩天大樓,大樓隨即崩塌,也就是短短幾秒鐘的事情。雙子星代表西方的力量與價值,兩棟大樓的灰飛湮滅意味著某種可能性——力量可能瓦解,價格也會貶值。熊熊的火焰、崩裂的牆面、驚逃的人們、滾滾的煙塵,未來毀滅的場景,頓時搬到眼前。轉喻法(metonymy)、預辯法,無限上綱。
除了壓縮、誇張之外,還有別的危機。以往,在公眾討論中,科學被賦予特別尊崇的地位。今天,它只被視為一種意見。憤怒與誤解已經侵蝕辯論中(特別是在虛擬空間裡)最低限度的禮貌與相互尊重。我們越來越懶得尋找共同的語言,鼓勵價值觀與我們本質不同的文化與民族,一起加入討論。對於言論自由的容忍度逐漸流失,甚至有越來越多的人,希望能加以箝制,這種論調不只出現在專制社會,甚至在自稱尊重言論自由的西方國家也不時聽聞。
這種負面趨勢源自一股糾集了政治、文化與科技的力量——這力量超越單一意識形態、利益團體與國家機構。健康的公眾語言能夠把大眾與政治領袖連結在一起,是因為它有能力將老百姓拉進辯論中,導向更好、更受支持的政治決策。而公眾語言一旦喪失了解釋與激勵的力量,等於威脅到人民跟政治領袖的廣泛聯繫。我相信我們的民主政體就是碰到了這個麻煩。
**************
你必須勉力了解萬事萬物,既需直視無可搖撼的現實核心,也需參透缺乏洞悉力的俗人之見。你就知道他們的意見,千篇一律。除此之外,你無法了解世人為何對於真理,會有這般的印象與態度。
——女神巴門尼德(Parmenides)的詩作
●語言與信任
你是誰,就是誰,不要試圖欺騙群眾。
請把公眾當成年人看,跟你希望能投票給你的選民,分享你確實的想法,包括痛苦卻經過仔細算計的利益交換。千萬不要瞧不起他們而言不及義:絕大多數受你服務的選民,的確不具有經濟、規畫與公眾健康的專業資格,但不意味著他們很笨,看不懂證據、聽不懂辯論。如果你能了解,也許他們也能。
幾乎所有現代公共政策的決定,都是細膩平衡下的結果。如果證據不確切,就意味著辯論雙方都擔負一定的風險,決策衡量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確定性。請承認這一點。將公眾納入你的信任範圍。如果你不準備相信他們,他們大概也不會相信你。承認錯誤,不閃躲,要快速。
別想遮掩真相。如果你是左派,發現貧富差距逐年惡化,沒有改善的跡象(就像英國在金融崩潰之後出現的現象),或者世代落差比階級不平等還嚴重,請不要固守意識形態的利基,故意否認這個事實。實事求是——然後向公眾剴切說明,為什麼這會掀起有關社會正義的爭議,或者製造未來的問題。
將複雜的公眾政策提煉成庶民語言,並不容易,卻非做不可。大致來說,現代治理就是溝通。但是在各部會或國家部門負責溝通的單位,主要的工作卻是製作懶人包。釐清來龍去脈,請幾個真正的寫手。增聘幾名動畫師、攝影師與多媒體製作人,製作更鮮活的文宣產品。在你著力於強化內容之餘,也要讓你倚靠的技術官僚群學會清晰、直率的表達方式。不管喜不喜歡,強迫他們面對攝影機與麥克風。你的焦點團體、A/B測試平台,不是用來攻擊政敵、發掘最犀利的政治語言,而是善用這些工具,讓公共政策選項,盡可能清楚的呈現在大眾面前。
民主政治在本質上,必須要有反對黨;政黨(有時是個人)的政治利益,自然會支配你的所作所為。但進入公共政策討論之際,請考慮演化生物學家所謂的交互利他主義(reciprocal altruism)。……同時切記:千萬不要掉進假設的陷阱——誤以為最好的公共政策,一定落在兩個政治極端中間。我們應該思考的是:無論政治歧見有多深,都要設法把論點基礎,攤在大眾眼前,接受公評。
●和而不同
當「觀眾」(audience)這個字的意義,不再僅是觀眾,至今在英文中還找不到百分之百滿意的對應字眼,公眾這個詞又該怎麼辦呢?媒體高層在冷冰冰的字眼中擺盪:使用者、消費者、顧客;政治人物嘴裡則是冒出個別投票者或是整體選民。這些詞展現一種工具性:我們是根據我們想從受眾身上抽離出什麼,才來界定他們的意義。如果你不想引發一夥人戴上法式三角帽(tricorn hat)揮舞燧發槍(flintlock,譯註:法國大革命時的配備)跟你拚命的話,「市民」(citizenry,譯註:法國從一三○二年開始召開三級會議,解決政治或稅收難題,分別由教士、貴族與市民組成。一七八七年,日益壯大的市民階級不滿教士貴族的專斷,發動武裝革命,攻占巴士底獄)這個詞請慎用。所以我們還是使用「公眾」(public, 譯註:政治學者經常使用public sphere,「公共領域」這個用語,即下文所指的意義)這個詞好了,至少把我們的注意力,轉到一群人占用的領域:在他們覺得必須離開私人生活的時候,可以聚集在一起,傾聽大家的聲音,或者,有時也能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他們使用的語言,就是本書的主題。一個健康的、高效率的公眾語言會帶給他們什麼好處呢?他們跟我們想要提升公眾語言的品質,應該走出怎樣的第一步呢?
我們都同意公眾審議是民主最核心的理念——老百姓衡量議題的輕重緩急,決定支持哪種對策,再選出他們認為最具治理能力的黨派與領袖——那麼,「審議」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呢?在英語世界,最簡單也最有影響力的模式,就是陪審制度。陪審團審視所有證據、聽取雙方論述,考慮判決;這意味著個別的陪審員必須透過討論以及辯論,化解歧見,獲得一致的結論。
思考完美的公眾政治審議,難免聯想到陪審間的情況、想到對話過程,原則上,每一個公民都需要奉獻心力,引領最終決策。每個人——包括反對者——都有吃重的戲分。我們當然知道實際狀況複雜得多,陪審員的歧見可能更分散,但多多益善:越多關切、越多辯論、越多人投入,結果就越好。
問題是,這種期許現實嗎?陪審團需要每位陪審員到場。由於缺乏特殊的公眾職責,絕大多數的老百姓並不會表達看法,更不會批評別人的意見,只有一小部分的線上新聞讀者,會把他們看到的內容分享給朋友,更少數的他們會寫評論。在加入政黨悉聽尊便的國家,成為黨員並不附帶任何社會與生涯利益,大多數的人也不想參與政黨活動。我們不該吝惜掌聲,鼓勵這些積極參與政治的人、加油打氣的啦啦隊長、部落客、異議分子,但是民主政治的正當性,並不是靠這些人維持,而是剩下的90%,甚至更高比例的老百姓。他們不曾參與任何政黨或公眾活動,只在私底下,看、聽,或是發表意見(如果他們真的會議論政治的話)。
當代的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制度也不是靠(至少不會比雅典直接民主更倚賴)每一位市民,期望他們積極參與政治辯論,或者例行性的決策過程。它倚靠的是有願意、有能力吸收事實、傾聽辯論的尋常老百姓,期望他們在這樣的基礎上,每隔幾年選出代表他們行使政權的人。
也許這聽起來太溫和、太被動。但在民主政治,這是一切。超過政黨、超過領導者,事實上,這就是民主。本書的論點就是:今日政客與媒體向公眾說話的方式,讓這個民主本質性的職責更難解除;但結果卻導致公民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一併捨棄他們的憲政角色。願意花工夫參與政治的人,又受到扭曲現實的觀點支配,只剩眼前的選擇。如果我們想在短時間內,凸顯問題的嚴重性,政客與媒體就要擔起責任;但是公眾本身要做些什麼,才能讓自己成為更好的民主政治主人呢?
修辭,永遠引發爭議——如果辦得到的話,柏拉圖會很樂意在修辭剛誕生的時候,直接把它掐死。我們在書裡一再發現:視而不見,或是假裝可以徹底揚棄修辭,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請傾聽巴門尼德詩作中的女神智慧珠璣,也就是我放在本章開頭的引文。至少我讀起來,在這個發人深省的片段裡,女神很清楚的分辨出真知與意見間,是有差別的,卻也提醒我們:在直抵問題核心之餘,也要注意俗人錯誤的意見,兩者在本質上一樣重要。而修辭就是這些意見成形與分享時的語言。
女神在指令中暗示:意見與意見的修辭永遠黏著我們,如影隨形。世上並沒有什麼魔法棒或者美化工程,能把我們從現實世界傳送到另外一個地方,在那裡,只有完美的事實、完美的真實性,不管什麼,都沒有瑕疵。這不是我們人類的本性,自然也不會是語言的本質。
讓我們把公眾語言放進公民教育的核心。憲政史、政府分權的結構設計、法案如何變成法律、法庭的運作實況——這些內容當然應該進駐孩子的課程表,但是沒有一個比得上駕馭公眾語言。極少公民有機會參與立法程序。即便全盤掌握英國下議院或美國參議院的工作細節,也無法幫助搖擺選民拿定主意。但每一次他們讀或看一則新聞、聽一場演講、打開一個行動應用程式,甚至看一則廣告——全都是無所不在的修辭。寄望修辭能成為理性思辨、批判說服的藝術,再也沒有比讓批判受眾(critical audience)崛起更重要的助力了。
我們要教孩子分析每一種公眾語言,從行銷話術到電視、廣播、網路與社交媒體裡最高尚的政治宣示。年輕人應該學習政治修辭與廣告的歷史,研究個案,用文字、照片與影像,開創他們自己的公眾語言。
媒體,尤其是有使命感的媒體,像是BBC或者《紐約時報》跟各類機構—博物館、智庫與基金會一樣,扮演重要角色,推進觀眾對於科學以及其他政策領域的了解。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遇到立場偏執、論述可疑的訊息要示警;還要幫助閱聽大眾,在每個主要政策領域——經濟、地緣政治、科學與社會——建立自己的思考模型,將每天的統計數字、政治宣示,調整成適當比例,放進可能性評估的情境裡去了解。他們要知道怎麼挑戰不同模式,在不斷變動的環境裡,又要如何調整。
如果真有什麼黏著劑可以穩固脆弱的公眾領域,比較可能的是正確修辭,而不是某種睿智的新法令。讓我們記住一件事情:這種修辭跟其他的人文學科一樣、跟各種偉大的藝術一樣,面對人類社會最糾結的難題——我們要怎麼樣跟他人相處?請教導我們的孩子修辭。
| FindBook |
有 16 項符合
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公民教育的核心,從思辨、論述到說服的藝術(新封面版)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
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公民教育的核心,從思辨、論述到說服的藝術(新封面版) 出版日期:2021-04-10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公民教育的核心,從思辨、論述到說服的藝術(新封面版)
在謊言幹話充斥的當下,我們更要洞悉公眾語言
紐約時報執行長、前BBC總裁馬克.湯普森剖析
為何走過一九八四的年代、數位革命之後,民主更顯脆弱,社會更冷漠?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作者邁可.桑德爾特別推薦
「從柏拉圖、伯里斯克利,談到川普的崛起與推特的效應,視野遼闊。這本書文采斐然、據理力爭,在欺騙、野蠻、謊言,橫行今日政界之際,這是眾所期盼的解藥。」
――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
▌理性的公共論述,才能帶來優質的民主與建全的社會
在網路、自媒體時代,沒有比批判受眾崛起更重要的力量了
今天,我們接收了更多的資訊,擁有更多辯論重大課題的機會。但是,政客、媒體與大眾之間的關係,卻充斥著猜忌、疑惑與冷漠。究竟出了什麼事情?
社會越開放,公眾論述(修辭)越重要,無論是政策內容與價值的討論、追求正義公平的法庭辯論,或者在公眾領域裡說服他人,都需要客觀理性的檢視。但我們卻越來越不鼓勵價值觀不同的族群相互對話,陶冶共通的語言,反倒希望箝制異議。
政治人物為了擴張政黨勢力、圖牟私利;媒體為了突破營收窘境,一意媚俗。公眾語言,尤其是政治語言,難免意識形態、民粹主義的操弄,在數位科技的推波助瀾下,變得虛矯、混淆、模糊,充斥著謊言與扭曲,犧牲論述所需的從容解釋、引領思辨的複雜性,歧見幾無容身之地。新聞一發生,幾秒鐘內,立刻情緒炸裂,酸言循環,壓縮理性對話的空間。公眾語言難敵機關算盡的「演算法」,擁有強大運算能力者,將握有最大的權力。
「我們的百姓於公於私,對政治都極感興趣。在一般勞工身上,你也會發現他們對於公共政策,不乏真知灼見……不像其他人,我們雅典公民會為我們自己共同決策,至少會設法獲致清晰的理解。我們並不相信辯論會阻擋行動── 反倒是未經充分辯論的施政,窒礙難行。」
――修昔底德(Thucydides),歷史學家
《紐約時報》執行長,前BBC總裁、Channel 4執行長馬克.湯普森,2012年秋,赴牛津大學主持探討公共語言、政治與修辭的系列講座,獲得熱烈回響。本書是這位資深媒體人近身觀察政壇近四十年的所見所聞與所思。他從兩千五百年前細數至今,旁徵博引修辭的重要性,以及玩弄公眾語言對國家及個人所帶來的災難與浩劫。
馬克.湯普森深切的提醒我們:如果沒有正確的修辭,理性對話將不存在,再好的法令也無法穩固脆弱的公眾領域。蓄積更厚實的批判能量、建立健全的公民社會,讓自己成為更好的民主政治主人,就必須緊追不捨的探究事實,把公眾語言放進公民教育的核心,讓每個人都有能力辨識在公共平台閱讀到的資訊,客觀理性的陳述意見。
▌各界推薦
「馬克.湯普森精闢的分析了我們被過度簡化的公共語言。本書揭露了當今真相崩解、充斥著『仇恨、憤怒及謊言』的社會,令人驚喜,振奮人心。」
--哈洛德.伊凡斯,《美國世紀》(The American Century)作者
「書中的每一頁,都可以看到馬克.湯普森的洞見。這本書試圖成為一個調查報告的典範、一段歷史記載、一本實用的說明手冊,以及一則警世寓言。」
--《出版人週刊》(Publisher Weekly)
「中肯而深刻的揭露……如同喬治.歐威爾。」
--《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一本重要的著作……論述得極為優雅。」
--《衛報》(The Guardian)
▍各章簡介
第一章 迷失在字裡行間
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無一不陷入政治空轉、民粹橫行的窘境。儘管有很多嫌犯導致這種局面,例如:特定政客與政黨,甚至,媒體的失能,但,就作者來看,這是因為乘載政治訊息的語言出了狀況,變得強調張力、訴求極端,喪失包容諒解的能力。這個觀點可以解釋歐記健保為何遭到狙擊、川普因何崛起。
第二章 油腔滑調口是心非
分辨事實與意見的差別。許多論述義正辭嚴,其實僅是個人意見,並非事實。政治語言偷工減料,且有誇張的傾向。早在亞里斯多德時代,就有專著論及。政客含糊其詞,爭取基本盤,是西方政治的重大弊病。至於中國與俄羅斯這種素來缺乏公眾辯論傳統的文化,情況更難樂觀。
第三章 你又來了!
歐洲則進入共識年代,因應蘇聯陣營的挑戰;卻陷入表面和諧的窘境,排擠無法進入戰後利益圈的人民,如美國黑人。政治人物以鮮活的字句,擺脫官僚口吻,卻掉入自己為是的陷阱,如英國的鐵娘子柴契爾夫人。美國雷根的應付就得宜得多。但傳統的政治論述難以對付接下來的挑戰。
第四章 選轉與反轉
川普以毫不演掩飾的庶民語言,迷惑選民。在英國,精算師布萊爾,則以「旋轉」的策略,操控媒體。所謂的旋轉,是利用科技,測試用字,選擇適當時機發布,發揮訊息的最大力量。只是這樣一來,算計超過內涵,政治語言淪為幹話,百姓憤怒,更無從宣洩,為民粹主義崛起鋪路。
第五章 為什麼這個混帳騙子騙我?
懷疑是記者的天職,但推到極端,卻會引發不安。BBC一度偏好聲色俱厲的質疑政客訪問,慢慢轉成持之有故的調查報導。各種發聲管道雨後春筍般興起,對於政客的懷疑更難消弭。傳統媒體獲利消減,各言爾志,各種意見頻頻衝撞,了無寧日。新媒爭取點閱率,內容務求刺激,公眾對話的願景,成為泡影。
第六章 不「保」證「健」康的辯論
民智已開。決策成本激增,資源投入卻在遞減。埋首政策制定的技術官僚著重邏輯與證據;政客強調動員,濫開支票。英國健保改革議題繁複至極,民眾無力瞭解,只能憑直覺,決定支持與有。政客只求一時之利,信口開河;民眾期望越高,失落越甚。情勢失控,就連脫歐公投,都在意外中通過。
第七章 如何修補破碎的公眾語言
從歐威爾到希特勒,再到川普各自用獨特的方式,修補破碎的公眾語言。作者分辨出兩種不同的思維:理性主義與真實主義。前者是強調語言必須對應能描述、能分析的事物,去除虛妄的成分,缺點是不合人性;後者根本質疑事實,認為所有的敘述,都是故事,往往遭到濫用,川普就是玩弄真實主義的高手。
第八章 賣得掉的句子
廣告是一種獨特的公眾語言,目的是促銷,而非周延推理。而這也是政治行銷的邏輯──只求衝擊,無須理性。這種思維進入決策領域。新的資料科學帶動演算風潮,訊息甚至可以精準鎖定個人。民眾只能靠與生俱來的實踐智慧加以判斷,但許多人質疑,認為民眾只會受人操弄。
第九章 付之一炬
政治行銷的邏輯,就是說故事,務求動人,強調衝擊,而非理性思考。這種思維傾向已經逐漸入侵決策領域。新的資料科學更進一步帶動演算風潮,選民區隔更精準,訊息甚至能鎖定個人。幸好民眾仍有與生俱來的判斷力,這也是陪審制度的基礎。只是這種「實踐智慧」近年來招到許多質疑。
第十章 戰爭
驅策人民生死以之的戰爭,是政治人物終極的修辭考驗。邱吉爾允稱箇中高手,但後繼無人。布萊爾的伊拉克戰爭演說,力論薄弱,說服力大打折扣。現在戰爭論述起源於一次世界大戰,宣揚為國犧牲,但戰爭正當性的辯論始終不足。現在戰爭更加殘酷,但理性辯論、誠實描述戰爭的公眾語言,至今難產。
第十一章 廢止公眾語言
表達自由是一種影響他人的自由,只有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才得以限制。近年來,少數族裔常以文化敏感性壓抑表達空間,甚至導致查理週刊屠殺。少數族裔處於主流社會,飽受歧視,固然值得同情;但作者強調,無人擁有不得冒犯的權力,更不得暴力相向。以法律制裁語言霸凌並非良方,只能與之公開辯論,尋求公評。
第十二章 保持冷靜,無須杞憂
作者的最後忠告,鼓勵政治人物揚棄誇張,而應說明基本的論述理念,終結惡鬥。審議是民主政治的本質,靠的是民眾的「實踐智慧」,分辨語言的能力,因此至關重要。幾乎所有民主社會都面臨了「川普考題」,選民無力分辨對話與胡謅的差別。幸好在文化的邊緣,如嘻哈音樂,還保留翻新公眾語言的動力。有關「公平」的討論,也蘊含能量,所以不必懷憂喪志,只需善用判斷力,挑戰虛偽的語言,等待適切公眾語言的復興。
作者簡介:
馬克.湯普森(Mark Thompson)
現任《紐約時報》執行長,曾任BBC總裁(2004~2012)與Channel 4執行長(2002~2004)。畢業於史東尼赫斯特學院(Stonyhurst College)與牛津大學墨頓學院(Merton College Oxford),專研英國文學。1979年進入BBC,曾任時事部門研究員、導播、新聞編輯,2003~2004年以製作人身分駐派紐約。在Channel 4擔任執行長兩年後,回到BBC接掌總裁,兼任執行長與總編輯,任內促成BBC由傳統到數位媒體的轉型。2012年,前往牛津大學擔任修辭學與公共說服藝術訪問學者。
譯者簡介:
王審言
研讀新聞與國際關係,資深記者,現仍存活於新聞界,二十年來,目睹不少怪現象。
章節試閱
●迷失在字裡行間
公眾語言(public language)至關緊要。文字免費供應,政客、記者、市民取之不竭。卻有論述者發現自己必須決定未來走向,用字必須精審的關鍵時刻。長久以來,領導者、評論者、行動家,或者理帶同情,或者能言善辯,不僅從人民的情緒中汲取養分,甚或影響情緒的形成。結果呢?和平、繁榮、進步、不平等、偏見、迫害、戰爭,不一而足。公眾語言,因此,至關緊要。
這當然也是個公眾語言的時代。尤有甚者,我們正歷經一場無與倫比、尚待開展、猶未定型的公眾語言蛻變。在我們考量、辯論現代政治與媒體的實況——政策與價...
公眾語言(public language)至關緊要。文字免費供應,政客、記者、市民取之不竭。卻有論述者發現自己必須決定未來走向,用字必須精審的關鍵時刻。長久以來,領導者、評論者、行動家,或者理帶同情,或者能言善辯,不僅從人民的情緒中汲取養分,甚或影響情緒的形成。結果呢?和平、繁榮、進步、不平等、偏見、迫害、戰爭,不一而足。公眾語言,因此,至關緊要。
這當然也是個公眾語言的時代。尤有甚者,我們正歷經一場無與倫比、尚待開展、猶未定型的公眾語言蛻變。在我們考量、辯論現代政治與媒體的實況——政策與價...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chapter1 迷失在字裡行間
大憤怒/我們失去事物真正的名字了
chapter 2 油腔滑調口是心非
亞里斯多德與修辭學/兩種困惑
chapter 3 你又來了!
共識年代/傾軋之處/你又來了
chapter 4 旋轉與反轉
發布壞新聞的好日子/小丑與祕密警察
chapter 5 為什麼這個渾帳騙子騙我?
迎向諒解的偏見/回嘯(Howlround)
chapter 6 不「保」證「健」康的辯論
推特與扭曲/被排擠的中道
chapter 7 如何修補破碎的公眾語言
一幅語言的特殊圖像/血與土/失去的平衡
chapter 8 賣得掉的句子
你的前十個字/幾個關鍵要點/不是...
大憤怒/我們失去事物真正的名字了
chapter 2 油腔滑調口是心非
亞里斯多德與修辭學/兩種困惑
chapter 3 你又來了!
共識年代/傾軋之處/你又來了
chapter 4 旋轉與反轉
發布壞新聞的好日子/小丑與祕密警察
chapter 5 為什麼這個渾帳騙子騙我?
迎向諒解的偏見/回嘯(Howlround)
chapter 6 不「保」證「健」康的辯論
推特與扭曲/被排擠的中道
chapter 7 如何修補破碎的公眾語言
一幅語言的特殊圖像/血與土/失去的平衡
chapter 8 賣得掉的句子
你的前十個字/幾個關鍵要點/不是...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