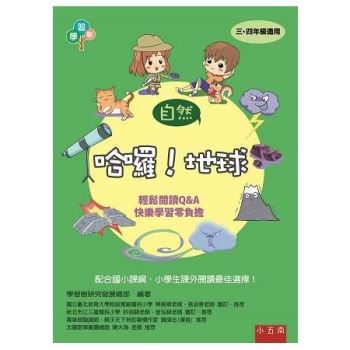屋外淅淅瀝瀝的雨,有越下越大之勢。
從醒來到現在,十多個日夜了吧?
一切似乎安寧安靜,又似乎變幻了天地。
翹楚在榻上有些慵懶地復趴回枕上,榻下,一雙炯亮大眼和她眼瞪眼。
她一笑,撫撫獸王的頭。
獸王頗有靈性又大模大樣地點點頭,將身子一盤,閉上眼睛繼續打盹。
門是關了的,有笛聲隨著淅淅瀝瀝的雨聲從屋外淡淡地傳來。
翹楚閉眼傾聽。
她自是知道那是誰的笛聲。
每天這個時間,上官驚鴻總會在屋外吹笛。
他似乎知道,她會在這個時間醒來。
他變換著曲子,一直吹奏到近午膳的時間,他就到村子的人家裡,去拿些菜蔬和魚肉回來。
她會倚在榻上,淡淡看他在廚房出入,或是繼續合眸休息,直到他將飯菜做好端出來。
他給她做的是肉和湯,然後,他會沈默卻自覺地拿了他自己的素菜走出屋外,在院子吃飯。
院子沒有桌椅,他將門關上,就坐在屋門外的臺階上吃,而她和獸王在屋子裡吃。
每當她擱下碗筷不久,他就會進來,拿碗到廚房刷了,然後到屋外去,直到該準備晚膳的時間,他便又到天人家裡去。
晚膳過後,他會給自己和她燒水洗澡。
他先洗澡換衣,再幫她將一個大浴桶灌滿水,才會將不情願的獸王一併拉出屋外去。直到泰半時辰,估摸她洗完澡了,才將獸王放進來。
晚上,他就在院子裡過夜。
如此,日復一日。
猶記得在醫廬醒來那天的情景。
當她睜開眼睛,知道自己再次像隻小強一樣存活下來的時候,守在她榻旁滿臉疲憊,雙目卻如星璨的他,一向冷靜的他,眼底淺淺浮著激動,他微微顫抖,用力將她抱進懷裡,斥責她傻,說箭他能避開,緊接著又想和她說什麼重要的話的時候,她止住了他,說出所有事情。
包括他的身分,他們真正的關係。
告訴他,他在外面還有一個正室,一個他深愛的女人,若雪一家是什麼人,他答應過她幫她救汩羅的事。
最後,她說,她想求他一件事,希望他百年後,不要修陵寢。
她說,他們以前常常做交換。
汩羅的事,是他已答應她,是交換而來的。
她問,陵寢的事,他能不能給她承諾,在他覺得她其實無須替他攔下那一箭的時候,在她拿不出什麼東西和他交換的情況下。
給她一個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堅定的承諾。
她輕輕在他耳邊說,他環抱著她身子的手臂緊繃得讓她背脊隱隱生痛。
她沒有告訴他,其實,他曾答應過她,如果她肯安分地待在他身邊,他可以為她辦任何她喜歡的事情。
她沒有說,因為知道他們即將回去,回去之後,她便會離開。
她完成不了留在他身邊的承諾,他自然不可能答應她陵寢的事情。
甚至,在他記起前事的時候,他會恨她,因為他一直認為,在崖上的時候,是她有意放的手。
所以,她只能藉著此時他眼裡的神色來問他。
最起碼,她知道,無論失憶與否的他,都會喜歡很多女人,但這一刻,他對她總是有些愧疚的吧?
他一直沈默地聽她說著,直到她說得微微喘著氣的時候,他在她耳畔淡淡地說:「翹楚,我答應妳。無論日後發生什麼事,我死了就一把灰揚了它,絕不修建陵墓。妳真是個……不可思議的女人,我百年後的事,妳也要關心。」
她聞言,渾身一顫,她自由了!
她終於自由了嗎?
他又問:「告訴我,為何不願我修陵寢?」
她一怔,隨即淡淡道:「修陵寢有什麼好?或者你在還年輕的時候就死去呢,我愛你現在的容貌,傾國傾城。
「若你壯年就死去,放你在陵墓裡,棺木做得再好,防腐的手藝再妙,終有一天你的身體還是會腐爛的,會發出難聞的氣味,那樣很醜。就一生傾城,不好嗎?」
她說罷有些緊張,不過是隨口捏造的一番話,以他的精明,能信嗎?
他復沈默,過了很久,她聽到他一陣低沈的笑聲。
末了,他淡淡又道:「翹楚,我知道,妳要我這樣做,其實非我傾城。但若妳喜歡,那便那樣吧。」
他果然不信!
她反沒再說什麼,免得越描越黑,只是伸出手。
他盯著她的手掌,說:「總覺得,我這一生從沒如此答允過別人什麼事。」
他說罷也伸出手。
空氣中三聲清脆響聲。
她自由了!
「那你這個第一次便給我吧。」她聽到他又是一陣淺笑。
她放下手,心裡卻一下歡喜,一下空茫,低頭盯著自己的手掌看了良久後,說:「我們明天便出發回去吧。」
他駁止。
「不,依妳現在的身體狀況過不了寒潭,強行離開,日後落下病根,晚年身子將破敗痛苦。」
她一笑,淡淡道:「沒有晚年了,我知道我自己的情況,這次過後,最多只能苟延殘喘半載光景。」
他聞言,兩手捏緊她的肩膀,方才的淡然一下子變成略有些咬牙切齒的聲音。「妳有!」
她也不和他爭,隨意點了點頭,突然想起靈、魅兩族,一驚出聲。「兩族族人都還好嗎?」
「嗯。苟延殘喘這些話莫要再說了,我不愛。」他擰眉警告地看了她一眼,才鬆開手,向藥房走去。
她既能醒來,便是說狐王讓他做的他都做了嗎?
她心裡滑過忐忑,卻又想起一事,吸了口氣。
「你和翹眉,你們有沒有……」
她聽到自己聲音裡的緊張,笑自己傻,那幾名侍女不是說,有一晚他就宿在翹眉那裡……
她其實不想問,也知道不該問,終於問出來,卻是知道自己即將離開,她沒了許多顧忌,只怕他犯了禁忌。
他聞言轉身,嘴角浮起絲笑。
「我早就懷疑妳認識若雪,原來果是真的。」
他沒有答她,笑意越發凌厲,卻又帶著極深的愉悅。
「妳不惜捏造妳我身分的謊言,是因為妳心裡那個人本就是我,我是妳第一個男人。妳說我在外面有一個深愛的女人,翹楚,妳一直在芥蒂我愛的不是妳。」
她一怔,隨即笑了出來,一邊笑,一邊撫住心口。
他眉頭一皺,大步過來將她撈進懷裡,拍開她的手,替她輕輕揉著傷處,沈聲道:「我不管妳心裡怎麼想,妳昏迷了兩個日夜,從兩天前開始,我便當妳是我的妻子,唯一的妻子。」
她登時一震,又聽到他淡淡道──
「我吻過翹眉,但沒有和她做歡愛之事。妳將我逼走那天,我在她那裡過了一晚,因為我知道那些風言風語會傳進妳耳裡,妳會想見我,派人來找我。」
她說不出是喜是驚,但吻一個人又代表什麼?
他以前最是厭惡這事,會吻她也是因為懲罰。
她心裡屈辱,自嘲一般扯了扯嘴角,一指門口。
「我現在就不想見到你!你若希望我在這裡靜養幾天,就不要讓我見到你,否則咱們明天就回去。
「當然,你大可以不必理會我,本來你八爺就是最高貴的皇親貴胄,我不過是你的一個側妃,也沒有父母庇蔭,你喜歡對我施暴便施暴,你最愛的女人想我死,你也可以毫不猶豫地要我的命。
「我能芥蒂什麼?在你眼中,我連芥蒂的資格都沒有。」
她說著,笑著別開頭,趕緊伸手揩去眼角的水沫。
總是這樣,說過不哭的話總是像放屁。
她突然想,離開真好,有些話終於可以毫無顧忌地說出來,酸酸的又怎樣?
他本不溫不火,摸著她的頭,笑著說,小醋罈。這時,他的手微微一僵,從她髮上滑了下去。
身上大傷未癒,行動不便,但翹楚實在不願讓上官驚鴻照拂。後者變得沈默,然而,卻再也沒有如往日用強。
最初兩、三天,過來照拂她漱洗燒飯的卻是紀書記官家的兩名媳婦,其中一個正是平兒的娘親。
翹楚隱隱嗅到了不尋常的氣息──
靈族的人怎麼還肯任他差遣?
動了翹振寧,無異與整個靈族為敵,他二人還能在這裡居住,本來她已覺得奇怪。
她也不拐彎抹角,直接問平兒的娘,才知道,那天上官驚鴻搧了翹振寧耳刮子以後,狐王一聲長笑,說──
「你果聰明,不聲不響便出手,否則,還真未必能打到那個畜生。犯罪的是那個男人,其餘兩人便罷。再者,你也不可能動到她們。」
因為彼時靈族的人已將上官驚鴻團團圍住。
翹振寧不怒反笑。
「上官驚鴻,我禮賢於你,你竟愚鈍到中狐王的計,對我動手?我的妻女你自是動不了的。你以為她真能救翹楚?即使能,你怎不問問我靈族准不准你救!」
若雪臉色蒼白。
狐王只是負手而笑。
兩方的人或憤怒、或諷刺地看著場中的男人。
上官驚鴻動手之後,一直盯著不遠處地上的她,聞言,目光從翹振寧和狐王身上緩緩掠過,一字一字道:「狐王,我不管妳是不是在耍我,我早說過,若我的妻子死了,魅族的人,我一個也不會放過。翹族主,你族裡的人也給我們陪葬吧。」
平兒的母親說著眼露懼色。
旁邊的嫂子也是如出一轍,苦笑著顫聲說:「族主和長老說過,上官公子是凡人,可他哪裡像個凡人?
「本來他的念力毫不費力就將村裡一些房屋夷為平地了,後來,他甫一擱話,立刻就捏了個手訣,族主和狐王都大驚,說那是主佛的佛訣,那佛訣只有古佛、佛祖和幾名主佛會,當時我們兩族的人被他困在佛訣幻化的結界裡,一動也動不了。」
她一腔茫然,苦笑。
他還會佛訣?
發燒會長高,這失憶了還能有超能力?
只怕他自己也不知道這能力吧?
既然有前世今生,他前生是什麼厲害的人嗎?
上天也欺人,為何有些人無論到了哪裡都有生殺予奪的能力,便像上官驚鴻。
她終是要離開的,聽罷也沒再去深究,正如她不知道,也慵懶地不想去思考為何獸王沒有傷害她,倒是略略想了想他說的「你族裡的人也給我們陪葬吧」。
我們?
不知是出於上官驚鴻的威脅還是什麼,狐王最後果然出手救了她,原是取獸王的內丹割下一小片給她服食。
獸王嫡傳自潭中神獸,還在天界的時候,那神獸不知為何無故傷人,才給飛天鎮了收在此潭。
因此,獸王的內丹就是最好的解毒之藥。
後來,上官驚鴻將魅族遣了出村。
原來,魅族在月圓夜裡才能進村,若不當晚出村,便要等下一個月圓之夜才能出去。
他將獸王留了下來,狐王倒沒有阻止,獸王自己也願意。
她自是明白他的意思,若她好不過來,獸王的內丹便危險了,他必定毫不客氣地將整顆給她。
天神村裡也沒有人敢惹他。
眾人看過他對付魅族的手段,雖然暗襲未必行不通,但玩陰的他是鼻祖,翹振寧不敢動手,他要人來侍候她,更沒人敢說不。
那兩、三天除去進屋吃飯、洗澡,他多在屋外,坐在臺階上盯著她看,但看平兒的娘她們妯娌戰戰兢兢的模樣,她傷勢稍好,便讓她們回去了,又讓他將平兒的解藥給二人。
他淡淡道:「本來就不是什麼毒藥,昏迷一晚罷了,這時早便生龍活虎了,哪像妳……」
他眉頭一皺,又道:「這兩個人妳不喜歡,我找些人過來讓妳挑。」
她半開玩笑,說:「不必了,我現在自己勉強也能漱洗,你負責燒飯、燒水。」
後來,便有了她屋內、他屋外的這些日夜。
平兒娘她們妯娌在醫廬的時候,雖有獸王守著,他卻不給她關門;她們走了之後,這七、八天裡,她大多數時間都把門關上。
眼不見,彼此乾淨。
只是有一晚,她半夜噩夢醒來,卻見他坐在榻邊癡癡看她,她醒來得快,他的動作不知為何不到平常十分之一的迅敏,仍還坐在那裡,手在半空,似乎想碰一碰她的臉頰。她一驚,怔怔的說不出話來,他反忽地恍然如夢初醒一般,一下就走了出去。
……
思緒在雨聲中拉回,現在,外面的雨越下越大,越大越下,他在外面,衣服都濕透了吧?
翹楚翻來覆去地想了很久,終於忍不住坐起身來,她想出去將他叫進來。
走到門邊的時候,她才發現笛聲早已驀然而止。
她一怔,走到窗前,將窗紙微微戳了個洞,看了出去。
院裡,兩人一傘站在雨裡。
撐傘遮著他的是……
若雪?
她慢慢退了回來。
沒多久,似乎聽到腳步聲遠去。
她怔在原地,獸王走過來用頭蹭蹭她的腳。
當她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開門出去了。
院裡,雨水漣漣,若雪已連著上官驚鴻消失無蹤。
前方,父親母親、族中長老和眾多族人已經在望,他們列隊在雨中候著,以示誠意,等她將上官驚鴻領過來。
父親雖心仍憤怒,但到底顧全大局,更要維護自己的權力,於是今日讓她親自過來請上官驚鴻好好商談一番,並再談她和他的婚事──
二女共侍一夫。
她明白父親和族中長老的心思,只要她和上官驚鴻成婚了,那麼上官驚鴻自當敬重她父親,也會為族中做事,再次對付狐王。
誰不愛傾城?
他們始終認為,當日上官驚鴻不過有感翹楚相救之恩,即便狐王沒有讓他住手,當日他也斷斷不會動她。
她最初不願,後來竟也答應了。
她愛他。
情不知所起。
可當看到他渾身濕透地站在院子裡吹奏,她憐惜地遮住他的時候,他卻神色淡漠地請她走。
她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在院裡淋雨,她更想不到他的絕情,跺腳便走。此時咬緊牙關,卻又滿腹悲傷,她恨翹楚!
她快走近的時候,卻見父親為首,所有人都是神色欣喜,她一怔,突然意識到什麼,猛地轉過身去,果見背後上官驚鴻在雨中走過來。
他追她過來?
她又驚又喜,撩起裙襬,便朝他快步奔去,將雨傘攏到他頭上,正想和他說話,眼梢卻見一個女子從前方的雨簾裡慢慢走來。
雨水將女子的模樣打得委頓模糊,她卻輕輕揚起嘴角。
翹楚不知道上官驚鴻和若雪之間發生什麼事,似乎若雪走了,上官驚鴻去追她……
二人一前一後,直到此時交會在一起。
但無論他們之間怎麼都好,她竟怔怔地便出了門,沿路走出來,似乎沒有目的,更不知道目的地,卻就這樣出來了。
還是二人一傘……
她看著跟在她旁邊、同樣被雨水打得濕漉漉的獸王,才恍然回過神來,淡淡笑道:「親愛的,我們回去吧。」
前方,上官驚鴻高大的身影背對她而立,若雪嘴角噙笑,挑釁地盯著她。
這神色,她自小便認識。
翹振寧、鳳青幸災樂禍地微微笑著,人們則是驚怔地看著她,神色不一,有複雜,也有譏誚嘲弄。
她沈靜地一一看回去後才轉過身,卻無意識地一下便咬住唇。
走得一步,忽聽獸王一聲嘶鳴,她一驚,身子已被人攬進懷裡,耳邊的聲音隱隱蘊著絲怒意──
「翹楚!這鬼天氣,妳不打傘亂跑出來做什麼?」
雨水讓她的眼睛有些睜不開來,翹楚瞇著眸,有些費力地看著身旁的男人, 意識有些抽離,似乎不想應答什麼,但看對方眸含怒氣,壓迫地盯著她,似乎在等她答覆,否則,隨時要將她狠揍一頓,於是隨口道:「喔,上官驚鴻。」
上官驚鴻難得地眸色又焦灼了幾分,一按她的肩膀,沈聲道:「等我一下。」
她怔著,微微側身,卻見他身影一閃,已回到若雪身邊,若雪本驀然站在原地,看著二人,這時笑靨方再次綻開。
翹楚一點也不願去做這荒謬的等待,她正要轉身,那邊上官驚鴻已劈手奪過若雪的傘,她又是一怔,在她還愣著的時候,上官驚鴻已回到她身邊,復將她帶進懷裡,一把傘嚴嚴實實罩到她頭頂。
她沒反應過來,愣愣地問:「你為什麼要拿了她的傘?」
「她距我們最近。」上官驚鴻理所當然地說著,伸袖替她抹拭滿頭滿臉的雨水後,又微微沈聲催促道:「快回去,莫要又病了。」
「嗯。」
她看著數步以外若雪臉如死灰,翹振寧、靈族人滿臉震驚的神色,仍有些反應不過來,說:「你追出來不是找若雪有事嗎?我先回去,你去忙你的吧。」
「我找她有什麼事!午膳的時間到了,我出來討些菜肉回去燒飯的。」散落在她耳邊的聲音登時凌厲了數分。「妳不該出來,這要病了,我……我……必定熬些苦藥給妳吃!」他狠狠盯著她,「我」了幾下,才道出個所以然來。
她怔了半晌,嘴角一繃,沒繃住,終於輕輕一聲笑出來。想起他從最初的不會燒飯做菜,他將醫廬廳中一張貴妃軟椅搬進廚房,讓她坐在上面,讓她指揮著他做這做那,從手忙腳亂到最後的不慌不忙,又默然收住笑意。
反倒上官驚鴻微微怔住,凝視著她看了好一會兒,才啞聲道:「快回去,換套衣裳。」
他從不廢話,抱緊她便往回走,一把傘幾乎全籠罩在她頭頂上方,她陡然聽到一聲尖銳的叫聲從背後悲慟而來──
「驚鴻──」
雨水很快將背後女子的聲音以及所有人的驚怔完全遮蓋住。
直到他們走進屋,他極快地扔了傘,將她一把抱到榻上,拿起榻上一張薄毯將她裹緊,用力擦拭起來,她還在想著雨水裡的聲音。
想起若雪,又想起人們嘲弄的目光,其中不少原因來自她臉上的傷疤,現下的她是醜女。
但她很快就被身上陣陣摩擦之感驚醒。
上官驚鴻的手在她身上上下滑動著,滑過胸前腹下,毯子薄,他的手所到之處,無一不引起她微微的顫抖。
她一驚,已拔高了聲音。
「我……自己來。」
上官驚鴻慢慢撤了手,她臉上熱著,抬頭便碰上他幽深黝黑的眼睛,直勾勾地盯著她、她的身子看。
她頓時羞惱,瞪了他一眼。
他方輕咳一聲。
「換身衣裳,好了喚我,我進來給妳燒點熱水,讓妳泡泡身子。」
他說著握了握手,有些艱難地轉過身,向屋門走去,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翹楚看著他微微彎曲的身子,聽著屋外下得倉倉皇皇的雨聲,像珠子打在盤子上,心裡竟微微一酸,終於還是心軟地將他喊住。
「就留在屋裡吧。」
上官驚鴻當即返過身來,深深看著她。
翹楚有些後悔,側開頭道:「我換衣服,你背過身去。」
「嗯。」
他應著,聲音乾脆,卻又奇異的有些沙啞。
換洗的衣服摺疊著放在榻裡側,翹楚趕緊去拿,飛快地將身上的濕衣連著內衣褻褲全部褪下來。
她就坐在榻邊,突然足下傳來些輕癢,她一怔,見卻是獸王用濕透的頭顱蹭她的腿,似乎在怨艾牠沒她來得幸運,有人侍候。
她渾身赤裸,對方雖是獸,她還是有些不習慣,輕輕蹬了獸王的肚子一下,嗔道:「一邊耍去!」
獸王呼哧叫了出來,有幾分洋洋得意的意味,只是尚未得意完,前方,上官驚鴻驀地轉過來,一指藥房的方向,目光甚厲。
「進去!」
獸王被恫得退了一步,尾巴一甩,逃也似地向藥房走了進去。
翹楚看著獸王,覺得好笑,很快卻怔呆在原地。
她身上此時什麼都沒穿,甚至繡鞋也脫了,光著腳掌踩在地上,正一絲不掛地站在他面前,站在上官驚鴻面前!
她登時滿臉熱得像火燒,剛說得句「轉過去」,卻見上官驚鴻的注意力早已從獸王身上移到她身上,緊緊地盯著她看,眸光明明暗極,卻又燃著火苗。
她心頭怦怦直跳,心裡的弦繃得緊緊的,也瞬間有了個認知──
上官驚鴻不會聽她的。
果然,她還在怔怔的、不知所措地想著的時候,他已向她壓了過來,她的手剛撈著衣尾,他的手已將衣服扯過,扔掉。
她被他整個壓到榻上,他堅硬如鐵、滾燙的身子抵在她不著寸縷的身子上面,在他一手罩上她一側胸乳的時候,他低頭去吻她的耳垂,剛一碰上便將肉珠勾起銜住了,用力吮吸起來,她的身子登時被激起一陣顫慄。
她又慌又亂,想去推他,他卻將她壓得更緊。
她的手被他壓在胸膛之下,他含著她的耳骨,聲音模糊卻又堅決無比,散落在她的耳朵裡,要她聽好,記住。
「楚兒,我知道,妳恨以前的我,但那是以前的我,現在的我只對妳好,妳要我怎樣都行,但是,要我放了妳,不碰妳,那絕不可能。我本來想,等妳願意了再碰妳,可我等不了了,我現在就想要妳。」
「你還是像以前一樣,不管我願不願意,只要是你想,你就可以如此待我。」
翹楚自嘲一笑,艱難地來回側頭,極力躲開頸項男人的吻,卻始終躲避不過,一側乳尖被他拈弄得挺拔起來。
她咬緊牙,不去屈服,不讓一絲聲音逸出……
他卻一手抓起她兩手壓到枕上,另一隻手開始攻擊另一邊的柔軟。
不知道是不是過了這些天的山居日子,平靜悠和,雖然她有意不和他多說話,他也隨著她而沈靜,一門之隔,她卻有種相依為命的感覺。
這段時間,她其實不是沒有一絲快樂的。
所以,現在的抵抗竟也不如在營帳時的激烈嗎?
她方才想說的是「如果我不願意,你也要對我施暴嗎?」,只是卻被他極之迫切卻又近乎溫柔的動作緩了緩。
不同於以往哪一次,此刻他待她是溫柔的。
這時,她咬了咬牙,把方才的話完整說了出來。
卻聽到上官驚鴻突然從她脖頸裡抬起頭來,氣息微粗,卻又有些自嘲的淡漠。他吻上她的嘴,唇抵在她唇上。
「碰不碰是我的事,但允不允在妳。」
他說著,竟出乎意料地從她身上下了來,倚著榻背,只復將她重抱進懷裡,將頭埋在她肩上。
翹楚驀然怔住,她沒想到他會這樣,凌亂中,她拿他的話反駁他。「你說只對我好,你卻吻了翹眉。」
「那天,我是恨妳,只是故意。」上官驚鴻微微沈聲說著,自嘲一笑。「我一直待她友善,是因為我總覺她身上有一股妳的氣息。」
翹楚一震。
上官驚鴻說著微有些咬牙,復又吻住她的唇,當他剛平靜下來的氣息又開始急促起來的時候,他緊緊握了握手,卻終究無法抑制地伸手往她身子深處探去。
翹楚竟沒有制止,不知忘了還是因為其他……
陽光從帳簾縫隙灑進,這是夕陽的光照,翹楚從一個人的懷裡幽幽醒轉過來,就像作了個漫長的夢。
撫住微眩的額頭,車窗外是無數馬車行走的聲音,卻驀然對上低頭看她的一雙眼睛,這人臉上戴著鐵面。
她背脊打了個激靈,想起,距離夢裡最後那個情景,已有八天了。
第七天的時候又是一個月圓夜,他們將獸王帶出天神村,狐王一身紅衣在紅字藍印碑前安靜地站立著。
她跪下,給狐王叩了三個頭,輕輕喚了狐王一句婆婆,謝謝救命之恩。
狐王一怔,突然,她旁邊的上官驚鴻也一掀衣襬跪下,在她和狐王的驚訝眼神下,做了相同的事情。
上官驚鴻說:「狐主,這是晚輩當日欠妳的,謝謝妳救了我的妻子。」
狐王看了兩人一眼,沒說什麼,領著依依不捨的獸王離去。
翹楚莫名的鼻子一酸,總感覺狐王其實是很孤獨的。
她在這個魅族族主背後低喊道:「婆婆,可以的話,月圓夜莫要再到這邊來了,放了他們,也放了妳自己。」
狐王腳步頓了頓,卻沒有說什麼,領著獸王消失在另一端的森林裡。
那邊又是一個天地。
呂宋一直沒有再回天神村,他們並沒有管若雪等人,靜靜離了谷。
猶記寒潭岸邊,無數軍士驚愕地看著從潭底走出的男女。
兩人均以布巾遮面。
上官驚鴻淡淡說──
「告訴皇上,睿王和睿王妃在這裡。」
聽那語氣,她始知,記憶沒有了,有些人還是有些人,天生的一種人。
有禁軍去報。
蒼鬱的林木中,皇帝率眾走來。
她突然掙脫他的手,悄悄讓開。郎霖鈴從人群裡奔出,過來緊緊抱住上官驚鴻,上官驚鴻一拍這正妃的肩臂,眼梢朝她一瞥,便鬆了郎霖鈴,向皇帝下跪行禮。她忙隨他行跪禮。
皇帝身旁,太子輕聲道──
「八弟平安歸來便好。」
沈清苓眉目之間有些憔悴,又若有所思。
皇帝卻很是激動,連連抱了上官驚鴻數次,並問起可在附近見過翹眉沒有?
上官驚鴻只說沒有。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非我傾城:8之4(爺兒吃飛醋)(拆封不退)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181 |
中文書 |
$ 181 |
文學作品 |
$ 196 |
小說/文學 |
$ 205 |
穿越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非我傾城:8之4(爺兒吃飛醋)(拆封不退)
第一最好不相見,如此便可不相戀;
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文創風037《非我傾城》‧8之4〈爺兒吃飛醋〉
大婚前先是與他的太子二哥曖昧不清,大婚後又和九弟夏王眉來眼去?
想不到翹楚這姿色平平的女人,還真有活活氣死他的本事!
她那破敗身子毒病一堆,沒幾年命好活了,竟還有閒功夫到處勾搭他的兄弟?
民間姑娘、勾欄場所的花魁,幾時看九弟真心對待過一名女子了,
而今不僅一直戴著她給的荷包,還贈她千年白狐做成的名貴狐裘,這算什麼?
怎麼著,難不成九弟這次竟看上了自己的嫂嫂、看上他用過的女人嗎?
只是,他這個好弟弟似乎忘了一件事——翹楚是他的女人!
即便他上官驚鴻不愛,他上官驚驄也休想染指她一分一毫,
不論是死是活,這輩子她翹楚都只能是他八爺的妃!
本書特色
重量級好書名家墨舞碧歌大作
高潮迭起的精采情節。愛恨交織的揪心情感。
一部絕妙黏手的磅礡鉅著。
紅袖添香小說網點擊率破2200萬!
從近十萬部參賽作品中突圍而出,
成為2012年華語言情大賽總亞軍!
★隨書附贈東陵王朝人物關係表
作者簡介:
墨舞碧歌
女,紅袖添香小說網大神級作者,新穿越小說八大代表作家之一。2009年因為愛好寫作而無意間闖進網路文學之中,胸中故事纏綿于思緒,鳳舞龍騰,噴薄而出。遂以網線為弦,筆歌宛轉,墨舞翩躚,設奇謀暗伏流觴文字,展睿智鋪就錦繡文章。
尤擅磅礴構架,情節曲折旖旎,意蘊深遠。文中眾生百相,相相色彩分明。機關謀略紛紜,芸芸奇思妙想。潑墨處,談笑間,華美演繹「如果愛,請深愛,一生一次一個人」的世世情深。平生唯冀與有緣人,相遇、相知、相交,傾心相伴,笑看紅塵,且歌且行。
作品《非我傾城》:從近十萬部參賽作品中突圍而出,成為2012年第四屆華語言情大賽第一賽季冠軍、大賽總亞軍作品。
章節試閱
屋外淅淅瀝瀝的雨,有越下越大之勢。
從醒來到現在,十多個日夜了吧?
一切似乎安寧安靜,又似乎變幻了天地。
翹楚在榻上有些慵懶地復趴回枕上,榻下,一雙炯亮大眼和她眼瞪眼。
她一笑,撫撫獸王的頭。
獸王頗有靈性又大模大樣地點點頭,將身子一盤,閉上眼睛繼續打盹。
門是關了的,有笛聲隨著淅淅瀝瀝的雨聲從屋外淡淡地傳來。
翹楚閉眼傾聽。
她自是知道那是誰的笛聲。
每天這個時間,上官驚鴻總會在屋外吹笛。
他似乎知道,她會在這個時間醒來。
他變換著曲子,一直吹奏到近...
從醒來到現在,十多個日夜了吧?
一切似乎安寧安靜,又似乎變幻了天地。
翹楚在榻上有些慵懶地復趴回枕上,榻下,一雙炯亮大眼和她眼瞪眼。
她一笑,撫撫獸王的頭。
獸王頗有靈性又大模大樣地點點頭,將身子一盤,閉上眼睛繼續打盹。
門是關了的,有笛聲隨著淅淅瀝瀝的雨聲從屋外淡淡地傳來。
翹楚閉眼傾聽。
她自是知道那是誰的笛聲。
每天這個時間,上官驚鴻總會在屋外吹笛。
他似乎知道,她會在這個時間醒來。
他變換著曲子,一直吹奏到近...
»看全部
作者序
不覺間,進入網路寫作已三年多。
總覺得,這些年在我身上發生了太多的意外——意料之外。
就像高中的時候最喜歡的科目是文史英語,結果因為和同桌玩的好,捨不得分離,隨她唸了政治班。
就像明明同樣喜歡國文,最終卻選擇了外文作為大學專業,一讀數年,並做了相關工作。
就像其實是特怕寫作的人,老師佈置的日記,每每到最後一天、最後一刻才能寫完,是以總記不清陰晴,以致老師批閱日記的時候會說,這週的週幾週幾明明是雨天,別人在天氣一欄寫的都是雨,怎麼到了妳那裡就是晴天,妳穿越了嗎?到我的辦公室來一...
總覺得,這些年在我身上發生了太多的意外——意料之外。
就像高中的時候最喜歡的科目是文史英語,結果因為和同桌玩的好,捨不得分離,隨她唸了政治班。
就像明明同樣喜歡國文,最終卻選擇了外文作為大學專業,一讀數年,並做了相關工作。
就像其實是特怕寫作的人,老師佈置的日記,每每到最後一天、最後一刻才能寫完,是以總記不清陰晴,以致老師批閱日記的時候會說,這週的週幾週幾明明是雨天,別人在天氣一欄寫的都是雨,怎麼到了妳那裡就是晴天,妳穿越了嗎?到我的辦公室來一...
»看全部
目錄
第四十六章 山中不知歲月長 閒看花開靜聽雨
第四十七章 打翹容正式宣戰 記憶錯失來日險
第四十八章 深情呵護終有時 再見故人自有意
第四十九章 恣尋釁西夏來客 群情湧玄湘酒樓
第五十章 素葉莫共花爭發 寸寸相思寸寸灰
第五十一章 誰敢笑誰太瘋癲 誰又笑誰看不穿
第五十二章 承卿一諾征北地 宮宴西夏起風雲
第五十三章 風恨吹不散眉彎 決然回首言不悔
第五十四章 不知道如何開始 如今卻這般結束
第五十五章 太子暗計試睿王 翹楚涉險顯身孕
第四十七章 打翹容正式宣戰 記憶錯失來日險
第四十八章 深情呵護終有時 再見故人自有意
第四十九章 恣尋釁西夏來客 群情湧玄湘酒樓
第五十章 素葉莫共花爭發 寸寸相思寸寸灰
第五十一章 誰敢笑誰太瘋癲 誰又笑誰看不穿
第五十二章 承卿一諾征北地 宮宴西夏起風雲
第五十三章 風恨吹不散眉彎 決然回首言不悔
第五十四章 不知道如何開始 如今卻這般結束
第五十五章 太子暗計試睿王 翹楚涉險顯身孕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墨舞碧歌
- 出版社: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9-20 ISBN/ISSN:978986240901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12頁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