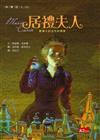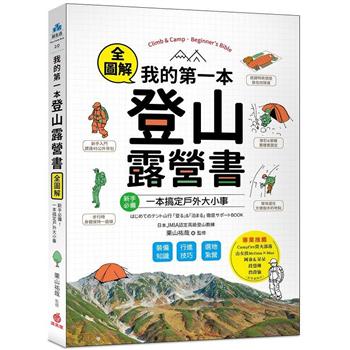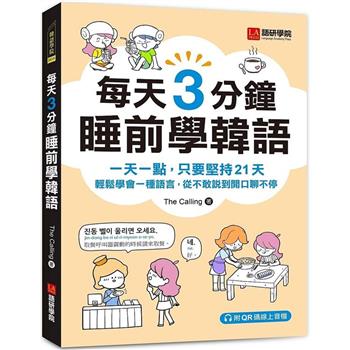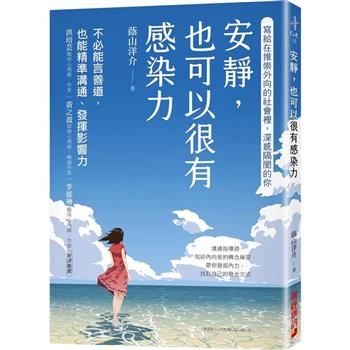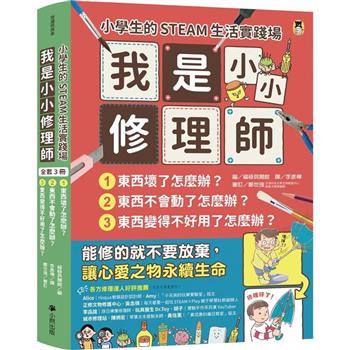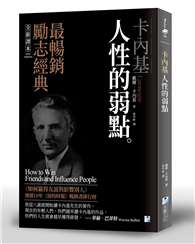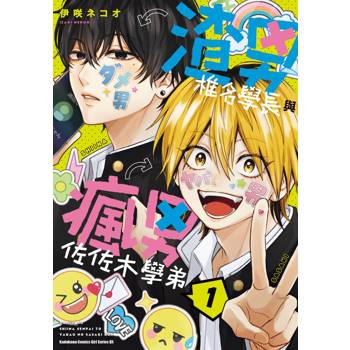前言
瑪麗.居禮(Marie Curie)冒著生命危險研究科學,那種熱情無庸置疑。但是她那些頂著聖徒光輝、勇敢忘我的傳奇,比起她實際經歷的複雜人生,卻遜色多了。
她的確是個天才,不只得過一次諾貝爾獎,而是兩次--先得物理獎,後來又得到化學獎。她跟一位天才科學家結婚,夫婿為了協助她,放棄自己的研究工作,因為她做的是更具開創性的研究。她把自己的天才基因遺傳給女兒,女兒後來也得到諾貝爾獎。
瑪麗的聲名為什麼歷久不衰?因為她發現了兩種無法再以化學方法進一步分解的新物質,也就是新的化學元素──鐳和釙。自然界中存在著許多化學元素,如今我們已經知道的有一百多種,而且還有人不斷發現新元素。但是正如一九一一年諾貝爾委員會所指出的,鐳的發現「遠比其他元素的發現更重要」。瑪麗的家人後來知道,鐳所釋出的放射線足以致命,但是鐳預告了癌症治療上多項令人振奮的發展,並且開啟了原子物理學的嶄新世界。
瑪麗發現了鐳,不只在醫學上貢獻卓著,她針對放射性元素所做的實驗,也促使世人更了解物質的特性。「放射線」這個詞就是瑪麗創造的。她以驚人的先見之明,在第二篇關於放射線的論文中,就說:放射性是一種原子現象。
原子是組成所有物質的基本單位。從遠古時代開始,人們就認為原子是自然界中最小的組成單位,不可轉換、無法分割;是瑪麗的研究,為後代科學家鋪了一條路,讓他們得以探究原子內的究竟。她刺激了次原子粒子(也就是組成原子的粒子)的發現,她的研究間接促成史上最致命武器──原子彈的研發。如果她地下有知,一定不願意看到這樣的事!儘管如此,瑪麗的確協助奠定了今日這個原子時代的基礎。
瑪麗有她嚴酷的一面。她很固執,全心投入工作,有一點烈士的味道。但她不是個呆板的人,也不會去迎合別人。事實上,她曾經說:「我強烈感受到每件事都有它粗野暴力的一面。」
這是一個許多男性揚言要單挑的女性。她對科學的熱愛,強烈到會用九個驚嘆號來記錄實驗順利。她害怕在媒體上曝光,但是狗仔隊卻始終追著她不放。瑪麗在三十五歲左右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她是報紙問世後,常出現在小報頭條新聞的人物之一。她的真實人生有:破碎的愛情、死亡的威脅、搞降神通靈、競爭的焦慮、桃色緋聞、慘重的損失等;還有最特別的,她激烈反抗十九世紀社會的種種束縛。她的一生,都在對抗當時無所不在的「女性止步」標誌。
幸運的是,她似乎擁有無比的耐心和毅力。進大學以前,她做了八年不如意的工作。後來,她花了將近四年的時間,才離析出新的化學元素──鐳。她的故事中最發人深省的是:科學研究需要持續不斷的辛勤耕耘。
就像瑪麗自己說的:「偉大的發現,並非來自科學家的靈光一現,而是無數準備工夫累積的成果。」換句話說,偉大的科學家絕對不是一夕成名,而是經過長年累月的努力,而且要能善用前輩的心血。就像牛頓的那句名言:他是靠著前人的努力,才能夠看得更遠。那麼,幫助瑪麗看得更遠的人是誰?
其中一位是和牛頓同一時代的英國「自然哲學家」波義耳(Robert Boyle)。(「科學家」這個詞,一直到一八三四年才創造出來。)雖然波義耳是個一心想將不值錢的金屬變成金塊的煉金術士,但是他編了一本重要的化學著作。一六六一年,波義耳在《懷疑的化學家》(The Skeptical Chymist)這本書中,提出一個新領域的初步想法,其中包括元素的定義:所有無法再分解成更單純物質的物質,就是元素。
接下來的一百年中,在法國人拉瓦節(Antoine-Laurent Lavoisier)的努力下,化學有了大幅進展。拉瓦節領導當時世界上最傑出的私人實驗室,於一七八九年寫成了《化學基本論述》(Elementary Treatise of Chemistry),為元素下了更詳細的定義,並提出第一張「已知元素表」。五年後,富人拉瓦節因為向人民徵稅,在法國大革命時,不幸被送上了斷頭台。
雖然拉瓦節的腦袋已經不在了,但是俄國化學家門得列夫(Dmitri Mendeleyev)還是站上他的肩膀。一八六九年,門得列夫寫了一本《化學原理》(The Principles of Chemistry),他從自己最喜歡的撲克牌遊戲「單人牌戲」得到靈感,按照類似出牌的方法,橫排是不同的花色,直列是不同的數字,製作了一張元素排列表。他稱這張表中的橫排是「週期」,而且還定下週期的模式,設計出我們如今熟知的「元素週期表」。門得列夫在世時,被正式認可的化學元素約為六十個,例如氧、氫、氦,以及在一七九八年被人發現的鈾。我們今日使用的化學週期表,就是來自門得列夫。
到了瑪麗的時代,科學家所處的社會環境,比法國大革命時進步多了,這有一部分可歸功於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他在一八六八年發現細菌可能引起疾病,因此促使醫學發生革命。這位法國民族英雄認為:實驗室是「聖地」,是「讓人類成長、強壯,而且變得更好」的地方。這種說法,讓瑪麗深受鼓舞。
瑪麗的早期研究多半受到丈夫皮耶.居禮(Pierre Curie)的鼓勵和協助。對瑪麗來說,工作是人生最重要的動力,除了居禮這樣一位本身就是重要的科學家之外,很難想像瑪麗還可以嫁給什麼樣的人。一八九五年,居禮夫婦開始對德國科學家倫琴(Wilhelm Rontgen)以及法國科學家貝克勒爾(Henri Becquerel)的研究感到興趣,前者發現了X光,後者正在研究鈾放射出的各種射線。瑪麗在這兩位物理學家的研究基礎上繼續鑽研,找到了能夠讓自己一輩子著迷的事,那就是:在門得列夫週期表上增加兩個新元素──鐳及釙,並且做進一步研究。
這以後,在成立知名的鐳研究所的過程中,瑪麗貢獻了她的餘生,為新生代科學家提供了可以登高望遠的肩膀。
她的所作所為是那麼的勇敢無畏。瑪麗和居禮後來都因過度暴露在鐳之下而得病,但是正如她那段最知名的話:「生命中沒有什麼可怕的事,只有許多待理解的事。」她沒有把科學看作是痛苦或折磨的根源,而是將它視為一種英勇的探險。她說:「如果我身上有什麼重要特質,那肯定就是永不動搖的探險精神。」瑪麗就像是一個裝滿了鐳的試管,始終以她奉獻的熱情發光發亮。
對於聚焦在科學家身上的聲名,瑪麗曾說:「在科學上,我們必須對事感興趣,而不是對人。」那麼,她會喜歡這本書嗎?可能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