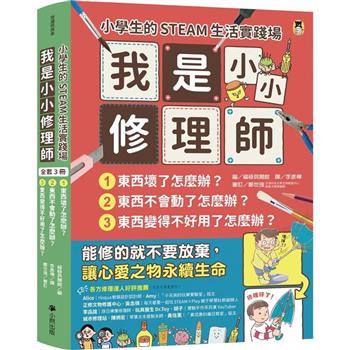推薦序
東方塵世中的修養
黃光國
河合隼雄是日本著名的心理治療師。他自京都大學數學系畢業後,改唸教育,獲得博士學位後,再到瑞士蘇黎世榮格研究所進修,成為日本第一位榮格學派的精神分析師。回國後長期在教育界服務,曾經出任文化廳長官,十分重視日本青少年的適應問題。
榮格本人對東方文化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跟傳統心理分析學派重視心理發展的取向完全不同。在榮格學派的影響之下,河合對日本青少年問題的分析,也特別著重在儒家文化影響下日本人的精神結構。這一點,他的作品跟華文世界的讀者有了極大的共同性,他對日本青少年及父母所提的各項建議,讀來也很容易讓人產生親近感。
舉個例子來說吧,我最近在《諮商心理學家》(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修養:儒家社會中心理治療》(中指出:在基督教文化「告白」(confession)傳統的影響之下,西方從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所衍生出來的各種心理治療方法,治療師大多是採取笛卡爾「主 / 客」二元對立的方式,試圖用各種不同的途徑來理解案主。在儒家文化影響之下,這本書一開始,河合就特別強調:「人心是無法百分之百理解的」。
像儒家文化中大多數的心理治療一樣,他在文化的層次上,分析「大多數人」經常遭遇到的問題,然後對父母及青少年提出他的《心的處方箋》,至於案主要如何用這些「處方箋」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則是「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完全要看自己的修養工夫。
在本書中,河合強調「獨立是靠依賴支持的」,對於西方的主流心理學構成了極大的挑戰。唸過社會心理學教科書的人大多知道:當代主流社會學中最流行的「自我」理論,也是採用「主 / 客」二元對立的方式,認為:西方人的「自我」是「獨立我」(independent self),而東方人的「自我」則是「相依我」(interdependent self)。對東方文化稍有暸解的人,都不難看出這種二分法的偏頗,但卻很少有「心理學者」敢對這種「主流理論」提出挑戰。河合卻是根據自己的文化經驗,娓娓道出他的真知灼見:「獨立是靠依賴支持的!」
不久前,我剛出版了一本書,題為《反求諸己:現代社會中的修養》。以這本書的視野來看河合先生的著作,真是令我感到「處處驚艷」:像河合所說的「一頭栽進去的人才能真的離開」、「權力的位置要求孤獨」、「有時唯有背叛才能保持距離」、「拋離權力才能磨練出內在的權威」,其實都是用現代人的語言,在講儒家「盡心知性以知天」的「慎獨」工夫。我的太太常常批評我的著作太「硬」,太過於學術性,一般人不容易讀,讀完河合先生的這本《心的處方箋》,才讓我看到自己的缺點!
河合指出:日本人凡事太過認真,這又讓我想起西藏喇嘛構作「沙檀城」的儀式。我在最近出版的《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一書中,曾經提出一個「自我的曼陀羅模型」,西藏佛教中的壇城,稱做曼陀羅(Mandela),通常是以彩色繪成,象徵佛菩薩的莊嚴世界,其基本結構為內圓外方,意即慈悲與智慧。在藏傳佛教的大法會中,通常會請幾位僧人用一、兩個星期的時間,用五彩細沙,製作壇城。沙壇城的製作,有一定的規矩,製作過程便是一種禪定與智慧的訓練。製作完成的沙壇城,圖案對稱,色彩鮮豔,壯麗莊嚴,加持法會會場和平吉祥,同時也加持參加法會的大眾所願皆遂,法喜充滿。
法會結束之後,僧人立刻以手指將沙壇城劃破,再將彩色細沙分由信眾帶回家供養,剩下的沙子則灑在河中或大地。壇城象徵佛教修持對自身生命境界所造成的轉化;壇城由製作到毀壞的過程,象徵自身生命的成、住、壞、空;製作和對待壇城的態度,則蘊涵了佛教最高的生命智慧:「凡事認真,卻不當真」。佛教相信業力因果,「生滅隨緣至」,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一切事情的成敗苦樂都要由自己承擔,所以要凡事認真。另一方面,佛教又相信緣起性空,世間萬事萬物皆變化無常,所以不必當真。
西藏僧侶製作壇城的過程中,所蘊含的智慧,幾乎已經包含了東方文化中自我修養的主要概念。河合先生的著作,則是從日本社會中的「世俗」角度,不斷地在詮釋東方的修養。賴明珠女士曾經先後翻譯過河合先生的三本著作《大人的友情》、《心的棲止木》以及這本《心的處方箋》,三本書都邀請我寫序言。她的譯筆流暢,譯作清新可喜,我每次閱讀河合隼雄「言簡意賅」的著作,總有「深獲我心」之感。不幸的是:河合先生在二○○七年時,以七十九歲之齡過世,以後再也讀不到他的作品了。人生在世,知音難覓,這是最令人感到遺憾的吧!
(本文作者為國家講座教授、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譯者序
再續前緣
賴明珠
《心的處方箋》在日本受到非常多人歡迎。不僅在連載期間受到矚目,出單行本和文庫本之後,也長期受到許多人的愛讀。
由於河合隼雄的善解人意,使很多人願意對他攤開來真心深談。村上春樹就是其中一位。
河合隼雄和村上春樹曾經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見過兩次面,回日本後又在京都再度見面深談。所談內容刊登在《村上春樹去見河合隼雄》(時報出版)。
河合先生去世後,村上春樹如失去知音般。在寫完《1Q84》後接受新潮社編輯松家仁之採訪時特別提到,很遺憾在文學世界找不到像河合隼雄先生這樣能理解他的人。
他說「當我說到『物語』的時候,能把我想說的概念的總體完完全全整個理解的,除了河合先生之外沒有別人。在他去世以後的現在我還是這樣想,以後可能也會這樣。我對誰提到『物語』這個用語時,不太有人會有同樣的感覺。經常都意識到什麼地方可能稍微有出入。只有河合先生的情況,真的是完全吻合。在這層意義上,能和河合先生見到面,對我是很大的鼓勵。對於我想做的事,對於我心中模糊的願景,不用說明居然就有人能全盤接受的這件事。」
河合隼雄在無形中確實鼓勵了很多人。
松家仁之又說「河合隼雄先生被村上先生的小說強烈吸引,當然我想有很多原因,不過我想對會話對答的趣味大概也相當有感應。我想河合先生一方面留下了許多著作,另一方面他到最後最珍惜的,是和顧客的對話,聽他們說話,這種一問一答。他也許在自己的工作之間,也在讀著村上先生的小說。我一面讀《1Q84》一面這樣想。……在村上先生和河合先生的對談中,說過『所謂浪漫的愛並不會長久繼續。如果想讓浪漫的愛長久繼續的話,就不能有性關係。我認為一方面擁有性關係一方面要讓浪漫的愛的想法永遠繼續是不可能的。
我想《1Q84》說起來也是浪漫的愛情故事。關於這點您認為怎麼樣? ……」
村上說「這裡日常性就會進來。所謂日常性這東西是繼續的,繼續基本上是無聊的,因此無論如何各種東西都會褪色。如果說褪色這用語不好,也可以說會變質。也就是說會繼續進行價值的重組。在這層意義上,浪漫的愛這東西,也會隨著時間的經過,而當然有必要進行重組。
那要如何戲劇化下去呢?是一個很難的問題。例如《挪威的森林》中主角和綠如果在一起了,故事會變怎麼樣?因為是寫實的故事所以某種程度必須寫得真實,那可能會成為相當無聊的故事。那樣的故事不會想寫,我想讀者也會覺得無趣。
不過《1Q84》不是寫實的故事,所以可以考慮到各種可能性。浪漫的愛會變質成什麼樣的東西?會進行重新改組嗎?故事可能在寫實文脈以外的文脈中成立。」
我在翻譯《心的處方箋》之前和之後,正好翻譯了《1Q84》和松家仁之對《村上春樹的長訪談》。因此印象格外深刻。
事實上,松家仁之到台北參加吉本芭娜娜的新書發表會時,就特別推薦了河合隼雄先生的《心的處方箋》這本書。因此也可以說是這本中譯本的最初推手,在這裡應該特別感謝松家仁之先生。
有人實際上見過河合隼雄先生,聽到他說的話,更多人則是讀到他的書,間接受到他的鼓勵和影響。我有幸能在東京和台北親自見到他本人,聽到他親切幽默又充滿智慧的溫暖語言。感覺格外充實。
他在《心的處方箋》這本書中,舉了很多淺顯的例子。這些例子都是我們生活中很常遇到或聽周圍的人談起的事情。以前感覺不解或不知如何是好的,現在則有了新的看法,得到很大的啟發。雖然未必每件事都能完全解決,但至少有個譜,知道一些可能性和方向。
我在一面翻譯中,一面想像自己所遇到的類似困難,或想不通的地方,會忽然感到濃霧漸漸散了似的,豁然開朗。
心,漸漸清明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