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熱情與執念
山崎豐子的作品,在台灣流傳得非常廣泛,細數已經上市的繁體中文版譯著,就有《暖簾》、《花暖簾》、《女人的勳章》、《女系家族》、《白色巨塔》、《華麗一族》、《不毛地帶》、《兩個祖國》、《不沉的太陽》、《命運之人》等十部,因此,台灣的讀者們對她應該並不陌生。
但對於喜愛她的讀者(當然包括我)而言,心中或許存在著些許困惑。那困惑是:山崎老師從那裡生出來那麼大的創作動力?她的小說題材如此廣泛,是怎麼構建出來的?
這樣的疑點,只能從山崎豐子的三部傳記中找到答案。
天下雜誌出版部之前已經出版山崎豐子三部傳記中的《我的創作,我的大阪》,在那本書中,山崎豐子很清楚地說明了她早期的作品的創作概要,讀者因此而能了解她早期作品的背景,為何都以大阪(她的故鄉)為主。在這本《作家的使命.我的戰後》中,山崎更明確地交代她創作《戰爭三部曲》(《不毛地帶》、《兩個祖國》、《大地之子》)及後期作品《不沉的太陽》、《命運之人》的心路歷程。而創作這些小說時,山崎豐子可以說已經是一位非常成熟的作家,她在本書中談到她小說的創作、採訪的方式及小說家的使命,都非常的重要。個人認為,喜歡山崎老師作品的讀者不但應該一讀,有志朝小說創作之路邁進的年輕人,更應該仔細研讀,相信在閱後必有重大啟發。
以我個人的看法,我會認為,山崎豐子畢生的作品中,《戰爭三部曲》應該算是她最重要的創作。這三部作品之中,《不毛地帶》描寫的,是二次世界大戰後,被蘇聯俘虜並被流放至西伯利亞集中營的六十萬日本軍人;《兩個祖國》的背景,是珍珠港事件爆發後,被美國政府強制關到集中營的十餘萬日裔美國人;《大地之子》的主角,是二戰後被遺棄在中國大陸的戰爭孤兒。這三部鉅著,耗費了山崎豐子十八年的歲月。
二戰的記憶,一直是山崎豐子揮之不去的陰影,她曾回憶,在戰爭時期,跟她同年齡的男生都被拉去充軍,女生則被迫中斷課業,集體到兵工廠擦子彈。生活雖然困頓,但對照周遭一個又一個命喪戰場的同學,卻又幸運太多。她從那時就認真思考,「生還下來的人,到底該做些什麼?」人生不能重來,老天爺不能還她一個無憂無慮的青春歲月,她只能藉由小說創作提醒世人,勿忘戰爭的殘酷。《戰爭三部曲》一再重覆出現的主題就是:走過戰地的焦土,戰後的日本雖然富裕起來,但心靈是否仍是一片不毛之地?在本書中,山崎豐子就這麼呼籲,「忘卻戰爭是很可怕的事,幾乎與自殺沒兩樣。」
要創作這樣的題材,難度當然相當高。其中最困難的,就是如何蒐集素材。
山崎豐子自己承認,「我的作品裡的生命,來自採訪。」在本書中,山崎豐子也很大方地向讀者分享了她採訪的方式。
她說,她創作的步調是:四天採訪,三天書寫。但採訪時,並不是盲目的蒐集,她會先立訂作品的主題,將登場人物和故事大綱設定好,再開始採訪。
以《不毛之地》為例,為了採訪,山崎豐子獨自橫跨整個西伯利亞,從伯力一路走到莫斯科,之後,又飛到中東油田採訪。這部作品,山崎豐子前後寫了五年,用掉五千張稿紙。訪談三百七十七人,登場的小說人物達兩百一十人。
《兩個祖國》是山崎豐子嘗試將二戰時美國日裔俘虜集中營、太平洋戰爭、廣島核爆、東京大審四大主題結合在一起的小說。寫作的難度更高。因此,她光是設定主題、閱讀資料、採訪,就花了兩年時間,之後下筆,又花了三年多的時間才完成這部小說。
《大地之子》創作歷程耗時八年,由於書中主題是描寫滯留在大陸的戰爭孤兒及尋找血親的故事,為了採訪,她住在中國長達三年,待過農村、工廠,走訪過監獄,並曾四度進入中南海,晉見中共總書記胡耀邦。
在那個相當封閉的時空環境裡,山崎豐子在中國大陸的採訪工作,想必相當困難,但在她鍥而不捨地追逐下,連加入中國共產黨時,該如何填寫入黨申請書、加入後又如何宣誓的細節,最後都躍然紙上。
山崎為小說的採訪,不是只有《戰爭三部曲》才如此工程浩大。之後,她為了《不沉的太陽》採訪,曾以七旬高齡,四度造訪非洲。同時,為了清楚掌握航空史上最重大空難發生的經過,她採訪御巢鷹山空難遺族,並閱讀了全部的驗屍紀錄。
至於為了替《命運之人》一書採訪,山崎豐子遠赴重洋,到美國檔案局裡,面對數萬立方呎的檔案,抱著一本日英字典,逐頁逐字地查找資料,那種精神與毅力,自然更令人動容。
對於採訪,山崎豐子這麼告訴讀者:「採訪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技巧,一切只是在於誠實及努力。」但其實,要做到「誠實及努力」,就非常不簡單。
例如,山崎豐子為《大地之子》採訪,第一次晉見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時,胡耀邦以為山崎豐子要寫一部促進中日友好關係的小說,因此表示會盡力協助,但山崎豐子不改直言本色,很清楚的回答:「小說並不是一種意識形態,所以不會書寫歌頌中日友好的小說。但寫作的結果,若能夠促進中日友好,也是一樁好事。」而胡耀邦也很大方的說:「妳若想寫中國落伍的部分、缺點、陰暗的部分,都可以。我讓妳的採訪通行無阻。」
對此,山崎豐子一直感念在心,並認為胡耀邦是《大地之子》的親生父親。這部作品在日本連載期間,胡耀邦過世,令山崎豐子非常難過,兩年後,她排除萬難,趕赴江西省共青城,將已發行成上、中、下三本單行本的作品,獻在胡耀邦的墓前,作為對他的最敬禮。試想,如果山崎豐子當初為了怕被拒絕,而虛與委蛇地應付胡耀邦,事後,這部作品要如何獻在胡耀邦的墓上呢?
又例如,在為《兩個祖國》採訪時,山崎豐子想要訪問東京大審的語言審查官。在史實中,東京大審的語言審查官有四人,但在審判結束後,一人病死、一人自殺、一人被送入精神病院,最後一人下落不明。山崎豐子費了三個月的時間,好不容易找到這名下落不明的審查官,並進行連續多天的訪談,這才讓書中的相關情節活絡起來。
耗費這麼多力氣,這麼大量的採訪,真正能應用在小說裡的內容多不多呢?山崎豐子坦白地說,只有四十分之一而已。這幾乎已經是一種淬鍊了。
或許有人會問,資料的查找與蒐集,有必須做到這麼細緻化的程度嗎?對此,山崎豐子自謙解釋,「勇氣不足,若不詳細確認,就沒有辦法提筆。」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毋寧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也或許與山崎豐子早年所受的記者訓練有關吧。
除了資料的蒐集,採訪的另一個重點,在於人物訪談。山崎豐子自述,訪談時,每天早上十點開始到晚上九點才休息,用在受訪者身上的訪談時間,平均每人約在兩小時至兩個半小時左右。而採訪後,還必須紀錄、整理,工作時間自早上十點到半夜一點,每天工作至少十二個小時。
大量工作的結果,讓她的健康受了嚴重的影響。山崎豐子說,在《大地之子》的創作後期,她的右手食指和大姆指之間神經麻痺(橈神經麻痺症),她只能將鉛筆夾在兩指中間,再輔以左手,用兩隻手一起寫。
所以,山崎豐子自述,她在創作時,就有如入監服刑,一直要到寫下最後一個句點,才會有一種「出獄了!出獄了!」的解脫感。
剛開始創作時,山崎豐子曾立下「一年一作」的志向,但隨著採訪難度愈來愈高,創作格局愈來愈大,最後竟成了「十年一作」。當外人疑惑:「這麼久才創作一部著作,要靠什麼維生啊?」山崎豐子卻說:「耗費如此長的時間從事一項工作,最難的是必須對同一件事情持續抱持著相同的熱情與耐心。」
的確,要把八年、十年的時間,全心全意把心思灌注在一部小說上,連手術麻醉前都還掛念著:「啊!漏寫了…」,若沒有這種執念,長篇小說如何可能完成?「寫小說只有文筆好、素材好是不行的,重點是要表現出人情故事。」山崎豐子自述:「對於人類的喜愛,絲毫不曾厭倦。」這正是她創作的熱情來源。
身為社會派小說家,山崎豐子必須讓她的作品與真實社會的環境、背景及重大的社會問題相扣合,例如,《白色巨塔》問世時,日本的大學醫學院剛好爆發嚴重的醫界醜聞;推出《華麗一族》時,正巧碰上銀行問題;《不毛地帶》在雜誌連載期間,震驚日本的「洛克希德醜聞」也浮上檯面。而《命運之人》發表後,蒙受不白之冤的記者西山太吉也終獲回復名譽。
關於此一巧合,有人認為,山崎豐子的作品都預言了即將發生的重大社會事件,但山崎豐子卻認為,她描寫的題材都是社會現象,寫作的目標原本就朝著揭發社會弊端的方向前進,是因為小說的內容讓讀者們更加關注書中提到的背景,如醫界、金融業等,一旦關注後,這些行業中的弊端自然也就跟著被突顯出來。
所以,最終還是回歸到「人」的因素,因為對「人」充滿了興趣,才會不停的在作品中描繪人生百態。
小說的題材屢屢觸碰社會禁忌,山崎豐子可謂非常勇敢。
她認為,這正是身為社會派作家的使命。她曾說:「若失去財產,再賺便有;失去名譽,只要振作也可挽回。但是 ,人如果失去勇氣,那麼還不如不曾活過。」、「身為作家,我若失去勇氣去寫出應該寫的故事,那麼就等於我已死去。」
其實,旁人再多的介紹,還不如看山崎豐子如何省視一名作家的自我定位:「小說家這種工作,是挑戰並書寫自己未知的部分。」、「作家必須自懲,讓自己處於饑饉狀態。絕不發表無法超越舊作的作品,要讓讀者接觸新作品時,甚至忘了舊作品。」、「要寫超過既有作品的好小說,是多麼困難的事。而且我每天都會責備自己,為何選擇這樣的主題,然後,繼續痛苦地奮鬥。」、「作家這種職業,必須擁有超越生死的堅強信念以及生死觀。」、「與其寫出無味的作品,還不如不要寫。寫出無味的作品,才是對不起讀者。」
在小說界,山崎豐子就是一顆不沉的太陽。
范立達
(本文作者為資深新聞評論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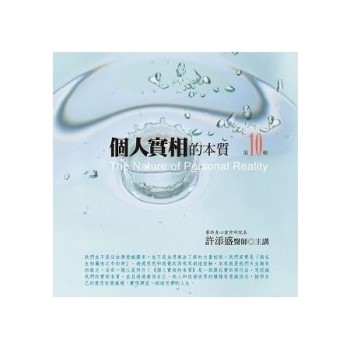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