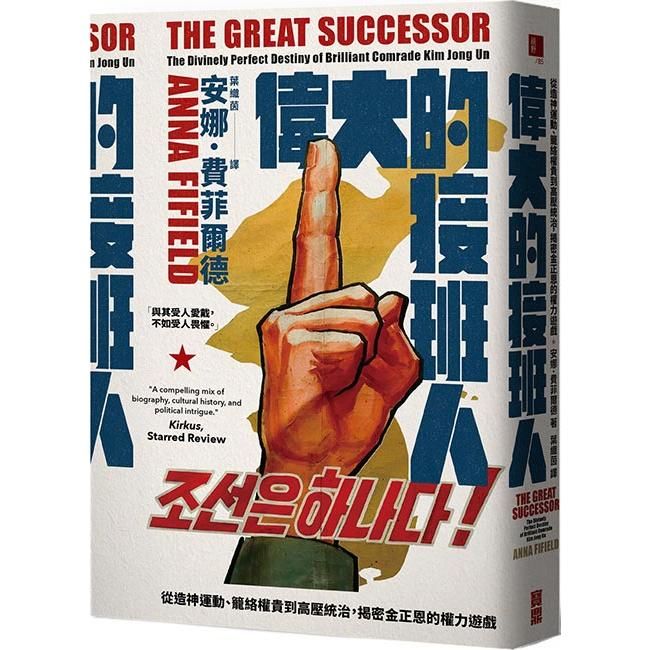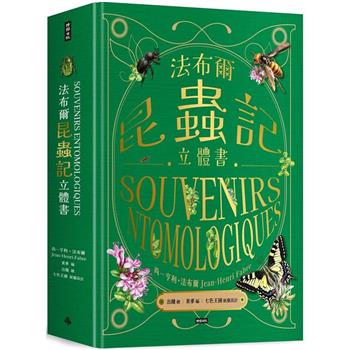圖書名稱:偉大的接班人
洛杉磯時報、衛報、金融時報、NPR報導
亞馬遜網路書店4.5顆星讀者好評
全球售出11國版權
七十年永垂不朽的金氏王朝祕辛
謎樣暴君金正恩的崛起和統治內幕
橫跨八國、超過數百小時的訪談
《華盛頓郵報》駐外記者第一手獨家報導
招牌誇張油頭與過時黑色中山裝、時不時就祭出飛彈恫嚇他國的「火箭人」⋯⋯一般人對於金正恩的印象,常止於他富有特色的外表、是網路迷因與諷刺漫畫的常客,但對於其人格養成與處事思維卻只能仰賴流言蜚語,更因資訊備受箝制而難以一窺其貌。究竟這個受過西方教育、血統並不純正的么子,是如何走向金氏王朝的寶座?沒有祖父金日成的英勇抗日事蹟,更沒有父親金正日的白頭山神話加持,他如何快速掌控搖墜不安的政權,鏟除異己、創造個人崇拜?
熟諳韓語的《華盛頓郵報》記者安娜.費菲爾德在專職報導這個神祕國度期間,決心追查相關情報並挖掘出這個接班人與該政權背後的真實面貌。她多次往返朝中邊境,訪問數十位脫北者及往返兩國的商人;獨家採訪金正恩在瑞士求學期間的監護人——阿姨高容淑和姨丈李康——和同班同學、金家壽司師傅暨金正恩兒時「玩伴」藤本健二、與哥哥金正男親如姐弟的表姐李南玉、彼此有著奇特友誼的NBA球星丹尼斯.羅德曼,並多次會見曾權傾一時的平壤權貴,如前北韓駐英大使太永浩與大財主李正浩一家。
本書將解答:
★在與世隔絕、環伺獻媚之人的生長環境,扭曲自戀人格如何從小養成?
★保密防諜、弒親又殺老臣,權貴為何甘願賣命,用血與汗建成平哈頓?
★從滑稽外表、鬆綁私有企業到誇耀核武實力,步步皆經縝密算計?
從平壤的摩天大樓到馬來西亞的太平間,從泰國的小旅館到美國的乾洗店,費菲爾德遠赴八國、累積超過數百小時的訪談內容,按圖索驥一步步揭開金正恩的神秘面紗,帶領讀者了解這個獨裁政權如何保持其完整性,對新一代造成何種影響,以及北韓和世界未來將會是何種模樣。
本書特色
1. 第一手詳實採訪報導與實地調查,彙整許多首次公開的獨家專訪內容以及和眾多長期關注北韓動向的專家學者意見,增加本書可看性與真實度。
2. 幫助讀者了解北韓社經狀況、對國際情勢的關係與影響、金氏家族的歷史以及金正恩為鞏固政權而使用的暴虐手段與決策內幕。
3. 人物觀察細膩、描寫生動,詳實描繪出身處北韓極權統治之下的困苦、金家與權貴極盡奢華的享受,以及鎮日惴惴不安於隨時可能入獄勞改的恐懼,讓讀者對於北韓政權的高壓統治有更深一層的感受。
作者簡介
安娜.費菲爾德
現任《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社長,此前則專注於報導北韓議題達八年之久。 先後任職於《金融時報》與《華盛頓郵報》,往返北韓數十次。曾獲選為哈佛大學的尼曼新聞學人(Nieman Journalism Fellow),以封閉社會中的變化為研究主題;2017年入圍亞洲協會(Asia Society)的奧斯本艾略特傑出報導獎(Osborn Elliott Prize);更於2018年憑藉出色的亞洲報導獲得史丹佛大學的肖倫斯特新聞獎(Shorenstein Journalism Award)。
譯者簡介
葉織茵
專職譯者。譯有《拿破崙並不矮:歷史寫錯了!》、《10分鐘入禪休息法》。聯絡信箱:esmeyeh@gmail.com,歡迎各方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