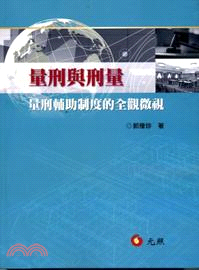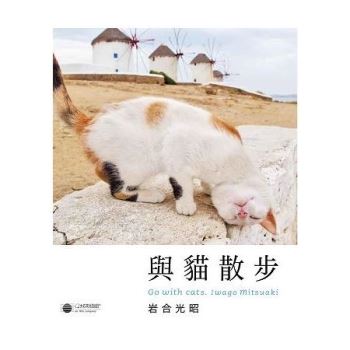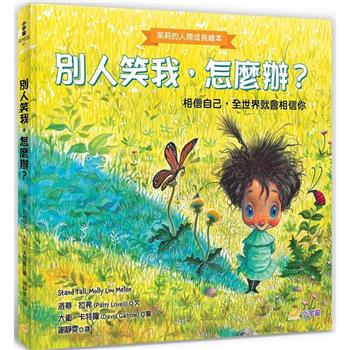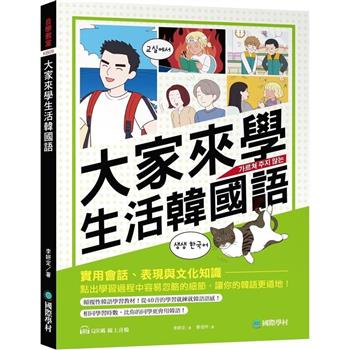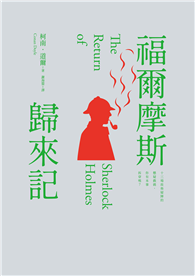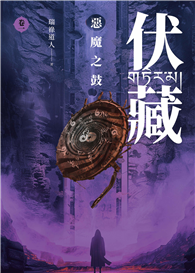自序
從正義的追尋開啟研究之門
誠如美國當代深具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John Rawls所言:縱使「正義」一直是個模糊的哲學概念,但「正義」仍是維繫社會體系的主要且絕對必要的德性。問題是「正義是什麼?」這個問題,對法官如何斷案固然非常重要,對置身於法庭的人們而言,更是重要。
史賓斯(Gerry Spence)認為:「正義就像生命一樣,無法給予適切的定義。」著名的律師丹諾(Clarence Darrow)也堅稱:「並沒有所謂的正義;事實上,這個字眼無法被定義,但它卻能被感受。」正義是神聖的迷霧,不可避免地與事物存在的狀態緊密關聯。我們多數人對正義只是模糊的意象,直到親身經歷正義被剝奪時,才會明白它的切確涵義;正如三餐不繼的貧困小孩巴望著高尚人們在高貴餐廳享用滿漢全席,他知道「不義」的意義,監獄中無辜的受刑人也明白;就連在街角為爭食一根骨頭而被打得遍體鱗傷的野狗,也知道「不公正」是怎麼一回事。
在字典裡,Justice有時是指「正義」,有時指「法官」,有時則是指「裁判」之意。而裁判的目的,在於公平正義的實現,被認為是一般常識。誠如橫川敏雄的定義,所謂Justice一詞,除了具有公平正義的意義外,尚包含裁判以及裁判官的涵義在內;正義是探討出來的,它不是固定不動的概念,而是根據個別存在的現實狀況去思考。以裁判為目的的Justice是藉法官在訴訟過程中,發現客觀正義之意;簡而言之,在訴訟中利害關係相對立的雙方當事人,基於公平競爭的精神,以攻擊防禦的形成,在主觀性正義相互論爭的基礎下,由公正無私的法院加以發現者,就是正義。
愛因斯坦曾說:「上帝是不會用骰子來運作宇宙的。」如果這個命題無誤,除非上帝根本不存在;否則,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為什麼好像都是由有權的人以擲骰子的方式來決定,是否為隨機造成的結果?將刑法中抽象的法令適用到具體的個案,不是、也不應僅僅是一個法律的或抽象的邏輯問題;而須從心理學、社會學的角度,把僵硬的法條經過審判行為主體的思維作用,適用到活生生的個人及社會生活世界。然而有思想的動物,都必然有自己的觀點。在不同的時、空環境,會從不同的面向,看待相同的事務。因此,司法的結論、當事人的命運,不但取決於司法官的邏輯推理能力、對法律概念的掌握,往往也取決於司法官主觀的感情、生活經驗,取決於一切足以使事務的面目在人們波動的心中隨時改變的細微因素。
社會學家耶爾利赫(Esaac Ehrich)稱:「長遠觀察的結果,除了法官的人格以外,正義沒有任何保障。」身為法官,尤其是刑事法官,對這一句話誠有必要不斷地體會,並自我警惕。
Learned Hand說過:刑事案件最可怕了;但對公眾而言,刑事案件也最吸引人。自從進入司法界,多年的法官生涯,絕大部分的時間擔任刑事審判職務。個人非常認同橫川敏雄的看法:刑事法官擁有極大權限,對被告命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在行使權力時,無論在程序法或實體法上,均具有廣泛的裁量權。實際上,法官擁有何種人性觀、國家觀、法律觀、審判觀或刑罰目的觀,多半會歸結在裁判上。因此耶爾利赫所言,確已突進問題的核心。一位刑事法官是否擁有溫暖的心腸,且能不斷地檢討自己的缺點,並具有為此而憂慮的謙虛性格;或者,是一位將所有問題都從論理性或事務性以為分辨?兩者對案件審理的方式、證據的評價與結論,將會發生很大的差距;縱使最後的結論相同,給予當事人間的印象,也將大為不同。
「公平正義」不會出現在刑法條文中,也不會在教科書中天然地形成。法律的生命不在於理論邏輯,而在於經驗。英國丹寧爵士(Sir Alfred Denning)在《通往公平正義之路》(The Road to Justice)一書中表示:「所謂公平正義,是大家無法看到的東西,並不是瞬間之物,而是永恆。那是心術公正的社會構成員,不依其智能,而是依其理性的精神,相信是公正之意。」現實個案中,真正涉及高深的法學理論爭議的,實為可數。雖然,為解決法律上的疑難問題,也曾付出不少的辛勞;但如果與訴訟指揮、事實認定、量定刑罰相比較,這樣的辛勞誠然微不足道。
尤其,刑事司法是一種適用法律、獨立的實踐活動,具有其內在規律性,既可能使罪刑法定化的「死法」轉化為「活法」,實現刑法的人權保障與社會保護的雙重機能;也可能破壞罪刑法定,使刑法成為具文。有認為刑事法官擁有廣泛的刑罰裁量權,如缺乏必要的自制,無異是立法者交給法官違法擅斷破壞刑法法制的鑰匙,濫權擴大裁量,敞開了量定刑罰中畸重畸輕的破壞法治原則的大門。但也有認為,法官應隨時試著改良法律,如果法律「要求他把某個寡婦逐出於平安夜的暴風雨中」,法官應該拒絕執行這樣的法律。當法律條文的貫徹可能與良心、正義的要求有所衝突時,那種心靈的煎熬,其實才是法官最困難的工作。
近年,司法改革的呼聲喊得震天價響。要建立國民對司法公正的信賴,制度的改革固然重要,但累積一個個單一個案正義的實際體驗,可能更具說服力。沒有冤屈,沒有司法過分的主觀恣意,沒有不合理的不公平對待,就是人民之於司法的期待!
清朝張問陶有詩曰:「此筆非刀筆,沉吟判語遲;案成真似鐵,律細過於詩。」這首詩點出裁判的筆事關重大。
目睹潮來潮往般的刑事被告,相信絕大多數的法官都能自期「勿枉勿縱」、「刑當於罪」、「刑及於罪」;但日復一日的審判職務,是否也會由於審判職務的嚴肅性、繁瑣性與反覆性,導致精神因過於忙碌而失去彈性,思維能力日趨僵化,模糊自己長久以來努力追求的目標。
從司法院的統計資料顯示,地方法院每年新收的刑事案件約三、四十萬件。經審理認定有罪科刑者高達半數以上。在這一、二十萬的「有罪之人」中,法官量刑是否都縱向的維持著不受時空因素改變的一致性;橫向的保持寬嚴等量的衡平性;質言之,我們是否真的能給予公平正義的對待?一直深切期盼能得到一個答案。
廣義的刑事司法學體系,雖包括刑事法學(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犯罪學、刑罰學與犯罪偵查學;但其樞紐,則為刑事法學中的法院的活動。法院的活動是一種司法程序,經由這個程序,法律的正義乃得伸張;各種刑事學理論建構所欲追求的目的,方能落實。
刑事法官在司法活動中的三大職責:一、研判與案件有關的各種犯罪事實與情狀;二、正確運用犯罪事實該當的法律條款;三、進行刑罰裁量(量刑),作成適當而公正的刑事判決。從司法機制的開啟,以迄判決的確定,此一過程中卻包含多元的爭議性問題,其中又以量刑最為困難;當中,乃廣泛地涉及刑罰學(尤其刑罰的目的觀)、犯罪學、社會學、心理學乃至統計學等,單從傳統的實體刑法及程序法的教育,其實無法肆應量刑上的需要。
畢竟,量刑是實現司法權威的一項重要活動,是法官最重要的職務行為;但法官面對的是千姿百態的人類行為,是氣象萬千的社會生活,是比法條和規範邏輯更為複雜的現實,因此,量刑也是刑事審判過程中最困難的工作。
其實,量刑歧異的司法現象,並非我國所特有,而是長期存在的、全球化的問題;也是推動量刑改革運動的重要根源。如何避免法官量刑歧異,建構公平的司法模式,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共同難題。早在1970年代中後期,由於實證主義的盛行與法官自由量刑權的廣泛運用,量刑歧異益形明顯。一股從美國開始的量刑改革浪潮席捲全球,各國都在積極探索有效規範量刑的機制,也陸續發展出各種成功的模式。甚至,刑事司法理念相對滯後的中國,最近幾年也有幾個法院研發出類型不同的量刑規範。
筆者長期從事量刑研究,並曾分別引述各國量刑制度改革趨勢,總括言之,其具體措施,都是從審判周邊的環境系統著眼,輔助法官量刑。包括美國、澳洲與英國的「量刑準則系統」、荷蘭的北極星求刑系統、德國的JURIS的資料庫、日本以KRP程式語言編制出包括實體法和訴訟法的檢索諮詢軟體……等,都是運用資訊科技將數量龐大的個案,進行持續不間斷的統計、類型化分析,提供法官量刑參考,以確保司法審判的一貫性、公正性,體現「同等情況,同等對待」平等原則的要求。運用資訊科技來輔助法官量刑,儼然是各國共同的趨勢。
司法院為順應各國趨勢,具體回應司法改革的呼聲,經審慎規劃並委託專業團隊研究後,正式推出「妨害性自主罪量刑資訊系統」,作為法官公正量刑的輔助工具,期能幫助法官舒緩沉重的工作負荷,進而提升裁判品質,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賴;此一措施如能有效推動,無疑是司法改革最重要的一個環節。但因國內部分論者仍停滯於上一世紀的理解,仍以為此措施是電腦取代法官,或認為可能侵害法官裁量權,壓縮審判自主空間,有違法官獨立審判的憲法規定。
正如學者Rose所言:「雖然每個國家或政府都有其獨特困擾的問題,但在不同國家中,相同的政策領域卻有其解決問題的類似經驗;因此,在面臨一項共同問題時,似可以將解決問題的經驗彼此分享,達到相互學習的效果。」但也誠如Erich Fromm所言:「隔離感是一切焦慮不安的根源。」許多好的國外制度被引進時,常常因為陌生而排斥,甚至因誤解而抗拒,殊屬可惜。
有鑑於此,本書主要分「量刑」與「刑量」兩大議題。前者特將代表幾個主要模式的英、美、澳洲、荷蘭制度,進行分析、比較,並藉此對照司法院現正試行的「量刑資訊系統」,規整其要旨、特色,期能讓國人充分認識各國量刑改革趨勢,轉而理解、支持司法院的努力。另,中國在法治發展上,雖為相對滯後的國家,但近年來未達均衡量刑的目標,部分法院也進行了一些改善措施,於此一併介紹、闡明。其次,歷敘司法院量刑改革的過程、現況與未來,期能啟發各界對司法院努力、用心的認同。並從質化與量化方面的研究,呈現現行量刑實務上的問題,藉以佐證建置量刑輔助系統的必要性。後者,則從犯罪學的相關理論,以少年犯罪行為為例,探討少年司法的一些重要議題。
誠如法蘭克.雪曼(Frank D. Sherman)所稱:「生命中的一大喜悅,是發現在每個人生道路的轉折處,都有和善健壯的手臂,扶我一把,助我繼續前行。」於此,我真誠感謝兩位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陳玉書老師與司法院秘書長林錦芳博士。玉書老師是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博士,治學非常嚴謹,對後學的指導與愛護,更是熱心。這一段研究歷程,最難能可貴的,與其說是學位的取得,毋寧是對一位良師的造詣與教學熱忱的深切體認。老師為了統計數據上的出入,不厭其煩追根究柢地再三驗證以求真解的研究精神,是我為學處事的最佳典範。林秘書長同樣也是畢業於美國杜克大學的法學博士,於90年代初期,開啟國內有關美國量刑改革研究的先河。此後,學術與實務兩界,在這個領域的探討,無論如何附加、調整,其實都不出林秘書長在十多年前所建構的框架。秘書長不僅在各國量刑改革模式的趨勢,多所啟發;關於實務的最新發展,更給予很寶貴的意見。其提攜後進的熱忱,令人感動!
當然,最重要的,我不能忽略我的家人。文仕於10年前以非司法人的視角,陸續在法學期刊發表「論刑事法領域內的司法造法權」、「再論刑事司法權的成長與極限」、「釋字263與刑罰裁量規範的邏輯思考」、「刑法類推禁止原則的當代思考」、「現代刑法規範內涵的道德解構」……等論文,收錄於《刑法類推與司法造法》一書。這一本書,對本書的寫作動機有很大的啟發作用。該書著重於概念的闡述,對於刑罰裁量雖點出問題,但如何解釋法官的量刑行為、如何經由實證分析找尋證據,並未進行探討;而這部分正是本書的核心議題。要特別感謝的是,為了讓我能全心投入研究,文仕除了要兼顧自己繁忙的內政部業務外,還需充當我各項疑難的諮詢對象,幫忙整理資料、排版、校正,並無條件地包辦所有的家務。耘非、夢非也非常懂事地讓媽媽能在繁劇的審判業務之餘,全心全力投入研究工作。面對許多電腦的突發狀況,耘非更扮演了救火隊的角色。
詩云:「不管大事還是小事,我們總得完成份內的工作。做不了大路,何不做條羊腸小徑;不能成為耀眼的太陽,又何妨是閃亮的星子。成敗不在於大小──只在於是否已經竭盡所能。」本書的完成付梓,代表著一個長期的刑事審判者實務經驗與理論探索的結合;當然,也結合了許多司法前輩與學術前輩的經驗傳承與鼓勵,也結合了諸位好友的協助,併致上最誠摯的感謝。
郭豫珍
2013年6月1日
誌於青山鎮 雲山之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