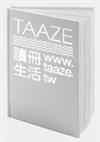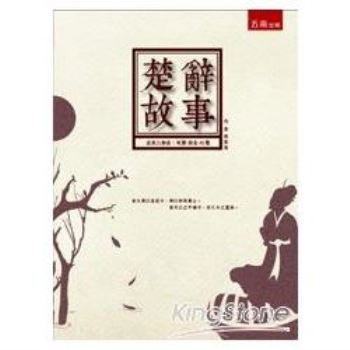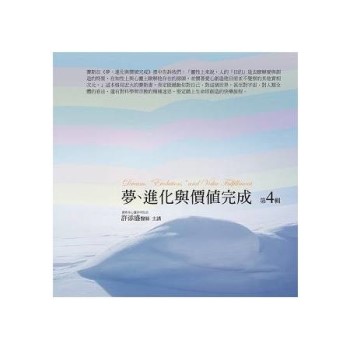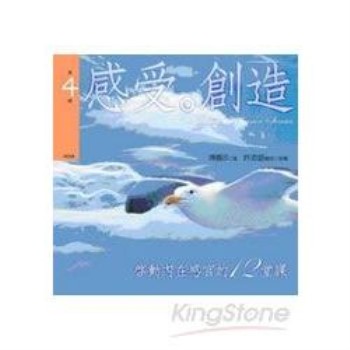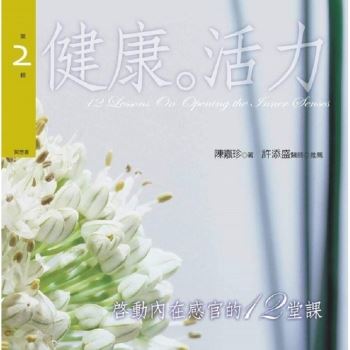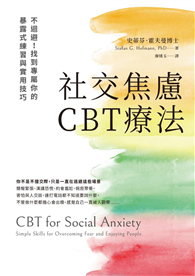本書是作者投入文化法學而思索的第二本學術專論,寫這本文化法專論的主要目的,從專論名為「文化基本權與多元文化國」可知:是嘗試從文化基本權與多元文化國建構文化法制的憲法基礎。對此的嘗試,將首先以我國相關的文化基本權條文作一個概括性的檢視(第二章);其次,從多元文化國的角度,討論通訊傳播自由的基本權保障(第三章)並將焦點集中在事業通訊自由,而進一步探討該自由的保障與限制可能(第四章);接著,針對建築文化資產的保存問題,探尋憲法依據與在文化政策上的實踐(第五章);此外,藉由比較法制的角度,以德國「文化國」的發展作為我國相關思考,作為形塑文化公民權的借鏡(第六章);最後,本書企圖將貫穿本書的基本理念,整合性地用來建構未明白規定於我國憲法基本權目錄的藝術自由保障(第七章)。而各章節之重要想法,將條列示的呈現在結論與建議中,希望能夠提供作為思索我國多元文化國與文化基本權法制時,一個提綱挈領的藍圖(第八章)。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文化基本權與多元文化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551 |
社會人文 |
$ 551 |
社會休閒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內容簡介
目錄
自 序
本書常用德文縮語中文對照表
本書引註格式說明
第一章 導 論
Ⅰ/1
Ⅱ/1
Ⅲ/2
Ⅳ/4
Ⅴ/4
Ⅵ/5
Ⅶ/6
Ⅷ/7
第二章 文化基本權作為文化憲法的建構
壹、前 言/9
貳、自我實現作為文化基本權建構的基礎/11
一、自我實現與多元文化社會/11
二、文化基本權、文化國與文化憲法/15
參、文化基本權作為文化憲法的主觀權利建構/22
一、教育基本權的保障/23
二、學術自由的保障/27
三、藝術自由的保障/34
四、宗教自由的保障/38
肆、文化國作為文化憲法的客觀法建構/45
一、文化國概念的歷史發展/46
二、基本法中文化國的內涵要素/51
三、作為文化基本權客觀價值決定的文化國/56
四、文化國、法治國與社會國/59
伍、結 論/62
第三章 多元文化國下通訊傳播自由的建構
壹、前 言/65
貳、多元文化國建構下的通訊傳播自由/69
一、自我實現、文化基本權與多元文化國/69
二、我國憲法上對多元文化國的規定/79
三、多元文化國下保障通訊傳播自由的憲法原則/83
參、通訊傳播自由的基本權保護範圍/95
一、通訊傳播自由的憲法保障依據/95
二、通訊傳播自由在我國憲法的基本權保護範圍/100
三、通訊傳播自由的基本權主體/105
肆、通訊傳播自由功能建構下的基本權保護法益/107
一、通訊傳播自由作為防禦權的保護法益/108
二、通訊傳播自由作為共享權的保護法益/120
三、通訊傳播自由作為客觀價值秩序的保護法益/124
四、通訊傳播自由作為制度性保障的保護法益/127
五、通訊傳播自由作為組織與程序保障的保護法益/132
伍、結 論/138
第四章 通訊事業通訊傳播自由的憲法保障
壹、前 言/143
貳、通訊傳播自由及其憲法保障/144
一、通訊與傳播的概念/144
二、通訊傳播自由的憲法保護領域/149
參、基本權功能建構下通訊事業通訊傳播自由的內涵160
一、防禦權/160
二、共享權/161
三、組織與程序保障/162
四、國家保護義務/164
肆、通訊事業通訊傳播自由的違憲審查體系建構/166
一、通訊事業通訊傳播自由的侵害/166
二、通訊事業通訊傳播自由受侵害的阻卻違憲事由/167
伍、結 論/199
第五章 多元文化國下建築文化資產保存的建構
壹、文化基本權、多元文化國與文化政策/203
一、人的自我實現、文化基本權與多元文化國/203
二、多元文化國下的文化政策建構/204
三、多元文化國下的台灣文化政策問題/205
貳、多元文化國下建築文化資產保存的政策檢討/208
一、大中華意識建構下的建築文化資產保存/209
二、鄉土運動與文化建設推行下的建築文化資產保存/210
三、以地方為主體的建築文化資產保存/211
四、在地文化風潮影響下的建築文化資產保存/212
參、多元文化國下建築文化資產保存的憲法保障/214
一、多元文化國的文化行政中立原則/214
二、多元文化國的文化行政寬容原則/218
肆、多元文化國保障下建築文化資產保存政策的建議/220
一、人民文化基本權保障的落實/220
二、地方文化教育的規劃與推廣/221
三、社區總體營造概念的導入/222
伍、結論與建議/227
第六章 文化國與文化公民權
壹、前 言/231
貳、自我實現、文化基本權與文化國/236
一、自我實現與文化基本權/236
二、文化基本權的主觀權利與客觀法建構/238
三、文化國作為文化基本權的客觀價值決定/243
參、德國文化國的發展、內涵及國家職責/247
一、文化國的歷史發展/247
二、文化國的內涵型塑/250
三、文化國、法治國與社會國/255
四、文化國作為國家目標的國家職責/259
肆、我國文化公民權的可能型塑/266
一、文化公民權的緣起與定位/266
二、多元文化國下文化公民權的公民概念/268
三、文化公民權作為文化國的社會整合職責/271
四、文化公民權作為文化國的文化權保障/274
伍、結 論/278
第七章 文化國下的藝術自由憲法保障
壹、前 言/283
貳、以自我實現為核心的文化國/288
一、自我實現、基本權與法律/289
二、自我實現、文化基本權與文化國/294
三、文化國、法治國與社會國/299
參、憲法上藝術自由保障的建構/308
一、藝術的概念/308
二、我國憲法上藝術自由的保障根據/320
三、藝術自由保障的作用方式/331
肆、文化國下藝術相關基本國策作為國家目標/344
一、藝術相關基本國策作為國家目標的源由與效力/345
二、憲法上藝術相關國家目標條款的類型/355
三、文化國下國家保障藝術自由的憲法原則/364
伍、結 論/372
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377
參考書目 /389
索 引 /419
序
自序
最近,看了一部令人感嘆的電影,片名叫作:「我的名字叫可汗」(My Name Is Khan),很難得,看片的過程中我兩度流淚,這是近幾年來難得的淚水,是一種出自內心的自然湧出,源源不絕的悲情。
這是一部描述一位印度人的生命故事,他罹犯了亞斯柏格症,從小受盡別人的欺負,母親一直教導他待人寬容與判斷善惡的道理,在母親用愛和耐心教導之下,他學會最簡單的道理:「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壞人的不同,沒有其他的差別。」母親過世後,他跟隨唯一的親人(弟弟)到了美國。信仰回教的他在美國遇到真愛,在癡癡推銷化妝品的過程中,認識了一位信仰印度教的美容師,幸運地相愛結婚。這位美容師與前夫有一個6歲的小孩,後來成為可汗最好的朋友。
當小孩13歲時,美國發生了911恐怖攻擊事件,讓美國境內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有許多穆斯林的商店都受到攻擊,連帶冠有穆斯林姓氏的印度人也受到歧視與質疑。然而,小孩因為喜歡繼父,一直都掛著父姓「可汗」。問題是,「可汗」這個姓,一聽就知道是個穆斯林教徒。在一次校內的足球練習中,因為其他中學生不斷的宗教挑釁,小孩與他們產生衝突,最終被毆打致死。
小孩的母親悲痛不已,她把過錯歸咎於父親的姓氏與信仰,將父親趕出家門,父親大聲呼喊:「我的名字叫可汗,我不是恐怖分子。」母親氣憤地咆哮:「你去跟美國總統講吧!」罹犯亞斯柏格症的可汗,口中一直唸著:「我要去跟美國總統講。」因此踏上尋找美國總統的路程。
在這段艱苦的旅程中,他曾經被誤以為是恐怖分子,而遭受到嚴格的逼供與訊問,也遇到了不少的善心人士,其中包含了喬治亞州小村莊教會的基督徒們。後來,這個小村莊遭逢洪水侵犯,可汗義無反顧地回到小村莊,主導了一切的救難工作。當媒體報導了他的故事之後,引起了全美的迴響。一個被誤以為是恐怖分子的回教徒,比基督徒更積極地在救援教會的基督徒,他的大愛終於感動了美國總統。最後,他終於有了千辛萬苦的機會,告訴總統:「我的名字叫可汗,我不是恐怖分子。」
或許,是因為可汗罹犯亞斯柏格症,所以具有單純的心智,才能執著完成這不可能的任務。也或許,因為可汗罹犯亞斯柏格症,才能將複雜的人性、宗教問題單純化,就像他媽媽對他說的:「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壞人的不同,沒有其他的差別。」因此,在人世間不必區分膚色、種族、宗教或文化族群,只管人們做的是好事,還是壞事。有時想想,如果真的能夠如此,讓全世界有文化族群仇恨的人,都可以罹犯亞斯柏格症,或許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事實上,人為的宗教歧視或文化偏見所帶給人們的痛苦,恐怕比先天的遺傳缺陷,還要更可怕許多。
臺灣,只是一個單純的島嶼,卻因為歷史上的種種因素,產生了複雜的族群對立。歷史的軌跡,應該提供我們的是借鏡與反省,讓我們能夠藉此創造善美的未來。然而,在輪替的執政者無法寬容下,臺灣的族群對立愈來愈嚴重,實在值得擔憂與面對。我們如何在臺灣,討論公共事務時,只是單純針對「只有對臺灣未來發展是好和壞的不同,沒有其他族群因素的差別。」這應該是當前臺灣執政者應有的多元文化胸襟。
就此而言,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明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這裡多元文化已成為我國憲法的國家目標,可視為憲法明文保障多元文化國的依據。因此,國家必須承認不同文化社群間存在文化差異,並有義務積極防止文化差異質變為主流文化社群的壓迫與宰制。事實上,國家是由社會成員組成,國家權力的行使,須透過社會大多數成員之代表的民主決定。因此,要求國家對不同文化的寬容,其實也就是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寬容。
最後要強調的是,這是作者投入文化法學而思索的第二本學術專論,寫這本文化法專論的主要目的,從專論名為「文化基本權與多元文化國」可知:是嘗試從文化基本權與多元文化國建構文化法制的憲法基礎。對此的嘗試,將首先以我國相關的文化基本權條文作一個概括性的檢視(第二章);其次,從多元文化國的角度,討論通訊傳播自由的基本權保障(第三章)並將焦點集中在事業通訊自由,而進一步探討該自由的保障與限制可能(第四章);接著,針對建築文化資產的保存問題,探尋憲法依據與在文化政策上的實踐(第五章);此外,藉由比較法制的角度,以德國「文化國」的發展作為我國相關思考,包括如何型塑文化公民權的借鏡(第六章);最後,本書企圖將貫穿本書的基本理念,整合性地用來建構未明白規定於我國憲法基本權目錄的藝術自由保障(第七章)。而各章節之重要想法,將條列示的呈現在結論與建議中,希望能夠提供作為思索我國多元文化國與文化基本權法制時,一個提綱挈領的藍圖(第八章)。
周敬凡、李惠圓、張立群、林宗翰、莊惠婷、蔡汶含、許介仁、張永暉、馮欣中、李佳育、林修睿與黃宗菁等同學,都對這本書的出版有所貢獻,感謝他們。尤其是敬凡與佳育協助格式化與校對等繁重工作,在此特別致謝。此外,這本書的完成,還要感謝元照出版公司的良善互動與積極鼓勵,才能在此與讀者相見。
最後,這本書要用心獻給讓我一直成長的臺灣,她就代表著多元文化的開展,在我身上生生不息。
2014年2月14日
寫於成大社科大樓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