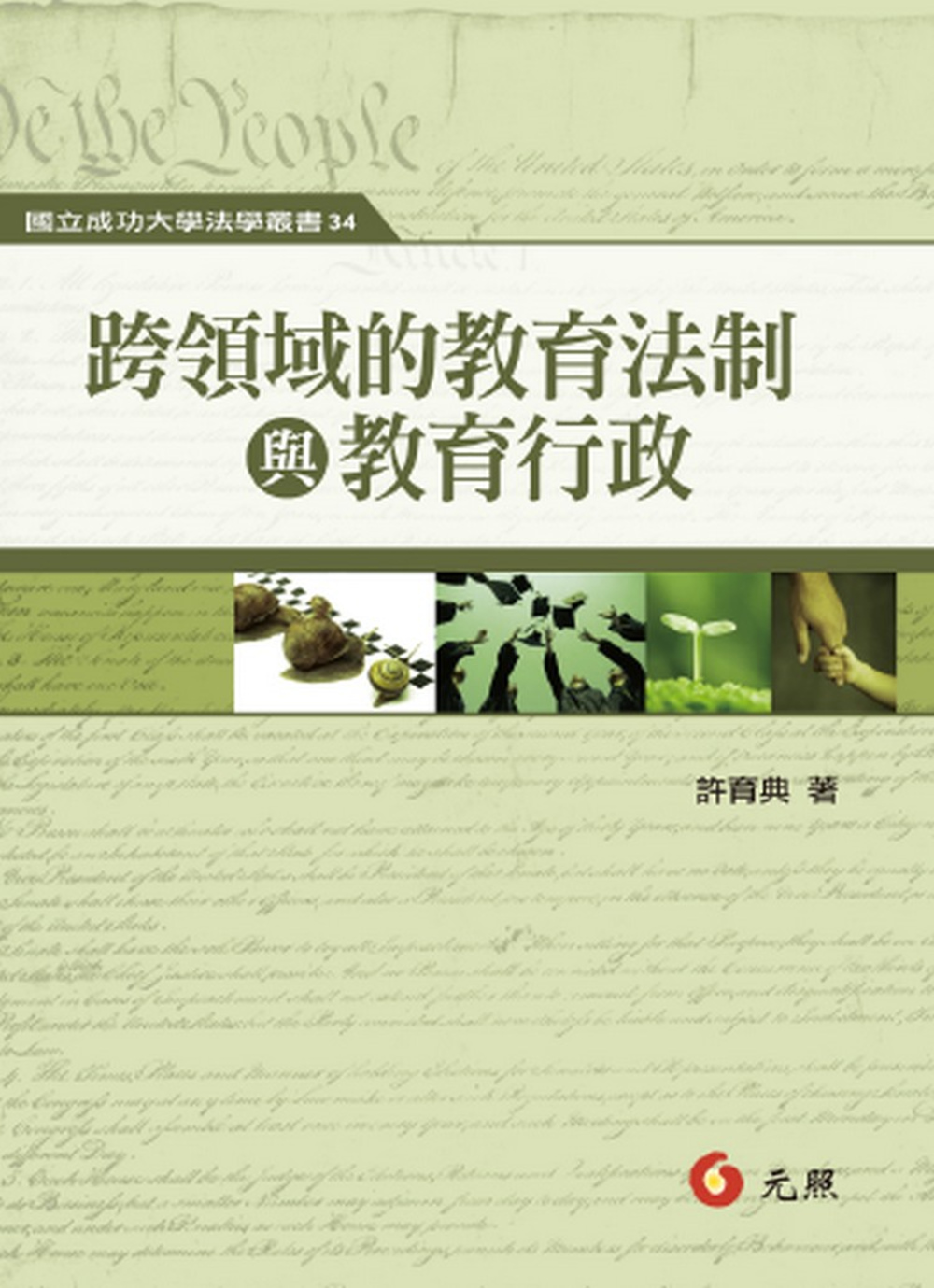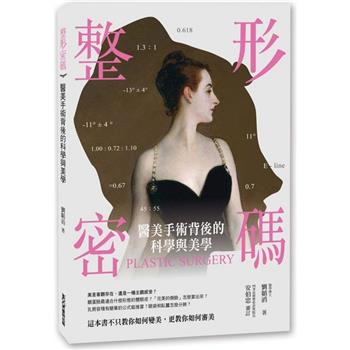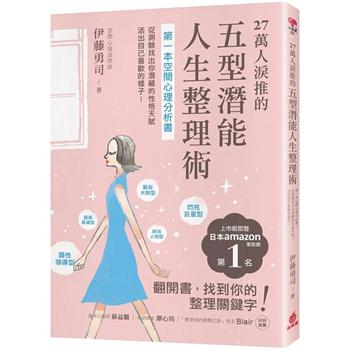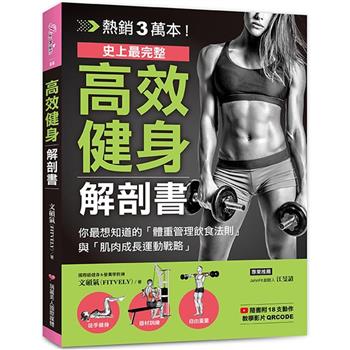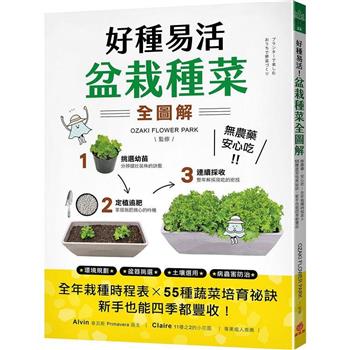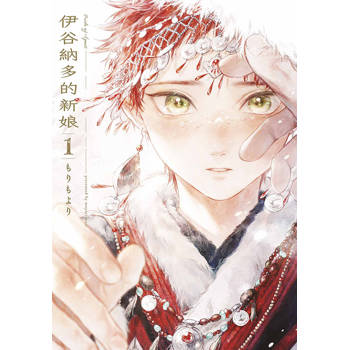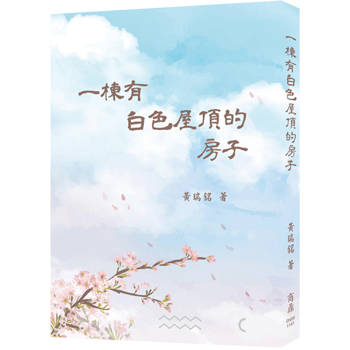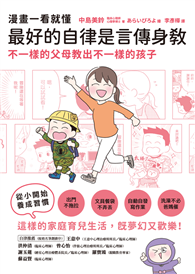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跨領域的教育法制與教育行政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跨領域的教育法制與教育行政
內容簡介
《跨領域的教育法制與教育行政》這本學術專論,是作者在台灣學術界完成的第五本教育法專論,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主要是針對其他跨領域的教育法制問題加以探討:首先,從多元文化國的要求,探討應如何在性別平等方面建構一個能讓學生自由開展人格的學習環境(第二章);其次,嘗試討論在社會國原則底下,幫助新移民子女也能夠享受同等的教育機會(第三章);再者,對於作為國民教育重要媒介的教材,國家應該介入監督到什麼地步,以及遵守怎樣的憲法原則(第四章),包括北北基曾經實施的「一綱一本政策」,在教育憲法與教育行政法上應作如何的評價(第五章),也是本書所欲闡明的議題;接著是討論對於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如何養成現代公民的媒體素養教育(第六章),與涉及尊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零體罰政策(第七章);而在跨領域教育議題中同樣重要的是,如何消弭因為貧富差異與城鄉差距所造成的教育機會不平等(第八章),以及跨越年齡、讓每個人都有機會自在學習而實現自我的的終身學習教育(第九章);最後,當實證法上以「有損師道」為由而限制教師工作權時,應當如何用憲法所要求的原則來加以檢驗(第十章)。這些分散於不同議題的思考,會在結論與建議中作簡明陳述,希望有助於我國教育法制的整體建構(第十一章)。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許育典
【現職】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心(ERCCT)諮詢委員
澳門法學學術顧問委員
台南市法規、教育、教師申訴審議委員會委員
【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
國立成功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主任
德國洪堡學術基金會資深訪問學者(2014)
德國洪堡學術基金會研究獎學金(2006-2007)
國科會暨德國學術交流總署研究獎助(2003、2004、2005)
中華民國第47屆十大傑出青年
教育部法規委員
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委員
原住民族委員會法規委員
【學歷】
德國杜賓根大學法學博士
德國杜賓根大學宗教學院研究
德國杜賓根及哥廷根大學教育學院研究
許育典
【現職】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心(ERCCT)諮詢委員
澳門法學學術顧問委員
台南市法規、教育、教師申訴審議委員會委員
【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
國立成功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主任
德國洪堡學術基金會資深訪問學者(2014)
德國洪堡學術基金會研究獎學金(2006-2007)
國科會暨德國學術交流總署研究獎助(2003、2004、2005)
中華民國第47屆十大傑出青年
教育部法規委員
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委員
原住民族委員會法規委員
【學歷】
德國杜賓根大學法學博士
德國杜賓根大學宗教學院研究
德國杜賓根及哥廷根大學教育學院研究
目錄
自 序
本書常用德文縮語中文對照表
本書引註格式說明
第一章 導 論/1
第二章 從多元文化國建構多元文化教育環境:以我國性別平等教育法為例
壹、前 言/9
貳、以自我實現為核心的多元文化國/10
參、多元文化國、多元文化教育環境與性別平等教育/22
肆、多元文化教育環境下我國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落實/35
伍、結 論/46
第三章 從憲法上社會國原則建構教育機會均等:以新移民子女為中心
壹、前 言/49
貳、以自我實現為核心的新移民子女教育基本權/50
參、社會國原則作為教育機會均等的憲法建構/55
肆、教育機會均等作為新移民子女教育基本權的檢討/61
伍、結論與建議/77
第四章 教科書審定制的合憲性探討
壹、前 言/79
貳、教育改革後的我國教科書編制分析/81
參、審定制對教科書出版者的出版自由限制/97
肆、教科書審定的形式合憲性檢驗/109
伍、教科書審定的實質合憲性檢討/122
陸、結論與建議/135
第五章 北北基一綱一本政策的法律分析
壹、前 言/141
貳、一綱一本政策對教育基本權的侵害/143
參、以依法行政原則檢驗一綱一本政策/156
肆、對教育部反制一綱一本手段的檢驗/163
伍、結論:建立教育行政的法治文化/170
第六章 媒體素養教育在我國公民教育的現況與檢討
壹、前 言/173
貳、教育基本權下公民教育的實施/175
參、媒體素養教育在公民教育的實施/184
肆、媒體素養教育在公民教育的檢討/195
伍、結 論/204
第七章 以學生為教育主體的零體罰教育政策
壹、前 言/207
貳、零體罰作為我國教育基本原則/208
參、學生作為基本權主體的拒絕體罰請求權/218
肆、學生作為教育主體的零體罰政策落實/235
伍、結 論/246
第八章 社會國原則在教育行政的落實:從補助營養午餐費用和消弭城鄉教育差距談起
壹、前 言/249
貳、社會國的發展、內涵與依據/250
參、從補助營養午餐費用檢驗社會安全的落實/258
肆、從消弭城鄉教育差距檢驗社會正義的落實/266
陸、結 論/273
第九章 終身學習教育法制的建構與實踐:以社區大學為例
壹、前 言/277
貳、終身學習權vs.教育基本權/278
參、終身學習權的憲法基礎/280
肆、終身學習教育法制在社區大學的實踐現況/281
伍、學習成就認證作為終身學習教育法制的整合建構/283
陸、開放大學法作為終身學習教育法制的整合建構/288
柒、結 論/294
第十章 當教師工作權遇到學生自我實現權:釋字第702號解釋的憲法疑義
壹、前 言/297
貳、本案系爭規定所涉及的基本權/300
參、法的明確性原則在系爭規定的檢討/304
肆、校園中學生自我實現權與教師工作權的利益衡量/312
伍、結 論/317
第十一章 結論與建議/321
參考書目/339
索 引/373
本書常用德文縮語中文對照表
本書引註格式說明
第一章 導 論/1
第二章 從多元文化國建構多元文化教育環境:以我國性別平等教育法為例
壹、前 言/9
貳、以自我實現為核心的多元文化國/10
參、多元文化國、多元文化教育環境與性別平等教育/22
肆、多元文化教育環境下我國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落實/35
伍、結 論/46
第三章 從憲法上社會國原則建構教育機會均等:以新移民子女為中心
壹、前 言/49
貳、以自我實現為核心的新移民子女教育基本權/50
參、社會國原則作為教育機會均等的憲法建構/55
肆、教育機會均等作為新移民子女教育基本權的檢討/61
伍、結論與建議/77
第四章 教科書審定制的合憲性探討
壹、前 言/79
貳、教育改革後的我國教科書編制分析/81
參、審定制對教科書出版者的出版自由限制/97
肆、教科書審定的形式合憲性檢驗/109
伍、教科書審定的實質合憲性檢討/122
陸、結論與建議/135
第五章 北北基一綱一本政策的法律分析
壹、前 言/141
貳、一綱一本政策對教育基本權的侵害/143
參、以依法行政原則檢驗一綱一本政策/156
肆、對教育部反制一綱一本手段的檢驗/163
伍、結論:建立教育行政的法治文化/170
第六章 媒體素養教育在我國公民教育的現況與檢討
壹、前 言/173
貳、教育基本權下公民教育的實施/175
參、媒體素養教育在公民教育的實施/184
肆、媒體素養教育在公民教育的檢討/195
伍、結 論/204
第七章 以學生為教育主體的零體罰教育政策
壹、前 言/207
貳、零體罰作為我國教育基本原則/208
參、學生作為基本權主體的拒絕體罰請求權/218
肆、學生作為教育主體的零體罰政策落實/235
伍、結 論/246
第八章 社會國原則在教育行政的落實:從補助營養午餐費用和消弭城鄉教育差距談起
壹、前 言/249
貳、社會國的發展、內涵與依據/250
參、從補助營養午餐費用檢驗社會安全的落實/258
肆、從消弭城鄉教育差距檢驗社會正義的落實/266
陸、結 論/273
第九章 終身學習教育法制的建構與實踐:以社區大學為例
壹、前 言/277
貳、終身學習權vs.教育基本權/278
參、終身學習權的憲法基礎/280
肆、終身學習教育法制在社區大學的實踐現況/281
伍、學習成就認證作為終身學習教育法制的整合建構/283
陸、開放大學法作為終身學習教育法制的整合建構/288
柒、結 論/294
第十章 當教師工作權遇到學生自我實現權:釋字第702號解釋的憲法疑義
壹、前 言/297
貳、本案系爭規定所涉及的基本權/300
參、法的明確性原則在系爭規定的檢討/304
肆、校園中學生自我實現權與教師工作權的利益衡量/312
伍、結 論/317
第十一章 結論與建議/321
參考書目/339
索 引/373
序
自序
教育,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政府在國民教育事務到底應該扮演什麼角色?一個12年國民教育的政策,為何可以一變再變,完全沒有原則可言。
事實上,教育部從原先堅持不排富原則,經行政院長與教育部長會商後,又確定改採高中排富、高職不排富的雙軌制原則。本來,排富基準採家戶總所得114萬元以上,預估一年可省下34億元。之後,高中的排富線又改訂在148萬,也就是高中生家戶所得148萬以下,與高職生一樣都免學費,這個法案最後在立法院通過了。問題是,在短短8天之內,12年國教政策卻一變再變,而且是極端地從不排富原則變到排富原則。我們要問的是,憲法保障的國民教育到底有沒有原則?政府規劃了好幾年的國民教育,為什麼常在一夜之間說變就變呢?
不是說,教育是百年的大計嗎?怎麼可以讓百年大計在一夕驟變呢?政府不是一直宣稱我們是個法治國家,為何遇到國家重大決策時,政府往往不經意地又走到過去人治的舊途!一個教育部規劃了好幾年的12年國教政策,本來應該從國民教育的本質出發,在國民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上加以設計,卻因為政府高層考量的種種民粹因素,將教育規劃的專業考量拋於雲霄之外,忽略了以學生自我實現為目的的國民教育本質,從而導致了朝令夕改的現行12年國教政策爭議。
說實話,政府從朝令夕改的一開始規劃,就出了問題。為何當初會選擇將排富門檻基準訂在114萬元?難道政府不知道114萬元同時也是學生申請就學貸款門檻嗎?一般而言,學生會去申請就學貸款,不是意味著家境無法負擔學費嗎?這裡根本有點貧富不分的荒謬性!即使是之後門檻由家庭年所得114萬元提高到148萬元,政府也一直宣稱一年可省下25億元。問題是,國家省錢哪裡都可以省,在國民教育上省這些錢,試問我們還看得到國家的未來嗎?國民教育可說是一國的根本,國家為了推動證所稅一年就短收了500億元,卻因為落實國民教育在意這25億元,這實在是本末倒置!因此,應該讓12年國教的討論,回到憲法上的規定。
整體而言,憲法第21條規定了國民教育基本權的保障,但因為國家財政可能的有限性,賦予立法者針對國家預算可供人民共享的分配性,以法律決定國民教育基本權的保障內涵,這也是國民教育基本權作為社會基本權的特質。在此,憲法第21條國民教育基本權落實的前提之一,是人民必須可以共享這個國民教育實施的內容。就此而言,憲法保障國民教育的關鍵所在,是在於應堅持國民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也就是每個人民可以「平等」地共享政府所提供的國民教育。問題是,眼下政府所規劃的12年國教,是否符合這個強調人人「平等」的原則呢?
首先,12年國教如果就原先教育部的規劃,採取所謂的不排富原則,應該會符合每個人民可以「平等」共享國民教育的憲法保障內涵。事實上,行政院一開始就應該尊重教育部專業規劃好幾年的12年國教政策,筆者相信教育部當初規劃之時,可能已經考量了排富恐有違反憲法第21條規定的疑義。這個問題突顯了我國的憲政危機,在各部會反覆沉澱多年的專業政策,究竟可否在內閣會議中,因為人治的上下權力關係而說變就變,而且時間緊迫下可能無法顧及政策的違憲疑義!
其次,即使之後經過上下權力關係而改變的12年國教內涵,也應該盡可能符合憲法第21條規定的保障,考慮平等共享的原則。在此,如果政府真的要訂下排富的門檻,應該要跟人民說明的是,這裡針對高中排富、高職不排富的差別待遇,在憲法上是有意義的區別,也就是可以找到憲法上的規定來合理說明。問題是,政府的理由大多似是而非且無關教育目的,例如:高中生多家境較好,高職生多弱勢家庭;因就業需求鼓勵學生往高職發展;……等等,實在難以說明差別待遇的憲法意義!在此,我們可以看出:政府將規劃的政策形諸法律之時,並未謹慎回到憲法保障內涵加以探討,教育法制與教育行政的合憲努力,一直需要我們的投入。
《跨領域的教育法制與教育行政》這本學術專論,是我在台灣學術界完成的第五本教育法專論,可說是我在完成《法治國在教育行政》與《教育憲法與教育改革》兩本教育法總論後,持續完成《學校法制與學校行政》與《大學法制與高教行政》兩本教育法各論後,對台灣其他跨領域教育法制問題的教育法學思考。整體而言,在我的教育法學的體系建構中,完成教育法總論之後,應該至少嚴格區分學校法制與大學法制,因此在完成這兩個基本模式的教育法制建構後,最後對焦在剩餘其他跨領域的教育法制與教育行政。
作者寫這本教育法專論的目的,主要是針對其他跨領域的教育法制問題加以探討:首先,從多元文化國的要求,探討應如何在性別平等方面建構一個能讓學生自由開展人格的學習環境(第二章);其次,嘗試討論在社會國原則底下,幫助新移民子女也能夠享受同等的教育機會(第三章);再者,對於作為國民教育重要媒介的教材,國家應該介入監督到什麼地步,以及遵守怎樣的憲法原則(第四章),包括北北基曾經實施的「一綱一本政策」,在教育憲法與教育行政法上應作如何的評價(第五章),也是本書所欲闡明的議題;接著是討論對於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如何養成現代公民的媒體素養教育(第六章),與涉及尊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零體罰政策(第七章);而在跨領域教育議題中同樣重要的是,如何消弭因為貧富差異與城鄉差距所造成的教育機會不平等(第八章),以及跨越年齡、讓每個人都有機會自在學習而實現自我的終身學習教育(第九章);最後,當實證法上以「有損師道」為由而限制教師工作權時,應當如何用憲法所要求的原則來加以檢驗(第十章)。這些分散於不同議題的思考,會在結論與建議中作簡明陳述,希望有助於我國教育法制的整體建構(第十一章)。
周敬凡、凌赫、林維毅、陳碧玉、林宗翰、許介仁、張永暉、馮欣中、林修睿與黃宗菁等同學,都對這本書的出版有所貢獻,感謝他們。尤其是敬凡與宗翰協助格式化與校對等繁重工作,在此特別致謝。此外,這本書的完成,還要感謝元照出版公司的良善互動與積極鼓勵,才能在此與讀者相見。
最後,對於在學術路途開展上陪伴我的學生們,心裡一直存著深深的感激。在教室裡,面對著他們求知的投入臉孔,讓我的研究與講學產生播種的互動,在思考的脈絡上生生不息。有了他們熱情的參與討論,法學的種種變得生動了起來。因此,這本書要用心獻給與我一起為學術奮鬥的學生們,不管是平時在學術相互討論的投入,還是彼此在學術共同努力的扶持,他們都是我在教育上起心動念的出發點,感恩他們所付出的一切。
教育,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政府在國民教育事務到底應該扮演什麼角色?一個12年國民教育的政策,為何可以一變再變,完全沒有原則可言。
事實上,教育部從原先堅持不排富原則,經行政院長與教育部長會商後,又確定改採高中排富、高職不排富的雙軌制原則。本來,排富基準採家戶總所得114萬元以上,預估一年可省下34億元。之後,高中的排富線又改訂在148萬,也就是高中生家戶所得148萬以下,與高職生一樣都免學費,這個法案最後在立法院通過了。問題是,在短短8天之內,12年國教政策卻一變再變,而且是極端地從不排富原則變到排富原則。我們要問的是,憲法保障的國民教育到底有沒有原則?政府規劃了好幾年的國民教育,為什麼常在一夜之間說變就變呢?
不是說,教育是百年的大計嗎?怎麼可以讓百年大計在一夕驟變呢?政府不是一直宣稱我們是個法治國家,為何遇到國家重大決策時,政府往往不經意地又走到過去人治的舊途!一個教育部規劃了好幾年的12年國教政策,本來應該從國民教育的本質出發,在國民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上加以設計,卻因為政府高層考量的種種民粹因素,將教育規劃的專業考量拋於雲霄之外,忽略了以學生自我實現為目的的國民教育本質,從而導致了朝令夕改的現行12年國教政策爭議。
說實話,政府從朝令夕改的一開始規劃,就出了問題。為何當初會選擇將排富門檻基準訂在114萬元?難道政府不知道114萬元同時也是學生申請就學貸款門檻嗎?一般而言,學生會去申請就學貸款,不是意味著家境無法負擔學費嗎?這裡根本有點貧富不分的荒謬性!即使是之後門檻由家庭年所得114萬元提高到148萬元,政府也一直宣稱一年可省下25億元。問題是,國家省錢哪裡都可以省,在國民教育上省這些錢,試問我們還看得到國家的未來嗎?國民教育可說是一國的根本,國家為了推動證所稅一年就短收了500億元,卻因為落實國民教育在意這25億元,這實在是本末倒置!因此,應該讓12年國教的討論,回到憲法上的規定。
整體而言,憲法第21條規定了國民教育基本權的保障,但因為國家財政可能的有限性,賦予立法者針對國家預算可供人民共享的分配性,以法律決定國民教育基本權的保障內涵,這也是國民教育基本權作為社會基本權的特質。在此,憲法第21條國民教育基本權落實的前提之一,是人民必須可以共享這個國民教育實施的內容。就此而言,憲法保障國民教育的關鍵所在,是在於應堅持國民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也就是每個人民可以「平等」地共享政府所提供的國民教育。問題是,眼下政府所規劃的12年國教,是否符合這個強調人人「平等」的原則呢?
首先,12年國教如果就原先教育部的規劃,採取所謂的不排富原則,應該會符合每個人民可以「平等」共享國民教育的憲法保障內涵。事實上,行政院一開始就應該尊重教育部專業規劃好幾年的12年國教政策,筆者相信教育部當初規劃之時,可能已經考量了排富恐有違反憲法第21條規定的疑義。這個問題突顯了我國的憲政危機,在各部會反覆沉澱多年的專業政策,究竟可否在內閣會議中,因為人治的上下權力關係而說變就變,而且時間緊迫下可能無法顧及政策的違憲疑義!
其次,即使之後經過上下權力關係而改變的12年國教內涵,也應該盡可能符合憲法第21條規定的保障,考慮平等共享的原則。在此,如果政府真的要訂下排富的門檻,應該要跟人民說明的是,這裡針對高中排富、高職不排富的差別待遇,在憲法上是有意義的區別,也就是可以找到憲法上的規定來合理說明。問題是,政府的理由大多似是而非且無關教育目的,例如:高中生多家境較好,高職生多弱勢家庭;因就業需求鼓勵學生往高職發展;……等等,實在難以說明差別待遇的憲法意義!在此,我們可以看出:政府將規劃的政策形諸法律之時,並未謹慎回到憲法保障內涵加以探討,教育法制與教育行政的合憲努力,一直需要我們的投入。
《跨領域的教育法制與教育行政》這本學術專論,是我在台灣學術界完成的第五本教育法專論,可說是我在完成《法治國在教育行政》與《教育憲法與教育改革》兩本教育法總論後,持續完成《學校法制與學校行政》與《大學法制與高教行政》兩本教育法各論後,對台灣其他跨領域教育法制問題的教育法學思考。整體而言,在我的教育法學的體系建構中,完成教育法總論之後,應該至少嚴格區分學校法制與大學法制,因此在完成這兩個基本模式的教育法制建構後,最後對焦在剩餘其他跨領域的教育法制與教育行政。
作者寫這本教育法專論的目的,主要是針對其他跨領域的教育法制問題加以探討:首先,從多元文化國的要求,探討應如何在性別平等方面建構一個能讓學生自由開展人格的學習環境(第二章);其次,嘗試討論在社會國原則底下,幫助新移民子女也能夠享受同等的教育機會(第三章);再者,對於作為國民教育重要媒介的教材,國家應該介入監督到什麼地步,以及遵守怎樣的憲法原則(第四章),包括北北基曾經實施的「一綱一本政策」,在教育憲法與教育行政法上應作如何的評價(第五章),也是本書所欲闡明的議題;接著是討論對於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如何養成現代公民的媒體素養教育(第六章),與涉及尊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零體罰政策(第七章);而在跨領域教育議題中同樣重要的是,如何消弭因為貧富差異與城鄉差距所造成的教育機會不平等(第八章),以及跨越年齡、讓每個人都有機會自在學習而實現自我的終身學習教育(第九章);最後,當實證法上以「有損師道」為由而限制教師工作權時,應當如何用憲法所要求的原則來加以檢驗(第十章)。這些分散於不同議題的思考,會在結論與建議中作簡明陳述,希望有助於我國教育法制的整體建構(第十一章)。
周敬凡、凌赫、林維毅、陳碧玉、林宗翰、許介仁、張永暉、馮欣中、林修睿與黃宗菁等同學,都對這本書的出版有所貢獻,感謝他們。尤其是敬凡與宗翰協助格式化與校對等繁重工作,在此特別致謝。此外,這本書的完成,還要感謝元照出版公司的良善互動與積極鼓勵,才能在此與讀者相見。
最後,對於在學術路途開展上陪伴我的學生們,心裡一直存著深深的感激。在教室裡,面對著他們求知的投入臉孔,讓我的研究與講學產生播種的互動,在思考的脈絡上生生不息。有了他們熱情的參與討論,法學的種種變得生動了起來。因此,這本書要用心獻給與我一起為學術奮鬥的學生們,不管是平時在學術相互討論的投入,還是彼此在學術共同努力的扶持,他們都是我在教育上起心動念的出發點,感恩他們所付出的一切。
許育典
2013年7月7日12時
寫於成大社科大樓研究室
2013年7月7日12時
寫於成大社科大樓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