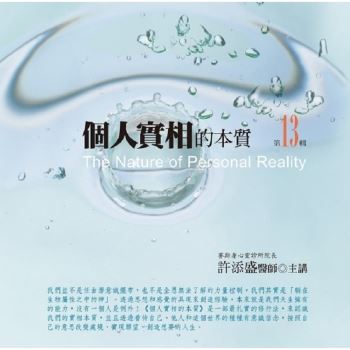導讀
永恆的神話創作 不朽的宗教關懷
一般認為神話創作(mythopoeia)為印度文化所特有,從最早的讚歌詩集-《梨俱吠陀》(□gveda)到兩大史詩--《摩訶婆羅多 》(Mahabharata ) 和《羅摩衍那 》, (Ramaya□a),以及諸多往世書(Pura□a)都可見到歷史時間被架空,人物之敘述超越現世時空,敘事者想在現世時間外找尋永恆的意義。其跟歷史敘述(historical narrative)之人間性(temporal),或人間秩序及其延續之水平式(horizontal)之敘述大異其趣。印度神話與史詩是一種試圖跨越人間時空範疇的垂直式(vertical)敘事。
印度人為何鍾情於神話敘事呢?這跟在其社會最具優先性之宗教觀息息相關。說來古代印度人的時間敘事是一種深度與奧秘的表現方式。他們當然知道年、月、日的時間計算(time-reckoning),但因宇宙觀(cosmology)、末世觀 (eschatology) 與救贖觀(redemption)等宗教關懷的關係,時間成為一種隱喻(metaphor),烘托出人在浩瀚的時間洪流中的渺小。而不管是宇宙紀元(yuga)或是劫(kalpa)等時間單位都跟宗教上的相關重大關懷不可分離。以宗教前提為本的神話敘事根本上即是要跟現世關懷的人間歷史區隔開。想透過不受限於時空之非歷史性敘事觀點,來傳遞具有神聖意義的永恆關照。
不過,雖然神話是印度敘事傳統,但一般不會把《梨俱吠陀》當成史詩,而《摩訶婆羅多 》和《羅摩衍那 》則被視為印度史詩,差別何在?基本上,吠陀經典,特別是《梨俱吠陀》被當為天啟聖典(sruti)對待,而《摩訶婆羅多 》等則被視為人間傳承。之所以如此,可能跟外道對於吠陀的詆毀有關。不過,若從史詩對民族或宗教社群之形成具有關鍵性塑造力量之史詩框架(epic framework) 來看,則《摩訶婆羅多 》和《羅摩衍那 》對印度(教)社群之形構,提供了無可取代之思想關聯,而《梨俱吠陀》則無。總的來說,在吠陀時代,特別是《梨俱吠陀》,對於真理或真話(□ta, satya)的闡釋與維繫不遺餘力,密多羅(Mitra) 跟伐羅拿(Varu□a)成了真理或真話的守護神。而在史詩時代,真理或真話的守護並非最為重要的,法(dharma)-不管是種姓法(svadharma)或王法(rajadharma)才是關注的焦點。《摩訶婆羅多 》或《羅摩衍那 》裡面對於有關印度(教)種姓社會相關價值觀的形成有著莫大的關係。
上面提到吠陀時代與史詩時代在思想雰圍是不一樣的。如果神話是要來傳遞超越現世的神聖意義,那神話裡面之敘事主題與人物特質是不是會隨著時代改變呢?的確,神話敘事並非是一成不變的人物與主題重複。從《梨俱吠陀》到《往世書》的一千多年時間,故事的敘述方式改變了,人物也更迭了,傳達的意義也隨之更迭。在《梨俱吠陀》裡面重要的神祇在史詩時代常成了配角。以帝釋天(Indra, Sakra)為例,他可說是《梨俱吠陀》裡面最重要的神祇,開天闢地,允文允武,為眾神所畏懼,也是人間祈福的主要對象之一。然而,在往世書裡面他卻成了一個已軟弱無力的神明,不但跟濕婆(Siva)、毘濕奴(Vi□□u)或梵天(Brahma)的威力根本無法相比,甚至不是阿修羅(asura)惡魔的對手,跟《梨俱吠陀》裡面的描述完全不一樣,為什麼會有這麼重大轉變呢?
原來神話還是有其時代性的,也有其社會性跟文化上面的意函,在梨俱吠陀的時代,帝釋天當為一個雷神具有呼風喚雨的能力,可以看出那個時代裡面人跟自然的關係,以及人對自然的依賴。不過那個時代裡面並非只存在著人對自然的看法,也存在著人對於普遍秩序的追求,前面已提到真理或真言被視為是最高普世道德準則,有其至高無上的意義,密多羅跟伐羅拿成了監督人間秩序之二合一神祇,只要人們不守規定,不照誓言行事,不履行契約,則會受到在天上凝視著人民一舉一動的二合一神祇之嚴厲懲罰。由此,吾人可以看得出在梨俱吠陀社會遵守合約的重要性,以及講真話說實情所具有的普遍意義。雖然在《梨俱吠陀》第十卷第九十頌《原人歌》(Puru□a Sukta)裡面提到四大種姓之源起及名稱,然而,此時法的重要性比不上對真理的堅持,對社會階序的分殊化之思考尚未凌駕於普世的共同宗教倫理關懷之上。
而在梵書(Brahma□as)時代,生主(Prajapati)成了最重要的神祇。原因無它,梵書所關係到的是一個專權而複雜的祭祀萬能時代,生主身為祭祀之神,萬事萬物皆由生主所生,也就是靠祭祀來維繫一切意義。在這個時代裡,婆羅門當為祭司種姓的意識型態終告確立。這當然不是一夕之間發生的改變,而是慢慢的演變。不過,由梵書裡面婆羅門與剎帝利之間,為了祭祀權而發生鬥爭的神話故事裡面,吾人可以見出,婆羅門在印度種姓社會上面的精神指導地位,跟剎帝利在政治領域的權威地位,是兩者之間取得某種程度的妥協與共識之後,才有辦法來完成的。在梵書時代,婆羅門與剎帝利在種姓社會裡面的地位逐漸確立,種姓之分界寄更趨於嚴格與完備。
種姓社會完成之後,種姓法的嚴格遵守變成了最為重大的事情之一。在《摩訶婆羅多》裡面剎帝利種姓法的遵守變成了婆羅門史詩敘事者常加傳揚的訊息。在《摩訶婆羅多》裡面最著名的故事《薄伽梵歌》(Bhagavadgita)當中,黑天(Krishna)諄諄告誡阿周那(Ajurna)要遵守剎帝利的種姓法,在戰場裡面要勇猛殺敵,不能退縮,即使所面對的敵人是親人手足也不能手軟,一切都得照規定自身之法行事,不計結果為何,但問自己是否盡了剎帝利之義務。由此可以看出在摩訶婆羅多時代,種姓秩序的嚴峻以及階級網羅之森嚴了。
這種種姓社會愈來愈趨嚴密的情形,我們亦可從往世書裡面更看得出來:殺婆羅門被視為罪大惡極,不可饒恕之事。在梨俱吠陀時代的帝釋天可說是無所不能,為所欲為,神力無邊。然而這樣一個神祇在往世書裡面卻因為被視為有潛在殺害婆羅門,破壞神聖種姓法的可能,而被排斥在外,變成次要的角色。對此情形,我們可以說:在往世書時代不但種姓法已經牢不可破,婆羅門更被提升到梵天一般,也就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最高地位了。種姓社會更成了牢不可破之神話。
從神話的內容以及關心議題之改變,我們也可以看出印度宗教思想大致的演變情形,在早期婆羅門祭祀思想當道的時代,比方說《梨俱吠陀》裡面對於火神阿耆尼大量的歌頌詩歌裡面,充分表現出吠陀時代人對於火的仰賴與尊崇。
到了印度教神祇受到尊崇、祭拜的年代,濕婆與毗濕奴乃從吠陀時代次要的角色搖身一變為舉足輕重、法力無邊的神明,這點從史詩與往世書裡面透露無遺。特別是濕婆這位眾神之主更是變幻莫測,令人畏佈。從史詩時代的書中對於神力不可測的鋪陳敘事裡面,吾人發現此時已是濕婆教派與毗濕奴教派全面當道的時代了。而在印度教神祇升天時代,雖然對於火的伺候依然,然而火供(agnihotra) 卻變為護摩(homa),成了密續(tantra)的基本儀軌,不管在濕婆派密續或毗濕奴派密續皆然。而其主要作用乃為召喚及籠絡諸神祇,藉其神力以獲取現世間利益(siddhi)。阿耆尼當為眾神之師的時代已過,其獨立神格也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透過火供來操弄眾神,以遂其所願。
不過,印度神話敘事除了在不同時代印度有其不同的關懷主題之外,彼此之間的傳承、借用與創新之處亦不能加以忽視。一般認為《摩訶婆羅多 》成書年代約在西元前四世紀至西元四世紀之間。梵語之「Maha」原意為偉大,「Bharata」則是部族之名,因此書名《摩訶婆羅多 》(直譯是「偉大的婆羅多族之故事」,以列國紛爭時代的印度社會為背景,敘述了婆羅多族兩支後裔俱盧與般度族爭奪王位繼承權的爭鬥。這部以梵文寫成敘事詩的巨作全書共分十八篇,計有十萬頌,比荷馬的《伊里亞特》加《奧德賽》多了好幾倍,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書之一,也是古代文明世界中最長的一部史詩,因此常被喻為「史詩中的史詩」。現代的印度人認為自己是婆羅多族的後裔,所以獨立後的印度乃自稱為「婆羅多國」。
《摩訶婆羅多》不但為長篇英雄史詩,還穿插有大量神話傳說和寓言故事,和有關宗教、哲學、政治和倫理等教理對話。因此《摩訶婆羅多》的內容除如書名所示為「偉大的婆羅多族之故事」之外,事實上也是一部「印度教百科全書」,恰如史詩結尾部分所宣稱的那樣,囊括了人生「四大目的」(Puru□artha)(欲、利、法和解脫)的全部內容:「正法和利益,愛欲和解脫,這裡有,別處有;這裡無,別處無。」(十八.五.三十八)。
然而,歸根究底,婆羅多的概念來自古老的《梨俱吠陀》。在《梨俱吠陀》裡面有多次提到婆羅多的相關字眼。其中最有名為第三卷第三十三頌。內容為婆羅多族的詩人遍友(Visvamitra)與兩條河流的對話。在對話中,遍友要求湍急的河流讓掠奪牛群的婆羅多族人安全渡河。河流最初不肯答應,後來終於首肯,卻對遍友提出條件,要求詩人在人間永遠傳頌對河之讚歌。在這裡,詩乃代表真理之言,婆羅多族則為傳揚詩歌真理之族群。而在《摩訶婆羅多 》裡面,詩人則藉著婆羅多族後裔俱盧與與般度族爭權之戰,陳述出印度教社會的人生真理。梨俱吠陀的婆羅多與史詩的婆羅多雖代表著兩種不同的宗教文化象徵,卻又有著甚為巧妙的呼應關係,終究讓婆羅多得以不朽。
而《羅摩衍那》的故事,吾人在佛教巴利《十車王本生》(Dasaratha Jataka)裡面亦可找到。然而在本生經裡面,羅摩與悉多(Sita)原先是兄妹而非夫妻的關係,情結的發展也限於印度本土,並沒有羅摩大軍遠征楞伽島之事,內容也相對簡單,主要是探討羅摩與其同父異母兄弟婆羅多(又是Bharata!)之間為了王位而相互承讓的經過,彰顯出所謂倫理秩序的重要性。而《羅摩衍那》所宣揚的是印度教之核心價值。悉多成為貞婦的代表,羅摩成為法王(dharmaraja)的化身。而種姓秩序的護衛更是法王所不能片刻放鬆之事。比方說首陀羅修行者商部伽(Sambuka)因為違反種姓規定行苦修,竟導致婆羅門之子夭折。而在羅摩親手將其斷首之後,婆羅門之子又死而復生(後篇,第六十四到六十七章),在在都可讓吾人感受到史詩故事變異之用心,及其與時代主導意識之間的密切關係。
此外,《羅摩衍那》所述及的一個重大主題即是羅摩與魔王羅波那(rava□a)之間的爭鬥。如果說羅摩代表正義之師的話,則羅剎王代表著對於王法的威脅以及社會秩序破壞的他者。羅剎王國的存在是對正法王國在權力上的挑釁與挑戰,這包括家庭的保全。如果說《摩訶婆羅多 》代表著婆羅多族對自我之認同意義,則《羅摩衍那》乃牽涉婆羅多族與與異族的互動關係,可以代表著印度教對於異教徒的的一種觀點。然而在近代,《羅摩衍那》裡面所描繪的他者卻成了明喻(simile),穆斯林成了妖魔鬼怪,就因為蒙兀兒王朝統治印度期間,不少印度教徒改宗伊斯蘭,後來在英國殖民者離開後,印度次大陸又形成印度與巴基斯坦分立的局面。近年來倡導印度教徒魂(Hindutva)的政客不斷地發起回到羅摩時代的討回公道的政治運動,導致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社群之間的衝突不斷,如何來看待《羅摩衍那》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黃柏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