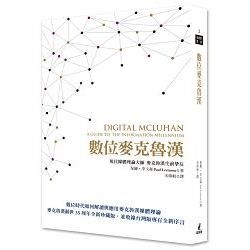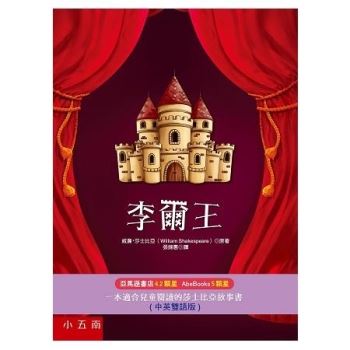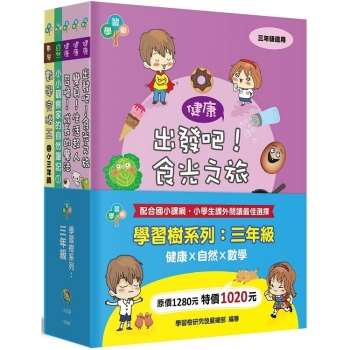新版作者序
十幾年前,我撰寫了《數位麥克魯漢》這本書,現在台灣的貓頭鷹出版社即將出版本書新版,我想也是時候更新一些相關的資訊──尤其是關於麥克魯漢身為社群媒體引導者的價值。還有,我將社群媒體稱為「新新媒體」,因為所有的媒體本身都是社群性的,而我們所稱的社群媒體正是這種新式的媒體,如部落格、推特等,都不同於只是單純的管理跟撥放資訊的播放器,如舊式的媒體iTunes。使用新式媒體的消費者本身即成了製作人,儘管在我們文化中普遍地使用著「社群媒體」這個詞,但我認為,在本篇序中使用「新新媒體」這個名詞是最適當的。
麥克魯漢的媒體四大律是用來開始談論本篇的好工具。
媒體四大律
媒體四大律,簡而言之,是一種跨越時間紀錄科技的衝擊跟相互間關係的方式。它會向每種媒介或是科技提出四大問:這個媒介在文化上有何增強之處?削弱了什麼?所重拾回的焦點是什麼,畢竟在這之前這已經被削弱了?以及當被推展到極致,這個新媒介會轉化成了什麼?
譬如說,照片會擴大視覺記憶,補捉世界實際的樣子;也削弱了繪畫、圖畫和素描,因為這些都是依賴畫家的詮釋跟圍繞著創作的主題。照片能夠從一池水中重拾世界的倒影,倒影中反映的即是這個世界真實的樣子。然後照片轉而成為動態圖片、3D立體全像攝影,或是最近的全球即時數位影像。
落在第四律經轉化過的媒體具有多重性,像是動態圖片、全像攝影、數位攝影,也能夠運用在媒體四大律的探討之中。照片同時也削弱了事件本身的口頭和文字描述,也因此一張照片能夠勝過千言萬語。一張照片也能重拾栩栩如生的回憶。但是,轉化提供了通往未來的入口,因此我們就來揭開照片是如何轉化成數位影像。
自拍就是一個照片轉化成新新媒體的最佳例子。在我將我跟麥克魯漢、其子艾瑞克麥克魯漢在媒體四大律會議的合照PO到推特上之後,我就了解到這一點。這個研討會是我在一九七八年在費爾里.狄金生大學(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所舉辦的。媒體理論家艾恩.伯各斯特(Ian Bogost)在推特上問我有關照片的事情,「第四個(人或是定律)在哪?」我馬上推文回覆:「第四個就是自拍。」意思是,相片中在一九七八年尚未出現的第四人就在那三個人之中;但到了二○一四年,我們就知道這三個人之中任一個對著自身拍照就是在自拍。在自拍照中,在手機上的相機轉化了,它的鏡頭轉向了,從向外拍攝到鏡頭可以向內對著拍照者本身。
這種情形也發生在媒體四大律上。我們能夠將被轉化的媒體作一個四大律的分析。因此,自拍增強了拍照者跟被拍照者間的融合,將我們的世界削弱成只是布景,重拾回我們水中或是鏡中的倒影,以及轉化成……像是Snapchat的應用程式。Snapchat能夠散佈影像,包括自拍照。這些影像在幾秒鐘或是幾分鐘內就會消失。
當我們將照片視為能記錄永恆的媒體或是時間的延伸時,Snapchat也的確能被視為是照片轉化而成的媒體。電影評論家安卓.巴新(André Bazin)便將照片的效應完美詮釋。他說:「照片能夠拯救影像自身於時間中的腐化。」在這樣的脈絡之下,照片削弱了飛逝的影像與回憶,重拾了定在過去(carved into stone)的影像,然後在這樣的數位時代中轉化回到Snapchat稍縱即逝的立即性。
再進一步應用媒體四大律才能更了解社群媒體革新中產生的其他視覺新媒體。以Google眼鏡為例,就非常符合眼鏡經過四大律分析之後的第四律──轉化。眼鏡能夠增加清晰度,減少視力不良,重拾我們年輕時曾有的裸視視力,然後轉化成Google眼鏡,使我們能在網路上隨時、隨地看見任何事物。雖然Google眼鏡無法吸引大眾持續的關注,卻引領出「穿戴式」媒體的方向,隨後的Apple Watch也如同Google眼鏡延伸我們的視野一般,將手錶帶入一個新紀元。我們也能為Apple Watch作獨立的四大律分析:傳統的手錶能報時,轉化成Apple Watch之後,當我們使用Apple Watch上網時,我們能夠
看透<$>錶面所顯示的時間來著眼過去,或至少可以參考過去。
媒體四大律當然也能夠使我們更了解我們所見的以及我們用眼睛在做的其他事情,如閱讀。這引發了一場討論是麥克魯漢對於Kindle電子閱讀器可能持有的看法。這個主題的重要性值得我們以一個篇幅來專門討論。
Kindle電子閱讀器
書本轉化成了Kindle電子閱讀器,不只是以銀幕取代了紙張,用像素取代了印刷,同時還開啟了對媒體把關影響深遠的改革。在數位化時代前,那曾是媒體資訊傳播的特徵。
我曾因為湯瑪士.葛雷在〈鄉村教堂墓園中的輓歌〉一詩中所描述的對人類所失去的而感到震撼。那是一首對所有「無聲、臭名的米爾頓」(mute inglorious Miltons)的頌調。(#譯註: John Milton,知名史詩《失樂園》( Paradise Lost <$>)的作者,他的作品<論出版自由>( Areopagitica<$>)則是為反對出版審查制而做。%)這些人長眠於地下,沒人聽聞過他們的偉大作品,因為命運拒絕垂憐他們。
命運通常是以媒體把關者的形式出現,他決定了什麼能付印,什麼不能。有時候,我們能夠一窺這些媒體把關者,策畫編輯和出版商,會將約翰.甘迺迪.圖爾這類的人排除在外。圖爾的小說,《笨蛋聯盟》( A Confederacy of Dunces <$>)在出版一年後獲得普立茲小說獎,這也是在作者因屢次遭傳統出版商拒絕而自殺的十一年之後。
當我在二十世紀末撰寫《數位麥克魯漢》時,當時一些媒體把關的關卡已經微開。但是直到二十一世紀初時,新新媒體的到來才將這些關卡各個擊破。部落客開始可以隨心所欲地在任何議題上發表自己的想法,無須經過任何人的同意。然後是臉書跟推特提供了任何議題即時性的、全球性的評論。
Kindle則是讓出版書籍能夠如虎添翼。即使麥克魯漢也無法免於傳統出版具破壞性的媒體把關的影響。我記得當他從多倫多到紐約來參加我剛剛提過的媒體四大律會議時,就帶著一箱「廉售」的《以今日論:高級主管中輟生》( Take Today: The Executive as Dropout <$>),就是已經下架,然後一本書給作者一塊錢版稅的書,因為出版商已經認定了這本書的銷售不佳,不足以支持它再版。
亞馬遜的Kindle對書籍所做的便是讓所有的作者、所有的人,不論是麥克魯漢或是無名氏,都能夠出版書籍。身為一個作者,我自己也因此獲益。我的科幻小說自二○一二年開始供應Kindle閱讀版本──這些之前都被傳統大出版商以精裝本或是平裝本的方式出版過。我的小說以Kindle版本賣出去的也比之前用傳統出版方式的要來的多。對於作者而言,相較於傳統的書籍出版,Kindle其他好處還包括:在書完成之後的幾小時內便能出版(傳統出版則需要幾個月或是幾年),書出版之後也能夠隨時進行編輯,作者/出版商可以隨時看見銷售數字或是每月的版稅收入(傳統出版業要一年才能看到這些數字一兩次)。還有,這些版稅通常是書籍定價的七成,相較於下,作者只能從傳統出版業拿到書籍銷售的一成。
讀者也能夠從立即性獲得好處。在報紙的時代,書的時事話題性只能透過報紙附印還有一天中不斷的更新才能達成。麥克魯漢在《認識媒體:人的延伸》( Understanding Media <$>)中以同意的口吻引用法國詩人阿丰斯.德拉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在一八三○年的哀嘆:「這書來的太遲了。」十年之後,麥克魯漢也觀察到:「施樂影印機讓每個人都成為出版者。」我將二○一四年發表在〈視覺文化期刊〉(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 <$>)中有關麥克魯漢文章取名為〈Kindle來的正是時候,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出版者〉( The Kindle Arrives in Time and Makes Everyone a Publisher <$>)以強調Kindle在書籍進化中所扮演的角色。關於媒體四大律,Kindle除了重拾作者的掌控之外,還重拾了經典、多重版本的報紙的立即性。(關於轉化部分的分析,因為Kindle太新了所以還無法清楚評斷。)
阿拉伯之春
報紙使媒體的政治前因後果變得清楚、可理解。麥克魯漢最冒險、最具爭議的嘗試便是測量媒體的政治效應。例如,他在《認識媒體》中說道:「沒有收音機,我們就不會有希特勒的出現,因為他的言辭是無法經得起平面媒體對他的邏輯檢視。而且,希特勒的樣子看起來根本就不符合他自己所鼓吹的亞利安人典範。也因此,他在電視上看起來,根本就跟他自己所言的自相矛盾。」
在《新新媒體》第二版中,( New New Media, 2nd edition, 2013 <$>)中,我檢視了社群媒體是否為阿拉伯之春中必要的條件。相較於「充分的」這個描述,「必要的」作為「必要條件」的形容詞在此是相當重要的。就如同電梯對摩天大樓是「必要的」,但並不是「充分的」條件──「必要的」意思就是說建構所有高樓需還需要這一項科技的,對阿拉伯之春來說,需要的不只是一個可以觸及推特、youtube的新管道、以及掌控在人民手中而非在政府手中的媒體。但是社群媒體的必要性,尤其是發生在突尼西亞和埃及的早一波阿拉伯之春浪潮之時就廣泛地評論著。像是埃及的瓦埃勒.高寧就告訴CNN:「這場革命始於網路…這場革命始於臉書。」(see Evangelista, 2011, and also Levinson, 2011, for more).
阿拉伯之春缺乏全面性的成功並無法否定新新媒體在推翻政府中扮演助力的角色。即使革命可能是因為任何其他的因素促成或是煽動的,包括媒體,革命遠程的成功通常是取決於公民生活是否有實際的改善,這遠比革命初期時所傳播的民怨來得重要的多了。
因此,埃及在穆巴拉克下台之後的動盪顯示了社群媒體的侷限。社群媒體不是社會改變的推手卻是加強統治的手段。同樣的方式也可應用在社群媒體在民主社會中對選舉時的和選舉之後的影響。
麥克魯漢推特人
推特不只是一種媒體的象徵,能夠「軟性地定調」(softly determined)阿拉伯之春,也是麥克魯漢為什麼而寫作以及麥克魯漢如何寫作的樣板。所謂的「軟性的」是一個必要的條件,「硬性的」則指的是充分的條件。的確,作為一個媒體,推特捕捉到媒體的一種形式:注釋或是篇章名。(glosses or chapter titles; 譯註:在《古騰堡星系》中,麥克魯漢刻意將此書分成一○七的短篇,或稱之為注釋。每個注釋僅有兩到三頁的篇幅,就像是一大片馬賽克中的一個部份。)這種形式麥克魯漢應用在他最廣為人知也最重要的著作《古騰堡星系》中( The Gutenberg Galaxy <$>)。
在這一○七個注釋中,我最喜歡的是:「精神分裂症可能是識字必須的後果。」以及「新的電子相互依賴症將世界重新改造成地球村的樣子。」這些注釋簡單扼要地說明了推特的理想以及一百四十個字符的限制—言簡意賅致力成為機智的靈魂。除了,在麥克魯漢的例子中,這些注釋傳達了不只是機智還有他熱切、簡潔、影響廣泛以極具預言性的智慧。
如同我在《數位麥克魯漢》中所說的,麥克魯漢預見了數位時代並不是因為他有預言能力而是因為他的想法與人類溝通的需求同步。在數位時代,這些需求都能夠被提供並且得到滿足。但社群媒體,或稱新新媒體,的來臨卻帶來了更多:麥克魯漢的溝通模式便是嘗試打破這些在傳統印刷媒體中受到嚴格管制的責難。這些責難不只會妨礙有才的作者出版書籍,還會讓這些能夠出版的作者只能以某些特定的方式寫作,必須是長篇加上短篇名。《古騰堡星系》打破了這些限制,而像推特這類媒體上的寫作形式出現也顯示了麥克魯漢的表達模式不只是奇特或是挑釁的,而是在根本上符合人性的。
希拉蕊柯林頓的「冷」競選宣言影片
在麥克魯漢理解媒體的工具中,最知名、也是最常被批評跟誤解的便是他將媒體區分為「冷」媒體與「熱」媒體。熱媒體是高調的、熱烈的,提供消費者許多知識。相較之下,冷媒體是低調的、軟性的、模糊的,提供消費者較少資訊。麥克魯漢令人吃驚的看法是冷媒體能引起較多的參與。這些閱讀大眾被拉進來參與以消弭彼此之間的鴻溝。以下有幾個好例子:詩(冷媒體)相較於相當長度的散文作品(熱媒體)較能夠引起更多的想法跟討論而動漫圖片(cartoon drawing;冷媒體)比一張清晰的照片(熱媒體)更能引起仔細檢視。
麥克魯漢喜歡將這類的區別應用到政治跟媒體上面。最有名的便是他評論一九六○年約翰甘迺迪在電視競選辯論會上擊敗尼克森,因為約翰甘迺迪比較適合用電視這類的冷媒體。而這樣的分析也相當適用於二○一五年的政治事件當中。
二○一五年四月,希拉蕊柯林頓不是在電視上而是在youtube上宣布投入二○一六年美國總統選舉。許多評論員都相當驚訝,候選人希拉蕊竟是在這支競選影片的後半段才出現。通常,候選人都是一開始就出現在影片中,而且會占滿影片的所有篇幅。但是麥克魯漢的冷熱媒體區別解釋了這樣的選舉策略:希拉蕊正在營造出一個低調的、平靜的氣氛,吸引觀眾用他們想要從競選人口中聽到的競選承諾來填滿影片。這對希拉蕊來說是有利的,畢竟她的立場已經眾所皆知,只是需要藉由影不斷地強調與訴說。
除了我一看到影片就PO上部落格的文章,其他的評論家也引用麥克魯漢的理論來分析這個重大政治事件。多數情況下,學術界持續擁護麥克魯漢試圖想去征服的傳統。但是對於麥克魯漢作品一直以來的興趣,本書的第二版即是最好的例子,顯示出麥克魯漢的思想以及表達模式皆是與超越傳統出版、學術、政治分析的文化接軌,且與人類擅於理解瞬息萬變世界的表達模式相連結。
二○一五年四月,保羅.李文森於紐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