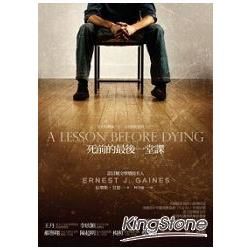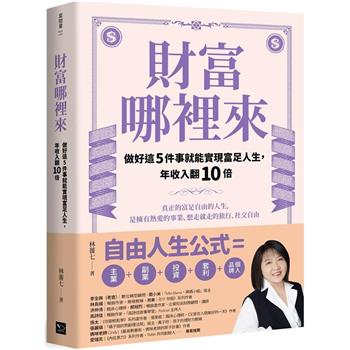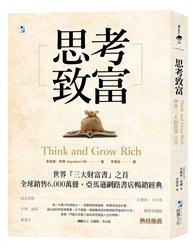一場生命價值的自我追尋
和煦、高貴,令人默默動容
歐普拉欽點,人人必讀的當代經典
美國國家書評小說獎桂冠,全美中學文學課指定讀物
銷售突破250萬冊,蟬聯數週暢銷書榜冠軍
感動猶如《姊妹》,摯情媲美《梅岡城故事》
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人厄寧斯.甘恩,最觸動人心雋永經典之作
繁體中文版首度面世------本書榮獲------◇ 美國國家書評獎
◇ 普立茲獎提名
◇ 歐普拉讀書俱樂部選書
◇ 美國青少年圖書館協會(YALSA)年度好書
◇ 改編電影《死亡記事》(實力演員唐奇鐸〔Don Cheadle〕主演),抱得兩座艾美獎
真正的勇敢,不一定是拚命抵抗四○年代的路易斯安納州,二十一歲的黑人傑佛遜因為好奇,捲入一樁雜貨店搶案,不料,行搶的友人及老闆當場喪命,只有他一人倖存。無人能證明他的清白,不願為自己辯護的他,被白人法官判了死刑,必須坐上電椅。
同是黑人的葛蘭特自外地學成歸鄉,在區裡的教堂教課。獨善其身、能言善道的他,一直以為自己可以和家鄉的同胞不一樣,然而一切似乎不如所想,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逃離這裡。當他得知傑佛遜的判決後,本想冷眼看待,卻在親友的逼迫之下,勉為其難地走進監獄,為傑佛遜上臨死前的最後一堂課:要帶著尊嚴與自傲而死。
受挫而自甘墮落的傑佛遜能否找回為人的價值?矛盾而掙扎的葛蘭特如何尋得救贖的意義?這是一堂教導,更是一次領悟。美國南方的種族歧視,黑人教師的不甘抱負,無知少年的受挫人生,交織出最堅韌、不捨的生命情誼。甘恩以濃厚的在地情懷,對生命奮鬥的深摯同情,以及人物心理狀態的細膩刻劃,寫出了一部歷久彌新的經典。
作者簡介:
厄寧斯‧甘恩(Ernest J. Gaines)
生於美國路易斯安納州,出身佃農家庭,為家中長子,下有十一位弟妹。自小由姨媽撫養長大,就學時每年幾乎都有五至六個月在棉花田裡工作。十五歲時,甘恩搬至加州與母親及繼父同住。十七歲時於舊金山州立大學的校園雜誌上發表第一部作品《烏龜》(The Turtles),隨後獲得了史丹佛大學的寫作獎助,自此開始在文壇上綻放光芒。自一九八四年起,甘恩固定在舊金山與路易斯安納的拉法耶(Lafayette)兩地大學教導寫作。現與妻子居於路州奧斯卡鎮(Oscar)。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死前的最後一堂課》是甘恩最受讀者推崇的作品,本不僅在銷售上獲得肯定,更榮獲一九九三年美國國家書評獎小說類首獎等諸多獎項,改編HBO電影《死亡記事》,也抱得了兩座艾美獎。甘恩的其他作品還包括《老人的聚會》(A Gathering of Old Men)、《珍.彼特曼的自傳》(The Autobiography of Miss Jane Pittman)、《愛與塵》(Of Love and Dust)、《父親的家》(In My Father's House)、《血統》(Bloodline)等書。
甘恩曾獲國家藝術基金會、古根漢基金會、麥克阿瑟基金會、美國文藝學會等機構頒發獎章,並榮膺路州年度人文學者,且由法國政府受封為藝術與文學騎士。甘恩於二○○四年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譯者簡介:
柯乃瑜
英國巴斯大學口筆譯碩士,自由口筆譯者。天性愛流浪,嗜好嗑文字,永遠長不大。譯作有《搞定怪咖情人》、《荒野之月》、《向生命說Yes!》(合譯)、《異教徒的女兒》、《廁所之書:第一本廁事大全》、《愛無忌憚》、《標本師的魔幻劇本》等。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從堅強、令人無法忘懷的角色性格中,厄寧斯‧甘恩給了我們一個一輩子都受用的教誨。」
- 歐普拉讀書俱樂部(Oprah's Book Club)
◇「高貴而令人動容,足稱當代經典,值得用一輩子去研讀、鑑賞、領受。」
-《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
◇「《死前的最後一堂課》再次確立了甘恩身為美國重要作家的地位。」
-《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深觸人心……成功地激起了一代人的難忘記憶。」
-《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強烈且野心勃勃的小說。」
—《新聞日報》(Newsday)
◇「沉著而動人,帶領我們重遊舊地,為生者上了一課。」
—《舊金山記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厄寧斯‧甘恩以樸實但劇烈的語言,呈現這寶貴又適切的一堂課。」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甘恩能夠喚起逝去時代的生命底蘊,使其栩栩如生,宛如昨日之事。」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睽違十年推出的第一部小說,可能就是甘恩的文學最高成就。……縱使故事的終局早已落定,裡頭仍然充滿熱烈的情感與人世的共鳴。
—《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 簡單的文句和尋常的語調,宣示著令人難以承受的哀苦情感,然而甘恩寫出的不是一部要教人痛哭流涕的小說,而是一部豐美無限的經典。
-《柯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媒體推薦:◇「從堅強、令人無法忘懷的角色性格中,厄寧斯‧甘恩給了我們一個一輩子都受用的教誨。」
- 歐普拉讀書俱樂部(Oprah's Book Club)
◇「高貴而令人動容,足稱當代經典,值得用一輩子去研讀、鑑賞、領受。」
-《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
◇「《死前的最後一堂課》再次確立了甘恩身為美國重要作家的地位。」
-《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深觸人心……成功地激起了一代人的難忘記憶。」
-《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強烈且野心勃勃的小說。」
—《新聞日報》(Newsday)
◇「沉...
章節試閱
我不在場,卻也在場。沒有,我並沒有參與審判過程,我沒有聽見判決,因為我從頭到尾都知道會是什麼結果。我彷彿跟其他人一樣出席了,不是坐在姨婆和他的教母後面,就是坐在她們旁邊。兩位婦女都體型壯碩,但他的教母更壯實。她的身高普通,約五呎四、五呎五,體重卻將近兩百磅。她和我姨婆找到了他跟法院指派律師同坐的桌子後兩排的位子,之後便如巨石或橡樹、柏樹樹樁般,一動不動。她一次也不曾起身去喝水,或使用地下室的洗手間。那男孩和律師同坐在前方桌子,而她就坐在原位,盯著男孩剃淨的後腦杓,就連他已經離開法庭,等待陪審團的判決時,她的視線依舊維持同一方向。她沒聽見法庭上任何一句話,沒聽見檢察官說話,沒聽見辯護律師說話,也沒聽見我姨婆說話。(噢,對了,她只聽見一個字,這個字她一定聽到了:「豬。」)是我姨婆的視線跟著檢察官在法庭上左右來去,看著他握拳重擊自己的掌心,重擊他擺放文件的桌子,重擊法庭上區隔陪審團的欄杆。是我姨婆跟隨著他所有動作,不是他的教母。她根本沒在聽。她已經聽膩了。她知道,如同我們都知道,最後結果會是什麼。白人男子在搶劫過程中遭殺害了,而雖然兩位搶匪已經當場斃命,只有一位遭到逮捕,不過這一位也得死。雖然他對他們說,沒有,他跟這個案子沒有關係,他不過是去白兔子酒吧,途中碰到老哥跟大熊開車經過,說要順道載他一程。他上車後,他們問他有沒有錢。在他告訴他們自己一毛錢也沒有後,老哥跟大熊就開始討論賒帳的事,說葛洛培老頭應該不會介意讓他們賒一品脫的酒,畢竟他們那麼熟了,而且他也知道,榨糖季節快要到了,到時自然有錢付給他。
店裡空無一人,只有老店主艾爾西‧葛洛培坐在櫃台後方的板凳上。他先開口。他問候傑佛遜的教母。傑佛遜說他的奶奶很好。葛洛培老頭點點頭。「你幫我跟她問好,」他對傑佛遜說。他看向老哥及大熊,但他不喜歡他們。他不信任他們,傑佛遜從他的表情就看得出來。「小子們有什麼事?」他問。「葛洛培先生,來瓶那個白蘋果,」大熊說。葛洛培老頭從架上拿下酒瓶,但他沒把瓶子放在櫃台上。他看得出那兩個小子已經喝過酒,他起疑了。「你們幾個小子有錢嗎?」他問。老哥跟大熊把口袋裡所有的錢全攤在櫃台上。葛洛培老頭用眼睛數了數。「這些不夠,」他說。「拜託啦,葛洛培先生,」他們哀求他。「你知道等到開始榨糖,你就可以拿到錢了啊。」「不行,」他說,「到處都缺錢。你帶錢來,才能拿酒。」他轉身把酒瓶放回架上。那個叫大熊的小子往櫃台後方走去。「你給我停在那裡,」葛洛培對他說,「退回去。」大熊已經喝了酒,眼神發亮,步伐不穩,始終咧嘴大笑著繼續往櫃台後方走去。「退回去,」葛洛培對他說。「我說真的,最後一次機會,退回去。」大熊繼續前進。葛洛培快速走向收銀機,從裡面拿出一把左輪手槍開起槍來。很快地,另一個方向也傳來槍聲。當周遭再次安靜下來後,大熊、葛洛培及老哥都躺在地上,只剩傑佛遜還站著。
他想跑,但是他跑不了。他甚至無法思考。他不知道自己在哪裡,不知道自己怎麼到那裡的。他連自己上過車這件事都想不起來。當天做的事情,他一件也想不起來。
他聽見呼叫聲,以為聲音是從酒櫃裡傳來的,然後他才發現葛洛培老頭還沒死,是他在叫。他強迫自己走到櫃台尾端,他的視線得越過大熊才能看見店老闆。那兩個都躺在櫃台與酒櫃之間。許多瓶子都破了,酒與血灑遍了他們的身體和地板。他站在原地,呆望著倒靠在酒櫃下半部的老人。酒櫃裡擺滿了一加侖與半加侖裝的葡萄酒。他不知道自己該走向老人,還是該跑離商店。老人繼續呼叫他:「小子?小子?小子?」傑佛遜開始害怕。老人還活著,他看見自己了。老人會把他供出來。這下他開始胡言亂語。「不是我,葛洛培先生,不是我,是老哥和大熊。老哥開槍打你的。不是,他們強迫我跟著來的。葛洛培先生,你要跟警察說清楚。葛洛培先生,你聽到了嗎?」
他只是在跟死人講話。
他還是沒跑,不知道該怎麼做。他不相信發生了這種事。他又一次想不起來自己怎麼到了這裡。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跟老哥和大熊一起去的,還是事發後自己走進來看見這一切。
他的視線在屍體之間來回。他不知道該打電話找人還是逃跑。這輩子從沒撥過電話,但他看過別人用電話。他不知道該怎麼做。站在酒櫃旁,他突然發現自己需要喝酒,而且迫切需要。他從櫃上拿了瓶酒,扭開瓶蓋,瓶底朝天,動作一氣呵成。威士忌如火焰般灼燒著他,燒他的胸,燒他的肚,甚至他的鼻孔。他的眼眶泛淚,於是搖搖頭讓腦袋清醒。這下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在哪裡,開始真正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他知道他得離開那裡。他轉身,看見收銀機裡的小鐵夾下壓著錢。他知道拿人家的錢是錯的,奶奶告訴過他永遠不可以偷東西。他不想偷錢。但他口袋裡一毛錢也沒有,而且附近一個人也沒有,誰能說他偷了錢呢?絕對不會是地上的死人。
他才越過一半店面,錢剛塞進口袋,半瓶威士忌拿在手裡,兩位白人男子便走了進來。
這就是他的說法。
**********
傑佛遜鬆開緊扣的手,開始用右手食指刮左手的指甲尖。他發紫的指甲十分堅硬。
「什麼時候復活節?」他問。
「明天是耶穌受難日。」
「那是祂復活的時候?」
「不是,他是復活節復活的。」
「那就是祂死的時候,」傑佛遜對自己說。「一聲都沒吭過。沒錯,吭都不吭。」
「安布洛斯牧師來看你的時候,你跟他講話了嗎?」我問傑佛遜。
「一點點。」
「你應該要跟他講話,這樣對你奶奶有好處。她希望你跟他講話。」
「他叫我要禱告。」
「你禱告了嗎?」
「沒有。」
「對你奶奶會有好處。」
他看著我,一雙血紅大眼很是悲傷。
「你覺得我會上天堂嗎?」他問。
「我不知道。」
「你覺得葛洛培先生上天堂了嗎?你覺得老哥和大熊上天堂了嗎?」
「我不知道。」
「那我禱告做什麼?」
「為了你奶奶。」
「奶奶不需要我幫她上天堂,要是有天堂她就上得去。」
「她希望你能跟她一起在天堂,那裡沒有痛苦,沒有憂愁。」
他朝我露出短暫嘲諷的得意笑容。
「威金斯先生,你禱告嗎?」
「沒有,傑佛遜,我不禱告。」
他哼了一聲。
「但話又說回來,傑佛遜,我迷失了,」我認真地看著他。「此時此刻,我什麼都不相信,不像你奶奶那樣相信,不像安布洛斯牧師那樣相信。但我希望你能相信。我希望你能相信,這樣有一天或許我也會相信。」
「威金斯先生,是相信天堂嗎?」
「如果對在世的人有幫助的話,傑佛遜。」
「安布洛斯牧師說我得放棄這裡的東西,他說世上已經沒有我的東西了。」
「他是指身外之物,傑佛遜。車子、金錢、衣服……這一類的東西。」
「威金斯先生,你看過我開車嗎?」
「沒有。」
「看過我身上有超過一塊錢的時候嗎?」
「沒有。」
「威金斯先生,有超過兩雙鞋子嗎?除了一雙星期天上教堂穿,一雙平常工作穿?」
「沒有,傑佛遜。」
「那我有什麼可以放棄的,威金斯先生?」
「你不曾擁有過任何可以放棄的身外之物,傑佛遜。但有些東西比身外之物還要重要,那就是愛。我知道你愛她,也願意為她做任何事。你不餓的時候不也吃下了燉肉,只為了讓她開心?現在我們要的也就是這樣而已,傑佛遜。做點什麼讓她開心。」
「那我呢,威金斯先生?別人做過什麼是讓我開心的?」
「她不是曾做過許多事情讓你開心嗎,傑佛遜?為你煮飯,為你洗衣,你生病的時候照顧你?她現在生病了,傑佛遜。她只有一個要求,要你像個男人那樣抬頭挺胸地走路,在天堂與她相會。」
「你們的要求都很多,威金斯先生,向我這種什麼都沒擁有過的可憐黑鬼要求。」
「她就會為你這麼做。」
「威金斯先生,她會代替我坐上那張椅子嗎?你會嗎?有任何人會嗎?」
他等著我回答他。我不願回答。
「不會的,威金斯先生,我得自己去。就只有我,威金斯先生。安布洛斯牧師說只要我祈求上帝,祂就會在那裡陪我。威金斯先生,你覺得如果我祈求上帝,祂會在那裡陪我嗎?」
「他們是這麼說的,傑佛遜。」
「威金斯先生,你相信上帝嗎?」
「是的,傑佛遜,我相信上帝。」
「怎樣?」
「我認為是上帝讓人能相互關心,傑佛遜。我認為是上帝讓孩子能玩耍、讓人能歌唱。我相信是上帝讓所愛的人能夠相聚。我相信是上帝讓樹發芽、讓土壤長出食物。」
「威金斯先生,那是誰讓人能殺人的?」
「他們殺了祂的兒子,傑佛遜。」
「然後祂吭都沒吭過。」
「他們是這麼說的。」
「我就想要這樣結束,威金斯先生。吭都不吭。」
我不在場,卻也在場。沒有,我並沒有參與審判過程,我沒有聽見判決,因為我從頭到尾都知道會是什麼結果。我彷彿跟其他人一樣出席了,不是坐在姨婆和他的教母後面,就是坐在她們旁邊。兩位婦女都體型壯碩,但他的教母更壯實。她的身高普通,約五呎四、五呎五,體重卻將近兩百磅。她和我姨婆找到了他跟法院指派律師同坐的桌子後兩排的位子,之後便如巨石或橡樹、柏樹樹樁般,一動不動。她一次也不曾起身去喝水,或使用地下室的洗手間。那男孩和律師同坐在前方桌子,而她就坐在原位,盯著男孩剃淨的後腦杓,就連他已經離開法庭,等待陪審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