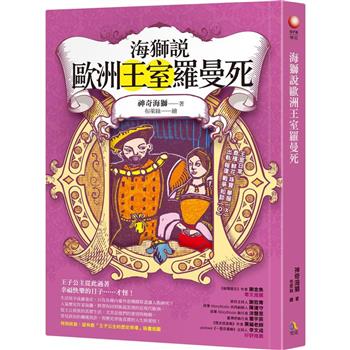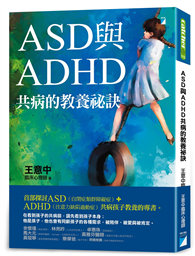名人推薦:
王家衛、白先勇、董陽孜、蔣勳、蔡康永‧跨界聯合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列)
林青霞、張敏儀、董橋‧專文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列)
推薦序
冬心緣/董橋
我和楊凡有一段冬心緣。冬心是金農(金壽門),號冬心,乾隆年間大畫家、大書家、揚州八怪的一怪。楊凡七○年代末向一位四川友人買了金冬心一冊花果冊,共十開,畫枇杷,畫西瓜,畫竹筍,畫菖蒲,畫水仙,畫古松,佈置幽奇,點染閑冷,真是畫評上說的「非復塵世間所」。楊凡讓了兩開給老先生羅桂祥,自己留了八開。
二○一○年蘇富比給楊凡編印的《鏡花緣》圖錄收了這件花果冊,我逐開細賞,第七開古松題句最長,一看眼熟:「白苧袍,青絲履,清旦山行松里許。松風為我一掃地,忽作水聲吹到耳。耳中生豪但願如松長,此身落落如松強。試問有錢百萬河東客,可買松陰六月涼?」我翻箱一找,找出舊藏一件清代紫檀束腰小筆筒,刻的正是楊凡花果冊第七開的古松和長題,連冊子裡最尾一開署款也刻了:「乾隆辛巳秋日七十五叟金農畫于廣陵客舍」。我高興了好幾天,慢慢也就淡忘,幾次碰到楊凡都不記得說。金農筆筒好多年前收進來,沈葦窗先生當年看過說一定是照冬心冊頁臨刻,刻工那麼精美,非乾嘉高手辦不到。沈先生真厲害,一猜猜著了。玩字畫可以修煉文采。楊凡文章辨識人事,平易生姿,洞見底蘊,難怪識者讚嘆。
底蘊二字如今少人用了,辭書上多說內容詳細即是底蘊,不說內心蘊藏的才智見識也叫底蘊。《新唐書》寫魏徵,說他「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黃宗羲說觀荊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和盤托出」。我少小時候到煮夢廬學做舊詩,老師亦梅先生寫<元日懷人詩>,有兩句是「最是江州舊司馬,十年心事訴琵琶」,坐在籐椅上抽菸的雪翁讀了說:「得此二句便好,全詩盡見底蘊!」書齋外面風過處幾片枯葉飄落荷塘。我問先生什麼叫底蘊?先生笑說:「荷塘水面無端多了幾片枯葉,荷塘便也托出些底蘊了!」我好像懂了,其實不懂。五十多年過去,讀楊凡文章,我幾次想起煮夢廬那天情景,漸漸懂了底蘊。《楊凡時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十篇文章搭成一道悲歡離合的遊廊,偷閑再遊一遍,雕欄無事,語燕呢喃,冷不防又飄來幾片落葉,窸窣聲裡多了一層輕愁,晚風依舊習習,故事依舊好看。忘了早年在哪裡認識楊凡。也許是戴天晚宴席上,也許是玫瑰夫人下午茶座,清清貴貴的玉堂公子,談字畫,談舞蹈,談攝影,談電影,談摩耶精舍裡的郭小莊。然後看他拍的一些電影,流金歲月裡玫瑰開了又謝,桃花謝了又開。然後在拍賣行展覽廳看到他珍藏的字畫,真是老民國庭院才子的品味,頹廢而華美的鏡花因緣。難怪齋名叫謫僊館,八十四叟張大千給他寫的匾額稱他曼石仁兄:多麼五四的名號!楊凡喜歡邵洵美,也喜歡邵夫人盛佩玉寫的自傳。盛佩玉是盛宣懷的孫女,晚清夕照胡同口款款走進民國華燈搖曳處:「因為看了邵洵美和盛佩玉的事蹟,才知道什麼是得失與聚散,才知道應怎樣妥當地處理這得失與聚散。」楊凡說。拜會赤地劫後的沈從文,他跟隨黃永玉稱呼沈先生叫沈叔叔:楊凡顯然捨不得書裡的邊城,也捨不得戲裡的翠翠,文章於是寫得那麼遠,也寫得那麼近。遠是遠心,曠達深遠,唐代楊炯說的玉振金聲,筆有餘力,遠心天授,高興生知。
近是近思,習知易見者思之,《論語》說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為了鑑定文徵明署款「文璧」的山水長卷真偽,他到台北中央圖書館翻遍古籍找到這卷真跡的著錄,還請江兆申一語定案,一九八五年長卷在紐約蘇富比高價賣出,楊凡拍了《玫瑰的故事》。這齣山水傳奇我聽江先生談天談過:「楊凡其實眼界不低,真用功!」他說。江先生跟我講古畫,也講過遠心,講過近思。那天我陪他到古玩街找高古銅印,到了大雅齋二樓,他一個下午買了幾十枚珍品,走下斜街,我怕他累了,讓他坐在小公園長椅上歇歇腳。夏陽似酒,蟬鳴似夢,我問他石濤他講石濤,我問他八大他講八大,晚上一圍人吃飯,他悄聲說,回台北謄寫一冊印拓寄給我,裱成冊頁玩玩。江先生走了好多年了,那冊《靈漚館印拓》平安無恙:「六月一日與董橋兄同在骨董肆中得此,通身綠鏽,背有雷文……」。我比楊凡老得多,楊凡比我小不少,我們有緣跟江兆申那一代前輩交往,胸襟從此沾了老歲月一絲清芬,那是福分。楊凡花前月下袖拂筆舞,輕易描繪得出六朝煙水、陶庵燈影,沾染的恰恰是三兩鴻儒詩餘硯邊三巡過後的酒香墨香。更難得的是他在國外遊學多年,巴黎、英倫廣交雅人逸士,美國各州享盡春花秋月:「但是在那些時尚的後面,我沒敢告訴別人的是我自己的徬徨與空虛,自己的無助與無奈,到底,要上一堂怎樣的課程?」沒有徬徨,沒有空虛,沒有無助,沒有無奈,楊凡其實也成就不了楊凡。我素來知道他不愛應酬。我也不愛應酬。書畫展覽廳裡好幾回遠遠看到他,我都沒有過去打擾他。邀他寫稿,我也勞煩林道群居間聯繫。稿子來了,讀了,喜歡,我總是只跟道群誇兩句。楊凡從前那部精裝攝影集我至今偏愛,他送了我一部,我又買過兩部分送給北京、台北的文友。
我跟幾位談得來的英國朋友、美國朋友都這樣,沒事絕不煩來煩去。幾十年前我住干德道,楊凡也住那一帶,上山下山偶然碰得到。那時候老半山很幽靜,我住的三十五號要上幾級台階穿過天井一片花木才是正門,像歐洲小城小宅院。下面一條街是羅便臣道,六○年代我也住過,鄰居是林太乙和黎明,林語堂常從台北飛過來盤桓一段日子,說是喜歡半山這一彎老香港。楊凡寫的旭和道一號也漂亮,韓素音五○年代聽說也住過那邊。干德道現在的謫僊館,我上個月去吃過一頓豐美的晚餐,樓上樓下佈置得很倫敦、很巴黎,楊凡臥室外那幅傅抱石是絕品,一幅夠了,比十幅凡品金貴。審美眼光沒得學,天生的。林海音從前來香港總要找人帶她去放映室補看大陸許多電影,林先生太愛看電影了,她說才華難遇,品味難求,好片子看的是導演的才華和品味,跟寫一本好書一樣難。楊凡拍電影追求完美。看他寫這本新書也看出他還在追求完美,一筆一劃勾勒得乾淨、整齊、考究。這些環節我比他還要偏執,看了《楊凡時間》的裝幀,我終於服了。寫書賣文忌浮躁、忌浮泛、忌浮漂,下筆還來不及推敲穩妥,不要拋出去丟人,難怪斯文闌珊處,楊凡水袖一拂秋波一蕩,三分冷傲點得亮幾程字海。前兩天台灣一位學長來我家談天,看到《楊凡時間》:「書衣那麼考究,這本書內容好嗎?」他問我。我說豐子愷畫過一幅春遊圖,畫媽媽姐姐妹妹郊遊回來手上都拿著一枝花,題句「折取一枝城裡去,教人知道是春深」:「這本書正是那樣一枝報春花!」豐子愷畫的是桃花,似乎不如我家張大千一枝墨梅清雅,戊子年一九四八除夕在香港畫給夫人徐雯波。楊凡跟張家熟,看了難免勾起念想:歲月還是老的好。
《花樂月眠》(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裡寫徐雯波那篇小品,我讀完再讀,心中難免浮起一絲人琴之感。張大千不在了,徐雯波也老了,繁華過後,金粉飄零,舊院寥落,難得楊凡忙中不忘飛去台北看看她、陪陪她,桃李春風暖著一杯酒,江湖夜雨守護十年燈,恍惚中老太太興許才會指望明朝巷口的賣花聲。做人如做文,琴台呼酒,闌干拍遍,楊凡靜靜給予的總是海棠開後燕子再來的欣悅。寫完《楊凡時間》再寫的《花樂月眠》,筆底牽念的畢竟還是江水的嗚咽、浮雲的無語。那是生命的戀執,也是藝術的難捨,只有楊凡的閱歷和修煉才懂得在笑傲中踐諾,在關鍵裡赴約。看人幾十年,看書幾十年,我看了太多沒有根的人,也看了太多沒有根的書,愈發省悟根的珍稀,難怪張大千早年一句題畫詩說「眼中恨少奇男子,腕底偏多美婦人」。有根才有奇。楊凡一手文章勝在一個「奇」字:經歷之奇,處事之奇,鋪排之奇,取捨之奇,感思之奇,吐屬之奇。大千居士視他為奇男子不奇怪,大千居士腕底不少美婦人都歸了他也不奇怪。
推薦序
Baby Baby One More Time/張敏儀
有句話說:Beauty is only skin deep.
絕不。美麗並不膚淺,美麗不止於皮相。可是文字能夠美麗,就不簡單了。
張愛玲愛看小報,為的就是今天的副刊吧。後來她在美國大綑大綑收的書報大概就是這些。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輩律師,只買星期日的《蘋果》,只看「蘋果樹下」,只為董橋。董先生那一爐線香把「蘋果樹下」一群薰得沉醉,半睡半醒,忽然來了個分花拂柳的楊凡,有如驚夢!那段期間,說是奔走相告並不為過。人人問有沒有看楊凡?
這對長期寫的朋友好像不公平。可是副刊才俊多年來已成為自己人,大概不介意
貪新不厭舊。
電視劇《她從海上來》有一個鏡頭我喜歡。演胡蘭成的趙文瑄躺在椅上第一次看張愛玲,如在今生今世中形容,看著看著就坐起來了。楊凡筆下那些俊男美女,令星期天的油墨也透著花香。
成書之後從頭再看,才真正知道,如他所說,是一本有感觸的書。一生跑遍世界與電影苦戀。少年時與兄長大吵,沒飯吃也要拍電影!在好萊塢做臨記,那時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我的電視師傅音樂大師林樂培,今天八十五歲,常常提起當年在好萊塢做臨記是多麼寶貴的經驗。楊凡可真是浸過來的。後來單身匹馬走坎城,巧遇孫寶玲和法國電影眾生,令人看得津津有味。楊凡偶成此書,是因為驚覺自己已成懷舊文物。的確,要從小看遍中外電影、戲曲,從第一影室走來,對圈中人事熟悉的過來人,才有充分共鳴。
楊凡的筆友日子多令人嚮往。他第一個取得簽名照片的是美國明星約翰蓋文。超級美男子。他來港那一年,我到告士打道舊麗的大廈找人帶我去取簽名。還拍了照片。他很高,我站在他面前像個小孩子。楊凡,找到的話給你看。
唉,如果找到的話。
那時我上中學,為什麼和你一樣喜歡《Back Street》(芳華虛度)那樣冷門的電影?到現在還記得蘇珊海華(Susan Hayward)在片末那張臉。
還有,我也見過孫寶玲,去過她那幽魅的余氏古堡,看過一些半懂不懂令人懸念的《迷》的片段。
多少年來,和楊凡擦身而過,誰也不是誰的那一片雲,影淡風輕。多少年來,在各自的軌跡上繞著地球轉,忽然在一個交會點上發現他已變成一杯醇酒。以前在遠處看他的飛揚不羈,現在看見他眼中筆下的慈悲。世路已慣,以前的中場蝴蝶,現在不喜歡多人的聚會。我倒是現在才知道他當年的進取,不是不值得欣賞的。爭取到那麼多珍貴的時刻,才有今天的寶藏。他明顯地非常勤奮,對長者用心。隨侍張大千、黃永玉、胡金銓不是人人做得到,想想多難得!我連問何佐芝先生威廉荷頓的軼事都不敢呢!
有個傳說,楊凡賣一幅名畫拍一部戲。Wow!張婉婷羨慕地話自己只是餐搵餐食(意即月光族)。可是鍾楚紅早就說導演用的是辛苦錢,肯為他拍特別宣傳照。
不管怎樣,楊凡和電影的愛情比較華麗。他形態像貴公子,不是賈寶玉,是《源氏物語》的光之君,會舞。
你知道水仙花本來就是美男子。
有沒有見過他偶然用手指托腮?還有把那豹皮襯裡的黑大衣一揚,轉身?
可是你要好好看完這本書。在「別記」那頁桃紅色調子裡,他承認那個無所畏懼的年輕人內心徬徨、無奈。才二十多歲自信十足的外表,克服一切走到今天,有幾許淒清?
楊凡最近在路上遇到一個攝影師,叫他不要再拍電影,給自己留一些尊嚴。這大概如利刃穿心。他倒是寫下來,還牢記住了,理性地沉寂。
其實那人錯了。他大概聽說楊凡的題材偏鋒、票房慘淡才這樣以為。其實有多少人能忠於畢生所愛?只計付出,不計收穫,永不言悔?拍那些什麼什麼大業才有尊嚴嗎?毛尖引用過的中西聯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I would rather be a gay,這才是楊凡,他自己的唯美鴛鴦蝴蝶派教主。
楊凡不談政治,但他隱隱然有些失傳已久的莊敬自強因子。不明的話,請看<淚王子>,他為什麼會拍?像林夕寫<六月飛霜>,硬是不肯改為二月或十月,禁就禁吧。文化人,許多時從小處見真心。
楊凡自序說一路上忘記感謝許多人。真的,那是揮揮衣袖不帶雲彩的歲月,他是個向前闖的美少年,沒有人怪他。陸離不是到今天還偏心你嗎?看見你用筆揮出彩霞滿天,奼紫嫣紅,開心還來不及呢!
只有楊凡能寫楊凡。古蒼梧正好說了,如杜麗娘自畫丹青。有幸不用埋在梅花樹下,白白等幾年。
柳生們還在等回生呢。多謝鄧小宇,楊凡時間只是中場時間。珍芳達七十三歲寫的才叫Prime Time!
又要引毛尖的精句了。
雕欄玉砌應猶在,
Baby baby one more time!
推薦序
醉舞狂歌數十年/林青霞
我是個夜貓子,經常是天亮了才熄燈,熄燈前有時候會接到一通電話,我接起電話也不問對方是誰:「HABADAY早安!」對方一定是個輕柔的男音:「HABADAY 晚安!」然後雙方哈哈大笑。HABADAY 是我和他的暗語,這個暗語代表多重意思,好玩、好笑、生氣、快樂、可說的、不可說的,都隨著說話語氣的轉變用這個做暗號。暗語的由來是,在愛林未滿一歲時,楊凡教她唱生日快樂歌,她因咬字不清,把Happy Birthday 唱成HABADAY ,從此我和楊凡就拿這個做暗語。因為我晚睡晚起,楊凡早睡早起,我睡覺的時間正是他起床的時間,平常找不到適當的時間聊天。有一天天剛亮,他打電話給我,講了一個鷹與狼的故事,他最愛在電話裡跟我講電影情節:「一位武士和美女相戀,被巫師下毒咒,把武士變成狼,美女變成鷹。武士晚上是人,白天變成狼;美女白天是人,晚上變成鷹,他們兩人只有在月亮隱去太陽升起時才能同時變成人,但是只有很短的相聚時間,那部電影是《Ladyhawke 》。」我說:「那你是武士囉。」以後他就經常在月亮隱去太陽升起的時候和我聊天。
認識楊凡是在一九七七年我來香港拍《紅樓夢》的時候,《明報周刊》找我拍封面,由楊凡攝影。拍攝當天我穿著一條深藍緊身牛仔褲,上身不鬆不緊的白底紅色橫條POLO 衫。他不聲不響從房裡拿出一件白底藍直條大襯衫叫我換上。那是他的襯衫,我拿在手上有點遲疑。那大襯衫罩在我瘦瘦的身上竟然挺灑脫。於是我瞇著眼迎著風扇,一頭長髮隨風飛揚,楊凡順著音樂節拍輕盈的按著快門。他總是有本事讓被拍者感到輕鬆自然。
二○一一年我寫作出書的時候,楊凡還未正式下海,短短的一年裡他竟然出了兩本書。在他寫作之初,有一天和我喝下午茶,他眼睛閃著光,不停的在我身上打轉,問這問那,兩人離開等電梯的時候,他說,我要寫妳。到家沒多久,他打電話來興奮的說已經寫了一部分,我要他念給我聽,念到一半我說:「楊凡,我哪有那麼晚起床。」「啊呀!晚睡晚起是藝術家與美人的特權,何況妳既是藝術家,又是美女中的美女,加多幾小時絕不為過啦!」這個楊凡,為了達到目的什麼話都說得出來,「你給我提早兩個鐘頭。」「這樣子我就不寫了。」「不寫拉倒。」掛了電話我用簡訊傳去四個字「猴巴擺媚」?(廣東話「好巴閉嗎?」意思是「好了不起嗎?」)
第二天我和女兒去歐洲渡假,到了巴黎接到他的電話,說《蘋果日報》副刊「蘋果樹下」星期日會刊登他寫我的那篇文章。「你怎麼沒先讓我看過,龍應台說的,文章裡有涉及到他人的話,應該先讓那人過目,徵求他同意才好。」「來不及了啦!」我撥個電話給董橋,「董橋,你幫我看看楊凡那篇文章,告訴我這個朋友還值不值得交。」「很好呀,沒問題,他很有才情。」
我和楊凡就像童心未泯的孩子,兩個人有時吵吵鬧鬧,很快又和好如初。楊凡是個有心人,知道我開始看書了,就送我一個放書本的木架子,讓我看書的時候不用手持厚重的書。知道我想寫作了,就送我厚厚的稿紙,他說:「我知道妳還有很多話想說,妳就透過這小方塊把它寫出來吧!」
歐洲回來,看了他寫我的那篇<今夜星光燦爛>,反而被他最後一段打動,那段寫的是他自己:「回顧我的一生,不學無術,憑著自己的小聰明,闖蕩江湖。適逢幸運,薄得名利,花甲之年,本應罷手,以享天年。然而因緣際遇,把握機會,將自己的經歷做個回憶。..因為性格剛烈自私,是處不多,如此長篇道來,只希望讀者看到走過的路和交往的友人情誼,得到某些啟示。」還真有曹雪芹feel。其實,楊凡才真正的有話要說。他一身傳奇,透過《楊凡電影時間》裡一篇篇動人有趣的故事,除了描繪出許多不為人知的名人軼事,也把自己璀璨的一生勾勒得有聲有色。
楊凡對畫很有鑑賞力,手上的每一張畫都價值連城,十五年前他送了幾幅畫給法國博物館,只記得有一幅是張大千的六呎青綠潑彩<湘夫人>,還有一幅是明朝畫家唐寅的<抱琴歸去圖>,其他的我就不記得了,但肯定張張都是精品。法國政府頒發騎士獎章給他,我剛好也在巴黎,就一起去出席盛會。他穿著一套深色絲絨西裝,胸口配上紅寶石胸針,內襯粉紫襯衫,領口打著絲絨領結,活脫脫一個小王子。在法國總統宣讀楊凡對法國文化上的貢獻時,我看著眼前的景象,心想,這個總統一定沒想到,眼前這位小王子,幾十年前因為在香榭麗舍大道上跳中國民族舞蹈被法國警察抓去關了一夜的事。
最近楊凡賣了幾幅畫,變成大富翁,他打電話跟我說:「有一件事妳聽了一定很高興。」我以為他要告訴我他的畫賣了多少錢。「我不拍戲了。」我聽了真的很高興:「恭喜你啊楊凡。從此不用為你操心了。」
他倒真的說到做到,收拾行囊到處旅遊,過著閒雲野鶴的生活,這會兒他正在巴黎給《壹周刊》寫文章。我在電話裡說了許多讚美的話,說他能夠真正的做到「瀟灑」兩個字,不簡單,簡直可以媲美莊子了。他被我誇得正不知說什麼好的時候, 我說:「不過,你有一個缺點。」他屏住呼吸。「記仇!」我連珠炮式的發表言論:「你真夠狠的,就因為我怪你未經我同意,把我、你和法國總統頒發騎士獎章拍的照片,刊登在蘇富比的拍賣書上,你的《花樂月眠》裡,就一張我的照片都不放。」說完我們兩個哈哈哈哈……,笑個不停。他說:「青霞,妳一定要把這一段寫下來。」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自序
我們仍然真摯/楊凡
這是一本偶然誕生的書。
多年不曾動筆, 二○一一年三月香港電影節放映拙作《流金歲月》修復版,邀稿。於是為文千來字。影節編輯來郵,只能節錄文字數百,惟恐不敬,請見諒。於是拿著篇不長不短的千字文,不知如何是好。適逢影片上映在即,門票尚餘八成,於是添加數百字,厚顏交付「蘋果樹下」,冀望登載,博求宣傳之效。孰知奸計得逞,上座「激增」。
為文見報,喜悅之情不在話下。於是第二周再蛇一篇<旭和道一號>,並附上電影劇照一張。編輯傳來董橋先生言,來文照刊,然照片稍具娛樂版。奸計已破,立即懇請樓上畫家馬明先生趕繪插圖,再博宣傳。也算是影片放映前的自我推廣。
影片圓滿放映完畢,與觀眾對話交流之時,方知時至今日盛行「共同回憶」,而自己已成一懷舊物品。於是膽敢將自己戀愛的一生,呈獻讀者,冀望耐心聆聽。對不起,別誤解,是與電影戀愛的一生。
電影啟發了我的童年,豐富了我的一生。其實每個人的故事都同樣:成功與失敗、快樂與悲傷,有些人對不起你,有些人你對不起,有的多些,有些少點,結局雖說大有分別,其實想通還是一樣。
於是我勇敢的寫,某些感恩,泰半懺悔,並非尋求原諒或認同,只是客觀地把這一生的情信拿出來與眾共享,希望這段看似纏綿卻無可厚非的愛情,仍然真摯。
是的,希望我們仍然真摯。
因此這書本中每個人物,無論具名與否,都是千真萬確。起碼在我浮沉的記憶中如此這般。有時想去追尋某些的樣貌,卻怎樣也拼湊不來。像是古亭國小的謝蜜老師,她並沒做過任何令我畢生難忘的事,但是卻終生記得她的姓與名,因為她是我第一位老師。聖保羅的熊鳳嬋老師,則由於她的冷豔與從無重複的旗袍,再加上認真的教學態度,只要閉上眼瞼,她的相貌立即浮現。又是不久前,在馬路上經過一位坐輪椅的女士,似曾相識,我轉回借問:「妳是陳清梅老師?」她慈祥地說:「是的,但是你要告訴我你的名字,我現在記不得樣子。」我報上本名楊曼石,她說,「你現在是有名的導演。」頓時一股暖流湧上心頭。在這繁忙現實的物質社會,居然還有春風化雨的感覺。
這些人與物,都不曾在相簿中留下寫真,抑或是在歲月轉移中遺失。想起自己也還曾是為他人攝真乞食之人,怎會對照片的保存如此忽視?畢竟因為自己拍攝名人明星,再加上一些天生的交際本能,才有今天《楊凡電影時間》的出現。不珍惜就是忘本。
於是想找尋第一張付印海報的照片,那是一九六七年盧景文在香港大會堂的「歌劇選曲」,捎了個伊媚兒給盧老師,他說事隔多年,有些難度。於是想到照片的主角江樺女士,年輕音樂才俊高小弟,神通廣大,不消一句鐘,馬上聯絡,原來幾乎半個世紀之後,她還是在香港莘莘教學。到九龍城見到江老師,完全看不出她已年逾八十,身型高挑,步伐輕盈,談話間,對人生的寬容與感恩盡顯在美麗的嗓音間。她送了一本自己的故事《江樺唱情歌》,樸素的文字與印刷,完全上海閨秀風格大家,再附加音樂上的超然造詣,本應像瑪麗亞卡拉絲(Maria Callas)般母儀天下,然而在這快遞的社會,仍然如此淡定。感謝她借出當年的照片,忽然愧疚自己這本浮華回憶,微不足道。
的而且確,我的一生散漫不羈,零亂不堪,組織能力一如影評道訴我的電影劇本。許多稿件或照片都相繼失散,曾嘲笑若誰人寫我則自尋煩惱,孰知今日楊凡寫楊凡,某些存在記憶的影像,則需四處張羅,除了感謝江樺老師、胡燕妮小姐、泰迪羅賓先生提供我失傳的照片,更加感謝「國際攝影」高仲奇先生,他的林黛與李麗華確實豐富了許多人的想像,至於歐美的Eric Boman 、Willie Christi ,以及長住英國的Chiu ,不只提供照片,更親訴自己一生尚未為人所知的戀情。特別感謝古老師與邁克先生和皇姐(黃鴻端女士)在初稿及定版期間不厭其煩為文校對。
一件事能從開始到完成,是靠著許多人的善意與支持。更加感謝董橋先生、張大姐、林美人的序。感謝「蘋果樹下」。感謝出版社的諸位同仁,以及讀過我文章的朋友,你們才是我最大的動力與支持。套用田納西維廉斯在《慾望街車》對白, I have always depended on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最後,我希望這是一本還有點感觸的書。
二○一三年四月六日重整於香港干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