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推薦序
西方霸權的興起,抑或終結?
/ 許倬雲
台北的商周出版社正在出版重新翻譯的麥克尼爾《世界史》,要求我作一篇介紹。
這本書在六十多年前出版,轟動一時,成為世界史的標準教科書。麥先生在這本書以前,以《西方的興起》一書著稱於世。這本世界史,也可以說是從西方興起的基礎上,陳述若干非西方文化,各自發展的過程,但是後半段幾乎都是敘述西方文化對非西方文化的衝擊。從這個主題上,麥先生在《世界史》之後,又發表了一連串的著作,分別討論瘟疫、動植物、商業、能源等等,最後歸結到西方的霸權。譯者黃煜文先生中文譯本,文字通順,具有相當的可讀性,值得推薦。
由於這本書的啟發,後來許多學者開始跳出區域研究或個別文化的研究,分別注意到大文化區之間的彼此交流和影響。例如,有人就討論到,大洋航道開通以後,如何從海上追尋香料, 一步一步走向以兵艦支撐的西方強權。也有人注意到,各地人口的轉移和分散,文化和信仰的傳播與改變。從全球格局看,歷史學家們注意到,自然環境和人類快速交通之後發生的影響,例如,疾病的傳播、瘟疫造成的災害、各地物價落差造成的經濟差異、大區域間的多角貿易、等等。現在的歷史教學與研究,世界史已是顯學。過去以國家歷史為主題的史學,竟在逐漸轉變為全球史觀。從這個角度看,麥先生的書,的確有發踪之功。
可這本書究竟還是六十多年前多版的名著。到今天,幾乎三個世代累積的知識,對於許多問題已經有更深一步的想法。例如,《世界史》中,各地古代史部份,都因為六十多年來考古的發現,增加了許多資料。麥先生當年提出來的一些綜合理論,有相當部份需要修正。單以中國考古學而論,今天我們對中國史前歷史,其理解的程度有極大幅度的不同。中東考古學、新大陸的考古學、甚至連歐洲地區的考古學,或多或少,都與麥先生的時代所見的古代史,很不一樣。
麥先生是從西方的興起作為出發點,討論世界的整盤歷史。雖然他沒有種族的偏見、也沒有文化優勢的驕傲,但是這西方中心論還是無法避免的。二○一二年,史丹福大學的一個考古學家,伊恩.摩利斯(Ian Morris)出版了一本《西方的霸權,還在今天?》(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這本書也是討論西方五百年來主宰世界。從書的標題就可以理解: 一方面他還是著眼在西方文化霸權的出現,另外一方面,他又提出疑問:西方霸權是否到今天就要終結?這本書毋寧是麥先生《世界史》的續集,對六十年前幾乎無可質疑的西方霸權,開始討論其如何興起、以及是否已經走到盡頭?
這本書的論點,是西元一五○○年前,他稱為「東方」的亞洲,和稱為「西方」的歐洲,以各地發展而論,東方並不輸於西方。而一五○○年以後,西方突飛猛進,到今天,東方不僅趕上西方,而且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趨向。他在整部書中的潛台詞,毋寧是拿中國作為西方的對照面。他解釋西方興起的原因,是從地理上的偶然,使得西方可以一步一步從中東逐漸發展,終於主宰了非洲,也佔有新大陸。由於他是西方古典文明的考古學家,在古代的部份著墨不少。他也設法量化各種資料,將東方和西方的發展程度,分別以生活水平和戰備能力,作為對比的指標。這一個方法,從細節上說,不無值得深一步推敲之處,但是這種借用量化對比的方法學,固然有其一定的限度,也有其值得注意的長處。
麥先生的《世界史》,在台灣曾經有過賈士蘅女士的譯本,不知何故後來絕版了。商周出版社願意重新翻譯,以供台灣的學子作為讀物和教材。當然是好事情。我也盼望商周是不是也找人翻譯摩利斯的新著,兩本書合着一起看,對於我們了解走向今天全球化世界的歷史背景,有比較明確的了解。台灣長期以來,雖然和世界各處商業往來,各處的物質文明進入台灣,也相當程度地改善了台灣的日常生活。但是,台灣心理上的閉關,卻是常常令人擔心。有幾本好的世界史書籍,應當是我們樂見其成的好事。
《附記》六十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學讀書,麥先生是我校年輕教授中的新銳明星。我對他十分欽佩;可是因為我的專業是古代史,竟沒有選讀他的課程。一九六七年,香港邀請三位歷史學者,為他們籌畫大學歷史課程。領隊是英國的波特費特爵士,麥先生是中生代,我是隨習的第三代,三人合作,共事一場。這一段香火緣,給我學習機會,終生難忘。這回有此機緣,為麥先生的名著中譯本撰序,是我的榮幸,也借此向二位前輩致敬。
許倬雲
匹茲堡 2013年5月2日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推薦序
世界如同劇場,歷史是部大戲:麥克尼爾《世界史》導讀
/ 周樑楷
假使有人想找一本中文(或中譯)的西洋通史或世界通史,我建議先到Google,直接搜尋「麥克尼爾」或「William McNeill」就對了。
麥克尼爾於一九一七年在加拿大的溫哥華出生。這個年代難免讓人想起俄國曾經先後發生兩次革命,結果不論是正面的或負面的影響,都改變了二十世紀的整個世界。麥克尼爾十歲的時候,跟隨家人遷往芝加哥,而後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八年間,就讀芝加哥大學。日後他回憶說,那段時間曾經讀過《共產主義者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年出版),而且多少也感受到馬克思主義(Marxism)中的使命感,不過他始終都沒有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
這種人生境遇剛好與霍布斯邦(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1917─2012年)形成強烈的對比。霍布斯邦也在一九一七年出生。由於猶太血緣的背景,他輾轉從埃及、維也納、柏林,最後到倫敦,入籍英國。十五歲時,如宿命的安排一般,他參加了共產黨的青年組織,並且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洗禮,終生不渝。他的著作等身,建構了一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史觀,但有別於共產國家中那套教條化的說法。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順便Google一下,其中有不少中譯的著作,在台灣的銷售量相當可觀。
麥克尼爾和霍布斯邦這兩位同年出生的史家,分別都成為世界史的名家。他們的觀點不同,卻共享聲名,好比史學界的雙子星,近五、六十年來一直受人矚目。
麥克尼爾的著作中,屬於通史、宏觀性的可以分為兩種。一是西洋通史或歐洲史;另一種是世界通史。這兩種著作就版本來說,都有各自的起源,然而都在一九六○年代期間發行出版。他的《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首先於一九六三年出版,書名正好與德國思想家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的《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出版)唱反調。這兩本書的內容對近五百年西方世界的看法,分別為一樂觀,一悲觀。麥克尼爾的樂觀正好呼應了二次大戰後至一九六○年代期間美國的富強,尤其與當時盛行的現代化理論(Theory of Modernization)相互共鳴。難怪這本新書出版相隔一年,便贏得美國政府的大獎。這本書到了一九九三年,作者本人先後增訂了四版,直到今天仍然受歡迎,有人拿它當作教科書或相關考試的用書。假使讀者嫌本書的篇幅過多,讀起來還是費時,不妨讀讀《歐洲史的塑造》(The Shape of European History,1973年出版)。麥克尼爾撰寫這本簡明版的歐洲史,由劉景輝教授夫婦翻譯,中文初版叫《歐洲史新論》(1997年)。而後再修訂,改名為《歐洲史的塑造》(2007年)。
麥克尼爾的第一部世界通史就是《世界史》(A World History)。這本書的原著於一九六四年殺青,緊跟在《西方的興起》之後一年。內容除了埃及、中東外,還拓展到印度和中國等古文明。不過,純粹就歷史的分期法來說,這兩本通史卻是一致的,那就是:1. 從遠古時代到西元前一七○○年;2. 西元前一七○○年至西元前五○○年;3. 西元前五○○年至西元一五○○年;4. 西元一五○○年之後。然而值得我們好奇的是,麥克尼爾如何把全球幾千年來經驗世界中的史實組織起來,融會貫通呢?在本書的前言中,他雖然已經簡要的表示,但是我還想把他的這段話理解成兩句,以便進一步向本書的讀者說明:
不管在什麼時代,各種文化之間的世界均衡關係都免不了受到干擾。這些干擾起源於一個或多個中心成功創造出極具吸引力或較大的文明。
與這些中心直接或間接相鄰的文化,在受這些中心吸引或逼迫下改變了自己的傳統生活方式,有時候借用其技術或觀念。但更常見的是調整改變外來事物,使其能平順地與本地文化融合。
上述這兩句引文中的第一句,與人類學學者的說法有關。麥克尼爾在芝加哥大學就讀時期,曾接受雷德費爾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年)影響。麥克尼爾坦承借用了人類學中「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之說,強調在世界史上數不盡的文化(Culture)裡,有些屬於所謂的「文化核心」。在核心裡,不僅有較多的創造契機,而且有較高超的技術,更有種種地緣上的優勢與交通上的便利。「文化核心」如果能集合種種正面的條件,再配合「文化流」(Cultural Flow),就很可能形成所謂的「文明」(Civilization)。這裡所謂的「文化流」,換成歷史學界中淺顯易懂的行話,其實就是「時變」或「歷史意識」了。麥克尼爾身為史家,當然在應用「文化流」這個觀念時,要有憑有據依照史實,寫得很有「時變」的流動感。另外,在麥克尼爾的「文明──文化」模式中,介於「文明」與「野蠻」(barbarian)之間,有所謂的「文化斜坡」(Cultural Slope)。斜坡上好比梯田一般,有一階又一階水準高低不同的「文化」。就理論的層次來看,這種說法頗能自圓其說,值得參考。不過,可玩味的是,麥克尼爾在這本世界史裡對那些「文化核心」的分析,似乎比較偏向「地理──物質──經濟──科技」等層面的因素,以至於鮮少有「思想──觀念」的影響力。這種觀點可以說,也就是「現代化理論」的世界史翻版。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照拙文:〈麥克尼爾世界史新架構的侷限:兼論「文明」的自主性〉(刊於《當代》第六十七期,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至於上述引文中的第二句話,涉及「文化」與「文化」之間互動的關係。字裡行間透露著英國史家湯恩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年)那套「挑戰與反應」的史觀。湯恩比的理論打從《歷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的前三卷於一九三四年出版後,曾經風靡一時。在歐洲史及世界史的領域裡,湯恩比的名聲不讓艾克頓(Lord Acton,1834─1902年),和魯賓遜(J.H. Robinson,1863─1963年)專美於前。英國史學家艾克頓從十九世紀末年開始主編《劍橋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厚實的一套叢書,闡述近五百年來西方的自由民主進步史。同時期,美國史家魯賓遜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開啟西洋史的教學和研究,他所編著的教科書也一度成為美國各大學的典範。麥克尼爾在史學界比艾克頓、魯賓遜和湯恩比至少晚了一輩。尤其值得注意的學術背景中,湯恩比的鉅著出版的時候,麥克尼爾剛好是歷史系的新生。他一方面有意邁出艾克頓和魯賓遜在通史上的權威,另一方面活學活用湯恩比的理論,並且融會人類學學者的文化模式為一爐。當然其中也需要個人智慧,才能成一家之言。
任何歷史書總是有觀點的,而且有觀點的歷史書才有可能成為佳作。我們應該從觀點的層面深入分析麥克尼爾的著作,而不是把它只當作教科書或考試必備的參考書而已。
「觀點」這個詞彙讓人比較歡喜,聽起來沒有像「理論」那麼嚴肅唬人。其實「理論」的英文Theory字源來自thea,本意與觀看有關,引申就是觀點了。英文裡的theater,也和這個字源有關,指的是供人觀看的場所,或是事件發生的場所。就前者來說,供人觀看的場所,相當於中文裡的戲院或劇場。而後者,重大事件發生的場所,其中可能指某個戰場或戰區。
在戰場中有我方和敵方之分。人類的歷史從遠古氏族社會以來,就有自我與他者的認同(identity)問題,因此現實意識與歷史意識也永無終止的互動。如果我們同意戰場(theater)指的是廣義的,有關自我與他者各種衝突的場域,毫無疑問的,我們的世界就如同戰場一樣,而且就語意來說也如同劇場。從戰場到劇場,再到理論,這一切種種都源自「觀看」,所以我們可以說,「觀點」反而比「理論」更貼切現實人生。
我的書房裡掛著一幅版畫,那是美國一個行動劇團的海報。畫上只有一張面孔,雙眼裡各有一個「see」,畫面全是墨色,張力十足。另外,在畫中頭部上方留白處印有「see the world」幾個字,用紅色呈現,與整幅畫的墨色相襯,非常突出。有一回有位主修文化批評的英國學者來訪,特別喜歡這幅版畫。他說,「the world」要比「globe」(全球),讓人感覺更有人文和文化的氣息。我深表同意。的確,「全球」或「全球史」似乎有些冰冷,好比韋伯(Max Weber,1864─1920年)所比喻的,近代世界在一味地傾向理性化之後結果成為「鐵籠子」(iron cage)。也好比從衛星觀看的地球一樣,美歸美,但看不見人影。怪不得近來有些標榜「全球史」的著作,總是少了人的「主體性」(subjectivity)以及「人們製造歷史」(Men Make History)的感覺。包括麥克尼爾父子在內,他們兩人於二○○七年出版的《文明之網》〈The Human Web〉,反而比不上他之前寫的《世界史》來得有人情味、更像場大戲。
我對這位英國學者表示,特別受那個see字所吸引。See是種觀點,而world是種種事件發生的戰場或劇場。世界歷史的發生既是讓眾人觀看的,也是作者依個人觀點編撰的大戲。
周樑楷
台中青松齋 2013年5月20日
(本文作者現職台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中興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各界好評
「麥克尼爾把人類歷史視為一個整體,而人類歷史也一直朝這個方向在發展,到了我們這個時代,人類歷史確實已成為一個整體……麥克尼爾讓複雜的故事變得簡明易懂。」──《歷史研究》、《二十世紀美國法律史》作者、英歷史學家 阿諾德‧湯恩比Arnold Toynbee
「傑出的麥克尼爾教授是《西方的興起》的作者,他的新作再次顯示其廣闊的視野與綜合繁複史事的卓越能力。麥克尼爾尤其善於將各個文明模式串連成一個整體,並解說其中的意義,包括文明之間的學習與衝突,以及全體文明對世界歷史的貢獻。」──美歷史學家 喬弗瑞‧布魯恩 Geoffrey Bruun
「一部完整的世界史結合了清晰的地圖、插圖和實用的書目指引。」──美國西喬治亞州立大學教授 阿朗‧麥康瑞Aran S. MacKinnon
「麥克尼爾的研究是一部真正的世界史,整合了傳統的西方文明和世界其他豐富的文明。」──美國格魯學院教授 詹姆斯‧布朗James A. Brow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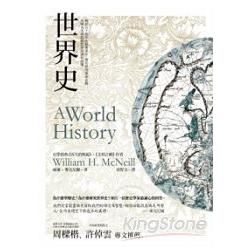
 2016/01/27
2016/0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