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推薦
寶萊塢亮麗下的殘酷現實
電影《貧民百萬富翁》開頭前十分鐘,一個跟隨孩子從孟買機場奔跑到貧民窟的鏡頭,帶出了這新崛起經濟體的城市風景——孟買國際機場是連結西方世界最大的門戶,但鄰近它的卻是最大規模的貧民窟,當飛機俯降孟買時,旅客們所看到的大片大片印度政府頭痛的「不體面」,這種不體面,對任何一個有野心的政府或發展者來說,都是必要剷除的。但對當地居民來說,他門的需求想望總是被忽略的。
而對大部分印度人來說,孟買這個第二大城,難道不該像「上海」?畢竟,它現在已是經濟大城,更因寶萊塢聞名。
孟買發展的速度很快,《貧民百萬富翁》中的主角就歷經了它飛速發展。主角傑默的哥哥薩林站在一個正在興建的大樓上,對這失散多年的弟弟說:「你看,那裡本來是貧民窟,現在都是高樓。」
如此的孟買,正是印度作家亞拉文.雅迪嘉(Aravind Adiga)第二部小說作品《塔裡的男人》的背景。故事中的大建商沙赫說:「這個城市有一條黃金線,一條讓人發財的線。」在他的構想中,聖塔克魯茲機場、班卓科勒金融中心和達拉維貧民窟連成一個黃金線,為什麼是黃金線?「航空業正在蓬勃發展,飛機多了,遊客也多了……班卓科勒金融中心無時無刻不在擴張。接著,政府開始在達拉維進行都市更新,亞洲最大的貧民區將變成亞洲最富有的貧民區。這個地方錢潮滾滾,每天都有人來……。」
不過,在這個建商大肆收購土地建造大樓、大部分居民也屈從這樣的發展主義的故事中,被收顧的土地住宅非真正貧民窟,而是鄰近於此的中產階級社區。和貧民一無所有不同,中產階級擁有一些資本卻也並非那麼多,有人脈但無法為所欲為,有知識不見得能夠拿來當武器;也和貧民毫無選擇不同,中產階級面對的通常是很多選擇、不同級數的選擇。他們生活算好,但渴望「更好」,他們可以在金錢和原則中做選擇,他們也可以在抵抗和順從中選擇。
於是,難免有人不願放棄自己的生活記憶和歸屬感,挺身當了「釘子戶」,但在官商勾結和人民貪婪自利、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冷漠下,故事結局未必如歷史演義或童話故事般完美。
亞拉文.雅迪嘉並沒讓故事人物扁平、二分化,他筆下每個角色都富有血肉,有其卑鄙也有其可憐,有其惡念也有其善良,那是一個人想要活成個人的掙扎體現,所以協助貧民戶的左派居民翻臉之快卻讓人不訝異,所以故事中最強勢的同意戶再不擇手段,但念著她對流浪狗的悲憫和對唐氏症兒子的愛,也不忍苛責。就連一般通俗故事中最擅長小奸小惡的那種角色,在亞拉文.雅迪嘉設計中,卻是撤腿最快、最是反省的人;最庸常無害的,反而可能是面不改色為惡者。
故事中那位堅持到底的「釘子戶」,是一位教師。原先為了挺老朋友而加入反對陣營,但最後只剩他一人,為的只是對抗「這種風氣」——在精打細算的世界裡見縫插針的風氣。
亞拉文.雅迪嘉成長於門格洛爾(Mangalore),中學時移民澳洲雪梨,求學期間深受英語文學經典影響,也期待自己像福婁拜、狄更斯或巴爾札克等作家一樣,透過文學去揭櫫當代社會的不公不義,「這不是要對抗自己的國家,而是一種巨大的自我檢驗過程。」而記者的資歷,更幫助他在虛構小說中,構築大量非虛構的骨架——他的印度沒有綺麗的異國風情,而是真實露骨的印度當代社會,並且能和世界各國的當下對話。
例如建商沙赫收購土地支持的建案名稱,就叫「上海」。沙赫在收購土地過程中,不停提到中國:「那些中國人有全世界最堅強的意志,而在這裡,自從獨立之後,我們的意志力連十分鐘都撐不到。」每當遇到挫折,沙赫便稱,在中國這些都不會發生,只要政府財團要幹嘛,一定都做得到。
有趣的是,亞拉文.雅迪嘉在前作《白老虎》中,也是以給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信為架構,並在文中屢屢暗示中國儘管經濟再好,擁有強權,但這個國家無自由民主無人權,印度再不堪再比不上,至少有個虛假的民主制度。這位深受西方影響的印度裔作家,恐怕是對這兩個名列金磚四國的兩大亞洲文明古國,有著同樣的期待,於是便給予同樣的毒辣批判吧。
阿潑(文字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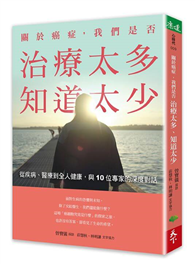







印度裔作者亞拉文.雅迪嘉曾經著有英國布克獎的《白老虎》(The White Tiger),本書是相當罕有的房地產相關的小說,繁中版一出爐自然吸引了我的目光。 故事是印度孟買有個地產大亨達哈曼.沙赫,他計畫收購一棟老舊破敗的住宅大樓,以利興建豪宅,他開出的價格足以讓大樓所有住戶一夕致富,只要全體住戶一致同意出售,然而住戶中有一個絕對不出售的住戶(用房地產業者的術語則是釘子戶),當然,結局留待有興趣拜讀的讀者自行去挖掘,我比較有興趣的是整個故事的過程和點點滴滴。 全世界由於資金氾濫,全球到處步入炒房、房價飆漲的夢靨當中,故事的背景孟買也不例外,特別是假借都更、老屋翻修甚至徵收圈地的名義,掠奪原來的弱勢屋主與農夫,而房地產價值飆漲的利益卻幾乎全數落入財團與開發商的口袋。 書寫的出發點極為正確,也探討了弱勢屋主在短期利益下所呈現的貪婪、開發商的心狠手辣、政客見縫插針的兩面手法、當然也見到了看透這一切、堅持不願出售的人的孤立無援。 但若就小說的閱讀,出場人物過多且略嫌扁平,許多故事的細節,除了讀起來相當陌生外,許多人物的互動、故事發展和內心感受略嫌瑣碎,讀習慣節奏明快的歐美日小說的讀者會感到一點點不耐煩,且印度的生活、制度乃至於宗教道德距離我們台灣過於遙遠,較難因為有切身感產生共鳴,善惡劃分過於二元,缺少了些想像空間也讓閱讀樂趣減損了一些。 書寫的出發點與立意相當正確且令人期待,但遙遠的印度對我而言有點距離感,我深深期盼台灣文壇有人願意書寫台灣的房地產相關小說,縮短這些距離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