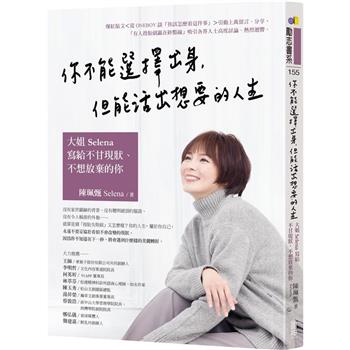追憶二十世代 經典人物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學博士 戴麗娟 推薦
在二十歲的時候,
在成為經典人物以前,
他們如何的思考、迷惘或造就一生的熱愛?
你會發現,那些以天賦為名的靈魂,
曾經也存在在你身上;
或者 現在 也正 依附 在 你身上!
「我粉身碎骨」,「但同時卻贏了」。
邪惡存在,但抵抗也存在。這件事情就像是預言未來般地,在這個正在脫離童稚的雨格諾派(huguenot)少年身上,揭示了一七五○至一七六○年間的那個叛逆的盧梭──此時,他還是尚沙克,正等待著覺醒。
一七三○年六月或七月,在洛桑(Lausanne)或在維威(Vevey)。在雷芒(Léman)湖——在這片水域的東岸,人們有時稱之為日內瓦(Genève)湖——湖畔,一個剛滿十九歲、愛夢想的青年走在順沿水岸的蜿蜒小徑上。途中,他停下腳步,坐在一塊「大石頭」上沈思,檢討自己目前的境遇。在他眼中,這種境遇頗難令人稱羨。他同時想像著自己未來的命運,希望那會是一片「無盡的純真喜悅」。湖面上的霧氣瀰漫,雷芒湖的柔和氛圍尤其適合感傷。三十年後,亦即在一七六五年,他在《懺悔錄》(Confessions)寫道:「在我眼中,日內瓦湖及其美妙水岸所構成的景象總是有一種特殊魅力。我無法解釋它〔…〕它不僅源自於景觀之美,並且來自於感動我、使我變得善感的一種無可比擬的趣味」。於是,這個年輕人感傷自憐;他有時會嘆息,或「像孩童般地」哭泣。「我為了這種愉悅且恬靜的生活而來到人世,但它卻離我遠去。每當渴求這種生活的熾烈慾望激發我的想像,浮現腦海中的景象總是鄰近此湖的沃(Vaud)邦地方之迷人鄉間。我絕對需要一片果園,就在這個湖邊,不是別的湖;我需要一個可靠的朋友、一個可愛的妻子、一頭乳牛、還有一艘小船。只有當我擁有這一切,我才能算是在這世界上享有美滿幸福。」他希望過著簡樸生活的夢想是否會實現?
這位青年就是尚沙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或更該說是舉世推崇(或厭惡)的那位公眾人物、小說家、教育家兼哲學家盧梭(1712-1778)之有潛力、不明確、默默無聞、似無指望、自我矛盾的雛形。在三十七歲之前,他未曾動筆寫過任何重要著作;他卻在晚年一面飽受攻訐,一面受到一群仰慕、虔信他的門徒熱情擁護。這種情形甚至在他死後仍持續了一段時日。仰慕,例如一位寫信給他的年輕牧師。為了幫他對抗正困擾著他的悲觀傾向,這位牧師寫道:「不,偉大的盧梭,您絕非無益於這個世界;有一些凡夫俗子一直盯著正在穿越沙漠 的您,您的奮鬥姿態鼓舞著他們。」虔信,一如出身阿哈斯(Arras)的律師馬西米連‧羅伯斯比(Maximilien Robespierre)。一七八九年四月,他被阿圖瓦(Artois)省公民選派,準備出席由法國國王下令召開之三級會議(états généraux)。幾個月後,在未考慮到是否公諸於世的情況下,三十歲的他寫了給自己看的《獻給盧梭之英靈》(Dédicace aux mânes de Jean-Jeacques Rousseau):「神聖之人啊,你教會我瞭解自己:你很早就使我知道,要珍視自己本性的價值,並思考社會的重要原則。〔…〕我要追隨你那令人欽敬的足跡,即使我在死後完全被後世遺忘:在我們的面前,空前的革命剛打開一條道路;但願我在這條艱難的道路上,能始終忠於我在你的著作中得到的啟迪。」
除非完全自溺於脫離現實世界的夢想中,否則,若我們跟盧梭一樣,不催促自己,那麼,二十歲並非人生最好的時光,甚至三十歲也不是。對於在一七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生於日內瓦的尚沙克而言,二、三十歲是一段流浪的生涯,是悲傷、徬徨、混亂的歲月,同時也是體驗、發現、吸收豐富知識、歡樂的時候。在二十歲或三十歲時,他如何自問這個問題:「我如何變成現在的我?」
關於自我的疑問無窮無盡。對此,尚沙克早先那段一波三折的經歷僅能提供部份解答,但它不該被忽視,如果我們想瞭解尚沙克如何成為盧梭的原模。
盧梭的作品對改造歷史有所貢獻,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都可以找到一些瓊.雅克.盧梭的影子:對自由的愛,那是我們每一個獨立的個體在社會生活中的選擇,對平等和公平的熱情,想要瞭解自己是誰的慾望。
這是一本豐富、精采的書,敘述對一切感到好奇和有趣的年輕「瓊‧雅克」,如何變成光明時代最有名、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和作家「盧梭」。追隨著這位年輕男人兼具情感、音樂、哲學和科學的人生過程,從日內瓦到里昂和巴黎,沿途經過亞納西、都靈、尚貝里、瑞士和法國西部。就是在經過這些土地的旅程中,讓這位「日內瓦的平凡市民」變成了世界思想家和民主評論家。這本書詳細貼近地追尋盧梭三十年的啟蒙軌跡,背景是十八世紀和法國大革命,過程充滿了曲折、豐富的情感和發現。
透過這本書,我們可以知道這些偉大作家的年輕時代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以及他們年輕時候的模樣。每一個年輕人,在二十歲的時候,都會自問自己想變成什麼樣的人,自己有什麼樣的天賦或特殊才能。這套書所描寫的都是改變時代的作家,每一個不同時代的作家都面對著不同的時代問題,每一個人在二十歲時的獨特和不平凡造就了後來的經典人物,也因此改變了世界觀。這套書的文字都很容易閱讀,但又不至於落入教條式的平鋪直敘,也有別於一般的自傳。我們可以在這些書中明顯地讀到一個思想是如何發展而成的,它通常是由實際的親身經驗而來,而不是來自書中的文字。
這套書的內容都具有一定的真實性,但是有時候也會出現因為欠缺部份資料,導致作家必須自己延伸事實的情況,一種方法是創造事實的場景故事,另一種是化身和假設,但是這兩種都有很確定的證據作為依據,所以也不能算是杜撰。不同的作者讓他們所寫得書具有不同的魅力,雖然都是描寫偉大作家年輕時代的書籍,卻不會讓人覺得每一本都一樣,讀起來不會覺得枯燥。每一本書都是一趟充滿學習的旅行,帶領我們穿越時空回到某一個時代,並且和這些偉大作家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