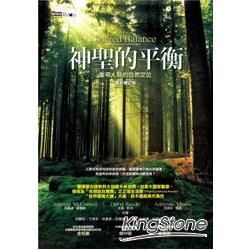修訂版前言 Introduction to the revised edition
十年前出版本書時,我企圖要說服世人承認人類需求的真正底線。那年是一九八八年,當時世界各地都認知到他們最關切的是環境問題。因應這股關切環境的趨勢,喬治‧布希(George H.W. Bush)在參選美國總統時曾經允諾,一旦獲選,要當一位「環保總統」。無奈在他上任後,他的施政表現旋即讓人明白,競選承諾不過只是造勢伎倆而已。
同年,英國首相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在電視上公開宣布她是一位綠色份子,而新上任的加拿大總理布萊恩‧馬爾羅尼(Brian Mulroney)則任命他團隊中最耀眼的政治人才呂西安‧布夏赫(Lucien Bouchard)擔任環境部長,以展現他關注環境的決心。當時我正在為加拿大國家廣播電台籌備拍攝「攸關生存」(It's a Matter of Survival)一共五集的系列節目,在布夏赫上任不久後,我便前去採訪他。當我問到目前加拿大面臨的最重大環境問題是什麼時,他馬上答道:「全球暖化」。
「有多嚴重呢?」我問。
「這威脅到我們人類的生存,」他答道,並且呼籲要嚴正看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
同樣也是在一九八八年,加拿大總理馬爾羅尼邀請備受推崇的政治家史帝芬‧路易斯(Stephen Lewis)擔任一場在多倫多舉辦的大氣層研討會的會議主席。當時,氣候學家對全球暖化的態勢感到驚慌不已,研討會結束後,他們發布了一份新聞稿,宣布全球暖化對人類生存的威脅「僅次於核子戰爭」,並呼籲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希望在十五年內將排放量降低到一九八八年的八成。
這件事當時深受大眾矚目,環境部長宣布全球暖化危及到人類生存,科學家則呼籲世人採取行動,設定出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若是我們認真看待這些警告,並立即採取相對應的行動,現在的排放量勢必遠低於後來京都議定書所設定的目標(在二○一二年時,達到低於一九九○年排放量的五~六個百分點),氣候變遷的問題也不會變得那麼棘手和複雜。偏偏當時我們就是沒把這些警告當一回事。
不久之後,看守世界研究中心(Worldwatch Institute)將一九九○年代定為「轉捩的十年」(Turnaround Decade),表示在這十年間,人類必須從自我毀滅的方向,轉往一條可永續發展的道路。儘管如此,環境議題卻逐漸在民意調查中消失。媒體的注意力轉移到從兩千點暴漲到一萬點的道瓊指數、網際網路公司股價泡沫化(dot-com bubble)、多家企業的財務醜聞,比如安隆(Enro)、世界通訊(WorldCom)和泰科(Tyco)等,以及千禧蟲(Y2K)的危機。
時至今日,轉眼過了將近二十年,世人再度關注起環境問題。多年來,我一直說想要搭巴士橫越加拿大,與大眾對話,這是我從二十世紀初期美國著名的肖托誇集會(Chautauqua Forum) 中得到的靈感。到二〇〇六年時,大衛‧鈴木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告訴我,根據民調顯示,環境議題在加拿大公民關注的各項議題中已經上升到第二位,僅次於衛生保健。遭受卡翠娜颶風侵襲的美國以及飽受長期乾旱之苦的澳洲,其民眾也日漸意識到氣候的變遷,並開始關注此議題。在我看來,健康和環境這兩者密不可分,要是我們所居住的星球不健康,又怎麼可能享有健康的生活。所以我們的團隊決定開著巴士穿梭加拿大各地,分享我們的想法,聽取公眾的意見,也針對「若你是現任總理,會為環境做些什麼?」這個問題,徵詢民眾的看法。
多年來,媒體持續報導超級風暴、野火肆虐、洪水成災,以及松甲蟲疫情等消息,這些事件不僅與氣候學家的預測相符,也提高了公眾的警覺,意識到應當有什麼地方出錯了。美國前副總統艾爾‧高爾(Al Gore)製作的電影「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就像一顆投入飽和溶液中的種晶,沉澱出世人對全球暖化的關注與公眾意識。
二○○七年二月,我從紐芬蘭的聖約翰展開我的巴士之旅時,氣候和環境已急速上升為加拿大公民最為關注的首要議題。澳洲總理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被迫承認氣候變遷的事實,而在美國,加州州長阿諾史瓦辛格因大力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意外成了環保運動宣傳海報上的寵兒。當我在二月二十八日到達卑詩省的維多利亞,並於兩天後飛往渥太華時,已經和三萬多人談過話,其中有六百多人同意我們進行拍攝,影片中他們都針對「若你身為總理,會為環境做些什麼?」這個問題發表了意見。種種跡象都顯示大眾想要針對重大環境問題採取行動,並且願意為一個更安全的未來做出必要的犧牲。
根據各項累積至今的證據顯示,氣候變遷涵蓋的規模極大。然而,由於我們過去沒有設定排放上限,並積極展開減碳行動,導致現在的減碳挑戰和一、二十年前相比,變得更加艱鉅和昂貴。儘管證據明確,反對大幅減少排放量的聲浪依舊存在,主要是由於反對者認為這些行動的成本過高,會因此減少就業機會並造成經濟崩壞。此刻,我們比以往更需要一個共同的真正底線,本書的首要目標便是推動這項共識的達成。
本書初版發行後的十年間,科學上又有許多新的發現能夠強化並擴大我們原先的基本前提,比方說操作和定序DNA的新技術揭露出人類的起源和遷徙至世界各地的路徑。本書將討論這些重要的新發現,以及許多其他關於大腦發育和可塑性的研究,同時也會介紹荷爾蒙在形塑我們的成長過程中,所扮演的精細角色。此外,我們也將探討諸多社會變遷的現象,像是日益強勢的消費主義、都會化以及過度保護孩童,使得他們探索自然的時間遠低於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這些改變不但對環境造成影響,同時也會影響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另外,本書還加入許多關於大氣和氣候變遷的新資訊。我們將踏上一段時空旅程,回溯到生命的最初,探究藍綠藻這種微小的微生物在發展出捕獲太陽能的特徵時,是如何改造了我們這顆星球。長時間下來,大氣層不斷改變,最後維持在能夠滋養萬物的富氧條件;如今,我們的大氣再度開始轉變。科學家發現,大氣中的污染物可以「跳」到距污染源數千哩外的區域。新的數據明確顯示出,亞馬遜雨林的任何動靜都會影響到世界各地的氣候和天氣模式。當然,目前最迫切的環境問題還是因人類活動而日益增加的溫室氣體濃度。
本書的修訂版更新了大部分的內容,比方說增加了人類基因組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的進展、加拿大伊利湖區和鹹海的現狀,以及地球生物多樣性的最新數據。從南北極、海洋,甚至是地殼中的生命調查中,可以看出人類對地球的生命多樣性所知甚少。研究者幾乎每個星期都會發現新物種,在某些區域的生命形式與交互作用豐富而多變,幾乎到了讓人嘆為觀止的地步,光是一大把青苔,就可以孕育出二十八萬個體。在進行生物研究時,我們所探索到的複雜連繫,完全超乎幾十年前的想像――不論是鮭魚和樹木之間的關係、森林大火和茂盛森林的關連,還是黏土和生命本身的連結。
最有趣的科學新知要屬「愛」的化學。在愛與被愛時,身體會經歷諸多化學變化。目前已有大量證據顯示,人類和動物在缺少情感滋養與觸摸的環境下,無法順利成長茁壯。類似的新研究也顯示人類可能天生就想要尋求精神信仰,而且與生俱來地傾向相信身體和靈魂之間是有區別的。
本書初版至今,唯一不曾改變的是:我們依然主張人類可以不破壞維繫生命所需的基本要素,過著豐富有益的生活。
從我一九六○年代投身環境保育運動以來,區域性皆伐、興建大壩與化學污染等問題一直是爭論不休的重要議題,各種分歧的意見總是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每個陣營都妖魔化了對手,因此不管結果如何,總是會有落敗的一方。在每次的衝突中,敵對的雙方各自擁護截然不同的信仰和價值觀。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被迫在斑點貓頭鷹和伐木工人、工作和公園、該保護環境還是拼經濟之間做出選擇。但是,倘若我們真的想為我們的子孫盡一份力,為他們保存一個美好未來,我們誰也輸不起。
在這些衝突中,我也試圖取得折衷:那些我所反對的人其實也是為人父母,擔心後代子孫的未來,也和我一樣,對自己抱持的立場深信不疑。有一次,我們為「萬物之道」(The Nature of Things)製作一集特別節目,那集的主題是「森林裡的聲音」(Voices in the Forest),並計畫拍攝一群溫哥華島的伐木工人。當我和劇組人員開始拍攝時,這群工人對環保人士大肆批評,指控他們搶走了工作。最後,我告訴他們,在我認識的環保人士中,沒有一個是反對伐林的,我們只想確保他們的子孫依然能靠伐木為生,而森林仍如今日一樣豐茂。
此時,有位男士打斷我的話,他說:「我根本不可能指望我的孩子將來長大後當伐木工人,那時樹早就被砍光了,一棵都不會剩下來!」那一刻,我感到十分震驚,並且意識到我們根本是在爭論不同的事情。伐木業者知道他們的伐木行為並不永續,但他們必須要先考量生活中更迫切的問題,應付各類帳單、房貸和車貸,而環保人士則在談論如何維持森林的完整性和生產力。在那個當下,我才明白,我們必須找到共同點和共通的語言,不能再繼續這樣毫無交集的爭論,任地球一點一滴地碎裂。加拿大在氣候變遷上的爭論正是說明這個現象最好的例子。環保人士和反對黨要求延續二○○二年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總理核准的京都議定書相關規定,然而到二○○七年時,聯邦政府的環境部長卻認為這樣草率定下的目標成本過高,加拿大的經濟根本無法負擔。事實上,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決議出一個每個人都能夠支持的「底線」。
環境對人類的存續至關重要,理當超越政治黨派,成為社會整體的核心價值。在此,容我以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我的意思。在一九四○年代初期,當我還是個孩子時,隨處可見禁止隨地吐痰的告示牌,否則人們會在樓房與電車地板上吐痰。換做今天,如果我們看到有人隨地吐痰,應該會當場吃驚得目瞪口呆,儘管現在已經沒有告示或標語提醒我們不要這樣做。這是因為在我們的社會中,大家都明白不該這樣做,不在公共場合隨地吐痰是約定俗成的基本道理,是理所當然的禮儀。我們與自然世界之間的關係也該如此,這麼一來,我們無須再告訴世人什麼是該做的,什麼又是不該做的。因為大家都明白,身為生態界的一員,我們的生存取決於自然以及它所提供的資源。也因此,政治人物左傾或是右傾的意向再也不是重點,因為作為社會的一員,他們也得接受共同的基本前提。
一九七○年代末期,我開始接觸原住民,也因此讓我萌生寫這本書的念頭。在他們身上,我發現另一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原住民認為,他們的存在不僅局限於人類的血肉之軀;對他們來說,大地就是他們的母親,他們的歷史、文化和生命的目的都體現在大地之中。原住民這種萬物相連的獨特世界觀其實也可以輕易地以無可辯駁的科學來證明。
本書以科學依據為核心,說明我們每個人都是源自於空氣、水、土壤和陽光這四個生命基本要素,並透過這顆星球上的生命網絡來進行潔淨和更新。此外,身為同時兼有社會性和精神性的生物,如果我們想擁有豐盈富足的人生,便需要愛與靈性。在《神聖的平衡》這本書中,我將介紹並講述這些人類藉以建構永續生活和社會的基石。
未來的歷史學家肯定會將二十世紀視為一段史無前例的時期,不論是人口的暴增、科技的鋪天蓋地、經濟成長,還是工業生產力都出現前所未有的變化,危及到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爆炸性增長的人口使得人類成為地球上數量最多的哺乳動物,日新月異的科技則讓我們得以大幅開採並利用各項地球資源,像是林木、魚類、礦物和糧食等。全球經濟剝削了整個地球的原物料,提供這個世界源源不絕的消費性產品。這些因素加總起來,深化了人類的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 ,而這些留在地球上的印記已超出這顆星球自我淨化與回復的能力。現在,我們首要的工作便是檢視人類根本的需求,再據此重塑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發展。
在二○○七年,有許多「綠色」團體和活動都冠上了「生態」這個字眼,環保人士自稱為生態鬥士,還冒出諸如生態林業、生態旅遊、生態心理學等眾多名詞。在英文中,「生態」(eco)一詞源自於希臘文oikos,意思是「家」;生態學(ecology)便是家的研究,而經濟學(economics)則是家的管理。生態學家試圖界定出左右生命興盛的條件和原則,使其不受時空或任何變異的影響。無論是社會整體或是我們的各項建設發展,像是經濟發展,都必須符合這些生態學所定義的基本要求。我們當前所面臨的挑戰便是重新把「生態」再放回經濟和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裡。
大衛‧鈴木,二○○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