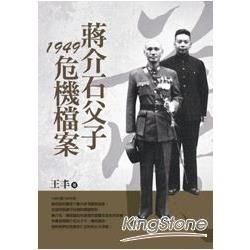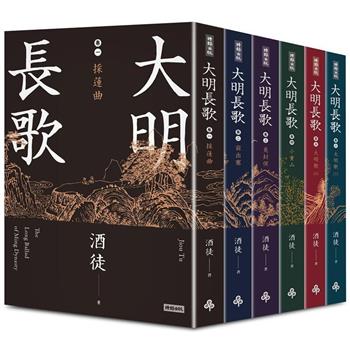1945到1949年,國民政府歷經了最大的考驗與挫敗。
從接收到退守台灣的關鍵時刻,蔣介石、蔣經國如何處理四面圍攻而來的危機?本書呈現蔣介石父子不一樣的面向,深入他們在危急存亡之秋的父子深情。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那時的中華民國雖然算是「戰勝國」,但長期的戰爭讓國家百廢待舉,讓共產黨有機可乘,不僅國共內戰蜂起,國民黨內派系之爭也沒少過。就在國共內戰、國軍在各個戰場接連失利,惡性通貨膨脹及金融亂局危如累卵之際,身為國民政府領導人的蔣介石,他要如何因應?為什麼最後他決定以台灣做為父隅頑抗的「復興基地」?
本書呈現1945到1949年,蔣介石處理政治危機的過程,從安排兒子蔣經國當接班人,讓蔣經國歷經政治的試煉,並處理金融亂局、上海打老虎,最後,終於還是在1949年,帶著故宮國寶與黃金等,全面播遷來台的故事。
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家書與函電全披露
國府高官與兩蔣父子函電大公開
蔣介石尋找接班人的心思之剖析
蔣經國從蘇聯、贛南到台灣經驗的轉折
國民黨情報系統的大改造
馳名中外的「金圓券政策」拖垮國府的內幕
蔣經國「上海打老虎」引起的家族風暴
國庫黃金、故宮國寶搶運台灣的現況重現
國府遷台,蔣介石頻頻召喚的杜月笙就是不來台灣……
|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蔣介石父子1949危機檔案(改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蔣介石父子1949危機檔案(改版)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王丰
自由工作者、傳記作家、電視歷史話題及時事評論員。
從事傳媒工作三十多年,歷任台灣多家報社採訪記者;時報周刊採訪記者、採訪主任、執行副總編輯;商業周刊、TVBS周刊、新新聞周報等雜誌總編輯。曾任大學大眾傳播系、新聞系兼任講師。
【著作】
我在蔣介石身邊的日子
宋美齡的美麗與哀愁
蔣家恩仇錄
蔣經國愛情檔案
蔣介石健康長壽一百招
蔣介石死亡之迷
相關著作
《蔣介石父子1949危機檔案》
王丰
自由工作者、傳記作家、電視歷史話題及時事評論員。
從事傳媒工作三十多年,歷任台灣多家報社採訪記者;時報周刊採訪記者、採訪主任、執行副總編輯;商業周刊、TVBS周刊、新新聞周報等雜誌總編輯。曾任大學大眾傳播系、新聞系兼任講師。
【著作】
我在蔣介石身邊的日子
宋美齡的美麗與哀愁
蔣家恩仇錄
蔣經國愛情檔案
蔣介石健康長壽一百招
蔣介石死亡之迷
相關著作
《蔣介石父子1949危機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