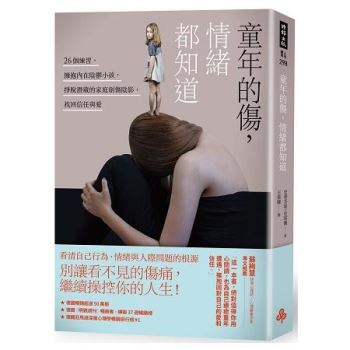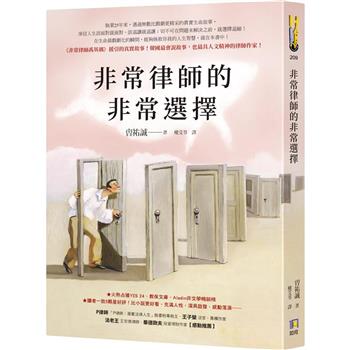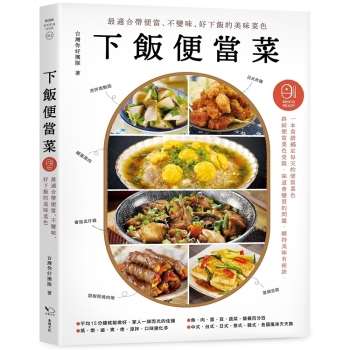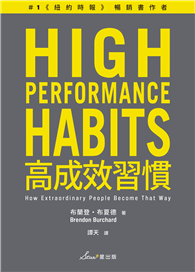◎ 兩屆雨果獎得主
◎ 星雲賞、軌跡獎、世界奇幻獎、史鐸克獎、世界恐怖作家協會獎等諸多大獎得主
◎ 作品全球銷售超過千萬冊,翻譯成30種語言
八千五百公尺高峰上,如影隨形的不只是死亡……
一九二四年,英國登山隊的喬治.馬洛里和安德魯.歐文嘗試從北坡登上聖母峰,最終一去不返。兩人是否成功登頂的爭議,成為人類登山史上非常知名的「馬歐之謎」。
一九二五年,馬洛里失事未拍板定案,各國登山界挑戰世界最高峰的競賽在失事的恐懼中暫時畫下休止符。三位充滿熱情的登山家——英國詩人兼大戰軍官、法國高山嚮導和滿腦子理想主義的美國年輕人——無法抗拒聖母峰的獨特魅力,決定一試身手。他們找上哀傷的布羅姆利夫人籌措資金。布羅姆利夫人的兒子波希一九二四年在聖母峰失蹤。夫人拒絕相信波希已經喪生,於是花錢雇請三位登山好手去找尋兒子的下落。
深入高山後,他們發現呼嘯狂風中似乎隱藏了一個超自然的恐怖力量,三人成為那人──或那物種──追獵的目標,生死一線間的噩夢在海拔八千五百公尺的高山上演。追逐他們的是什麼?一九二四年聖母峰失蹤事件是不是有另一個真相?被追獵的倖存者無路可退,只能朝「死亡地帶」逃命……
作者簡介:
丹.西蒙斯(Dan Simmons)
一九四八年出生於美國伊利諾州。長篇小說處女作《迦梨之歌》一舉為他拿下一九八六年的「世界奇幻獎」、《腐肉解饑》接連摘下恐怖類型最高榮譽「布蘭姆.史托克獎」、《軌跡》雜誌讀者票選獎恐怖小說類,以及「英倫奇幻獎」的桂冠。《海柏利昂》及《海柏利昂的殞落》雙料榮獲「雨果獎」。《極地惡靈》獲選為亞馬遜 2007 年度最佳科幻/奇幻小說。另著有《閃憶殺手》。
相關著作
《極地惡靈(全新書衣版)》
《閃憶殺手(改版)》
譯者簡介:
陳錦慧
加拿大Simon Fraser University碩士,曾任媒體記者十餘年,現為自由譯者。近期譯作:《塔裡的男人》、《簡愛》(新譯本)、《生死魔幻》、《雪中第六感》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我對丹.西蒙斯敬畏三分。──史蒂芬.金
丹.西蒙斯實在厲害。──科幻小說大師丁昆士
沒有人寫得比西蒙斯好。——聖路易郵報
西蒙斯是位大師。——奧斯丁政治論壇報
西蒙斯創造複雜角色並將他們羅織入緊張懸疑氛圍的能力,當今作家群中幾乎無人能望其項背。——出版人周刊
西蒙斯是卓越的小說家,尤其擅長鋪陳電影般的緊湊節奏。──美國公共廣播電台
西蒙斯是當代最富想像力的小說家。──聖安東尼奧快報
現代作家中沒有人能像西蒙斯一樣從容轉換於不同文體之間。更甚者,他在各種類型的創作都表現非凡,每次發表的新作功力都更深厚、更鞭辟入裡。──圖書報告網
西蒙斯擅長操縱百轉千折、撲朔迷離的情節……善於塑造龐大且複雜的架構。──洛杉磯時報
讀來興味盎然……西蒙斯筆下功夫出神入化。──華盛頓郵報
西蒙斯的想像力似乎無遠弗屆。──書單雜誌
西蒙斯是出類拔萃的文學萬事通,總是帶給讀書驚喜與愉悅。──舊金山紀事報
我願意追隨西蒙斯到天涯海角。我很幸運,因為他確實會帶我們到天涯海角……他太神奇了。──芝加哥論壇報
名人推薦:我對丹.西蒙斯敬畏三分。──史蒂芬.金
丹.西蒙斯實在厲害。──科幻小說大師丁昆士
沒有人寫得比西蒙斯好。——聖路易郵報
西蒙斯是位大師。——奧斯丁政治論壇報
西蒙斯創造複雜角色並將他們羅織入緊張懸疑氛圍的能力,當今作家群中幾乎無人能望其項背。——出版人周刊
西蒙斯是卓越的小說家,尤其擅長鋪陳電影般的緊湊節奏。──美國公共廣播電台
西蒙斯是當代最富想像力的小說家。──聖安東尼奧快報
現代作家中沒有人能像西蒙斯一樣從容轉換於不同文體之間。更甚者,他在各種類型的創作都表現非凡,每次發表的新...
章節試閱
下午我們沒花時間埋葬馬洛里,我很過意不去。風每小時都在增強。整個早上都盤旋在聖母峰峰頂上空那一團凸透鏡般的雲層,天黑以後來到我們頭頂上,降下紛飛大雪。如果我們繼續留馬洛里陳屍的北壁,就得多花一、兩個小時砍鑿冰凍的岩石,才能找到足夠的石頭來覆蓋他的遺體。但暴風雪節節進逼,即使只鋪上薄薄一層石堆,都超出我們體力與時間所能允許。我們仔細檢視了馬洛里的遺物,記住他墜落的位置與線索,做了記錄,記下附近的地標,方便我們在必要時能找到他的葬身地點。
大狄肯要我們動身,由西向東橫渡回第五營。我提出反對意見,我說,雖然天快黑了,風也在增強,我們還是應該妥善安葬馬洛里。回應我的是小瑞,她說,「雅各,他已經在風雪、陽光、星星和月亮底下躺了快一年了,多躺一夜沒什麼差別。我們明天再回來埋葬他。」
結果我們當然沒有回去。
我到現在仍然覺得過意不去。
我們雖然沒有時間挖掘冰凍的石頭來掩埋馬洛里,卻還是在酷寒中花了一小時圍在他屍體旁。我們在他衣服上找到了印有「G.馬洛里」的名牌,但大狄肯仍然希望能進一步確認他的身分。於是我們三個人一度用小刀挖開屍體左側結凍的砂礫,直到我們可以稍稍將他撬高,看清他的正面和臉孔。
那個過程就跟開挖漫長的嚴冬裡冰凍在泥土裡的木頭沒兩樣。
他毛料外套口袋裡有個高度計,跟我們的很類似,特別校準過,最高可以測到海拔九千公尺,可惜表面的水晶玻璃在下墜過程中撞破,指針也不見了。
「真可惜,」小瑞說。「我們永遠沒辦法知道他跟歐文是不是成功攻頂了。」
「他們應該帶了幾部相機。」大狄肯說,「諾頓告訴過我,馬洛里帶著一部柯達摺疊式袖珍相機。」
我們把馬洛里的隨身包拉到我們摸得到的地方時,我只戴內層手套,摸到裡面有某種堅硬的金屬物品。「我想我們找到相機了。」我大聲宣布。
結果不是。那一團硬東西是一大盒Swan Vesta火柴和一個肉餅罐頭,我們一一放回原位。我們在馬洛里口袋裡找到的其他物品是五花八門的個人用品,包括一截鉛筆、一把剪刀、一根別針、一個收納剪刀的金屬套子,還有一段可拆卸的皮革繫帶,用來連接他的氧氣面罩和皮革安全帽,馬洛里彷彿只是冬天裡出門到海德公園散散步。
手帕裡包著一些文件。裡面多半是一些私人信函,除了一封由某位女性給他的信件空白處用鉛筆註記了一串奇怪的數字。
「那是氧氣壓力讀數。」尚克勞德說。「也許是記錄他們最後那天剩餘的氧氣還能攀登多高。」
「這裡只有五個數字。」小瑞說,「他們從第四營出發時帶的氧氣好像不只五瓶。」
「確實不只。」大狄肯說。
「那麼這些東西都沒辦法說明什麼。」小瑞說。
雖然我們什麼都沒拿走,我還是覺得自己像在盜墓。我從來沒有翻找過死人口袋。大狄肯做得好像挺習慣的,之後我才想到,他當然很習慣,可能在西方戰線做過幾百次了。
其他的口袋裡我們只找到馬洛里的摺疊小刀和護目鏡。
「他的護目鏡放在口袋裡。」小瑞說,「這可能是重要線索。」
一開始我不太明白,因為我忙著咳嗽,但尚克勞德說,「嗯。他們墜崖時不是薄暮就是天黑以後……馬洛里是在目睹諾頓雪盲的隔天上攀攻頂,幾乎可以確定他會等到太陽下山才脫下護目鏡。」
「但他們究竟是上攀或下攀途中失足?」帕桑說。
「我猜是下攀。」大狄肯說。
「他們有沒有帶手電筒?」小瑞問。
「沒有。」大狄肯說。「歐岱爾在第六營帳篷找到手電筒,帶下山了。他們忘了帶唯一一把手電筒,足以說明他們是日出以後才從第六營出發,同時也說明馬洛里有多健忘。」
「我們別說死者的壞話。」我邊咳邊說。
「這不是壞話。」大狄肯說,「只是實話。馬洛里跟我一起參加前兩次遠征時,經常丟三落四,襪子啦、刮鬍用具啦、帽子啦、衛生紙啦。他個性就是這樣。」
「可是……」我想爭辯,卻無話可說。
「馬洛里屍體很完整,加上他設法自我制動,停止滑動後也還有意識,如此看來,他並不是從那麼高的東北脊摔下來的。」大狄肯確認了我早先的推測。「幾乎也可以確定不是從黃礫石帶的位置墜落。比較可能的是,他從更下面、離我們比較近的小峽谷或小一點的礫石帶摔下來。」
「所以金髮歐文可能還在上面等著我們?」小瑞說。
大狄肯聳聳肩。「或者是金髮歐文先摔倒,把馬洛里拉下山。除非我們找到歐文的屍體,否則永遠不會知道答案。」
「所以我們在馬洛里身上找到的東西都沒辦法說明他跟歐文是不是已經攻頂了。」小瑞說。「馬洛里的錶和高度計都壞了,連指針都沒了。」
「也許我們沒找到的東西提供了最佳線索。」大狄肯說。
我從骯髒的羽絨睡袋深處稍稍坐直一點。「柯達相機嗎?」
「不是。」大狄肯說,「是馬洛里妻子露絲的照片。諾頓和其他我問過的人都說,馬洛里在第四營出發時帶了他太太的照片,後來大家在第四營或兩個更高的營地都沒找到那張照片。他答應過露絲,會幫她把照片放在峰頂。」
「或留在他折返之前到達的最高位置,只有老天知道那是哪裡。」尚克勞德說。
大狄肯點點頭,咬著冷菸斗的柄。
「一張失蹤照片不能證明他到過峰頂。」小瑞說。
「的確不能。」大狄肯認同,「只能證明他把照片留在某個地方。也許如尚克勞德所說,留在他們折返之前的最高點……不管那是哪裡。」
「我對那台失蹤的相機很感興趣。」帕桑醫師說。他低沉的嗓音一如往常、溫和又從容。
「怎麼說?」我問。
「因為人什麼時候會把相機交給別人?」帕桑問。
「要別人幫你拍照的時候。」小瑞說,「所以馬洛里很可能在峰頂幫歐文拍過照片之後,把相機交給歐文。」
「純屬臆測。」大狄肯說。「目前有一件事可以確定:如果我們明天還想繼續搜索,現在最好睡個覺。」
「你說得倒容易。」我邊咳邊說,「我在這種他媽的高度根本睡不著。」
「雅各,別說髒話。」大狄肯說,「有女士在場。」
小瑞翻翻白眼。
「我帶了安眠藥,」帕桑說,「應該可以讓你睡個三到四小時。」
現場頓時鴉雀無聲。我想像大家腦子裡都浮現跟我一樣的想法,那麼我們就可以呼呼大睡,讓風把我們連人帶帳篷吹落懸崖。
我開口發表意見。小瑞卻舉起手,叫我別說話。「大家安靜。」她悄聲說,「我聽見聲音,有人在尖叫。」
我的手臂起滿雞皮疙瘩。
「在這麼大的風聲裡?」大狄肯說,「不可能。底下的第四營離我們太遠……」
「我也聽見了。」帕桑說,「有人在外面的黑夜裡尖叫。」
帕桑醫師確認他也聽到尖叫聲後的五分鐘內,我們三個人──大狄肯、帕桑和我──已經走出帳篷,站在漫天風雪中。
「你還聽得見嗎?」大狄肯大聲問帕桑。
「沒有,不過我看到東西。」帕桑說。他指向山下離我們約莫一百公尺、靠近我們原來的第五營兩頂帳篷的地方。
雪花在我礦工頭燈照出的圓錐形光束裡翻飛,所以我花了一秒才看見:一抹陰森森的紅光在底下那些大石頭後面閃呀閃地。
我們沒有浪費時間穿冰爪,三個人組成一個繩隊出發,由我先鋒,下攀這段陡峭的岩石斜坡。由於風勢極強,岩石表面的積雪不多,卻已經有相當厚的一層冰,讓岩面變得比平時滑。腳下只有平頭釘靴的感覺有點奇怪,我已經失去近日以來冰爪齒釘帶來的那份安全感。
不到十五分鐘我們就抵達第五營原址,有一頂帳篷被落石砸毀,另一頂也塌坍了。我們趕到的時候,紅光正好漸漸熄滅。顯然那並不是那種時間短暫的信號彈火光,而是我們帶來的那種手持式、時間較長久的鐵路信號彈,有紅、白兩種顏色。
距離信號彈約莫三公尺處,有個身穿登山隊羽絨外套的人仰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他躺的位置離那頂崩塌帳篷的開口處很近。
我們俯身向前查看,頭燈的光線在那人臉龐和圓睜的雙眼來回移動。
「是雪巴洛布尚,」大狄肯說。「他死了。」
星期一早晨我們在第六營碰面時,大狄肯說他前一天只帶了幾個雪巴到第五營,由洛布尚當領班。洛布尚個子矮小卻意志堅強,以不可思議的勤奮與超長的負重耐力,實至名歸地贏得代理領班的職位。此時他看起來的確是死了,嘴巴張開,瞳孔定住不動,也擴散了。
「今天這上面不准再有死人。」說著,帕桑卸下背包。我們三個人之中,只有他帶了背包。我從晃動的燈光和飛舞的雪花中看見他沉重的背包裡放著他的皮革醫療包。「裴瑞先生,」他說。「能不能請你拉開洛布尚的外套和上衣,露出他的胸口。」
我單膝跪在陡坡上,脫掉笨拙的外層併指手套,照帕桑的話做。但我不認為有什麼急救措施能在眼前這個看來已經死透了的人身上發揮作用。洛布尚的身體和臉頰已經鋪了薄薄一層被風吹來的冰晶粒。
帕桑取出一枝特大號注射筒,我從沒見過那麼大的注射筒。上面的針八成有十五公分長。那東西看起來更像是獸醫拿來用在牛隻身上的,完全無法想像可以施用於人體。
「抓住他手臂。」帕桑一面說,一面用手指在洛布尚袒露的褐色胸膛上摸索。洛布尚圓睜的雙眼仍然凝視著永恆。
為什麼要抓他手臂?記得當時我心想,這具死屍會跑掉嗎?
帕桑忙著數肋骨,尋找瘦巴巴的洛布尚皮膚底下的胸骨。之後,他用裸露的雙手把那根可笑的注射筒舉到洛布尚胸口上方七、八公分的地方,猛力戳進洛布尚胸口,穿透皮膚和胸骨,直達心臟。針尖穿過洛布尚的胸骨時,發出令人作嘔的「咔嗒」聲,即使信號彈還在嘶嘶響,風也在呼號,那聲音依然清晰可聞。帕桑壓下注射器的推桿。
洛布尚的身體向上拱起。如果不是我和大狄肯按住他,他這一彈就滾下山了。接著,他開始大口大口喘氣。
「老天!」大狄肯低聲驚呼。我有同感。這真是我所見過最誇張的醫療行為,在未來的六十多年也沒再見到過。
「腎上腺素直接打進心臟。」帕桑喘著氣說,「如果有什麼辦法能救他,就是這個了。」
帕桑把腳踩在洛布尚身旁,抽出洛布尚胸口那根針,就像士兵們都得學會、從敵人屍體上抽出刺刀的手法。洛布尚大口吸氣,眼睛眨巴個不停,掙扎著想坐起來。半晌之後,我跟帕桑一起扶洛布尚站起來。
神奇的是,洛布尚竟然稍微站得住腳。我跟大狄肯攙扶著又眨眼又喘氣的洛布尚,帕桑揹著背包緊隨在後,一行四人蹣跚地上攀、朝小瑞的大帳篷前進。如果說早先我們五個人擠在帳篷裡睡上一覺的機會已經渺茫,現在多了第六個人,根本別想睡。對於這第六個人死後復活這件事,我的心情真是很複雜。
洛布尚兩眼又瞪大。他用尼泊爾哇啦啦講了一串,看看四周,又十萬火急地用英語重述一遍。「你們一定要下山,你們現在馬上就要下去。雪人把基地營的人全殺死了!」
下午我們沒花時間埋葬馬洛里,我很過意不去。風每小時都在增強。整個早上都盤旋在聖母峰峰頂上空那一團凸透鏡般的雲層,天黑以後來到我們頭頂上,降下紛飛大雪。如果我們繼續留馬洛里陳屍的北壁,就得多花一、兩個小時砍鑿冰凍的岩石,才能找到足夠的石頭來覆蓋他的遺體。但暴風雪節節進逼,即使只鋪上薄薄一層石堆,都超出我們體力與時間所能允許。我們仔細檢視了馬洛里的遺物,記住他墜落的位置與線索,做了記錄,記下附近的地標,方便我們在必要時能找到他的葬身地點。
大狄肯要我們動身,由西向東橫渡回第五營。我提出反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