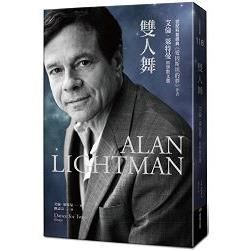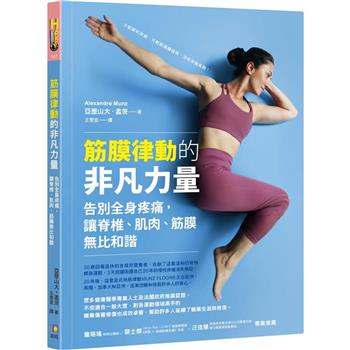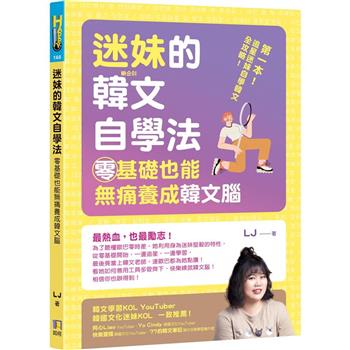推薦序
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但真正使「人之所以為人者」,孟子認為是性善與道德,生物學家則視基因組為演化的關鍵。儘管古往今來論述者眾,各執其理,但卻有一項人類特有的本質,成為劃分人與獸的分水嶺,那就是「對宇宙回應的能力」!這種回應不同於文字堆砌的華麗頌詞,亦非音符組成的娓娓樂音,無關乎複雜難解的方程式……而是懵懂孩童仰望繁星時,發自心靈的那一聲驚呼!人與宇宙間的命蒂臍連、對大自然的敬畏讚美,一切美感的起源、探索的萌生,都已不言而喻。
雖然這天賦的本質萬年未變,但隨著文化的進展,人類認識宇宙的方式多元化了。數百年來,以客觀判斷、理性思維與邏輯實證為主的自然科學,已經成為了解宇宙真理的主流。而以感性為出發點,透過情感、知覺等體認宇宙自然的美感經驗,則被歸類於藝術、哲學、宗教與文學所屬的人文領域。科學與人文在一般人心目中也儼然分流為兩種截然不同,甚至對立的思維模式。
不過「人」仍是所有學問與感知交集的主體,當回歸人的本位時,科學與人文其實都是認識宇宙的基礎,只是觀點與方法的不同而已。感知經驗所形成的直覺往往是理性思維的前導,而新思維的建立又會帶來迥然不同的全新感受。關於這樣的體認,當莊子在兩千多年前論及自然之美與天人合一時,便透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與「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加以闡明了。
許多學者對於科學與人文這兩種源本於一的文化,如今卻分道而馳發出了警示,認為這將戕害人類整體文化的發展。解決的關鍵在於培養人們透過科學體驗美感,以及從美感中看見科學的能力。這樣的引導工作需要具備扎實的科學素質與深厚的人文涵養,如沙根(Carl Sagan)、費曼(Richard Feynman)等科學家皆是代表性人物,而本書作者艾倫‧萊特曼(Alan Lightman)絕對亦是當代佼佼者之一。
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的萊特曼是位理論物理學家,也是著述廣博的文學家,同時開授科學與寫作兩種不同面向的課目。他的著作多達二十餘本,題材從專業的天文物理教材,如《天文物理中的輻射過程》(Radiative Processes in Astrophysics, 1979)到小說形式的《愛因斯坦的夢》(Einstein's Dreams, 1993)等,論理嚴謹而饒富趣味,述情生動卻不失縝密,篇篇值得深思回味。其中又以《雙人舞》(Dance for Two, 1996)這本散文集的風格最為獨樹一幟。雖然是由二十四篇完全獨立、主題各異的短文組成,寫作屬性也琳瑯滿目,從科幻、寓言、神話、紀實、傳記、哲理乃至愛情等等,但總能各以不同的角度,或由感性切入科學,或將物論揉合人性,讓整部文集宛如一幕幕精彩雋永的短片。
「欲罷不能」或「廢寢忘食」這樣的形容詞或許並不適用於《雙人舞》的閱讀經驗。事實上,我花了好幾個星期才讀完這本僅七萬餘字的散文集,足足用了閱讀類似篇幅書籍好幾倍的時間。這本書並非艱澀難懂,剛好相反,萊特曼的文字順暢優美,完全符合散文易讀的特性,他的思緒清晰,文字幽默充滿機敏。科學散文除了談人、述情外還兼得論理,在處理這最容易與讀者形成僵局的癥結上,萊特曼的妙筆不僅讓文章益發興味盎然迷人,而且更為讀者打開了無限的反思空間。於是,在閱讀過程中我不得不時時停下來感受、回想、探索、思考,甚至自我重整,才能心滿意足地理好心情與思緒,整備步上下一段不知通向宇宙何處的新篇章。另一個導致慢讀的原因是,這本書總會讓人情不自禁地一再回味先前讀過的篇章,不過有趣的是,即使單單改變閱讀的順序,竟也能體會到不同的韻味並帶來新的發現!這讓閱讀的樂趣與收穫都大大提昇。
〈雙人舞〉就從女芭蕾舞者多年苦練,在舞台上短短幾秒鐘的舞姿變換中揭開序幕。〈雙人舞〉是全書最短的一篇,萊特曼教授將牛頓定律、重力、庫倫力、轉動慣量、固態物理中的對稱,乃至原子的精細結構、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等,一一拉上舞台,融入了舞者的曼妙舞姿中,讓舞蹈之美、物理之美合而為一,將美感與科學並陳於讀者的視野與大腦中。接下來的〈笑顏〉再次透過極短篇,從男孩與女孩的湖畔邂逅切入,隨著女孩回眸一閃的唇影之光帶出了視網膜結構、視覺生理學、分子生物學。而女孩的一聲「哈囉!」,又把聲學、神經科學、心理學與認知科學融入了男女初識的浪漫情境。最後,男孩在注意力、意識、情感等決策判斷下,做出了反應動作:走向女孩。多麼浪漫而巧妙地結合了科學與感性啊!
但常把「科學」掛在嘴邊的我們,真的打從心裡崇尚科學嗎?萊特曼在〈地球是圓的還是扁的?〉中,邀請讀者一同反思,我們懂得運用科技但是否尊重科學?哥倫布和麥哲倫出航前,似乎並不確定地球是圓的,但又有幾人曾親手實驗證明萬有引力定律的正確性呢?自詡為「科學人」的我們,對知識的接收竟也只是人云亦云?這是個頗值得玩味的問題。但科學又為何會令人著迷呢?人性本身給出了答案,就是尋找真相、了解真理所帶來的滿足、愉悅與振奮。科學家正是對此上了癮的一群人。
萊特曼也毫不避諱地以自己在科學生涯所面臨的困境與感傷,為同樣投身於科學的同儕與後輩們做出見證。〈期盼成空〉客觀分析了為何科學家的顛峰總出現在年輕時,而經驗老成的熟手卻只能徒在性靈與衰老間掙扎。年過黃金歲月的科學家又如何面對現實、透過轉型繼續發揮自身的價值,從而完成童年夢想。〈牛頓先生來訪記〉同樣談科學家的創造力和研究的挫折,但這回卻讓偶像級大師親自作見證。透過一段與牛頓(Isaac Newton)邂逅的遐想,把話題延伸到科學家常有的迷思,如抱怨、傲慢、固執、偏見與不耐煩……當然,還有愚蠢。〈唯求真相〉中更具體地舉出了幾位以嚴謹著稱的物理學大師如蘭道(Lev Davidovich Landau)、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等,都曾難免因情感偏見而錯失科學真相的例子。萊特曼藉此向年輕學子們宣告,人性缺失並非罕見疾病,重要的是要認識自我、承認缺陷並嘗試克服錯誤。文末引用了培根(Francis Bacon)「順從人願的科學」(sciences as one would)來提醒讀者,理性中仍有意志與情感成份,這使得人們往往樂於接受自己寧可相信的事情,因而產生偏見,而交互詰難正是排除偏見的好法子。
談到科學家克服偏見尋求真相的精神,讓我想起今年(二〇一五年),「搜尋地外文明計畫」(SETI)創辦人之一的天文學家吉兒‧塔特(Jill Tarter)博士,與第一位發掘前寒武紀化石的古生物學家威廉‧夏夫(Willinam Schopf)教授應邀來臺所做的一場學術演講。當中有聽眾詢問他們本身是否相信地外文明是存在的,否則沒有這樣的信念支撐,又怎能畢生從事相關的探索?兩位科學家的回答令我印象深刻而感動,他們坦言對此沒有任何主觀的預設立場,而支持他們研究的唯一動力就是:尋找事實的真相!在極易受到情感影響的科學之途上,觀念與態度的傳承顯得格外重要。
「傳承」也是萊特曼相當重視的一個環節,他用了最長的篇幅,在〈徒與師〉中闡述了傳承的重要性。因為並非所有的東西都能從書中學到,除了知識之外,思維、謙遜,甚至直覺等都受到傳承的影響。無怪乎四一%的諾貝爾獎得主,其師門或團隊也都頂著諾貝爾桂冠的榮耀!
請試著用一千五百字寫一部傳奇小說,故事裡要有地理背景、歷史淵源、民族情結、哲學省思,外加神祕的氛圍,而且必須不假圖解、符號、專有名詞、數字和方程式,單靠文字敘述來把海市蜃樓的複雜大氣現象,以科學原理解釋清楚……最重要的,這些元素還必須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想看看萊特曼如何把這個故事說得精彩絕倫嗎?請翻到書中的精彩超短篇:〈幻影〉。
若想把宇宙大霹靂(Big Bang)後「暴漲」(Inflation)理論的起源,拍成一部類似二○○五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衝擊效應」(Crash)這樣的電影,劇本該怎麼寫呢?萊特曼教授〈十二月裡某一天〉或許是個不錯的選擇。在宇宙一百三十八億年中平凡的某一天,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狂吠的狗、騎車上學的大學生、開車到矽谷上班的男人、身穿時髦花呢套裝的女人和在書店翻看《一座小行星的飲食方式》的壯漢……他們之間到底有什麼神秘的關連?答案在午夜時分揭曉。天文學家艾倫.葛斯(Alan Guth)一人、一紙、一筆,在這平凡時刻寫下了宇宙最不平凡的一刻:剛誕生的宇宙經歷了超乎尋常的急速膨脹,形成今日宇宙裡原子、恆星、星系以及一切生靈的種子。而〈萬物之初〉和其他無法一一介紹的精彩篇章,則各以不同手法,承接講述宇宙大千的故事。
《雙人舞》這二十四篇深入心靈的科學散文,透過文字力量在內心所產生的巨大共鳴是淡然、悠遠而深切的,這股來自人性與科學在靈魂深處交會的迴響,正喚醒蟄伏千年「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的人類天賦。而在萊特曼獨到眼光與豐富涵養的引導下,原本殊途的科學與人文也終於得以重歸於一。願各位閱讀此書時,共饗天人合一的和諧之美。
吳志剛
(本文作者任職於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推薦序
對於科學的浪漫追尋
台灣的夏夜,抬頭可見三顆非常明亮的星星,俗稱「夏季大三角」。把手臂伸直、手掌全開,都無法涵蓋這三顆星的張角。其中離地平最遠、偏向北方那顆最為明亮,稱為「織女星」,它的右下角那顆是「牛郎星」,與織女相隔銀河兩方。織女左下那顆星是「天津四」,混雜在銀河眾多的雲氣與塵埃之中。要不是貴今賤古,民間流傳的牛郎與織女的故事,雖不若羅蜜歐與茱麗葉般有英國文豪加持,其實也相當浪漫。
說完了七夕與鵲橋,牛郎與織女的故事還沒結束。牛郎星距離地球約十七光年,也就是光線離開牛郎星表面,花了十七年才到達地球。織女星離地球約二十五光年,而天津四的距離不太確定,但差不多兩、三千光年。
「對了,怎麼知道它們的距離呀?」
「不說這個,先聽我說。
「這三顆星和太陽一樣,都是一團氣體,能自己發光。今晚走出戶外,所看到的牛郎星,是它十七年前的情形,於此同時,進入眼簾的,是二十五年前的織女,以及兩千多年前的天津四,很奇妙,對吧?我們得等到二十五年後,才知道織女星「現在」是什麼樣子(她總是年輕了二十五歲)。仔細想想,『現在』是什麼意思,又是誰的現在呢?」
「還有,天津四的距離比另外兩顆星遠了百倍以上,但是看起來卻沒有暗太多,這表示,如果把它們放在一起,天津四的光芒必定強烈得多。牛郎星與織女星正值恆星生命血氣方剛的時期,中央有充沛的氫氣進行核子反應,而天津四的內部氫氣已經消耗完畢,表面溫度雖然和織女星與牛郎星不相上下,但已步入晚年,體積大幅膨脹,像個臃腫老人,卻明亮異常。」
「我還是有疑問,隔了這麼遠的距離,怎麼知道星球的體積與溫度呢?」
「嗯,好問題,這也晚點再說囉。」
。。。
萊特曼這本書是早期作品,之前已經有別的中譯版本,以一貫深受好評的風格,也就是以生活冥想結合科學,用優美的散文開展。內容除了知識以外,充斥了科學家的人文軼事,讓原來看來生硬的理論,成了有血有肉的故事。但如果沒有一些自然科學背景,或許還是無法完全體會箇中巧妙。翻譯這本書絕對是個挑戰,以〈雙人舞〉來說,我本身學淺,閱讀原書時雖然可以體會作者洗鍊的英文,但因為有太多生字,根本不敢妄想翻譯這樣的文章。本書譯者功力高多了,下筆帶有古樸之風。看中文版當然會失卻欣賞原作文字之美,但凌駕於文字之上,是一篇篇遊走於歷史、哲學、宗教間的短文,好像幾次心跳便讀完一篇,很是過癮。
在牛頓之前,克卜勒整理了精確的行星位置數據,歸納出行星運動定律,這在書中〈尋星之時〉也有提到。其實,克卜勒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直到牛頓發展出萬有引力定律,才順利解釋了這些運動定律背後的原理。〈牛頓先生來訪記〉一文饒富趣味,假想跟牛頓對話,呈現科學知識的進展。牛頓力學至今仍然合用,但上個世紀發現在兩種情形之下,這個學說需要修正:一是當尺度小,也就是差不多原子般大小時,需要量子力學;另一種是速度快,也就是接近光速的時候,需要相對論。
我自己也喜歡這樣的神遊。萊特曼想像牛頓出現在現代,我則是經由時光旅行前往拜訪牛頓。正如傳說,他的脾氣不好,個性輕狂;但我來自未來,知道他將流芳千古,所以百般容忍。他似乎不因我可以穿越時空而困擾,可能這在當時還不會構成問題吧。牛頓對二十一世紀很有興趣,傳真機、飛機與火箭都讓他嘖嘖稱奇,但這些到底有多神奇呢?日常生活是否聽說一畝田可以產出百萬公噸的稻子(因為朗朗上口的E等於MC平方,一點點質量就可以產出巨大能量云云),或是隔空可以抓藥(因為空氣不是空的,而有我們賴以維生的氧氣,有很多潛在能量云云),這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根本就違反科學原理。然後江湖郎中就說,科學無法解釋的東西太多了,不要故步自封。
科學家當然最清楚求知是沒有盡頭的,因此對此不再反駁,於是郎中與糊弄成癮的名嘴當道。我常舉的例子,是第一次買樂透就中獎,我們對此驚呼不可能,因為機率太低了。要是有人宣稱沒有買也中獎了,我們的反應當然也認為不可能。當然,這兩種「不可能」層次不同,前者確實可能發生,後者則完全沒有道理,即使運氣超好都不會發生。話說牛頓對二十一世紀驚嘆之餘,他會發現傳真機的光學原理他可以理解,並沒有超出他所撰寫的光學一書,而飛機與火箭推動的原理,則基於他自己發現的反作用定律。換句話說,這些未來技術與工程的「奇蹟」,其實並沒有違反他所認知的科學原理。
在二〇一五年七月,藉著這些科學知識與工程技術,太空船飛了將近十年,從數十億公里之外,傳回冥王星的影像。在電視上看到這個新聞的阿公,轉過身來,說他有個朋友的親戚,聽說過有個人能夠通靈,曾經帶人去火星,他應該也可以去冥王星。這兩個題目電視名嘴或許都會討論,反正網路資料多得很,只要在標題後面加個問號,就不用負責了,然後說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世界沒有事情不可能。某些電視談話性節目,對於政治、社會話題,每個人都能談,反正沒有對錯,但說到科學,常常荒腔走板,但觀眾對此似乎不以為意,認為看電視就是要放鬆,只要專家講點嚴肅的內容,立刻就轉台了。我有多年教書經驗,也常四處進行科普演講,自以為有能力深入淺出。我認為被陌生人稱讚容易,要能夠讓周遭的人佩服,才是真了不起。所以我特別在意跟家人解釋科學,有時候無論如何靈活舉例,他們都聽不懂;認為只要是科學,就是無法理解的東西。每當遇到這種狀況,我就知道自己還要加油。我在想,是否科學家表達也要戲劇化,才能吸引人,然後劑量越來越重,終究不免嘩眾取寵;還是很多人根本失去了認真聆聽的耐心。學習科學不只是為了學知識當科學家,而是培養生活與思想的態度與習慣。
物理系大二的學生就能夠解微分方程,但往往缺乏數據誤差的觀念。要等到研究所寫論文的時候,才發現缺乏寫作訓練,也無法把話說清楚,因為從小學開始,老師在台上最常說的就是「不要講話」。國文科的閱讀測驗,不僅可以放文學作品,也可以選擇科學文章(啊,其實科學文章也可以是文學作品)。一般人如何讀懂產品使用手冊,工程師如何寫出說明清楚的使用手冊,如何讓電腦程式有效易懂,都是重要的語言訓練,而不侷限於爭論文言文的比例多寡。
〈別的房間〉是你我都熟悉的情境,我們的生活中大概都有個約翰或菲爾,學生時代他們舉重若輕,沒有特別用功,但成績很好,要不就有美術天分,或手指特別靈巧,要不就膽識過人,讓人羨慕。一九八四年的電影「阿瑪迪斯」 (Amadeus),演的是音樂奇才莫札特的故事,榮獲八項奧斯卡大獎,片中讓我印象深刻的,除了莫札特的笑聲,還有影片自述者安東尼奧薩列里,他在音樂上的苦練努力只能達到平庸的程度,對於莫札特的天賦忿忿不平。我在石溪大學博士班的指導教授麥可賽門 (Michal Simon) 有次談到認識的兩位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一位苦幹實幹,讓人覺得「有為者亦若是」,也就是自己努力些,也有機會達到相同成就,但是另外一位屬於天才型,一般人很難望其項背。看來,認清自己是最重要的,有哪些優、缺點,哪些事情讓我們感興趣。依照不同個性,有些強項適合繼續加強,讓七十分的實力增加到九十分,然而,想要進步到九十五分,可就需要付出龐大代價,甚至受限於天資。有時候,尤其是學生時代,得以名正言順改進弱項,從二十分增加到六十分。然而我們總是弱項居多,不應該盲目進行,而是培養解決問題的習慣與基本能力,隨著人生不同階段的興趣與時間,或鑽研梵文、非洲的生態更迭,或地球的磁極逆轉,這些也可以是娛樂。我曾經帶過一個研究生,剛入學時為電腦文盲,但他決意改變,畢業論文寫的是關於電腦模擬計算的題目。另外有位學生,號稱英文成績從來沒有及格過(我相信),但是經過兩年碩士班,有了長足進步,這些都是成功的例子。我自認學新東西容易上手,個性上又喜歡嘗試,所以有個八百分哲學,也就是每樣東西有八十分的水準,然後同時做十件事情。有些人在某個領域出類拔萃達九十九分,誰在乎他們人生總分呢,只有自己評斷是否快樂。
〈時光旅行與喬老爸的煙斗〉也是篇著名的文章。想要太空旅行,需要快速太空船,想要加速就需要能量,根據狹義相對論原理,東西變快了以後,想再快一點,必須用上多得多的能量,但只要有充足能量,理論上可以讓太空船越來越接近光速。要是能夠乘坐時光機,在過去與未來間穿梭,實在太吸引人了,但是邏輯矛盾也因此無法克服,例如,如果我回到過去阻止了父母認識,就不會有我,也就不會回到過去了。為了解決這些矛盾,有些科幻故事發揮想像力,例如時光機只能到未來等,但也都各自有無法解套的問題。
時光機是否可能的關鍵,在於目前我們仍不了解時間的本質,因此就不知道是否可以穿梭。要是時光旅行不可能,那我們就死了心,不要妄想跟牛頓討論科學、跟李白把酒言歡,或是到未來帶回救世解藥。然而,要是時光旅行可行,那麼時光機就只是工程與能量問題,即使現在做不到,未來一百年或一千年應該可以吧,那應該就有來自未來的人,就算有法律或道德要求嚴禁搭時光機過來,也無法管制未來不同時期、所有的人,那麼就應該有各式未來人才對,但是顯然並非如此。這代表的意義,要不就是時間本質上無法穿梭,要不……就表示人類文明無法持續到發明時光機的年代。
這話題實在太沉重了。讓場景回到郊外大草原上的那對年輕男女吧。
。。。
「在杜牧唐詩『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就提到了這兩顆星星哩!」
「對啊,這是描寫秋天的詩句,『臥』字用得好,臥看就是側著看。現在是夏天,入夜後牛郎星與織女星高掛頭頂,等到秋天時,入夜後它們就快西沉了,當然側著看囉。」
「耶,有流星,快許願!」
看到那道飛逝光芒的人興奮異常,沒看到的人則扼腕惋惜。對於綠茵之上、穹蒼之下的兩位戀人,這剎那絕對浪漫,正如唐朝喬知之的定情篇:「人間丈夫易、世路婦難為;始如經天月、終若流星馳;天月相終始、流星無定
「直到十八世紀,人們還不相信石頭會從太空掉下來,認為隕石應該是大氣現象。現在我們知道太空中充斥了大小不等的砂石冰屑,通過地球大氣時摩擦生熱,發出流星的亮光。小的流星體在空中就消蝕殆盡,大的造成非常明亮的流星,殘骸落到地面,成為隕石。」
「所以我們是對著石頭許願?這太煞風景了!」
「是嗎?」
「這些石頭在五十億年前跟地球一起形成,在太空孤伶伶的遊走,剛才與地球邂逅,剎那間的電光石火,居然被我們看到了」,女孩站起來,說:「我覺得~這~浪~漫~極~了!」
陳文屏
(本文作者為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教授)
推薦序
《雙人舞》中的感性與理性
我一直很喜歡讀散文,包含文學散文和科學散文,這裡的「文學散文」,指的是像余光中老師寫的《聽聽那冷雨》、《青銅一夢》、《粉絲與知音》,或者是簡媜老師的《女兒紅》、《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等作品。而「科學散文」則包含一般人所說的「科普文章」,以科學為主軸,透過流暢的文筆描述科學的精神和態度,傳達生活中的科學概念,例如高涌泉老師寫的《非物理不可》、郭中一老師寫的《科學,從好奇開始》,或者華爾達‧盧文與沃倫‧高斯坦合寫的《我在MIT燃燒物理魂》等等。
據我了解,一般人比較容易親近與閱讀文學散文,對於科學散文接觸則很有限,主要原因可能與我們的教育方式有關。學生在校面對物理、化學、數學等科目時,總有「退避三舍」之感,認為這些科目不容易理解、親近,更遑論主動去閱讀相關的科普書籍了。
科學散文與文學散文最大不同在於前者重理性分析與議論,強調說服力,後者則在感性抒發與描述,重視記敘的吸引力和抒情的感染力;文學散文往往傳達內心細膩的主觀感受與臆想,科學散文必須「有所本」的理論與實驗,必須事實和客觀並呈。坦白說,要把感性的文筆帶入理性的科學中,難度很高,誠如某首老歌中的歌詞「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能夠理性中有感性,感性中有理性,誠屬不易。
《雙人舞》這本書卻做到了,筆鋒兼具理性與感性,在文學散文的特色中不著痕跡帶出科學散文的理性。收錄在本書中的文章,幾乎都採用一部分的譬喻和寓言,也融入故事情境,科學名詞和原理的描述客觀呈現在感性的文字中,讓讀者在閱讀中認識科學家和理論,最重要的是,不會出現讓讀者畏懼的數學關係式。我想這應是作者艾倫.萊特曼獨特獨特的書寫風格吧!
如果讀完書中收錄的〈雙人舞〉,讀者大概就可以領略我的意思了。前三段文字輕巧曼妙地描述芭蕾舞步,「柔光照落,芭蕾女伶滑步舞台,凌空一縱,趾尖恍未點地……地板抵住舞鞋,推力正好與女伶重量形成均勢,兩者接觸點上的分子擠得恰如其分,產生相等的反作用力……萬一女伶身體的中心位置偏離這條線一公分,重力的力矩就會害她跌倒。儘管對力學毫無所悉,她卻能一次踮腳盤旋好幾分鐘,而身體不斷微調姿勢,流露出與力矩及物理慣性的親暱。」到了第六段,出現「牛頓定律」、「庫倫定律」、「電荷守恆」、「轉動慣量」等物理專有名詞。這些對非物理及工程領域的讀者而言,理解上有一定的難度,但作者把這些專有知識融入散文中,以「輕靈飄逸」、「深情內斂」、「翩然起舞」、「舉重若輕」、「獨有風韻」融化讀者畏懼的心靈,也能引導讀者融入女伶的舞蹈情境。
本書主題多元,還包含了聲音的傳播、光的反射與折射、人類登陸月球、地球是圓的還是扁的、鳥為何能飛而我卻不能、愛因斯坦相對論與時光旅行、哥白尼與克卜勒、放射性元素、宇宙緣起,以及有趣而幽默的半寓言故事,可說閱讀時,趣味橫生。
在〈地球是圓的還是扁的?〉提到圓的證據究竟為何,從月食期間觀察地球的影子向來呈現弧狀,也就是部分圓形,就知道答案。這一點自然涉及幾何學,也是「光是直線前進」的例證。
讀完本書,我想讀者應該會有初步的概念,知道海市蜃樓的成因是大氣層或物質與物質的交界面間密度不同,造成光線照射時會偏折,偏折後造成人眼的錯覺,因為人眼總覺得看直線,但看到的並不是真正物體,而是光線變魔術,讓我們看到虛線與虛線交集形成的虛像,這虛像摸不著,乃是實際光線遇到介質交界層偏折後的延長虛線造成的「魔術效果」。
其實,從李白的詩「渡荊門送別」:「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大概可以了解古今皆有海市蜃樓的物理現象,雲層與城郭結合幻化出海市蜃樓,只不過古人對此科學原理不了解,以為「蜃」是一種海中的大蛤,殊不知光線遇到不同的介質種類或狀態時,光線就會偏折,例如光線從暖空氣進入冷空氣時,因為冷空氣和暖空氣的密度不同,因此光線偏折程度不同,顯現出光會轉彎。因為人的眼睛視覺效果,以為偏折後的光線的延長線地方是真正的物體,其實不然,那只是真實物體的虛像,看到的虛像卻以為是真正的實體,那當然是視覺的錯覺了!
其他有趣的物理現象,如王維詩句「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在山林中看不見人,卻可以聽到樹林間人的對話聲,原因為何?這是聲波的繞射,因為聲波的波長與林木間距的尺度比較接近,所以容易發生繞射而傳出。
杜甫曾寫過詩句:「細推物理須行樂,何須浮榮絆此生。」杜甫的「物理」與現代人的「物理學」不盡相同,但也有一部分共通的意義,他所指的是探討大自然中事物的道理,有「格物致知」的涵義。以杜甫這兩句的想法,仔細推敲事物的道理是一件愉快的事,何必讓浮泛表面的名聲來牽絆我們的一生呢?我想,這就是「眼中有物,心中有理」的意思,也是我們學習科學所追求的境界吧!
簡麗賢
(本文作者為北一女中物理教師)
序
這本集子收錄二十四篇散文,選自十五年來的寫作成果;各篇都曾在雜誌或別種選集走上一遭。重讀這每一篇文字,最是讓我愉快。可以想見,日後再三翻讀,也還會是如此。時日推移之下,我了解到寫作之樂有三。首先,作者獨處時,能從寫作中領略一種狂喜。第二種快樂較關乎人我往來,出於以作品感動讀者。第三種快樂則於經年累月之後回歸己身,起自重讀一己值得留存的文字,重拾驚奇與感恩之情。寫作這一行大抵自私而獨尊自我。E.B.懷特(E. B. White)說,散文大概是最自我本位的文類。作者在文中公開個人思緒與放膽行徑,彷彿打了個小噴嚏、觀察到些小事情,都值得眾人關心。
動念寫第一篇散文時,我正舒舒服服坐在安樂椅上,抽著曾祖父的煙斗;煙斗散發出長年隱伏的古老氣味,吸起來真香。如〈時光旅行與喬老爹的煙斗〉一文所寫的,這支煙斗讓我和未及晤面的先祖有了親暱聯繫,從而思索起時光旅行來。更要緊的是,父親與我的關係也因為煙斗而重獲生氣。父親愛抽煙斗,不愛說話。有好些年,我完全無從探知他在想些什麼、是高興還是不快。但是,我上大學後,他時不時會拿收藏的煙斗送我,並說上一小段相關經歷。有一次,父親給了我一支二戰以來隨身的淡棕色凱伍迪牌煙斗。他還說,每回進攻前,常會邊在船上來回漫步,邊抽起煙斗。至於曾祖父的煙斗,原本在父親的抽屜裡躺了好一陣子。這支煙斗是用石南根所製,其上有古怪刻紋。父親將煙斗送給我時,倒是隻字片語也沒提。隔沒幾天,他寄來一張很棒的照片,照片裡沒有別人,只有喬老爹牽著年紀還小的他,爺孫倆兒站在裝設了護牆板的白色房子前。父親穿著燈籠褲,而喬老爹戴著帽子、蓄有鬚髭,和我吸著煙斗香氣時所想像的模樣半點不差。我寫了篇短文寄給父親。而後,說來奇妙,我們父子間萌生了真正的交流。我那時快變得和父親一樣靜默,但這件事讓我發現,寫作能讓我敞開心胸,觸及我所關心的人。
這篇開筆之作(及另外一篇)發表於《史密森尼》雜誌(Smithsonian)。接著,我長期撰寫每月專欄,刊在現已不存的《科學八○》(Science 80);這份優質雜誌於一九八○年代中期停刊,其後我便轉投其他刊物。為雜誌供稿能使剛起步的作者認清事實;寫作生手文筆稚嫩,往往自己愛得要命,一字一句都能熟背。到了雜誌上,經常是編輯大刀一刪,整句整句、整段整段文字就得讓位給下一篇報導,甚或版面上供讀者解悶的漫畫。僅管受到錯待,寫作的人依舊筆耕不輟;一但動筆成癖,便片刻也不得饜足、不得偷閒。
打開頭起,我就留意到,科學──這是初心所繫,也是職務所在──成了筆下題材:有時寫硬梆梆科學實事,更多時候則著墨人性質地與人心妙想,寫出科學裡活生生的人有何遭遇。對我來說,就屬科學最能嚴密呈現物質世界極致秩序。然則對此一秩序的渴求乃是人性──表達渴求的手段時常也是如此──與人類世界的情感及狂放發展奇特地相互依偎。兩個世界交會處,似乎應以文學之筆敘寫。同時,對同行的觀察,多少也促成我這樣做:最偉大的科學發現,通常起於科學家依循直覺而非方程式之時。換句話說,起於科學家最不「科學」的時刻。這項祕密歷史學家老早就明白了,科學家卻少有人知曉,如今成為貫串全書的伏線。
寫作時,科學與藝術、理性與本能之間的張力讓我深感著迷,進而文思泉湧 。我猜想科學之中多有本能,而藝術之內富含理性,於是問了些學界友人:他們思考時倚賴圖像還是等式,在研究中將美學準則應用至何等程度,又是否相信隱喻大有作用。我也問了些藝術家朋友:他們如何獲得創作靈感,如何使畫作架構和諧,而某一處又為何要這麼落筆。最終,我回歸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頗引論辯的評斷:自然法則,無邏輯之路可達,唯有取徑直覺與「心智的自由創造」(“the free inventions of the mind”)。科學家能如藝術家一般創造世界嗎?在心智之外,不是別有天地嗎?人類登陸月球而又回返。哪一個世界,哪一片天地,才真實?
某天,我第一次帶兩歲女兒去看海,心裡則尚存疑惑。和煦六月天微微起霧。我們離海還有半英里就把車停下,徒步朝海邊走去。沙地上一塊帶著斑點的粉紅色蟹殼引起女兒注意。再走一百碼,便聽聞潮聲陣陣、節拍有度;看得出來,女兒對聲響源頭大感興味。我一隻手將她抱起,另一隻手則指向大海。女兒沿著我的手往前一望,視線橫越海岸,望見藍綠色汪洋。她遲疑了一會兒。我不確定,初見無垠無邊,會是教她困惑,還是讓她害怕。燦爛微笑在她臉上綻放。我無須多說些什麼,也不必多作解釋。
我既是科學家,又是作家,難以明定身分,寫起散文倒相當合適。散文這種文類很大方,容得下哲學家、教師、好辯的人、健談的人、詩人。想寫散文,只需要下列三項:想個點子好起頭;願意為文章主題(通常也就是作者自身)掏心掏肺;能夠自律,該停筆時就停筆,別把短文寫成一部大書。以科學為主題,對寫散文的人而言特別是項挑戰,畢竟大多數讀者想讀的是「人」,或者說,至少是與人有關的事。但是,不消說,大部分科學毫無人味,與日常生活相距甚遠。由這點來看,醫學散文或心理學散文,先天就可能比化學散文或物理學散文來得吸引讀者。要寫科學散文,必須把「人」寫到文章裡頭,正如M.F.K.費雪(M. F. K. Fisher)把「人」寫進飲饌散文:晚宴賓客,請多少人最合宜?理由何在?又如,費雪女士還寫過,多爾多涅省那家小餐廳為她上菜的侍者,留著逗趣小鬍子。等到食物登場,令人垂涎欲滴,我們正已胃口大開。
本書多篇短文中,科學僅僅是跳板,方便我縱身人類行為這一難以捉摸的地帶。近半數選文帶有寓言──前人也許藉動物寓理,也許假托他事傳道──或故事的意味。寫作每一篇文章,除了題材相異,還得手法有別,才能使作者寫得暢快、讀者讀得盡興。和短篇小說一樣,散文的醞釀不成功便成仁。寫壞了的散文就該毫不留情扔進垃圾桶。但願該扔的我全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