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讀赫塞,開茅塞,不亦樂乎!
◎謝志偉
這本書可說是一九四六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畢生作品的精神濃縮版。從橫亙幾近一甲子的寫作生涯裡之書信,小說,評論,隨筆中所擷取出來的短句或話語,分門別類共十四項,計五五〇條:短的,精緻如格言,字字珠璣;長的,周全如短講,句句真誠,都有叫人驚豔之處。但如書前所引赫塞語,須得慢慢咀嚼,才能品其味,辨其意:「格言猶如寶石,因稀有而有其價值,且唯有小口細嚼而非大口囫圇才能到「味」。」通關密語是「別急」,而此「別急」其實是總體性地呼應了這本語錄的精神——用當代語言來說,其實就是「慢活」——也折射出赫塞身為上承十五六世紀的文藝復興,下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之新浪漫主義的典範之精髓所在。這點依本人之見,亦隱於本書原文標題之後。該標題 「Lektüre für Minuten」乃出於赫塞生前之手,直譯的話,應為「隨手讀:幾分鐘」。但是我們幾乎可以聽到其後還有一句隱而未顯、但卻呼之欲出的話:「Sinn für ein Leben」,直譯為「賞味期:一輩子。」作此解,須有所本。不急,有的。
西元一八九九年,西方工業革命一個世紀後,時年二十二歲、還在出版社當學徒的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以「輕微的喜悅」(Kleine Freuden) ——也許譯為「小確幸」亦可——為題,寫了一篇短文,大意在指出,人們終日為「時間」所驅到難以脫困的地步,不是「沒時間」就是「趕時間」,惶惶終日以致生活毫無樂趣可言,其後遺症就是,連娛樂性質的行為都充斥著「匆忙」(Hast)的緊張氣氛(nervös),這種情形,大人物加小百姓,無一倖免。他在這篇文章裡以修辭學的句型問說:「我們的父祖輩要作什麼事會挪不出時間?」(按:他指的就是文藝復興的時代)蓋無論是旅遊而倘佯在大自然裡,或在居家院子裡觀賞一枝小花,他們都能興致盎然地享受著心情的愉悅!赫塞在此的幾句關鍵話語日後也編進了本書裡:「強調分秒必爭,終日營營擾擾,無疑是快樂的最大敵人。他們的口號是「多多益善,劍及履及」,其結果就是:「娛樂愈來愈多,快樂愈來愈少」。(492條)這些話的原文若予以直譯,就是:「分鐘」(Minute)這個時間單位被賦予極高的評價,以及「急」(Eile)這個概念掌控了我們的生活裡外,此無疑正是扼殺了吾人之「快樂」的最危險敵人。對此,赫塞在該文裡開出的藥方叫(MÜßIGGANG),中文一般都譯為「懶散」或「游手好閒」,然而如此譯法是啟蒙思潮,理性主義和工業革命加資本主義「併發╱病發」後對「勤奮」(industrial──請注意這個字和 「industry」〔工業〕的拉丁文同源關係!)的正面思維及對「賦閒╱失業╱懶惰」(idlness──拉丁文本意有「無用╱沒有價值╱浪費時間」) 的負面評價。若從赫塞的體認來看,「MÜßIGGANG」應有兩種中譯版本:一為古典譯法,即「偷得浮生半日閒」;一為時下譯法,即「慢活」。
赫塞所拈出的「急」其實是在點出:歐洲已是個不折不扣「理性掛帥,感性掛彩」的地方,不但完全背棄了文藝復興的人文精神,其以「時間就是金錢」為表徵的機械文明更是掌控了一個已然形成的貪婪世界。一九一七年,大戰已經打了三年,赫塞發表了一篇題為〈論靈魂〉的短文,文中他寫道:「他們在金錢、機器及充滿猜疑的世界裡失落了他們的靈魂。」 赫塞的體認和與他同時代的社會暨經濟學家宋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為當時資本主義把脈的結果是一致的。宋巴特指出,從早期資本主義者的商人身上即可看出幾個特質,「計算,估算」成本和獲利以及「工作時間」無限制,隨時都在作生意。 這是由於人類的經濟活動在進入早期資本主義後就不再由「需求」(needs,參閱Sombart, 181)而是由「獲利」(profit, 參閱Sombart, 172)來主導。既然「獲利」是最高目標,那「每一天,每年,每個生命的每一分鐘就都獻給工作了……快速,還要快速」(Sombart, 181),「快速移動」成了商人特徵之一(Sombart, 176),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自然就會冷淡下來,因為早期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已是由絕對的理性所主控」(Sombart, 182)。早期資本主義的幾個特質和弊端:人情淡薄,追逐利益,凡與生意無關之人與事,都沒時間理會,既要「追逐」,動作就要快,分秒要必爭,哪來時間給別人?傳統的「欲速則不達」(對應之德文諺語:Eile mit Weile)已變成「欲望要速達」,而「凡事都需要時間」(對應之德文諺語:Alles braucht seine Zeit)則變成「凡事都需要節省時間」。現在吾人再翻閱當代德國學者柏夏德教授(Peter Borscheid)於二〇〇四年所寫的那本題為《「速度」這個病毒》的著作,就知道:城市的時間準則是「加速」,鄉村的時間準則是「放慢」。在該書中,柏夏德指出,「手工業者的時間是固定且和緩的」 ,而「商人的時間則是緊湊而機動的」。(Borscheid, 33)柏夏德特別點出,商人的時間之所以是緊湊而機動和遠洋貿易有直接的關係。(參閱Borscheid, 32)鐘錶之發明及普遍化不是為了知道時間,而是控制及縮短時間的:「沒有鐘錶之前,人們有很多時間,如今,人們有了鐘錶,卻沒有了時間」 這句話相當貼切。
赫塞作為觸覺極為靈敏之文學家,下筆自有其與眾不同之處,宋巴特書裡的鄉村在赫塞的生命體驗和文學創作裡,其實就是與機械、工業、理性、資本主義相對的大自然,而此大自然之代表於赫塞就是彼時「仍」未與大自然完全脫鉤的阿爾卑斯山,尤其是瑞士的阿爾卑斯山脈。須知,瑞士的阿爾卑斯山脈正是十七、十八世紀許多歐洲人體驗「崇高」(sublime)的聖地(「崇」字本身就是「宗」上有「山」的結構!)而啟蒙思潮和工業革命所帶來給歐人「進步」的成就感最終卻演成其「蝦米攏無驚」的高傲。大自然既然不再崇高,那人類在其面前就難心生「敬畏」(德:Ehrfurcht;英:awe)。之前是人類在崇高的山脈面前會心存敬畏而生中文裡類似「舉頭三尺有神明」的謙卑或戒慎恐懼之念,之後,全面理性化後的機器文明及獲利思維鞏固了「人定勝天」的堅定信念,從而「敬畏自然」逆轉為「睥睨天下」。從此「神話」成了「鬼話」。赫塞發表於一九〇四年的第一部小說《鄉愁》(Peter Camenzind)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天地萬物始於神話」 (Im Anfang war der Mythus),徇非偶然,其用意就在於點出歐人在一整個世紀的「急行軍」之後,已到了應該停下來思索、反省「進步」終將帶領人類伊於胡底的問題;「來,不急」的警示終究是「來不及」。十年後,一次大戰就爆發了。
在《鄉愁》的第一章,第一段話中對瑞士阿爾卑斯山的描述裡,就出現了「敬畏」這個概念的形容詞(ehrfürchtig),且是用來形容崇山峻嶺之天地玄黃, 如果我們將這一段對大自然,包括崇山峻嶺,湖泊小溪的細膩描述,其湖山之多色與多樣,天籟之賞心悅耳或發聾振聵拿來和歐洲同時期大城市裡有關工廠機器的吵雜噪音及工人污穢蒼白的臉龐對照一下,當知赫塞之苦心也。從而,即便是出處互不隸屬,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敬畏」這個概念在這本語錄裡多次出現(如189,199,223,227,229,258條等),為何?答案就留待讀者自己獨立思索了。總之,有心又有神,才能心領神會。至於何謂「神」?誰的「神」?單數?複數?赫塞在本書也提供了答案。
在此要指出的是,身為德語作家的新浪漫主義者赫塞,其對「自然 vs. 機器」的感觸與認知和其前輩英國浪漫主義畫家透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1775-1851)於一八四四年的畫作「雨、蒸氣和速度」(Rain, Steam and Speed)是前後呼應的。在該畫中,一列占了幾乎整整半個畫布、黝黑巨大的火車在雨中急行,火車頭上粗大的煙筒所噴出的熱騰騰之蒸氣在空中與雨水匯成漫天霧氣,火車頭本身像極一尊燒著熊熊烈火的魔頭,而畫布的左半面則一座拱橋,一條河流,還有一葉掛著搖櫓的扁舟,上有兩人對坐。由於霧氣及相對極為淺淡的色彩,橋樑、河流連帶扁舟加上人儘管也占了半個篇幅,卻都令觀者有「淪為背景」之感,蓋其雖與當時代表新科技的火車並存於畫,卻不並駕齊驅。火車頭前方不遠處,則另有一隻人眼幾乎難以辨識的野兔逃命似地撒腳狂奔。如果我們說,在十八世紀末工業革命興起之前,「大自然」對人類來說,依舊是「崇高 + 敬畏」(sublime╱德文:Ehrfurcht╱awe-inspiring)的代表,那麼在這幅畫裡,吾人就讀到了「大自然退位而新科技登基」的訊息了。依法國當代藝評家暨專業策展人Olivier Meslay所稱,則應是「崇高且令人敬畏的事物已經不再侷限於大自然,而是還有那出自於人手但卻地位如神的機器……」 。大自然退位而新科技登基,就在《鄉愁》出版的前十年,挪威畫家孟克(Edvard Munch, 1863-1944)那幅曠世名作「吶喊」(The Scream of Nature , 1893) 所標誌出來人與大自然間的緊張關係 ─ 吶喊的是大自然,感受威脅的是人類。曾幾何時,荷馬史詩《奧迪賽》裡女妖「賽壬」(siren)那足以誘引人類欲仙欲死到寧拋性命也在所不惜的「天籟」到了十九世紀末竟成了魔音穿腦般令人難忍?答案:赫塞報你知。
赫塞深深體會到,自然不僅在世上,也在人的身上,而人要因「教養」(Bildung)而高貴(參閱95,267,421條),這個高貴是和大自然裡的「崇高」相呼應的,是情操的高貴,是堅拒隨波逐流的個人,人人都是獨一無二的(86條),要與眾不同,他的德意志民族噩夢就是:一個被「對上馴服」的「對外強悍」民族!他那句話「自然裡沒有任何生物比所謂的正常人更邪惡、野蠻而且殘暴」(96條),而這句話就得和「只有那些不想扛責任或是不願思考的人,才會需要甚至要求領袖的領導。」(89條)一起來讀,兩句話合起來,其實就是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1963年針對納粹戰犯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nn, 1906-1962) 所寫的「邪惡的平庸」!
最後,出版赫塞語錄的中譯本,這不是第一本;一九七六年年底,遠景出版社就已出版了一本題為「赫塞語粹」的書, 但並非譯自德文原版(1971),而是譯自其英文版,經本人比對,應與本書所用德文原版同一。有意思的是,可能是「遠景」怕「員警」——一九七六年的台灣還處於戒嚴統治——在這本中文版裡,原本排在十四個分類主題第一順位的「政治」被挪到最後一個當墊底,語錄內容也從「七十六」條大幅縮減到個位數的「八」條!所有敏感語錄全都消失,彷彿不曾存在過。何以致之?原來,這些收在「政治」主題下的七十六條語錄主要就是經歷過一戰的帝國霸權及二戰納粹橫行的赫塞 針對「愛國主義」、「政客」(戰爭販子)、「法西斯」等概念所做的反思與抨擊和嘲諷。我們在此試舉一例:
戰爭不會憑空而降,它和其他人類行為一樣需要有所準備,也必須有許多人的醞釀和參與,才可能成真。可是希望戰爭並且策動戰爭的人或者政權,往往是可以從戰爭中圖利的。要不就是可以直接發戰爭財的,例如軍火工業(一旦有戰爭,許多善良的中小企業也變成軍火商,資金也會自然湧入這個行業),再不就是能獲取威望、聲譽和權力,譬如說那些賦閒在家而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將校軍官們。(第13條)
在這段話裡,除了對「戰爭」和「軍火工業」的抨擊外,更是狠狠地踹了那些自認是「愛國者」的軍人,尤其是「高階將官」們一腳;原來,沒有戰爭,這些「高階將官」就無用武之地了,因此,所謂「愛國」云云,乃是戰爭販子的遮羞布罷了。這點和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 1898-1970)於一九三〇年發表的反戰小說《西線無戰事》裡的一個場景有異曲同工之妙。幾個德國士兵在等候德皇來部隊親頒勳章時,有人問起「奇怪這一場大戰是怎麼開頭的」在確認「德國的一座山頭不能去得罪法國的山頭」後,一個老士官說:「一定是有些人,打仗對他們有益處……每一個身登大寶的皇上,起碼都要一次戰爭,否則怎麼會有赫赫有名聲?你們看看教科書吧。」此時,有個士兵再補上一句:「大將也是一樣,他們打仗才威名遠播嘛。」
讀本書,敬請注意赫塞處處隱藏的「辨證」機鋒,即「因果關係」的倒錯,如戰爭時,「愛國」最易被視為是最崇高之美德,因此,赫塞在第七條裡要說的是:愛國是因,戰爭是果,非反之也。他提醒我們,那些「愛國者」,為了提高自己身價及證明其存在之必要,然就會希望有戰爭。台語有云「別人的小孩死不完」,誠不虛也。
當然,相較於「納粹主義者」及「愛國者」,赫塞在這些語錄中對「共產主義」是較為同情的,對「和平主義」的支持更是無庸置疑。毫無疑問,這些極具說服力的語錄都曾使赫塞見棄於他的許多同胞── 納粹政府雖未禁他的書(作思想檢查的抓耙仔沒能看得懂),但也使出各種爛招逼使出版社「婉拒」出他的書,譬如,刁難、拖延、不發「出版許可證」或乾脆以「紙張不夠」為藉口)——以至於即便在一九四六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後,赫塞還寫了以下這句話:「就像諾貝爾獎可以落在某人頭上,屋瓦也隨時可以掉下砸到頭;後者發生的機率還高一些。」(475條)從而,在德國,赫塞曾因被「愛國主義者」視為是「叛國者」,而到了台灣,「紙張不夠」則換成「墨汁不足」。有意思的是,遠景版(1976)譯者在「政治」被沒收的那本譯書的末尾附了段「致讀者」的短文,其最後一句話是:「希望你在看這本書的時候懷著與一位智慧長者晤談的心情,試著去了解赫塞和他的苦心孤詣。」(頁225)。今天,眼前這本書能全文完整在台灣出版,並不是件理所當然的事。沒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台赫塞」不因邪惡壓迫而「ㄘㄨㄚˋ 塞」,恐怕別說「八條」,說不定只剩「二條一」(「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亦即「唯一死刑」)。
赫塞一生拒絕隨波逐流,以一枝禿筆,一身傲氣實踐了對所有壓抑「個人」的權力進行抵抗,除了靠他個人的修為(Bildung,有時可譯為「教養」,赫塞在本書多有深思著墨),「道法自然」對熟悉基督教,佛教和老莊的赫塞來說,並不陌生 。也許這是作為詮釋他對「唯兩端始有一貫」:「惡」之存在印證了「善」之必要──只是不能急,尤其不能急於放棄。你唯一該急的是:趕快揪人買這本書。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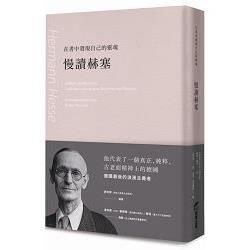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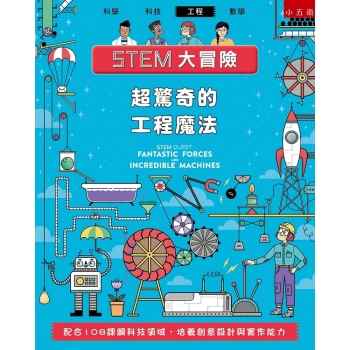










![114年一書搞定機械力學概要[國民營事業] 114年一書搞定機械力學概要[國民營事業]](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