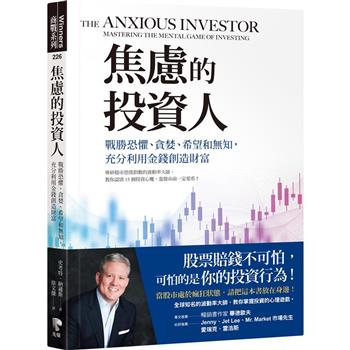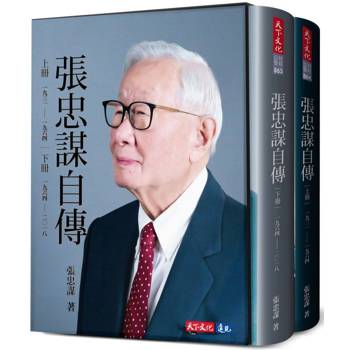第一章險失清白
七歲時,師父將流落街頭、饑寒交迫的她帶回山中。師父給了她一個名字,白離。自此她有了自己的名字,有了自己的家。
十歲時,白離多了一個比自己小三歲的師弟,白尚思。也是在那時她才知道,獨身一人的師父,其實心中一直占著一名女子。
「師父,那女子是什麼樣的人?」
「她心思狠絕,孤恩負德,詭計多端,無情無心。即使將她千刀萬剮,也不足以抵上她犯下的罪。」
白離的師父說得淡淡,白離卻聽得心驚。這便是師父放在心底,難以忘懷的女子嗎?為何在師父口中是如此德行?只是,即便白離的師父說著毫無讚譽之辭的話,白離卻依舊能從師父的眼中,看到她從未見過的濃烈情感。
「師父,她死了嗎?」白離問。
「死了嗎?」白離的師父輕笑一聲,帶著一絲淡淡的恨意說道,「她沒有死,她也不會死。她註定要在這世間徘徊,一世又一世。」
白離小心地打量著師父的面容,又小聲問道:「那她人呢?既然沒死,師父為什麼不去找她?」為什麼要天各一方,卻只拿著連面容也看不清的畫像思念?
「我自然要去找她回來,只是,她不願見我……可總有一日,我要將她找回來,綁在我身旁,看她有何能耐再躲、再逃避?即使是恨,我也要讓她在我身邊恨著我。」
十三歲的這一日,是白離的生辰,便也是白離的師父將她帶回山中的日子。
黃昏雨落,白離的師父佇立窗前。細雨蕭蕭,帶著些幽寂淒涼的滋味。
白離看著她師父的背影,問道:「師父,若是有一日,有個人很喜歡很喜歡您,您會願意接受她嗎?」
白離的師父沒有回頭,只是淡淡回了句:「不會。」
白離頓了頓,又問:「若是師父心中的那個女子不願回來,師父也寧可獨身,不再接受旁人嗎?」
白離的師父終於回過頭,黑如墨的雙眸注視著白離,靜默了片刻。
白離的心中緊張,背在身後的雙手握得緊緊。
師父閉了閉眼:「縱使佳麗萬千,這心是空的,要如何接受?」平靜而毫無起伏的語氣,卻讓聽的人心頭一涼。
四年眨眼即逝,白離已十七歲。
在下山的蔭林小道處,白離的師父淡淡說道:「妳離開,不許回頭。若是回頭一次,妳我便斷了這師徒情分。」
白離倒抽了一口氣,愣了片刻之後便笑了笑,向著下山的路走去。
白離知道,她師父說出口的話,向來不會收回。肩上的包袱是師父替她收拾好的,原來,師父早就有讓她離開的打算了嗎?
不許回頭!
白離身後,師弟白尚思依舊有些稚嫩的嗓音,帶著哭腔呼喚,其中還夾雜著對師父不斷地哀求。
抑制著想扭過脖子再看一眼的衝動,白離哼著歌,腳步悠閒地向前邁著。
師父太無情了!師徒十載,一別竟似永遠不願再見。曾經的幸福過往,在這山間的歡笑愁苦,轉眼之間,也將化為烏有。
抬起手,白離抹了抹臉。白離的腦海中浮現幼時問過的話:「師父,您為何要收我為徒?」
師父只是淡淡一句:「日後妳便知曉。」
如今長大的白離已經知道了,她的師父會收留她,是因為她的容貌肖似師父心中的那個女子。
十月十五下元日快到了!
白家村的人敬神敬鬼,在每年的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皆要進行一次祭祀,設壇祈福,以表虔誠。
送走最後一名學生,白若沁兩手空空地從學堂裡出來。她沒有直接回家,而是拐了個彎,向著相反的村口方向緩步而去。
此時的白若沁,便是當年的白離。
下山的那一年,師父把她的身世告訴了她,之後她尋覓了一陣子,才找到這些村民。六年過去,如今白若沁二十有三,早已過了少女思春的芳華之年。
回想起當年,有些事,她無論如何也想不明白。才過了六年多一點,她便已經忘了師父的模樣,如今在她的腦海,師父的臉已模糊不清。但只要一想到師父,她心口的某一處便會揪痛。唉,看來她也是個無情之人啊!
算了,不想了!想了讓人心痛,不如不想了!不想了!
彎進村子西坡的時候,白若沁正好看到白家村的村長,水伯。水伯坐在西坡的一棵大樹下,似乎正和什麼人在說話。和村長談話的人坐在裡側,被村長遮住了身形,看不到模樣。
白若沁邊暗自琢磨著,邊朝村長的方向走去。她才走近幾步,便聽到一個陌生的男聲傳了過來:「如此說來,白氏一族的歷史可不一般了?」低沉的聲音帶些恰到好處的沙啞,聽在耳中,酥酥麻麻。而他話語中雖然帶著興味,卻是不急不緩的語氣,可見其人性情之沉穩。
「那是。」村長將頭貼近那男子的耳畔,略放低了聲音說道,「其實,我們這村子的人本不姓白。」
白若沁腳步一頓,清嗓咳了一聲,隨之出聲喚道:「水伯。」
聽見人聲,村長立刻停止了談話。望見來人是白若沁時,村長就馬上站了起來,神態很是恭敬地喚了聲:「先生。」
白若沁點點頭,又微笑著說道:「水伯,怎麼還在這裡坐著?勇山的媳婦都做好晚飯了,勇山這會兒正帶著胖虎子,到處找水伯呢。」
白若沁一邊說著,一邊看向方才和村長談話的那名男子。只見那名男子漫不經心地坐在一塊石頭上,背靠著樹,半瞇的鳳眸也正凝視著她。
白若沁看不出男子真實的年紀,但他眉眼間的神態,帶著一種深不可測的深沉感,想來約莫已過而立之年。面目清雅,輕勾的薄唇帶著一絲看不清意味的笑意。一頭黑如上等墨色的長髮披在身後,頎長的身形著一身錦衣,自有幾分貴氣,一看便知不是普通人。雖然微挑的眉角,隱隱有些勾人心魂,但在眼底深處,卻有一股輕微的煞氣。
那男子也打量著白若沁,如電的雙眸觸上她帶著審視的目光時,嘴角笑意更深,面色依舊波瀾不驚。
對一個初見面的陌生女子,這樣的目光未免太過放肆了些。但白若沁自小在山中長大,性格非拘泥之人,便沒有將其放在心上,反而有禮作揖。
男子站起身徐徐回禮,道:「在下皇甫賢。」
「小女子白若沁。」
見他們互道了姓名,村長這才回過神來,上前道:「皇甫公子,這位便是我同你說的,我們村裡的先生。」
皇甫賢嘴角揚笑:「方才同村長閒聊之時,聽聞了許多白姑娘的事蹟,在下心中甚是欽佩。」
許多事蹟?不知村長說了多少白家村的事?若是村裡一些生活雜事也就罷了,只希望村長別失了戒心,將一些不該說的都告訴了旁人。都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了。
心思萬千,白若沁神色不變,客氣笑道:「不過是識些字,教教村裡的孩子而已。為村子盡點棉薄之力,也算不上什麼,倒讓皇甫公子見笑了。」
皇甫賢深深看了白若沁一眼,幽幽古井般的黑眸沉沉:「白姑娘過謙了!一路行來,在下所見女子不少,可白姑娘的所做所為,的確是值得佩服。」
白若沁瞥了瞥村長的臉,只見村長的表情有些茫然。轉移著話題,白若沁問道:「看來皇甫公子去過不少地方,不知皇甫公子是從何處來的?」
皇甫賢鳳眸一瞇,嘴邊又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他慢慢啟唇,答道:「月前自京城而來。」
京城?白若沁的眼皮一跳,努力回憶她所知道的皇親貴胄們。印象中,並無皇甫這姓氏,但出門在外,或許此人易名了也說不定。
白若沁保持著如常的微笑:「原來皇甫公子是京城人士,難怪看起來儀表非凡。」
微風吹過,一股淡淡的藥香味,自皇甫賢身上飄來。那混合了多種藥材的藥香並不嗆鼻,反而讓人聞之通體舒暢。只是這讓白若沁有種隱約的熟悉感,卻又不能確切地想起那到底是什麼。她微微有些恍神,隨後感覺到背後束起的長髮被人握起。她回過神來,不知什麼時候,皇甫賢竟走到了她的身旁,兩人離得極近,她幾乎能感覺到他溫熱的氣息。
「白姑娘,妳的頭髮……」皇甫賢瞇眼,目光落在他掌心間的髮尾,「髮色比一般人淺上不少。」話語淡淡地說了句。
不過是髮色淡些罷了,倒是這樣的姿勢,著實曖昧得讓人浮想聯翩。
「是啊。」白若沁面不改色地回答。隨後稍稍側身,從皇甫賢手中抽回自己的長髮,又後退一步,消散兩人那若有似無的曖昧之感後,笑著道,「天生如此,倒是吃了不少何首烏也不見效。」
「天生如此嗎?」皇甫賢再看了白若沁一眼,道了聲,「白姑娘,失禮了。」話音落下,皇甫賢便執起白若沁的手腕,為她把起脈來。
白若沁秀眉微蹙,稍用了些力,奈何竟是掙脫不開。
須臾間,皇甫賢已經診好了脈。他垂下眸,讓人看不清眸中的神色:「五臟虛損,脈象濁亂,似有寒氣侵體,而脈中又有一股邪逆相沖。白姑娘的髮色變淡,怕是緣由於此。」
白若沁眨了眨眼,面上微露驚訝之色。她是白家村中的醫者,自然清楚自己的狀況,可惜醫者不能自醫,延誤了時刻,又一直做著耗損之事,她的性命早已難全。她只是訝異皇甫賢的醫術非凡,她的身體非於常人,能將她的病況如此清楚地指出,此人自然不可小覷。
皇甫賢鬆了手,眼底是一種無關己身的漠然,只是眨眼間,眸中又是一片平靜。此人要不是見多了死人習以為常,練得一身無心無情,那便是他心思深沉,不露於外,是個演戲的好手。白若沁暗自欽佩,自認無法達到他那地步。
「白姑娘似乎早已知曉己身狀況,妳一點也不擔心嗎?」
白若沁頓了頓,然後半開玩笑地說道:「人生在世,生死有命。早知道了也好,可以為自己先準備好一口薄棺,免得走得突然,讓旁人手忙腳亂。」
皇甫賢微蹙起眉,不知在想什麼,身上的煞氣在一剎那似乎驟升幾許。可等白若沁再看時,哪有什麼煞氣?皇甫賢依舊是那個一身貴氣的儒雅公子。
皇甫賢自懷裡掏出一個小瓶子,慢慢說道:「這是天芝丹。身有疾者,用了百病可消,無病之人吃了,則能夠延年益壽。白姑娘體虛,妳且留在身邊,若有需要,也用得上。」
白若沁感到愕然。方才皇甫賢眼底的冷淡,讓她以為他是個冷漠之人。難道她錯辨了?還是京城的人都如此大方?
思索片刻後,白若沁搖頭笑道:「無功不受祿。如此貴重的珍藥,小女子受之有愧。」
皇甫賢嘴角微勾,道:「天下之大,妳我相會便是有緣,又何必言及有功無功?此藥於我並非難得,若有需要,我隨時可以拿到,還請白姑娘不必客氣。」
「皇甫公子的盛情,小女子心領了,只是這藥我實在不能收下。」
見白若沁並非假意客氣,而是真無接納之意,皇甫賢只淡淡一笑,也並不勉強,默默收了藥瓶:「白姑娘似乎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是人自然都希望長命百歲,只是我的身子,不是一般藥物能調理得回來。天芝丹是奇藥,可用在我身上只怕是暴殄天物,到最後反而辜負了皇甫公子的一片好心,倒不如將天芝丹用在更需要的人身上。」白若沁抬頭看了看,太陽已落下些許,見皇甫賢還未有離開的意想,她便問道,「皇甫公子是獨自一人出遊?身邊怎不見僕從丫鬟?」
「路過此地,見這村子風景秀麗,便進來看看,也順便讓馬匹歇息片刻。」皇甫賢看著白若沁,神色自然地答道,「我不喜歡丫鬟跟隨,身邊倒是有個護衛。」
「這樣啊。」白若沁心中已打好了主意,臉上卻假裝遺憾地嘆道,「若是時候早些,還能請皇甫公子用過晚飯再走。只是如今天色將晚,而白家村簡陋,並無客棧讓過往行客住宿。此地距離萬春縣約莫十餘里,若是快馬加鞭,想來是能在天黑之前到達。」白若沁是說得很誠懇,但話語間並無留客之意。
皇甫賢沒有應聲,只挑了挑眉,唇邊露出一抹了然的笑意。他漆黑的眼睛裡,彷彿有著靜潭似的深幽,卻又帶著風吹水動的迷人。
白若沁對皇甫賢意味難辨的笑容視若無睹,只是見他但笑不語,又提醒道:「皇甫公子,山野之路夜間難行,皇甫公子還是趁早上路才好。」
皇甫賢笑意不減,緩緩作揖,說道:「多謝白姑娘提醒,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告辭了。」隨後微微側頭,喚了聲,「回春。」
「爺。」一個穿著灰色衣裳的男子不知從何處出現,站在五六步遠的地方。
皇甫賢瞥了白若沁一眼,輕笑道:「我們走吧。」
語落,皇甫賢對著村長微微頷首,而後轉身越過了白若沁的身側,往村外走去。那個叫回春的冷漠男子目不斜視,也跟著皇甫賢一同離開。
白若沁非常恭敬地目送他們離去:「願皇甫公子一路平安,後會有期。」
今日一別,只望再不相見。
站在原地,等皇甫賢的身影消失在轉角,再也見不到了,白若沁這才回身,吁了口氣,說道:「水伯,下次最好別在外人面前,提及白家村的過去。」
村長垂下頭,抖著鬍子,顫顫巍巍地道:「先生教訓得是,是老漢大意了。」
看著村長戰戰兢兢的表情,白若沁緩和地道:「水伯,若沁只是提醒一下罷了,水伯不要太過在意。」
「是,是。」見白若沁的語氣溫和,並未有怪罪之意,村長才稍微放下心來,低聲說道,「老漢見那人並無惡意,又對我們村子的生活頗感興趣,便多聊了幾句。想來我們遷出京城已經快一百年,都是老漢爺爺那輩的事,老漢這才失了戒心,不小心說漏了嘴。」
村子裡已近一年未有生人來訪,也難怪村長會如此大意。
白若沁笑了笑:「我明白的,水伯。只是雖然事情已經過去很久,但怕是那些人並未停下對白氏一族的追捕。說給不知情的人聽也就罷了,若是讓有心人聽去,告了官,怕是事情又要麻煩了。」
聽著白若沁的解釋,村長臉上也露出了一絲後悔的神色:「對不起,先生。不過老漢還未說出什麼不該說的,先生便出現了。」
白若沁搖搖頭:「沒關係,我看那男子對我們也沒有惡意,如今他也已經離開,想來不會再有什麼事了。」
話音剛落,他們便聽到身後傳來一道低沉嗓音:「抱歉,我有一物遺落在此地了。」
白若沁驀地回頭,瞪大的雙目望著幾步遠外,那個閒適淡笑的男子,心中大驚。皇甫賢已接近他們身旁了,她卻沒有聽見任何腳步聲,連他什麼時候靠近也全然不知。
皇甫賢走到方才所坐的位置處,不知拾起了什麼,放入袖袋之中,又隨手撢了撢袖襬,掃去沾在上面的一點枯葉塵土,動作帶著特有的貴氣。隨後他回身望向白若沁,見她臉上仍是一副大驚的模樣,他才嘴角微微上揚,緩聲問道:「怎麼了?」
白若沁收回驚詫,盯著皇甫賢,審視著他臉上的表情。思索片刻後,白若沁還是開口問道:「不知皇甫公子是否聽到了什麼?」
「聽到什麼?」皇甫賢笑笑,「在下剛來而已,若有聽到什麼,也只是樹上幾隻山雀的叫聲。至於二位方才交談的,若是白姑娘願意相告,在下倒是也有興趣聽聞。」
皇甫賢是真沒聽見,還是裝沒聽見?白若沁眸光一閃,語調平靜,她微微地笑道:「不過是本村的一些無聊之事罷了。」
反正不管皇甫賢所言是真是假,她只有陪他把戲演下去。他真對白家村無惡意最好,若他有心告官,那麼無論如何,她也要動手將此人除去。她嘴邊帶笑,卻斂下眼睫,掩去眼中森冷的殺意。
一時之間,四周靜默而詭譎。
「姊姊,水伯。」正當白若沁想著下面該如何行事之時,遠遠的,傳來一聲清脆悅耳的聲音。
白若沁抬頭望去,一個十七歲的少女背對著夕陽,正邊揮動手臂邊輕快地跑來。桃花面,秋水眸,一張鵝蛋臉,麗質嬌豔。少女頭上挽著俏麗的髮髻,耳後梳著兩條長辮垂至胸前,顯得俏麗可愛。
少女的面容與白若沁有六七分相似,是白若沁同母異父的妹妹,白茹雪。同白若沁一般,白茹雪的嘴邊也時時掛著笑,只是白若沁的笑中僅存五分意,白茹雪則是笑意明媚。
等走得近了,就見白茹雪身後還跟著一名年輕男子。男子身材修長挺拔,眉目俊美,比之皇甫賢的清雅,更多了幾分狂野之氣。
男子的膚色略深,長髮盡數縛於頭頂,顯得乾淨俐落。這名男子名喚白楓林,與白若沁的護衛白容,既為一母同胞的手足,也是同出一門的師兄弟。白容與白楓林擁有相同的容貌、相近的身手和性格,若是讓二人並列而站,即便是相處了二十幾年的村人,也難以分出誰是誰。
「姊姊,我回來了。」跑到白若沁跟前,白茹雪帶著討好的笑容抱住她的手臂,撒嬌地蹭著。
白楓林站在一旁,看見白若沁後,恭敬卻有些疏遠地叫了聲:「大小姐。」
白若沁微微沉著臉,略帶責備的口吻說道:「出去玩了三日,終於知道回來了?」
「姊姊。」白茹雪抓著白若沁的手搖晃著,微微嘟起嘴,有點委屈地說道,「天天待在村子裡,人家很悶嘛。」
「姊姊並非不讓妳出去,只是希望妳出去前能和我打聲招呼,而不是話也未說上一句,便跑了個不見蹤影。」
白茹雪垂著頭,一副虛心受教的模樣。白茹雪朝有些擔心地望著她的村長吐吐舌頭,便又低下頭,囁嚅道:「姊姊,是茹雪錯了,茹雪下次不會再忘記了。」
白若沁搖搖頭。她這妹妹每回都是這樣,想來過不了幾天,便又會將她的叮囑拋到腦後了:「這次回來,妳就待在村裡,一個月之內不許再出去了。」
白茹雪聞言,立刻露出了難看的表情:「姊姊,一個月不讓我出去,我會憋死的。」
白若沁笑意盈盈,卻讓白茹雪的背後冷汗涔涔:「妳不會無聊的。這一個月,妳把書房中的那幾冊醫典看完,一個月後姊姊會考妳。若是妳答不上來,禁止出去的時間便再延長。」
「背醫典?姊姊,那會要了我的命的!」白茹雪頭疼不已,「姊姊,妳精通醫道,村裡已經有妳能替大夥兒看病了,為什麼還要我背醫典?我背來也沒用啊!」
白若沁張了張口,卻又閉上。要如何說,說她命不長矣?只能搖搖頭,表示此事沒有商量的餘地。
白茹雪垮下肩:「姊姊,妳不能這麼對我,那麼多的書,我記不下來。」
白若沁瞥了白茹雪一眼,硬下心腸:「妳天資聰穎,只要肯分出三分遊玩的精力,要記下那些東西並不難。」眼見白茹雪使勁地搖頭,她又涼涼加了句,「能討價還價,看來妳精神好得很。回去後,妳把醫典拿去抄上一遍。」
「先生,小雪丫頭平安回來就好了,她也知道錯了,妳就別再罰她了吧?」村長雖然有些畏懼白若沁,但卻壯起了膽子,為自己疼愛得如親孫女一樣的白茹雪求情。
白若沁嘆了口氣:「水伯,小懲大戒,不過是要讓她記住我的話。茹雪也已十七了,不再是個孩子,我只希望她能有些擔當罷了。」
「先生,小雪現在還小,還能再等幾年。至於這回,妳要怪,就怪老漢吧!當初小雪丫頭去城裡時和我提了,說是讓我同妳說一聲。都怪老漢的臭記性,一時間竟然忘了這事。先生……」
聽著村長急急地把事情攬在身上,白若沁無語了。她怎能對一個年紀可以當自己父親的老人怪責?她看向白茹雪:「這次先免了妳抄書的懲戒,但醫典還是得背。」
白茹雪的苦臉頓消,先是笑靨嫣然地抱了抱白若沁,接著又跑到了村長身旁,撒嬌地挽住村長的手臂:「就知道水伯最疼茹雪了,茹雪謝謝水伯。」
白若沁搖頭,淡淡一笑。是什麼時候開始,村民們對她的態度不同了呢?
對白茹雪是寵、是疼,如長輩發自內心地疼愛晚輩孫女一般;對她則是恭敬中透著畏懼,同她相處時,甚至也將身分放得極其卑微。將她捧到了極高的位置,卻也離得遠遠的。
白若沁站在一旁,看著白茹雪靠著村長撒嬌,說著一路上有趣的事情。白楓林則站在白茹雪身後,露出不同於平日的溫暖眼神,連冰冷的嘴角,都因白茹雪的話偶爾流露幾分笑意。
涼風吹過,衣袂飛揚,白若沁身上豔紅的衣色,在身後那片蕭索田野的映襯下,竟然平添了幾分孤意。
白若沁輕輕嘆了一聲,側過頭時,卻發現皇甫賢倚在樹下,正興味盎然地看著。
他竟然還在?真是個可怕的人,能將自己的氣息隱藏得幾乎讓人無視。若要與他為敵,後果恐怕難以想像。
微微蹙眉,白若沁帶著微笑開口說道:「讓皇甫公子見笑了,這是舍妹,白茹雪。」
白若沁喚了白茹雪一聲,白茹雪笑嘻嘻地轉頭後,頓時發現村裡有外人在,一雙晶亮的大眼睛,便直往皇甫賢的臉上打量著。
白茹雪突然眼睛一亮:「皇甫大哥,怎麼是你?你是來找茹雪的嗎?」說話的同時,她鬆了挽著村長的手,直衝到皇甫賢的面前,語氣中是說不出的驚喜與親暱。
皇甫賢嘴角輕翹:「我恰好路過此地,原來小雪兒也是白家村的人。」
小雪兒?不過甫認識的男子,白茹雪便讓對方喊自己的乳名?
白若沁蹙眉,無波的黑眸掩下萬般猜疑。
只見皇甫賢那張俊雅的面容微微帶笑,以不含絲毫調戲之意的口吻說道:「白家村山明水秀,也難怪小雪兒能生得如此靈秀。」
說起花言巧語,連眼皮都不眨。白若沁心中暗嗤。
但白茹雪聞此一言,紅霞立刻飛上雙頰,頓了頓,又說道:「前日皇甫大哥離開得早,茹雪在客棧裡找了大半日都沒找到呢。」話說出口,白茹雪才覺得這語氣略顯急切、大膽了些,因此咬咬下唇,又似解釋一般地說道,「我的意思是,一直沒找到皇甫大哥,連聲謝謝都沒來得及說,真是太失禮了。」
皇甫賢瞥了白若沁一眼,隨後望著春風滿面的白茹雪勾唇一笑:「不過是舉手之勞罷了。」
白若沁在一旁聽出了端倪,便淡淡問道:「茹雪,妳在外頭又惹麻煩了?」
白茹雪懷著少女心思,一心放在皇甫賢身上,就沒多在意問話的人,只是頗有些不服氣地說道:「還不是清和坊中的幾個登徒子!裡頭明明都是些賣藝不賣身的姑娘,他們還上前動手動腳的,我就是看不過去才出……」說到一半,白茹雪的話語戛然而止,頓時面露悔色,灰溜溜地看向白若沁。
「然後呢?」白若沁語調不變,靜湖般的眼眸看著白茹雪。
白茹雪偷偷覷了白若沁一眼,小心說道:「他們以多欺少,楓林又正好不在我身邊……但幸好皇甫大哥出現了,他幾下就解決了那幾個惡人呢。」眼見白若沁面上依舊沒有一絲波瀾,白茹雪心知不妙,急忙說道,「姊姊,妳別生氣,我去清和坊不過是想見見靜女姑娘,其他什麼事都沒做。」
白若沁的視線掃過白茹雪,白茹雪縮了縮脖子。
「大小姐,請不要歸罪於二小姐,是楓林保護不周。」白楓林上前,護住了白茹雪。
白若沁擺擺手,示意白楓林不用再說。
清和坊是萬春縣一家有名的舞榭歌樓,裡面的女子皆是色藝俱佳,姣好的姿色與身段,任挑一人,都比那花樓妓館裡的紅牌美上幾分。清和坊的姑娘雖然賣藝不賣身,可清和坊卻始終門庭若市。因為除了歌舞的確堪稱一絕之外,絡繹不絕的來客,更是為了清和坊中的名花--靜女。
清和坊開了一年多,但真正見過靜女的人,卻屈指可數。
傳聞靜女的容貌美豔絕倫,通曉音律書畫之外,連詩詞歌賦也無一不精。她最早現身於京城,在七王爺大婚的喜宴上獻舞。靜女的歌聲宛轉,妙如天音,揚袖飄舞,更是宛若九天玄女降世。那一舞讓靜女名動一時,可她卻也在一舞過後銷聲匿跡,等她再出現,便是兩年之後的此時了。
靜女的名號一出,京中的達官貴人們便都慕名而來,拋擲萬金,不過是想一睹芳顏。那些追花逐蜜的人,都是來自於危險的京師,這一直讓白若沁頗覺頭疼。但最讓她頭疼的,是自己那個不懂事的妹妹,閃避都來不及了,卻還自己送上門去。
白若沁暗自嘆了口氣,伸手揉了揉太陽穴。罷了,那些事能容得日後再提,如今之急,便是應付眼前這個充滿危險的男人。思及此,白若沁看向皇甫賢,客氣地道:「小妹給皇甫公子添麻煩了。」
「哪裡,小雪兒天真可愛,小小年紀便已胸懷俠義之心,日後想必不可小覷。」皇甫賢嘴角含笑,「而且小雪兒熱情好客,倒是很討人喜歡。」
白若沁聽懂皇甫賢的意思。是說她的逐客之道,非主人賢風嗎?她就是那樣的人,那又如何?
白茹雪聽到皇甫賢的一聲「喜歡」,一張俏顏更是通紅:「皇甫大哥喜歡茹雪?」
皇甫賢轉頭看向白茹雪,徐徐笑著:「這是自然。」
「那你今晚留下來嗎?」
白若沁微微一笑,道:「茹雪,皇甫公子不像妳整日無事,妳別耽擱了人家。」
皇甫賢瞥了面不改色,說著並非事實言論的白若沁,眸光頓時異彩流轉,似笑非笑。隨後他看向白茹雪,微微勾唇道:「待我事情辦好,自然會再前來拜訪。」
白茹雪雖然有些失望,但還是朝皇甫賢露出嬌豔動人的笑容:「那說好了,皇甫大哥一定要再來。」
白若沁的黑眸沉了沉,面上掛著淡淡微笑。那張略顯蒼白的臉,對比著豔紅的衣裳,更像一朵淡淡勾畫的水蓮。
皇甫賢對著白茹雪微微頷首,應承下來,而後便告辭離開。可當走過白若沁身旁之時,他輕微俯下了身,用低到只有她能聽見的聲音,在她耳畔輕聲道:「很期待我們的再次見面。」
因為皇甫賢走在另一側的關係,白茹雪等人無法看清他的動作,只像是見到他低頭在與白若沁說話。
未及白若沁反應,又是輕得幾乎聽不到的一聲:「小若兒。」
聽見這聲低喚,白若沁渾身一震。震驚地抬眼對上皇甫賢的俊容時,卻指見他眉尾微揚,唇畔帶笑,表情沒有任何不同。彷彿方才那聲稱呼,只是一時興起的叫喚。
「若兒,明日妳便下山去。」
「怎麼了?師父要若兒替您買什麼嗎?」
「妳已出師,此番下山,便不許再回來了。」
他是師父嗎?不,不是。
雖然在她的記憶裡,師父的臉已經模糊了,但她卻記得師父不是這副模樣。可為什麼皇甫賢也會叫她「若兒」?這稱呼,只有師父喊過……
但……師父已經不要她了!在他意識到她可能有的心意之後,便漸漸疏遠她了!
回到家,用過晚飯後,白茹雪如常地跑到了白若沁的屋裡。白茹雪鑽到床上窩著,向白若沁描述這次去城裡的見聞。
白若沁沏了壺茶,坐在桌邊,挑亮油燈,邊慢慢喝茶邊翻著書,偶爾應幾聲白茹雪的話,似聽非聽。
「姊姊,妳猜我這回進城見到誰了?」
「誰?」白若沁從桌旁起身,順手收好手邊的書,漫不經心地問道。
「素月姊。」
「素月?」白若沁思索著,手指輕敲著桌面,片刻後才開口道,「是六年前,和白井初一道離開的那個白素月?」
「嗯。」白茹雪點點頭,臉上滿是喜意,「算來已經有六年多沒見到素月姊了。不過素月姊一點都沒變,還是那麼漂亮。」
白素月並不是白家村的村民,而是如今白家村中,幾乎足不出戶的白清音的義妹。白素月小時家逢變故,流落街頭,後來白清音的父母在街上偶然遇見,可憐白素月孤苦無依,便將她收為義女,並帶回了白家村。
白清音性子靜,喜在家中看書,或做些女紅為家裡貼補家用;白素月性情較為活潑,與村中男子一同習武,加之她又生得美貌,因此頗得同齡少年的傾慕。
在兩人十五歲時,白清音的父母雙亡,二人自此相依為命。二十歲那年,卻因為青梅竹馬的白井初,姊妹反目成仇。按白茹雪的話說,就是白清音恨白井初選擇了白素月,便欲對二人施以毒手;而白井初為了保護白素月,身中劇毒,性命垂危。之後白素月就在悲憤之下,帶著白井初離開了白家村。
六年前事情發生後,白清音只有淡淡否認下毒,之後她便幾乎足不出戶。雖然事情最後不了了之,可白家村的人見到她卻仍有芥蒂。非但對她不理不睬,能避則避,村民更常常私下告誡孩子們,要孩子不能像白清音那般心思狠毒,絲毫不念手足之情。
白清音與白若沁的關係尚還好些,畢竟白若沁不怕村民說閒話,也沒什麼人敢說她閒話。對於白若沁的關懷,白清音心中感謝,卻從來不肯接受白若沁的接濟。白清音平日便在家中繡些繡品,月逢初一,白若沁替她拿去城中的繡樓賣錢,為她換些日常生活的用品。
白若沁靜默了許久,才問道:「妳在哪裡看到他們的?」
「我沒見到井初哥,只有見到素月姊。」白茹雪吐了吐舌頭,小聲說道,「是在清和坊。素月姊去年就回來了,只是怕還有人會傷害井初哥,所以不敢回白家村。幸好清和坊的老闆好心收留,這才讓素月姊有口飯吃。」
白若沁烏眸一瞇,將白茹雪的話在腦中篩了篩,又問道:「妳教訓的便是欺負白素月的人嗎?」
「是啊。」白茹雪一臉義憤填膺的表情,「那些該死的男人,把素月姊都氣哭了!」
「那些男人動手了嗎?」
「動手?」白茹雪瞪大一雙美眸,「動手的話那還了得,我非剁了他們一雙豬蹄不可!他們出口輕薄素月姊,說得真是難聽……哼,以為她是那些青樓的妓女嗎?」
白若沁笑笑,卻沒有再說,只若有所思地看著面前跳躍的燭火。
聽聞那白素月身手了得,她怎麼可能會任人欺辱?更何況,清和坊雖不同於妓館,可依舊是尋歡作樂的地方,姑娘被人輕薄之事雖少但絕非沒有。她在裡面待了一年,對於那種事的應對之策,怎麼可能還那般生澀?看來此女城府極深,只怕她這次回來是別有目的,說不定白茹雪會碰上那個場面,也是故意安排好的。
明日進城時,恐怕得去探探。
次日清晨,白若沁用過早膳,白茹雪還未起身她便進城去了。先將白清音的繡品交到繡房,換回銀兩之後,白若沁便拐到了西街。
西街是萬春縣的花街柳巷,妓院、相公樓都聚集在此。白若沁方進入西街街口,一種淫靡之感便襲上心頭。雖是白天,耳畔卻縈繞著絲竹管弦樂聲,一座座舞榭歌樓,豔歌妙舞的表演顯得十分熱鬧。
白若沁向前走著,未行多遠,便看到了目的地。高高的墨黑匾額中,紅豔三字寫著「清和坊」,字跡風流飄逸,彷彿舞伎們婀娜的舞姿。
白若沁頓了腳步,抬頭看了那匾額一眼,走了進去。方跨進門檻,幾個眉清目秀的少年便走上前來。
白若沁甫見幾位少年,倒是愣了一下,原來清和坊裡並不都是女子。一個身著青衣的少年恭謙地施了一禮,然後說道:「姑娘,清和坊夜間才開門迎客。」
白若沁微微一笑:「抱歉,我是來找人的。」
「找人?」青衣少年愣了一下,「不知道姑娘要找何人?青衣在清和坊已近一年,坊中之人倒也大多識得。」
名喚青衣便著青色衣衫?這倒是有趣。白若沁想了想,遂問道:「不知清和坊中,可有一位名喚『白素月』的女子?」
「白素月?」青衣低頭思索了片刻,猶疑地說道,「白素月這名字青衣聽來生疏,或許有,但恐怕來坊中後便改了名了。」
「是嗎?」白若沁微微蹙眉。
青衣見狀,又輕聲道:「不過坊中的邵華公子手上有本名冊,裡面記載著入坊之人的真名。若是姑娘急著尋人,青衣可以帶姑娘去找邵華公子,看看公子能否將名冊借姑娘一看?」
白若沁注視著青衣,微微一笑:「那就麻煩青衣相公了。」
青衣微微欠身,道了聲:「姑娘這邊請。」
步入坊中,隨處可見頭戴花冠,身穿華服,正為晚上歌舞做準備的女伎。白若沁跟隨在青衣身後一路無阻,不多時便進了清和坊的後院。
不同於前院的雕梁畫棟,富麗堂皇,後院顯得靜雅宜人,環境優美,帶著一種雅致的靜謐。道路兩側松柏蒼翠,鬱鬱蔥蔥,一山一石竟也精緻如畫。
白若沁走過了幾個院子,耳邊聽到潺潺的溪流水聲。拐過彎後,一條清澈明淨的小溪橫於眼前,溪上是一座拱石橋,曲徑通幽。
「你家老闆竟將溪水引進坊中,想法倒也獨特。」看著眼前如畫的景象,白若沁不禁發出一聲讚歎。
青衣轉過頭淺淺一笑,彎眸如月,對白若沁於自家老闆的稱讚倒也不謙虛:「老闆確實是個能人,否則也不可能在一年之內,便將清和坊經營至此。」
青衣話語剛落,兩人的身後突然傳來了急促的腳步聲。
青衣回頭望去,正見到一個舞伎打扮的女子追了上來。女子氣喘吁吁地拉住青衣:「青衣,老闆在找你呢。」
青衣扶了扶身形不穩的女子,之後便鬆了手,問道:「老闆找我何事?」
女子看了青衣一眼,似乎有些不滿地嬌嗔道:「我怎麼知道?她只是讓我來找你。」
「這……」青衣略為遲疑,「妳回去告訴老闆,說我帶這位姑娘去見邵華公子,片刻就回。」
女子有些不悅,跺了跺腳:「可老闆似有急事的模樣,連催了我好幾回呢。」
看著場面有些膠著,白若沁遂笑笑地開口道:「青衣相公,你儘管忙去吧。若是方便,請這位姑娘領我去見邵華公子也可以。」
青衣看了看白若沁,遲疑了下,還是點了點頭。隨後轉向女子說道:「雲鑼,妳領姑娘去清怡院,務必讓邵華公子見上一面。」
名叫雲鑼的女子側頭想了想,應道:「好吧,我帶姑娘去。那你快點去吧,讓老闆等急了發火,可別怪在我頭上。」
青衣點點頭,歉意地向白若沁行了一禮:「那青衣先行一步了。若是事情辦好,青衣會趕去清怡院的。」
「不麻煩青衣相公了。」白若沁搖搖頭,笑了笑,隨後便同雲鑼繼續前行。
雲鑼身上不知抹了什麼香料,氣味一陣陣撲進白若沁的鼻間。香氣濃郁逼人。聞久了,竟讓人有些昏沉。
走了幾步,雲鑼猛地一拍腦袋,蛾眉一蹙,焦急地喊道:「糟糕,我忘記告訴青衣去哪找老闆了。」
白若沁轉頭,臉上帶著了然的笑意看著雲鑼。雲鑼小臉一紅,隨之抱歉地說道:「姑娘請稍候,我去去就回。」說完,便匆忙地跑了。
這個雲鑼丫頭怕是對青衣有意,這才找藉口追去。無人引路倒也無妨,後院偶有人經過,雖然麻煩了點,但只要問問清怡院在何處,想來要找到也是不難。
如此想著,白若沁便緩步走到石橋一邊的涼亭坐下。溫煦的陽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她輕倚在涼亭的石柱上,一邊欣賞著後院景致,一邊看看能否遇見問路的人。
時節已入深秋,這清和坊卻彷彿將春色永遠留在了園中。溪中碧水,倒映著岸邊垂枝飄飄的楊柳,婀娜多姿,園中更有許多不知名的花草枝茂葉盛,蔥郁芬芳。
似乎走了太長的路,白若沁感到身子有些疲乏。她抬起一隻手,手肘支在側邊的欄杆上,微微閉上眼眸,想著略為歇息一會兒便好。
可等到白若沁清醒時,眼前的一幕卻讓她大吃一驚--此刻的白若沁,已不在方才休憩的涼亭內,而是在一間裝飾華麗的屋子中。入目是大紅銷金帳,連床柱三面的床板上,都雕著線條細膩優美的圖像,還是姿勢露骨的男女交合春宮圖。不僅如此,她還躺在一張雕花床上,身下的絲被柔軟細滑,想來絕非一般人家所用。
白若沁鬢髮蓬鬆,衣衫不整,歪著身子躺在床上,竟是感到渾身無力,連正常出聲也辦不到。如今到底是什麼情況?不知是被動了什麼手腳……白若沁閉上眼,回憶之前的情景,希望能找到一兩點的遺漏。然而記憶的最後一幕,只是那個暖風襲人的涼亭,除此之外,再無其他。
「妳醒啦。」一個帶著微微笑意的陌生男嗓,拉回了白若沁混亂的意識。
白若沁睜眸向聲源處望去,方才醒來時過於驚詫,她竟然沒有發覺房內還有一人。
只見對面的椅上坐著一個高大的男子,一身綢緞華服,俊雅如玉的面容上帶著一點的孤傲,一點的玩世不恭。男子原本斜靠在椅背,單手托腮地看著白若沁。見她清醒了,便動作優雅地起身,慢慢走向床榻。
「醒了就好,本王可不希望身下的女人像個死物,一點反應也沒有。」
說話的同時,男子褪下上衣並上了床榻。他的手臂纏上白若沁的纖腰,將她整個身子抱起移至大床正中,隨後壓倒在身下。
白若沁心中大驚,盡全力地曲起膝蓋擊向男子腹部。
若是正常時候,白若沁這一擊,男子非死也廢了半條命。然而此刻白若沁身中迷藥,力道幾無,她這一擊,也只是讓毫無防備的男子吃了個虧。
男子吃痛地退了開來,同時抓住白若沁襲擊自己的腿。他的黑眸中滿是詫異,皺眉問道:「怎麼回事?妳懂武?」
就在這時,白若沁注意到男子手上戴著的兩個指環。食指上的是色澤純粹的紅玉,而拇指上的扳指顏色墨黑,似是上好的玄鐵所製。
白若沁眸光一斂。
一年半前,她曾在京城一人手中見過相似的扳指。那個人讓白茹雪身陷險境,為了救白茹雪,她付出了相當慘痛的代價。加上男子剛才自稱「本王」。
比起醒時發現中計的意外,此時遇到不想遇到的人,更是讓白若沁大感糟糕。腦中思緒萬千,最後盡數化成了一句話:「穩住他,不能讓他發現我的身分。」
一瞬的紊亂過後,白若沁恢復了清明,她對上男子高深莫測而帶著些防備的俊眸。她的唇邊漾起諂媚笑容,朱唇輕掀,嬌羞卻無聲地用唇形輕喚了一句:「王爺。」
男子一頓:「妳方才是戲弄本王?」
白若沁垂眸,故作羞意地點點頭,又慌忙搖搖頭。
男子眼中的錯愕慢慢化為虛無,原來是為了吸引他而想的新招數嗎?民間女子果然多巧思。他點了點白若沁挺翹的鼻梁,低聲笑道:「妳這招倒是有些意思。」
慾望漸漸回歸眼底,男子又恢復了先前的慵懶模樣。
熱燙的手輕撫過白若沁的面頰,男子低沉笑著:「雖然年紀是大了些,但這長相倒還符合本王喜好。都言凝雅樓的花娘個個年輕貌美,以妳這般年歲還能在凝雅樓占據一席之地,果然也是有幾分『功夫』。」他以調笑的口吻說著話,「尤其,妳還有一雙如此美麗的眼睛。」他的手指輕輕撥弄著白若沁細密濃長的睫毛,原來這王爺把她當成青樓的女妓了。
白若沁雖不知為什麼會從清和坊被人弄到這,但若沒有猜錯,她怕是被人設計了。是誰?是一場意外,還是早就設好了坑讓她往裡跳?她又是什麼時候中的招?
在昏黃的燈火之下,白若沁的髮色比白日看來更淡了幾分。烏絲披散在大床上,襯著身上豔紅的衣裳和身下柔滑的白絲被,讓她帶著一絲勾人的嫵媚。
男子修長的手指勾住一綹長髮,放到唇間輕輕碰了碰,視線依舊不離白若沁靜秀的臉龐。
接下來該怎麼辦?白若沁靜靜地想著。
雖然如今渾身無力,但若是要施術恢復體力保全清白,也並非不可能,不過是損失了另外一部分的東西罷了。可她要考慮的並非只是自己能否逃脫,而是整個白家村的存亡安危。若是因為她逃了,反而引起男子懷疑……一個王爺,要在萬春縣的方圓百里內找到她,簡直易如反掌;而找到了她,就意味著白家村的暴露。
他們逃了皇族整整百年,戰戰兢兢地生活著,就是怕會遇到皇家的人,怕會因百年前護國祭司的潛逃而加罪於己身。而如今,她卻該死地遇到最不能遇上的皇家之人。
要她用清白,換取保全白家村嗎?
若是母親在世,她必會這般表示吧?那是身為白氏祭司必須承擔的,而如今她也要為了白家村,失去身為女人最重要的東西了嗎?
「妳在想什麼?」注意到白若沁的心不在焉,男子興味地問。這種時候,女人不都該是使出渾身解數,來討好、侍候他嗎?
陌生的男人氣息飄進白若沁的鼻間,帶著淡淡的龍涎香。
白若沁回神,唇邊的笑意,假飾成歡場女子的迎合和順從,而他眼中探索的興味也隨之消失。
男子的手慢慢鬆開指間纏捲的長髮:「忘記妳被他們下了藥,不能說話是吧?倒真是有些掃興!他們以為本王駕馭不了一個女子嗎?別說是個不賣身的藝女,即便是再頑抗、再貞潔的女人……」他低低笑著,手指掠過白若沁的頰面、下巴、頸項,指尖順著豔紅的衣裳,游移在曲線玲瓏的柔軟身子上,「在本王手下,都會化成繞指柔的。」
從未接觸過性事的白若沁,在男子的蓄意挑撥之下,身子微地一顫。
細微的顫抖取悅了男人,男人低頭,強勢地封住白若沁的唇。一熱一溫的交融,升騰的體溫,隱約的低啞喘息,讓朱紅帳內頓時春光旖旎。男人的黑眸因此堆積了更為深沉激狂的慾念,纏吻著她柔軟的雙唇,一手則挑開了她的衣領,順著優美的頸項一路滑行而下。
白若沁蹙起眉頭,隱忍地放任身體自主的反應。緋紅的臉龐,迷離朦朧的雙眸,壓抑不能自制的喘息。她無法反抗,也不能反抗。
男人笑意漸深:「羅衣,妳要遂了本王?妳賣藝不賣身的原則,為本王打破,也不悔嗎?」
白若沁更加貼近男人的胸膛,垂斂的眼底是淡淡的一點諷刺。點了點頭,又輕輕搖了搖頭。看到了白若沁的動作,男人滿意地笑了起來。
正欲更進一步時,門外低聲的稟告傳進屋中:「王爺。」
男人蹙起了眉頭:「何事?」
門外的人低聲回道:「西院夫人來了。」
「夕煙?」男人鬆開了攬著白若沁腰身的手,慢慢地坐起身,隨意說道,「讓她進來吧!」
門被輕輕地打開,一個消瘦精幹、蓄著白鬚的老者走了進來。老者步伐堅定,身骨筆直,顯然是有幾分功夫在身。他的身後跟著三四個捧著乾淨衣物,和一個端著沉香木盤的丫鬟。
幾人進門之後,門口處又出現了一個極為美麗的年輕少婦。少婦大約二十出頭,體態修長窈窕,容貌姣好,面上略施脂粉,眼角眉梢若有似無地流露著無限嬌媚。她身穿桃紅色的裙裳,在漆黑的夜色中彷彿嬌豔的桃花,烏黑的長髮盡數上挽,繁雜的髮髻,華麗的服飾,顯得豔麗而貴氣。這少婦就是此王爺所謂的西院夫人,名喚阮夕煙。
男人黑沉的眸子掃到少婦時,唇邊微微上揚:「夕煙何時來的?」
見男人懶洋洋地從床上起身,阮夕煙迎上前,仰著漂亮的臉蛋嬌笑地貼在男人身上,渾身軟若無骨:「妾身方到不久。因為許久未見王爺,思夫心切;加之京中有要函得呈給王爺,這才未等天明就來求見王爺。」勾魂的美眸掃過白絲被下遮掩的白若沁時,眸色未變,「擾了王爺歇息,是妾身不該。」
阮夕煙一邊說著,一邊從懷中抽出一紙封了蠟的信箋。纖纖玉指一彎一勾,有種說不出的風情萬種。
王爺勾了勾阮夕煙的下巴,笑道:「本王的西院夫人縱使有萬般的不是,都值得原諒。」
白若沁冷眼看著這對鴛鴦打情罵俏。
阮夕煙站直身子,指著那些丫鬟手上的東西說道:「放下吧,妳們先出去,王爺有我服侍就行了。」
「是。」
丫鬟們福了福身,相繼走了出去。而那個老者依舊留下,只是垂首侍立一旁,恭敬不語。
王爺隨意卸下身上鬆散的裡衣,而阮夕煙從桌上取過衣物,一件一件寬衣整裝,最後更是跪坐在男人腿邊的地上,細心地為他套上白襪軟靴。
「姊姊們在京中,也對王爺頗為想念。」一邊服侍著男人著衣,阮夕煙一邊輕言道,「夕煙聽得管家收到王爺的口信,說您如今在這萬春縣,夕煙便再也等不住。得了側王妃的同意,便隨管家過來尋王爺您了。」待得一切完畢,阮夕煙起身靠近男人,輕輕依偎著他,「王爺離京多日,卻連封信都不回給夕煙,怕是已對夕煙厭倦了吧?」
一點點的嬌嗔、一點點的幽怨,卻讓人打自心底升起一股憐惜。
男人低沉而霸道地笑著,伸手輕輕一攬,將阮夕煙摟入懷。在她一聲驚呼之中,隨即封了她的唇舌。待得放開,阮夕煙已然嬌喘嚶嚶,美目迷濛,倚靠在男人的懷中,柔若無骨。
男子有些粗魯地撫摸著溼潤的紅唇,眼中再次升起了野性的慾望。
阮夕煙嬌羞地搥了搥男人堅實的胸膛,若黃鶯啼鳴的柔音輕聲道:「王爺……別在這,回別館吧。」
看著愛妾嬌羞動人的模樣,男人心底愉悅,從喉嚨中發出低笑後,伸手捏了捏阮夕煙的纖腰,說道:「如妳所願。」
臨走前,他似是想起了床上一語不發的白若沁。轉過身,卻意外捕捉到了白若沁臉上的表情--像是鬆了口氣般安心的神色。
安心?他挑了挑眉。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公子你被看上了(卷上):宿命的圖書 |
 |
公子你被看上了 卷上宿命 作者:暖暖菜 出版社:夢田小筑 出版日期:2014-09-29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52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90 |
小說/文學 |
$ 220 |
羅曼史 |
$ 22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公子你被看上了(卷上):宿命
身為祭司,情愛無歸,但要生子以繼血統。個性溫和但骨子倔強的白若沁,她不信命定傳說、不睡身邊侍從,一心想找尋你儂我儂的真愛。差點失身於應寧王爺時,她遇上了清冷的邵華。所謂佳公子難求,俊美無儔的更難求,白若沁當然是厚著臉皮『上』了! 為了保住白家村的祕密,白若沁逼皇甫賢立下奪命血誓,可皇甫賢卻以真心相報,贈予珍稀靈藥又處處維護,企圖保下她的一條命。為什麼?他的目的又是什麼? 可是她自以為找到的真愛,卻惡狠狠地被命運捉弄了!東衡皇族步步緊逼,柯藍神使陰險設陷。 天下之大,竟無白若沁的容身之地。一身染血紅衫,無情地大殺四方,她只乞求上蒼垂憐,拜託讓她來得及,來得及救下那個人……
作者簡介:
暖暖菜,雙子座,喜歡大笑的人生,希望到老也是個愛笑的老太太。心裡住著一個老小孩,夢想當個天馬行空的說書人,用文字編織幸福溫暖的世界,那裡,每個人都是有福氣的孩子!
章節試閱
第一章險失清白
七歲時,師父將流落街頭、饑寒交迫的她帶回山中。師父給了她一個名字,白離。自此她有了自己的名字,有了自己的家。
十歲時,白離多了一個比自己小三歲的師弟,白尚思。也是在那時她才知道,獨身一人的師父,其實心中一直占著一名女子。
「師父,那女子是什麼樣的人?」
「她心思狠絕,孤恩負德,詭計多端,無情無心。即使將她千刀萬剮,也不足以抵上她犯下的罪。」
白離的師父說得淡淡,白離卻聽得心驚。這便是師父放在心底,難以忘懷的女子嗎?為何在師父口中是如此德行?只是,即便白離的師父說著毫無讚譽之辭的話...
七歲時,師父將流落街頭、饑寒交迫的她帶回山中。師父給了她一個名字,白離。自此她有了自己的名字,有了自己的家。
十歲時,白離多了一個比自己小三歲的師弟,白尚思。也是在那時她才知道,獨身一人的師父,其實心中一直占著一名女子。
「師父,那女子是什麼樣的人?」
「她心思狠絕,孤恩負德,詭計多端,無情無心。即使將她千刀萬剮,也不足以抵上她犯下的罪。」
白離的師父說得淡淡,白離卻聽得心驚。這便是師父放在心底,難以忘懷的女子嗎?為何在師父口中是如此德行?只是,即便白離的師父說著毫無讚譽之辭的話...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暖暖菜
- 出版社: 夢田小築 出版日期:2014-09-29 ISBN/ISSN:978986281729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52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