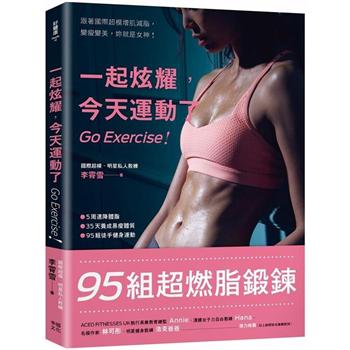前情提要
自現代魂穿到大名朝的譚七葉,清醒後便發現她的處境十分難堪,親人以她八字和奶奶相剋為由要將她送走。爹娘雖極力反對,但爺爺、奶奶非常信任神棍二叔,若不是疼愛她的鄰居沈夫人出手醫治奶奶,她恐怕難逃被送走的命運。
那知奶奶的病情才剛好轉,弟弟六郎卻病危而命在旦夕。奶奶不願出錢讓六郎看大夫,幸好六郎吉人天相,路上巧遇神醫溫修宜相助,因而撿回一條命。七葉為了改善大房的處境,決定運用自身的異能來幫助家人。在青梅竹馬沈南的協助下,她與鎮上的酒樓「悅客來」開始做生意。
堂姊三桃在鎮上遭韓大少調戲,對方意欲強搶,沒想到二嬸為了救女兒竟然七葉推出去讓人搶。幸好得沈夫人再次搭救,二嬸卻在親人面前顛倒黑白,將所有過錯推在七葉身上。親人的刻薄相待,讓七葉明白想要讓一家人過上舒心的日子,唯有分家一途。雖然孝順的老爹一開始極力反對,仗持老爹對家人的愛,她有信心能改變老爹的態度,決定慢慢進行她的分家大計。
第一章兄弟情深
趙氏開口對譚老爺子說道:「老頭子,請家法吧!」她的語氣十分柔和,無絲毫怒氣。
吳氏頓時渾身冰涼,她以前曾見過譚家行使家法的場面,只要一想起就會膽顫心驚。她在心中恨恨地罵著趙氏:「該死的老妖婆,拿了我的鐲子,逼我應了二郎的親事安排,現在卻要用家法來收拾我,妳怎麼不去死啊?老妖婆!」
譚德金和徐氏也變了臉色,特別是譚德金,除了震驚外眸底還有痛苦。因為十三年前,他曾受過一次家法,那種痛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吳氏拉了趙氏的褲腿哭著求:「娘,求您了,別請家法,我已經知道錯了,求您饒了我吧!」
譚德財也跪下來求道:「娘,您大發慈悲,饒了秋蓮這一回吧。秋蓮身子弱,可受不住啊!」
趙氏不為所動,冷冷地道:「吳氏以下犯上,本該休出譚家,如今我和你爹已經網開一面,你們還好意思來求情?」她的眼神不經意往徐氏這邊飄了飄。
譚老爺子也點頭贊同:「你娘說得沒錯,國有國法,家有家規,這次老三媳婦的確做得太過分。」說完,他起身走出去,片刻後,手中捧著一個方形的木盒回來。
譚老爺子打開木盒,將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七葉終於看清譚家的家法長什麼樣子,是一根長長的軟鞭。整條鞭上布滿硬疙瘩,再細看,那些硬疙瘩的邊緣都十分鋒利。
七葉的身上起了一層雞皮疙瘩,暗罵道:「好變態的家法,也不知是哪位先祖想出來的?這到底是對付家人,還是對付仇人呢?」
趙氏一腳踹開譚德財,罵道:「老三你敢再求情,我連你一塊兒打!沒用的死東西,看著吳氏打我,你吭都不吭一聲,白養了你這畜生。」
譚德財只得起身站去一邊,暗暗為吳氏祈禱。
考慮到吳氏是婦人,譚老爺子決定只打十下,由趙氏親自操鞭。
譚老爺子讓兒子們帶著他們的孩子離開,他也出了屋子,只留趙氏和三位兒媳在裡面。
七葉他們站在門外,聽到吳氏淒厲的叫喊一聲聲從窗櫺間飄出,激蕩著眾人的心房,大家的面色都十分沉重。
門打開後,徐氏是第一個走出來的,她的嘴唇泛白,臉色十分不好,可能是受了刺激。
趙氏喊了譚德財和二郎、四郎進去,過了一會兒,他們抬著吳氏出來。雖然吳氏的身上蓋著衣服,但七葉還是聞到了血腥味,吳氏已經暈了過去。
第二日,譚德財私下拿了錢去為吳氏抓了一些藥回來,為吳氏治傷。
吳氏已經醒了,她痛苦的呻吟聲在院子上空迴盪。她的血衣四棗拿去扔了,就算洗乾淨也無法再穿,因為都打爛了。
巳時,鄭婉如來到譚家為趙氏診病,一進院子就聽到吳氏的痛呼聲,眉毛不禁擰了擰。
七葉一直在等她,忙迎上去親熱地道:「伯母好,客人走了嗎?」
「嗯,剛送她坐馬車離開。」鄭婉如笑咪咪地應道。
昨日譚家發生的事,鄭婉如已從李嫂的口中知曉。現在聽到吳氏的聲音,猜吳氏應是受了趙氏和譚老爺子的責罰。這是別人的家務事,譚家人不說,她自然不會去問。
七葉牽了鄭婉如的手去到上房。
「沈夫人來了,勞煩您了。」見到鄭婉如進來,譚老爺子和趙氏趕緊起身相迎。
鄭婉如笑著擺擺手道:「客氣了。老夫人,身體現在感覺怎麼樣?可還有哪兒不舒服?」
趙氏青腫的眼睛,她視而不見,只在心裡搖頭嘆息。這一家子好好的日子不過,天天這樣鬧騰不累嗎?
趙氏伸伸胳膊,蹬蹬腿,然後笑著說道:「沈夫人,我現在渾身舒坦,只不過腿不太有力氣,其他倒都還好。」
鄭婉如點頭道:「您病了這樣久,身體還有些虛,我來替您把把脈。」
兩人坐下來,趙氏微捲袖口伸出手讓鄭婉如診脈。
徐氏和譚德金聞訊趕過來,在一旁安靜地等待結果,面上的表情十分緊張。
終於,鄭婉如鬆開趙氏的手,面上笑容漾開:「恭喜老夫人,您的身體已痊癒,可以再喝兩副藥補身體,也可不喝。這幾日莫做重活,三天後,恢復正常的生活即可。」
「太好了。」所有人都喜道。
徐氏和譚德金更是眼中有淚花,總算等到這一天,能為七葉正名了。
趙氏也笑著拭了下眼角,病了這樣久,都不抱希望了,誰料到竟然被治好了,怎能不高興?她誇張地笑道:「沈夫人,勞您再開兩副藥,您的藥是神藥,我要多喝些。」
鄭婉如也笑道:「譚老夫人,是藥三分毒,吃多了並不好。您之前枉喝了很多藥,現在還是不喝為妙,多吃些營養滋補的食物也是一樣的。」
「好,好,我一切聽沈夫人的安排。」趙氏立刻點頭同意,將鄭婉如的話當成聖旨來聽。
譚老爺子也轉過身抹了抹眼角,然後對譚德金說道:「老大,拿些錢去鎮上買些東西,晚上請沈夫人一家人過來吃飯。你娘這條命是沈夫人救的,這份大恩我們一定要好好感謝。」
鄭婉如伸手攔了譚老爺子要給錢的動作,認真地說道:「老爺子,不用如此客氣。只要譚老夫人身體無恙,我打從心裡高興。這樣,我就不用擔心七葉會被送走。您們該感謝譚大哥和譚大嫂養了這樣好的女兒,譚族長都誇七葉聰明伶俐,是十分難得的好姑娘。您們可要善待她,不然,我可就要搶回去當女兒了,呵呵……」
「七葉能得沈夫人厚愛,那是她的福氣。不過,要是沈夫人想搶回去做女兒,先得問過她爹娘,我們可不敢作主。」趙氏笑著說道,很會見風使舵,向鄭婉如表明態度,不會再隨便對待七葉。
鄭婉如欣慰地笑了。
七葉十分感動,有伯母如此,真是幾生修來的好福氣。
送走鄭婉如,譚德金、徐氏帶著七葉再次去了上房。
譚德金說道:「爹,娘的病現在已經完全好了,那當初德銀說那些話是什麼意思?他為什麼非要將七葉送走?您是不是該讓他給我們一個說法。」眸子裡已有怒火。
當初譚德銀說七葉剋趙氏和六郎,若不將她送走,趙氏的性命堪憂,甚至說了最後期限。譚德金夫婦因不捨七葉,被趙氏打罵過多少回,七葉躲進山芋窖差點送命。所有的一切,都因譚德銀的那句話。如今趙氏病癒,於情於理,譚德銀都該給譚德金夫婦和七葉一個解釋。
「好。」譚老爺子點了頭。
譚德銀正躺在床上假寐,聽說譚老爺子找他,起床去了上房。
譚德銀進上房後,從容自若地與大家打招呼,彷彿沒瞧見譚德金夫婦噴火的眼神。父親找他來為了何事,他心知肚明。他早想好了說辭,所以有恃無恐。
「德銀,方才沈夫人來過,替你娘診脈,說你娘已經痊癒。」譚老爺子說道。
譚德銀立刻面現喜色,說道:「太好了,娘,您總算是無恙,這些日子我的辛苦終於值得。」
譚德金怒道:「老二,是七葉求沈夫人來幫娘治病的,抓藥、煎藥你更沒動一根手指,你怎麼又辛苦了?」
譚德銀用一種鄙視的眼神看著譚德金:「大哥,你不會真的以為娘是吃藥吃好的吧?」
「這不是廢話嗎?當然是吃藥好的。」譚德金十分不悅地駁斥。
譚德銀冷哼一聲,說道:「大哥,我早就說過你不懂,你不信。當初我讓你們將七葉送走,你們死活不聽,說一句良心話,當時我真的非常生氣難過,想甩手不管這事。可我不能置娘的生死於不顧,那要遭天打雷劈的,於是我趕緊去山上求我師父。師父見我誠心救母,就傳我一道師門不傳之術,每天為娘唸經祈福,不然娘現在還不知會怎樣呢!」
徐氏冷著臉問道:「既然二叔有這樣的好本事,當初為何不先說一聲?讓我們天天為娘擔憂。娘的病一好,你就跑來說是你的功勞,你真將我們當傻子不成?」
「大嫂,此言差矣,天機不可洩露。當時我要是說出來,此法就不會靈驗。」譚德銀一本正經地說道。
七葉微笑著問道:「不知二叔用的是什麼法子?」
「此乃我們道家的法術,怎能隨意向外人透露?」譚德銀一臉鄭重地說道。
七葉點頭,又問:「二叔,這樣說來,以前您能未卜先知,現在還能治病救人了?」
譚德銀斜了她一眼,不悅地道:「什麼叫現在能治病救人?我一直都能未卜先知、治病救人,你們若早聽我的話,六郎的病早好了。」
譚德金氣得只想上前揍譚德銀,徐氏氣得面色泛白。譚老爺子和趙氏在一旁靜靜地聽著,至於信不信,只有他們心中清楚。
七葉輕撫下手掌,喜孜孜地道:「二叔,真是太好了!三嬸受了那樣重的傷,您趕緊去救她吧!不是有一句話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妳三嬸是前世作惡太多,這輩子必須要受此罪,才能洗盡前生的孽障。因此,不可去救。」譚德銀說得十分玄妙。
「哦,原來是這樣啊!」七葉一臉恍然大悟的表情,而後指著趙氏青腫的臉,「二叔,依您話中的意思,奶奶受傷的原因,也和三嬸一樣嘍。」
這是變相說,趙氏受傷也是前世作惡太多,此生要遭受苦難。
趙氏眼神一凜,瞪向譚德銀,罵道:「老二,你在孩子面前胡扯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
譚德銀掃了眼七葉,眸底閃過森冷的寒意,忙對趙氏擺手說道:「娘,您別聽七丫頭亂說,我說的是三弟妹,和您無關。您的傷是因您生性仁慈厚道,這輩子總要替家裡人受苦、受委屈。」
趙氏的面色稍緩。
七葉再次恍然地問道:「二叔,對不起,剛剛是我誤會了。奶奶是好人,那麼她的傷,您就可以醫治了,快將奶奶臉上的傷治好吧!奶奶病了這樣久,好長時間都沒出去透透氣,明兒我們帶奶奶去縣城裡逛逛,開心一下。」
這個建議趙氏十分喜歡,病了幾個月,哪兒都不能去,真的是憋得慌。她正好想去縣城大梅家一趟,問譚桂花的親事可有著落。
「是啊,老二,你就把我臉上的傷治治吧!明兒我想出去轉轉,這個樣子可不好出門。」趙氏笑著說道。
譚德銀嚥了下口水,搖頭道:「娘,您這傷要是現在治好了,那您為家裡受的苦就白受了,其他人會因此遭罪,不能治。」
「娘是家中的長輩,我們這些做小輩的,哪能看著娘為我們受苦?二叔儘管放心治,我們小輩不怕遭罪。」徐氏悠然出聲說道。
「難道二叔怕這罪落在您的身上,所以不願意為奶奶治?」七葉眨著黑眸問道。
「七葉,我是妳二叔,怎麼用這種口吻對我說話?」譚德銀的臉色變得有些難看,擺起架子來。
「老二,要是能治就趕緊治,要是治不了,就說實話吧。」一直沉默的譚老爺子開口了,眸子微瞇,看不清裡面的情緒。
「爹,當然可以治,只是並非立竿見影,要過幾日才能全好。」譚德銀應道。
「要幾日?」趙氏問道。
譚德銀沒說話,只是伸出左手,張開五隻雞爪子。
「要五天?」趙氏再問。
譚德銀點頭。
七葉忽然問道:「爺爺、奶奶,您們信不信二叔所說的這些話?」
「信,當然信。」趙氏毫不猶豫地答道。
譚老爺子沒回答,反問七葉:「七葉,妳為何這樣問?」
七葉答道:「爺爺,因為二叔的話我越聽越糊塗,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想著要是爺爺和奶奶明白,能否解釋給我聽聽?」
「有何不明白的,說出來聽聽。」譚老爺子溫和地抬抬手。
七葉說道:「爺爺,二叔說他治奶奶臉上的傷要五天。可大家都知道,奶奶臉上傷不重,不去管它五天也能好。可我就糊塗了,二叔如此超群的醫術,怎會和不治療的效果一樣呢?還有上次三郎和四郎哥哥受傷,二叔為何還要去抓藥,那豈不是浪費錢嗎?
「二叔說他能未卜先知,為何三桃姊姊差點被人搶走?為何三嬸會將奶奶打傷?吳家人來鬧事時,二叔不知去向。莫非他就是知道會發生這事,所以故意躲了起來,特意讓爺爺您蒙受奇恥大辱?爺爺,七葉愚鈍,您能為我解釋一下嗎?」
「老二,你解釋給七葉聽聽。」譚老爺子的聲音依然平靜無波,但仔細看,能發現他雙手的青筋突起,似在極力隱忍。
譚德銀恨不得一腳將七葉踹去天涯海角,這樣就不會被逼得要窒息。
「老二,七葉的事,你給一個說法吧!可不能白白讓她受了那些委屈。就為你的一句話,她差點失了性命,你難道就不覺得心虛嗎?」譚老爺子用煙杆子重重地敲著桌子問道。
「爹,我是真心為了娘,您為什麼就不信我,而信一個黃毛丫頭?七葉大字都不識一個,她說的話您也信啊?」譚德銀辯解道。
譚老爺子不屑地看著他冷笑道:「七葉大字不識一個?告訴你,她識的字不比你少,她自幼有沈夫人教導,見識比你強多了。今日面對吳家幾十號人,七丫頭毫不怯場,逼得吳家豪當場就白了臉,要是你,你能做到?呸!」
七葉識字?譚德銀感到驚訝不已,不服氣地道:「爹貶低我,您也沒什麼面子吧?」
「譚德銀,你給老子跪下。」譚老爺子終於變臉。
「爹?」譚德銀像被雷劈了,以為聽錯了。他轉而面向趙氏,「娘,您勸勸爹,這算什麼?我天天累死累活為了家,他卻這樣對我。」
趙氏抿抿唇,看向譚老爺子,說道:「老頭子,算了吧。」又對譚德金說,「老大,都是自家人,事情過了就算了,別鬧得這麼難看,七葉不是好好的嗎?都回去吧,這事就這樣了!」
「不行!」徐氏堅決地搖頭。
譚老爺子霍然起身,拿著煙杆對譚德銀的頭上打去。
「啊!爹,您這是做什麼?」譚德銀忙用手去擋,煙杆稍偏了下,但還是打中他的額頭。
「娘,大哥,救命啊!」譚德銀痛呼一聲,趕緊起身向門外跑去。
「打死你這死東西,讓你一天到晚胡說八道!」譚老爺子扔了煙杆,拎起一張小圓凳子,對著譚德銀的後背砸去。
「老頭子,使不得啊!」趙氏急著去拉,可惜已經遲了,凳子正中譚德銀的肩。
譚德銀的身子往前一個趔趄,差點摔倒,但不敢停留,忍痛跑回家。
譚老爺子實在是太過憤怒,主要是因為下午吳家來人時找不到譚德銀,他還撒謊。
譚德金忙上前拉了譚老爺子,扶他坐下:「爹,有您這態度,我們就知足了。這事就算了,往後我們也不提了。」
「唉!」譚老爺子長嘆口氣,點點頭。
趙氏不滿地罵道:「老大你現在才吱聲有什麼用?老二都差點被你爹打死,你還不趕緊去看看?」
「嗯。」譚德金點點頭。
徐氏眉頭擰了擰,連忙說道:「娘,二叔此刻正在氣我們一家人,德金去不合適,鬧不好會打起來。二叔那兒有二弟妹和孩子們,沒事的,我們先回了。」然後拉著譚德金出了屋子,七葉跟在後面。
譚德金卻指著東廂,有些猶豫,說道:「明秀,楊氏好像不在家,我去瞅一眼就回來。」
「你要是去了,就別再回來,和他們一家人過日子去吧!」徐氏鬆開他的胳膊,牽了七葉,頭也不回地往月亮門走去。
「別回來了。」七葉學著徐氏的口吻,也回頭對譚德金說。
譚德金看著妻女的背影,又看看冷清無動靜的東廂,面現難色。正在為難間,趙氏從上房出來,喊:「老大,你杵在那兒做什麼?還不和我去看看老二!」
「哦,娘,我……有些不舒服,先回去,等會兒過來。」譚德金找了個藉口匆匆跑向後院。
譚德金推門進屋,本來正在說話的妻女,忽然全部閉了嘴。六桔率先拿著針線活推門出去,緊接著是七葉和二霞,徐氏也掀了簾子進內室,獨留他一人在外面,十分尷尬。他抓了抓腦袋,厚著臉皮進了內室:「明秀,我……沒去。」討好地笑著說。
徐氏坐在六郎的床上縫一件男式舊褂子,頭也不抬地說:「去吧,那可是你的兄弟,反正他還沒將你女兒逼死。」
「明秀,妳別這樣。」譚德金訕訕地說。
「那我該怎樣?」徐氏猛地將褂子拍在床上,抬頭怒問,「譚德銀非要將七葉送走,這是畜生才會做的事。人家幾時將你當作兄弟對待過?你在那心疼他,難道還怕他死了不成?他不是能未卜先知會治病嗎?讓他給自個兒治病去吧!他要是死了,那是報應!」
譚德金被逼問得啞口無言,默默地掀了簾子出去,垂頭坐在小矮凳上沉思,想他是不是真的做錯了,傷了妻女的心。
「啊喲,我不想活了,你們將我打死算了,這還有沒有天理啊……」門外忽然傳來楊氏驚天動的哭喊聲。
譚德金下意識看了下內室,然後開門出去。身處內室的徐氏聽到動靜,也掀了簾子出去,七葉三姊妹從房間聞聲出來。
楊氏見譚德金夫婦出來,眸底深處閃爍著陰森的寒意。她快步上前一把拉了譚德金的胳膊,像個瘋子一樣叫道:「大哥,你也打死我算了,只要想想我家大郎,我就不想活了,這活著也是受罪,你打死我啊!」
徐氏忙上前將楊氏的手拉開,皺眉說:「妳這是什麼意思?」
七葉聽著楊氏的話,感到萬分不解,還以為她是為譚德銀被打一事來鬧,怎麼扯到大郎身上了?
楊氏揉了揉眼睛嚎道:「大嫂,當年德銀為了你們一家子,費了多少心思,甚至不惜毀了大郎,我就是來問問你們,還記不記得這事?德銀現在躺在床上不能動,你們高興了吧?現在你們家的日子好過了,就反過來要害我們家德銀了,你們還是不是人啊?」
七葉聽得莫名其妙,可譚德金和徐氏卻面現愧色,徐氏沉默半晌後,說道:「當年的事我們都還記得,只是我們並沒害二叔,是他想害七葉才被爹打的。」
楊氏的怒火又旺了起來,跳起來罵:「大嫂,妳還好意思提七葉?當年三叔要將她送官打死,是我和德銀拼死護著,才救她一條命。如今倒好,她長大了,翅膀硬了,不但不報恩,反而想著要害死德銀。要早曉得她是個害人精,當年就不該救,讓她死了倒好,省得現在天天興風作浪。」
「妳嘴巴放乾淨些,誰是害人精?七葉年紀小,妳身為長輩,少說這些缺德話。」徐氏立刻反駁,聲調拔高。
楊氏冷哼:「你們家七葉會說話就是反常,自從她會說話後,家裡發生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都是她惹出來的。」
「二弟妹,妳要再敢這樣說七葉,小心妳的舌頭。」一直沉著臉未開口的譚德金,終於冷冰冰地說。
楊氏不由自主地想起上次,他拿刀指向她的情景,腿有些軟。
正在這時,三郎匆匆地從月亮門那邊跑過來,邊跑邊喊道:「娘,爹叫您回去。」
楊氏回頭瞪他一眼,不理會,咬牙對譚德金夫婦道:「我和德銀從來沒虧待過你們大房,為了大房,我們失去多少東西,你們晚上睡覺摸著良心好好想想!」
三郎已走過來,伸手將楊氏往月亮門推去:「娘,爹有急事找您!」
楊氏低聲斥道:「呸,無用的死東西,我的話還沒說完呢!」
「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三郎低聲說道。
譚老爺子的怒吼聲傳來:「老二媳婦,妳在那兒做什麼?快給我滾回去,不然連妳一起打。」
楊氏臉一白,十分不甘心地跺了腳,臨走前指著譚德金和徐氏說道:「你們摸著良心想想,大郎成了什麼樣子,這樣害德銀你們還有沒有人性?」然後轉身離開。
「唉!回去吧!」徐氏擺擺手。
七葉沒挪動步子,皺緊眉頭問:「二嬸說二叔為了我們家毀了大郎,這是怎麼回事?」
「回屋裡說吧。」徐氏雙唇緊抿,牽了七葉的手,向屋裡走去。
一家人在屋子裡坐下,二霞為譚德金和徐氏倒了熱茶,安靜地在一旁做鞋。
有些話,壓在徐氏和譚德金的心底深處,現在孩子們大了,也不打算隱瞞,就如實說了。
徐氏懷六郎時因身子虛,一直有些磕磕碰碰,好不容易產下六郎。誰知六郎生下後面色泛紫,不哭不鬧的,一副氣息微弱,隨時會離開的樣子。穩婆怎麼拍六郎的屁股,掐他的小胳膊、小腿都無濟於事。
郎中曾說過,徐氏的身體底子壞了,以後想要再生孩子十分困難。這樣一來,六郎可能是大房唯一的男孩,譚德金急得跑去找譚德銀,請他想辦法救救六郎。譚德銀當時面現難色,說這事不好辦,譚德金還跪下磕頭。後來禁不住譚德金再三央求,譚德銀一臉凝重地答應試試。
大約過了一炷香的工夫,前院忽然傳來驚天動的哭喊聲,原來是大郎從院中那棵桂花樹上摔下來,暈迷不醒。幾乎是在同一刻,六郎「哇」一聲哭了出來,聲音響亮,譚德金和徐氏都喜極而泣。
事後,譚德銀告訴譚德金,為了保住大房唯一的血脈,他用大郎的後半生,換了六郎的平安無事。說這話時,譚德銀一臉的痛苦和無奈。
譚德金永遠記得,譚德銀當時說道:「大哥,我有兩個兒子,為大哥毀了一個,我無怨無悔,我不能看著你絕後。兒子毀了,我還可以再生,但大哥這輩子只有一個!」
為此,譚德金和徐氏一直對大郎心存愧疚,平日有什麼好吃的,都不會少了他一份。譚德金對譚德銀更是無比信任和諸多謙讓。這也是譚德銀受傷,譚德金會感到心疼的緣故。
「扯!真能扯!」七葉聽完前因後果後,只有這一個念頭。不說譚德銀沒這種逆天的本事,就算有,他這樣自私無恥的人,又怎會用大郎去換六郎的平安?她連忙問道:「爹、娘,您們不會真的相信是二叔救了六郎吧?」
「不管妳二叔他做過什麼,但六郎這條命真的是他救的,不能否認。」徐氏正色答道。
七葉急了,說道:「二叔的道行有多深,別人不清楚,您們還不明白嗎?六郎是經穩婆一番急救才醒過來,只不過大郎哥恰巧出了事,被二叔利用了。」
徐氏瞪了她一眼,道:「七葉,不可亂說得罪神靈。」
六桔和二霞也勸:「七葉,別說了。」
七葉只能無語看著屋頂。
夜幕降臨,一輛馬車停在沈家門口。一位中年男人下了馬車,他身量高大,頷下的短鬚梳理得光滑整齊,一身青色直裰顯得乾淨俐落。
李嫂早就開了大門,笑吟吟地迎上來道:「老爺回來了。」
「嗯。」中年男人輕應了聲,負手跨進門內。
中年男人是沈南的父親沈懷仁,年方四旬,相貌堂堂,只是表情略顯嚴肅。
鄭婉如從東次間出來,微笑著喚道:「回來啦。」往他身後瞧,笑容淡了些,問道,「南兒怎麼沒隨你一同回來?」
「夫人,此次回來,我正想與妳說南兒的事。」沈懷仁見到鄭婉如後,漾出一些笑容,語氣溫和。
「何事?」鄭婉如肅了臉色。
沈懷仁抬手輕握了下鄭婉如的胳膊,溫聲道:「夫人莫急,我們進屋來說。」
鄭婉如點頭,隨他一同進入東次間。
沈懷仁進內室換常服,用熱水淨了面和手,這才坐到桌旁,端起杯子品了幾口茶。
看他慢條斯理的樣子,鄭婉如面有急色,催促道:「老爺,有話就趕緊說,別讓我這顆心揪著,南兒又怎麼了?」
沈懷仁輕聲笑了下,道:「夫人,南兒也是我的兒子,我還能將他怎麼樣?為了他能安心讀書,不受他人影響,我決定從現在起,讓他住在書院,由青山照顧他起居。」青山是沈懷仁的貼身隨從。
「我不同意。」鄭婉如立刻反對,「讓南兒住書院,那還不像縛在籠中的鳥兒,一點兒自由也沒有?南兒十分自律,這些年一直住家中,何時耽誤過學業?」
「少時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夫人,我也是為了南兒好。他是很認真,可他畢竟還是孩子,有時會誤聽人言。上次那事想起來我還惱火,七葉那孩子以前不說話時,瞧著挺乖巧,怎地一開口,就教唆南兒去玩?」沈懷仁的臉罩上薄霜。
鄭婉如不悅,辯駁道:「老爺,你太不講道理!上次之事,我不認為南兒有錯,七葉更沒錯。他們並非去玩,我不想我的兒子,將來只是一個迂腐冷漠無情的書呆子。」她沉了臉色,並將臉撇去一旁。
沈懷仁見她生氣,緩了面色,輕嘆口氣道:「夫人,我知道妳寵南兒,見不得他受罪。我答應妳,先讓他在書院住兩月。若心思完全沉澱下來,再讓他回家來住,這總成吧?」
既然沈懷仁讓步,鄭婉如也不再死纏,點頭答應。
「這幾日與黃大人他們聚在一起,可說了什麼?你對重新入仕怎麼看?」鄭婉如轉移了話題。
沈懷仁的臉色再次沉了下去,長嘆口氣。他的眼神十分複雜,既有憤怒又有擔憂,還有一絲茫然。
「怎麼了?」鄭婉如見此忙問道。
沈懷仁再次長聲嘆氣!
鄭婉如的一顆心緊緊揪起,很少見丈夫這般黯然消沉。她握住丈夫的手,輕聲道:「老爺,到底怎麼了?說出來,讓我與你一起承擔,你這樣讓我很擔心。」
沈懷仁的心中一暖,反手輕拍幾下鄭婉如的手。他扭頭看了眼緊閉的房門,壓低聲音道:「入仕一事我不著急,時間尚早,有黃大人他們在。只是聽他們說了聖上的近況,我為我們大名朝擔憂啊!」
鄭婉如趕緊起身打開門瞧了瞧,見無人才重新合上門。雖然家中除了他們夫婦,只有何叔和李嫂,可涉及皇上,不能不小心提防。她坐到沈懷仁身旁,壓低聲音問道:「聖上怎麼了?」
「唉!聖上這幾年痴迷長生不老之術,在宮中遍設道場,養道士來煉丹製藥。去年又新招攬一批所謂的得道『仙翁』,開始煉製紅鉛,用摧殘宮女身心甚至殘害生命的方法,不顧一切地採取煉丹的原料。黃大人他們曾進言,可忠言逆耳,被聖上狠狠責罵了一頓,並說若有下次,全部罷官回家。唉!可悲可嘆啊!」沈懷仁滿心憤懣地說道。恨皇上的昏庸,憂朝廷的安危和江山社稷。
「紅鉛是什麼?它的原料與宮女有何關係?」鄭婉如不解地問道。
沈懷仁雙拳握了握,面露訕色,似有些不好啟齒。
「我們夫妻還有何話不可說?」鄭婉如看見他的猶豫,正色道。
沈懷仁輕輕頷首,可就算面對是妻子,還是不好意思大聲說出來,他在鄭婉如耳畔低聲說了。
「什麼?真是混帳!」鄭婉如得知原因後,忍不住高聲罵了句。
「慎言!」沈懷仁大驚失色,下意識地捂了她的口,辱罵皇上可是大逆不道的死罪!
鄭婉如推開丈夫的手,怒道:「他敢做,難道還懼人罵?真是慘無人道,如此下去,我們大名朝……真是太沒人性!老爺,我們兒子從今兒開始不用讀書了,全回鄉下來種田。」她本想罵得更難聽,可終究顧忌對方的身分,有些話生生嚥了下去。但心中對朝廷已經失望,有如此國君,國家還有何指望?讀書還有何用?
沈懷仁對她說當今皇上為了煉製長生壯陽丹,收取童女經血,並暗中在民間選擇幼女入宮,每次數百人。那些道士為了採集經血,用盡各種摧殘身體的方法,瘋狂採集,這些幼女進宮後不出一年全部慘死。
沈懷仁輕輕拍了下鄭婉如的手,溫聲安慰道:「夫人,不要如此悲觀。黃大人和朝中幾位閣老正在積極想辦法,希望能讓聖上醒悟,不再迷信什麼長生不老之術。」
「哼,越是身在高位,越是想長生,他哪會這樣輕易放棄?世間根本無長生不老之術,那只是痴人說夢罷了!而且他常吃那些丹藥,對身體百害而無一利,到頭來只會弄巧成拙。」鄭婉如冷冷地嘲諷道。
沈懷仁也搖頭,他當然知道人不可能長生不老,否則這世上豈不早就人滿為患?
「老爺,若聖上執迷不悟,我勸你莫再入仕,做一位教書先生未嘗不可?閒來無事,我們種田養魚,家中的田產足夠我們一家生活。我不求大富大貴,只求一家人平平安安,快快樂樂地過日子。再過幾年,等彬兒和霖兒成了家,我們可以含飴弄孫,多幸福,遠比官場上那些勾心鬥角要輕鬆得多。」鄭婉如說道。
沈懷仁的面上也有著平和的笑容,妻子所描繪的一切,真的十分祥和寧靜。可他的抱負並不在山野之間,且還有任務未完成。
「夫人,若是人人都不入朝為官,江山社稷要怎麼辦?等我將彬兒、霖兒和南兒的前程安排好,我就辭官引退,到時我們就可以過著眼下這種寧靜的生活。」沈懷仁柔聲說道。
鄭婉如也不勉強,輕輕地點頭道:「聖上如此,我真的不願意兒子們再為官,也不知將來是福還是禍?」
「夫人,莫要太過憂慮,事情總會解決的。」沈懷仁溫聲勸了,不想再繼續這沉重的話題,轉了話鋒,帶了笑容問,「夫人,妳對黃小姐印象如何?」
「你說的是蓉姊兒?」鄭婉如問。表情輕鬆了些,畢竟朝廷之事不是她一個婦人該去操心的。
「正是。」沈懷仁微笑著點頭。
鄭婉如面上有了淡淡笑意:「初次見面,看著是個知書達禮,斯文乖巧的小姐,你怎好好地說起這事來?」
「黃大人有意想與我們結成兒女親家。」沈懷仁笑著道。
「黃大人相中霖兒,還是彬兒?」鄭婉如面上也有了喜色。
沈懷仁笑著擺擺手:「不是他們,是南兒。」
「南兒?」鄭婉如愣了下後趕緊擺手,「不成,南兒年紀太小,此時議親太早。你說過要等孩子們學業有成後再談婚事,怎麼現在早早要給南兒議親?」語氣多有埋怨,要是沈彬或沈霖,她定會考慮的。
「要是旁人,我可能也不會動這個心思,可黃大人如今貴為尚書,將來對南兒的前程大有助力。蓉姊兒我曾見過兩次,容貌出色,舉止端莊,配得上南兒。要是能成,倒不失為一樁良緣。」沈懷仁說出想法。
鄭婉如不為所動,搖頭:「不成,南兒眼下正在苦讀,議親定會讓他分神。蓉姊兒我們只見過一次,真正的品性如何不好說。這事日後再說,不急。」說著,她就起身去廚房親自做幾道拿手小菜給丈夫吃。
次日,吃過早飯,楊氏攙著譚德銀來到後院的七葉家。譚德銀的額上腫了一個大包,譚老爺子那一下是真的用了力。他走路的姿勢很僵硬,不知是傷了腰,還是傷了背?
他們不是來吵架鬧事,而是真誠地向譚德金夫婦賠禮。
「大哥、大嫂,我對不住你們,讓你們受委屈了。」一進屋,譚德銀就淚眼婆娑地向譚德金夫婦致歉。他艱難地抬腳踢了下楊氏,「楊華鳳,妳這死婆娘,還不快向大哥和大嫂賠禮?妳好大的膽子,竟敢瞞著我跑來找大哥的麻煩!下次妳要再敢這樣離間我們兄弟的感情,看我不休了妳!」
楊氏的臉紅一陣白一陣,十分難堪。她的嘴唇囁嚅著,半天才說道:「大哥、大嫂,我是看德銀受傷心裡急,一時衝動才犯了錯,你們能不能原諒我這一回?昨兒說七葉的那些話,都是我一時心急胡言亂說,你們別往心裡放,就將我說的話當作放屁,不用理會。」
譚德銀夫婦剛進屋時,徐氏不樂意理睬,低頭縫著衣裳,可視線一直落在剪刀上。想著兩人要是再來胡攪蠻纏,她就拿著剪刀和他們拼了。可現在兩人說了軟話賠禮,她不好意思再沉默,抬了頭。
譚德金一直在注意她的舉動,見她動了,趕緊站起來對譚德銀說道:「老二、弟妹,我們都身為爹娘,任誰也不會看著自家孩子受委屈而不管不顧。那時七葉差點沒了性命,我和嫂子的心情,你們能理解嗎?」
「能理解,當然能理解。」楊氏接話,揉了揉眼睛,「大哥、大嫂,我身為一個母親,想當年為了大郎,我眼睛都差點哭瞎了,又怎會不知你們當時的心情?唉!」
提起大郎,徐氏和譚德金的心情又多了分愧疚。
徐氏說道:「其實我們昨兒去找爹娘,只是希望二叔能為七葉正名,誰知後來鬧出那些不愉快的事?我們也沒想到爹會發那樣大的火氣!」
「唉!我心裡清楚,爹生氣,不全是為了七葉一事。主要是為老吳家來鬧事時我不在家,讓他少了主心骨,心裡不舒服,這才借機打我幾下出氣。」譚德銀說道。
徐氏的心情稍好了些,但還是糾結七葉剋趙氏一事,於是又問道:「二叔,今兒只有我們四人,你給我說句實話,當初說七葉剋娘那事,到底怎麼回事?反正事情算是過去了,我們也不會再追究,只不過七葉年紀小,揹著剋人的名聲太難聽。」
譚德銀面現尷尬之色,他抓了抓腦袋,半晌後才掩嘴咳嗽一聲,道:「大哥、大嫂,當初那件事說起來也真是玄妙得很。一開始的確算出七葉與娘八字相沖,且也問過我師父,必須將七葉送去百里之外,兩人才會相安無事。誰料七葉躲進地窖暈迷醒來後,我再掐指認真一算,卻發現她的命格似乎悄然改變了。這也是後來我不再提送走七葉的原因,送走她,也無法治好娘的病。
「不過,我這人有個壞毛病,就是死要面子。要是當時跟你們說我算錯,你們還不得將我罵死?所以……就一直死鴨子嘴硬撐著。要早知會惹出這些令人不開心的事,影響我們兄弟間感情,我早該說出來,就為了這張沒用的老臉!」
譚德銀表情萬分誠懇,說出前因後果並承認錯誤。最後,狠狠抽了自己兩嘴巴,極度後悔當初的所為。事情已經說開,譚德銀挨了打、道了歉,譚德金與徐氏也不好再說什麼,只得點頭稱原諒了他。
譚德銀和楊氏連聲稱大哥和大嫂通情達理,然後笑著離去。
七葉聽爹娘說了這事後,她也有些迷糊了,不知譚德銀夫婦是真心懺悔,還是想耍什麼把戲?她的視線落在六郎的身上。
遵循溫修宜的醫囑,這些日子六郎一直在服藥,咳嗽好了不少,幾乎沒再劇烈咳嗽過。有時在院子裡與大郎、七郎玩耍得高興時,還會跑一跑,都無事,看來這藥是真的起了作用。再這樣拖下去,六郎的病就要痊癒了,到時想再提分家,可就難上加難。分家這事成不成,還得靠六郎。
七葉有些傷神,這事得有人幫忙才成,該讓誰幫忙呢?她揣著滿腹的心思,與譚德金一起去了悅客來。牛車上除了柴火,還有竹筍、蕨菜、河蛤和螺螄。
今日時辰還早,還未到吃飯的時候,悅客來內稍顯冷清,但韓和林已在等待七葉。年叔帶著七葉和譚德金去了帳房,大家客氣寒暄幾句後,分別坐下。
「河蛤一事,不知韓掌櫃是如何考慮的?」七葉開門見山地問道,不想浪費時間。
韓和林這次沒有再拐彎抹角,微笑著答道:「七姑娘,經過這幾日鄭重的考慮,我決定搏一搏,同意妳所提出的條件。」
「好,韓掌櫃果然是爽快人,那我們先簽一年的契約。」七葉笑著點頭。
韓和林爽朗一笑,道:「七姑娘性格爽直,我要是含糊,倒讓人見笑。只是這契約,我們能否多簽幾年?」
七葉正色道:「韓掌櫃,先簽一年比較好。現在您想多簽幾年,也許一年後,您有了其他更好的想法,不想再繼續做河蛤呢?到那時這契約可就猶如枷鎖,也有可能一年後,我有其他打算。當然,若一年後,我們對現在這種合作方式都滿意,那我們續簽就是。暫時簽一年,對我們只有好處而無壞處,都留有餘地。」
韓和林凝眸沉思後,看向年叔。年叔點頭,看向七葉的眼神中更多了讚賞,認為她考慮得很周全:「行,七姑娘說得很有道理,那我們就簽一年。年叔,準備契約。」
年叔很快拿著契約進來,對七葉道:「七姑娘,我讀妳聽著,要是認為不妥的地方,我們再商量修改。對啦,七姑娘可認識什麼比較有身分的人?請來做個見證。」
七葉有點疑惑,問道:「年叔,這契約我不能看看嗎?」
「當然能看,只是,這上面的字妳……」年叔欲言又止。
七葉這才明白,原來年叔認為她不識字,心中一暖,他考慮得可真周全。她笑著伸手:「我認識幾個字,年叔,讓我瞧瞧吧,有不認識的字到時您給我說一聲。」
韓和林和年叔都十分驚訝,年叔忙將契約遞向七葉,表情還帶著訝色。七葉笑著接過,仔細看著,契約簡單明瞭,主要確認雙方責任和義務,同時還有違約責任。七葉認真看了遍,沒有什麼問題,將契約的內容輕聲與譚德金說了。
譚德金低聲道:「七葉,這些東西爹不懂,畢竟是白紙黑字,妳可得仔細些,別讓人坑了。」
「嗯。」七葉微笑著點頭,對韓和林說道,「韓掌櫃,這契約沒有問題。只是見證人,一定要有嗎?」有身分的人,她只認識沈家人,可沈南在學堂讀書,伯母在譚家莊,特意請來太麻煩。
「七姑娘既識字,這見證人可要可不要。」年叔笑著答道。
「那就不要了。」七葉笑著擺手。
於是雙方在契約上簽字,並按了手印,韓和林還蓋了印戳。白色的紙上,多了鮮紅的指印和印戳,霎時鮮活靈動起來。
韓和林讓年叔去拿了銀票過來,他親手遞給七葉:「七姑娘,這是二百兩大通錢莊的銀票,全省通兌。」
七葉接過銀票時,手微微有些發抖。二百兩啊!剛來這兒時,家裡可是一個銅板也沒有呢!對銀子更是一點概念也沒,如今倒也成了小富婆。譚德金更是激動,鼻子有些發酸。
「多謝,韓掌櫃,預祝我們合作愉快吧!」七葉故作鎮定地將銀票收進袖中,笑著說道。
「合作愉快。」韓和林也笑了,黑色的眸子閃閃發亮。
談完大事,七葉一身輕鬆地去處理螺螄。年叔陪著七葉向後廚房走去,譚德金去搬柴火和河蛤等物下牛車。七葉去後廚炒了十斤左右的螺螄,先裝了兩盤出來,一盤給廚房中的師傅們嚐,另一盤是給年叔和韓和林。
「韓掌櫃、年叔,味道如何?」等韓和林與年叔吃了半盤之後,七葉笑著問。
韓和林用帕子拭乾淨手,笑著道:「沒想到小小螺螄味道會如此美妙。只是,這吃相有些不雅,還有些辣。」他指了指年叔滿手的湯漬,還有方才擦手的帕子,白色的帕子變成了油黃色。
年叔也咂了咂嘴呼辣:「要是少放些辣椒更好。」
七葉笑道:「韓掌櫃說得有道理,這螺螄比較適合普通百姓。三五好友,來兩份又香又辣的螺螄,再來一壺酒,邊吃邊話家常,十分愜意舒適。」
韓和林的眉頭輕皺了下:「如此一來,我們倒還要專門開間鋪子,有些麻煩。」
「不用專門的鋪子,露天擺幾張桌子,再添個爐子就成,十分簡單。當然,要是能簡單搭個涼棚更好,可以遮風擋雨。」七葉說道。
「七姑娘,此事我得再考慮考慮。」韓和林有點動心,但還沒有衝動到立刻答應。
這結果在七葉預料之中,她笑著稱好,便和年叔一起去後院看譚德金賣東西。河蛤全部給了悅客來,螺螄免費讓悅客來先養起來,竹筍留了二十來斤,七葉有他用。
「年叔,能否讓我將剩下的熟螺螄帶走?我想去看一位朋友。」七葉笑著問年叔。
年叔心裡是不捨的,可七葉開了口,且東西還是她的,他怎能不答應?忙吩咐人用食盒將螺螄裝好。
「多謝年叔。」七葉笑呵呵地接過食盒,和譚德金離開悅客來。
「爹,我們去縣城。」坐上牛車,七葉小手對著縣城的方向指了指。
「七葉,去縣城做什麼?」譚德金問道。
「去看人呀。」七葉笑著應道,卻不告訴譚德金要去看誰。
譚德金按七葉的要求將牛車向縣城趕去,在經過一家當鋪時,七葉讓譚德金停了車。
「七葉,怎麼了?」譚德金看了眼當鋪,又看向七葉,費解地問道。
七葉從袖中掏出一張當票,向老爹揚了揚,道:「爹,我們去贖當!」
「贖當?」譚德金一時之間沒明白,七葉已經向當鋪走過去,他趕緊將牛車拉過去。
七葉走進當鋪,踮起腳尖,將手中的當票向那高高的櫃檯塞去:「贖當。」櫃檯太高,差不多到她的脖子,根本看不清裡面的情況。
「等著。」櫃檯裡傳出冷冰冰的聲音,沒一絲感情。
過了好久,七葉等得不耐煩時,冷冰冰的聲音再次響起:「五兩五錢。」
呃,這利錢也太高了吧?徐氏上次當耳環,當了五兩銀子,不過十來日的工夫,就要多付五百文,喝血啊!但她知道與人爭執無用,這是行規,她只好如數將銀子放上櫃檯。方才的河蛤和竹筍、蕨菜共賣了九兩六錢銀子,只剩四兩一錢了。
七葉早就想將徐氏的耳環贖回來,只是之前銀子太少,贖了耳環後就所剩無幾,萬一有急用時麻煩。現在一下子得了二百兩,便立刻跑來贖當。她將譚德金喊進來,看看耳環可是徐氏之物,可不要被人糊弄。
譚德金仔細看了看,點頭道:「是妳娘的,兩隻耳環上都刻有妳娘的名字。」
七葉看了下耳環的背面,果然有「明秀」二字,看來這耳環是特意為娘打製的,娘以前在家還是很受寵愛的嘛!
「爹,您收好,回去送給娘,讓娘高興高興。」七葉將耳環用帕子包好,遞向譚德金,輕笑著說道。
「噯,還是妳考慮得周全。要不是妳點子多,這耳環這輩子也休想贖回去。」譚德金十分感慨。他垂頭看著手中的帕子,思潮起伏。他眼睛開始發澀,擔心被七葉看出什麼,忙將帕子揣進懷裡貼身收好。
七葉瞇眸笑了笑,和譚德金準備離開,忽然背後傳來冷冷的喝斥聲:「呸,無用的窩囊廢!」
譚德金的背僵直了,面色煞白,雙腿無法使力,站在原地不動。七葉出了當鋪的門,才發現老爹沒跟著出來,忙扭頭瞧。見老爹這副模樣,趕緊跑進去:「爹,您怎麼了?」
譚德金搖搖頭,然後十分艱難地扭頭環顧,像是想找什麼。
七葉隨著他的視線四處瞅,可並沒見到什麼,狐疑地問道:「爹,您在看什麼呀?」
譚德金低聲道:「沒事,我們走吧。」拉著七葉,快步離開了當鋪。
當鋪高高的木柵欄後面,有雙飽含憤怒的眼睛,死死地盯著譚德金的背影瞧。這雙眼睛屬於一位年近花甲的男人,銳利的眼神中不但有憤怒,甚至還帶著仇視。眸底深處,則是濃得化不開的痛苦,眼神十分複雜。
譚德金一路上沉默不語,神色黯然。無論七葉和他說什麼,他都一言不發。七葉忽然想起離開時背後那聲冷喝,難道那是罵老爹的?那人是誰,為什麼要罵老爹?
「爹,方才當鋪中有您認識的人?」七葉試探著問道。
譚德金雙唇抿著,沒說話,但頭微不可見地點了下。
「那人是誰呀?」七葉忙又問道。
這次譚德金再也不開口了!七葉有些鬱悶地抿了唇,這樣吊人胃口是不道德的!
牛車進了縣城,七葉去買了兩盒點心,一小罈酒,然後讓譚德金將牛車趕去楓林堂。
「七葉,妳是來看溫公子?」譚德金終於開口,神色有了些許暖意。
七葉點頭道:「沒錯,上次人家救了六郎,我們一直跟人家道謝呢。」
七葉和譚德金拎著點心、食盒、酒和竹筍,一起進了楓林堂。
有眼尖的小學徒認出七葉,忙跑上前招呼:「姑娘好。」
「小哥好,請問溫公子在嗎?」七葉笑著問。
「溫師叔正在會友,姑娘請稍等,我去和師叔說一聲。」小學徒忙應道。
七葉笑著道謝,小學徒匆匆離去。
小學徒很快去而復返,他身後一身白衣飄飄的俊公子正是溫修宜。看溫修宜輕快的步伐和紅潤的面色,傷勢應該恢復得不錯。
見到溫修宜出來,譚德金忙迎上前,感激地喚道:「溫恩公。」並彎腰行禮。
「大叔不用客氣。」溫修宜忙抬手,溫和出聲阻止。
七葉將手中的食盒遞向溫修宜:「溫公子,多謝您上次救了我弟弟,這些東西聊表心意。」
譚德金趕緊將酒和竹筍也拿過來:「溫恩公,竹筍是今兒早上才挖的,很新鮮。」
溫修宜掃了眼東西,璀璨如星的眸子看向七葉,唇角微揚,修長白皙的手指向食盒:「那是什麼?」他對食盒中的東西有些好奇。
「螺螄。」七葉將點心遞向小學徒,然後掀開食盒的蓋子,一股誘人的香味頓時撲面而來。
「好香。」小學徒禁不住輕呼。
溫修宜眸子更加燦亮,輕輕地吸了下鼻子,道:「麻辣小螺螄?」
「溫公子好本事,還沒見到東西就猜到是什麼。不過正確來說,應該是香辣小螺螄,因這裡面未放花椒,少了麻味。」七葉笑道。
溫修宜輕輕地笑了笑,對著花廳的方向做了個請的手勢:「大叔、姑娘,裡面請。」
「不……」譚德金擺手想拒絕,他想著將東西送給溫修宜,再說些道謝的話就走。
七葉搶著快速地道:「多謝溫公子。」然後就拎著東西向花廳走去。
譚德金無奈,只得向溫修宜歉然笑笑,跟著向那邊走過去。
到了花廳坐下,溫修宜早就吩咐小學徒沏茶上點心。
「溫公子,我弟弟按您開的藥方一直在吃藥,不知還要吃多久?可要帶他過來瞧瞧?」七葉說起六郎的病情。
溫修宜輕輕頷首道:「若有空,帶他來一趟也好。」
「多謝溫公子。」七葉忙點頭道謝。
譚德金更是連聲說謝,滿面的感激之色。
要是平時,七葉早就提出告辭,可她有求於溫修宜,目的還未達到,就這樣走了不甘心。可要直接說目的,又有些不好意思。
溫修宜似乎猜到了七葉的心思,輕抿一口茶,適時說道:「姑娘,上次我說的話是算數的。」
「真的嗎?」七葉笑得燦爛。
「一言九鼎。」溫修宜鄭重地點頭。
七葉笑著說道:「我就知道溫公子是重承諾的人,其實,我也沒什麼特別的事,只是想求您幫那麼小小的一點忙……」
過了大約一刻鐘左右,七葉和譚德金向溫修宜告辭,她面帶笑容出了花廳,心情無比愉悅。這溫修宜是位守諾言的人,竟然一口答應她的要求。只要徐氏和譚德金同意,分家應該指日可待了。譚德金則沒她那般開心,表情悶悶的。
七葉不去管他,坐上牛車,開心地喊道:「爹,我們回家嘍!」
譚德金高高揚鞭擊打著牛背,牛車往譚家莊駛去。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美食小魔女(卷2):分家大計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美食小魔女(卷2):分家大計
趙氏的病終於痊癒了,原本以為一切雨過天青,譚老爺子卻在此時宣佈了二霞的親事,結親的對象好得不可思議。七葉心生懷疑,為了大姊的幸福決定親自出馬,到胡林鎮查明真相,果然察覺這樁親事背後駭人的陰謀。未來的姊夫竟是個殺人狂魔,二霞若嫁過去只有死路一條。
偏偏利慾薰心的奶奶和二叔,為了謀得豐厚的聘禮,竟私自幫二霞定了親。對方財大勢大,眼見退親不可行,這些自私的親人竟決定逼二霞嫁過去送死……
為了擺脫無良親人的箝制,七葉決定非分家不可。為了達到目的,只好利用溫修宜欠她的人情,全家人合力演一齣感人肺腑、精采絕倫的親情大戲,不達分家目的誓不甘休……
章節試閱
前情提要
自現代魂穿到大名朝的譚七葉,清醒後便發現她的處境十分難堪,親人以她八字和奶奶相剋為由要將她送走。爹娘雖極力反對,但爺爺、奶奶非常信任神棍二叔,若不是疼愛她的鄰居沈夫人出手醫治奶奶,她恐怕難逃被送走的命運。
那知奶奶的病情才剛好轉,弟弟六郎卻病危而命在旦夕。奶奶不願出錢讓六郎看大夫,幸好六郎吉人天相,路上巧遇神醫溫修宜相助,因而撿回一條命。七葉為了改善大房的處境,決定運用自身的異能來幫助家人。在青梅竹馬沈南的協助下,她與鎮上的酒樓「悅客來」開始做生意。
堂姊三桃在鎮上遭韓大少調戲,對方意...
自現代魂穿到大名朝的譚七葉,清醒後便發現她的處境十分難堪,親人以她八字和奶奶相剋為由要將她送走。爹娘雖極力反對,但爺爺、奶奶非常信任神棍二叔,若不是疼愛她的鄰居沈夫人出手醫治奶奶,她恐怕難逃被送走的命運。
那知奶奶的病情才剛好轉,弟弟六郎卻病危而命在旦夕。奶奶不願出錢讓六郎看大夫,幸好六郎吉人天相,路上巧遇神醫溫修宜相助,因而撿回一條命。七葉為了改善大房的處境,決定運用自身的異能來幫助家人。在青梅竹馬沈南的協助下,她與鎮上的酒樓「悅客來」開始做生意。
堂姊三桃在鎮上遭韓大少調戲,對方意...
»看全部
目錄
第一章 兄弟情深 5
第二章 二霞親事 39
第三章 巧計分家 69
第四章 瘋子少爺 109
第五章 初試身手 139
第六章 真相大白 173
第七章 退親失敗 209
第八章 以死相逼 241
第九章 意外之寶 279
第十章 上門搶親 315
第二章 二霞親事 39
第三章 巧計分家 69
第四章 瘋子少爺 109
第五章 初試身手 139
第六章 真相大白 173
第七章 退親失敗 209
第八章 以死相逼 241
第九章 意外之寶 279
第十章 上門搶親 315
商品資料
- 作者: 蘇子畫
- 出版社: 夢田小築 出版日期:2014-10-27 ISBN/ISSN:978986281742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52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