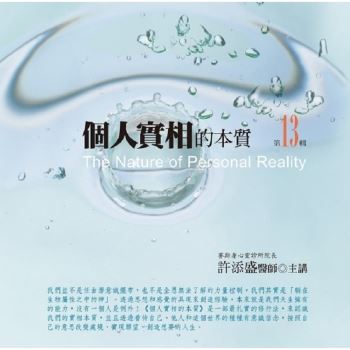徐氏滿心期盼要與閻思宏母子相認,哪知卻目睹大兒子欺負小兒子的場面。閻思宏不但不認徐氏,還惡毒地咒罵她,徐氏因過於傷心焦慮暈倒,差點命喪黃泉。七葉一家得知閻思宏的身份後,頓時陷入愁雲慘霧之中……
三桃癡迷韓大少,怎麼也不願與向光陽訂親,甚至不惜上吊自盡以明心志。譚德銀夫婦貪圖向家的富貴,不顧三桃的反對,逕自進行著親事的安排。當向家花轎來抬人時,三桃卻失蹤了……
七葉裝作不知溫修宜就是前世的男友賀峰,對他的態度冷淡而疏離。溫修宜不顧自身安危地救治五叔譚德佑,弄得自己奄奄一息,命在旦夕。七葉看著蒼白虛弱的溫修宜,感到十分愧疚,知道他這麼做是為了她,她的心動搖了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美食小魔女 卷5 美人命薄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美食小魔女 卷5 美人命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