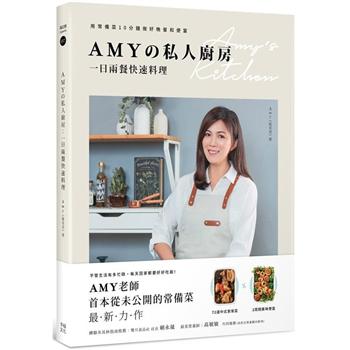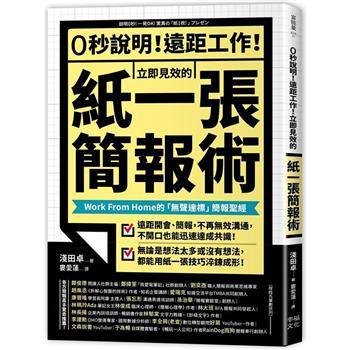上一秒出賊船,下一秒入匪坑,夏櫻桃只想大問蒼天,自己怎麼會這麼倒楣?
三度出航,她以命相搏,藉著李沐言相助,滅了呂家兄弟,終於替夏家報了血海深仇,可卻因自己在孤島上露了臉,未保性命,只好女扮男裝,混進了鎮北王府。
一入王府深似海,夏櫻桃沒想到,連當個最下等的小廝都要參與派系鬥爭,站錯邊就是三餐不繼,生活簡直比當村姑還要淒涼悲慘。所幸腦子好使,夏櫻桃幫著出主意、做水車,依附大管家,總算是求得鹹魚小翻身!
就在好不容易升到高級職位,可以跩跩橫著走的時候,夏櫻桃卻悲慘地發現了周銘遠的秘密:竟然是個表裡不一、心機深沉的黑心二少爺!而這時,李沐言也突然傳來重大消息,原來私販鐵料的幕後主使就是……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桃花桃花落誰家 卷4 改頭換面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桃花桃花落誰家 卷4 改頭換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