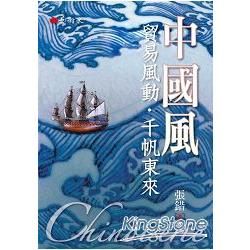中國風動‧幡然醒悟
《中國風:貿易風動‧千帆東來》出版後記(摘錄)
2012年秋季我在南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新開一門〈Chinoiserie中國風與外貿瓷研讀〉的文化研究課程,利用視覺文本來詮釋近代東西文化接觸與交流、誤解與了解、海洋與陸地、貿易與殖民的種種細節差異。本來要開一門新課,必須呈送學校課程委員會,更要有關院系加簽准許,以免誤闖人家的既得利益或研究領域。如果誤闖了,就叫「撈過界」,要撤回修改後再送,那是層層關卡、扇扇衙門、外行充內行、有理說不清之事。為了節時省事,我用了系內一個高級文學研究課程及課號,再加上中國風與外貿瓷研讀的副題,研究生自會按圖索驥,選修到這一門課。
上面事件顯示出兩種情況,第一,許多東亞系(或中文系)研究所現設的專業文學課程,已不夠應付漫不可擋的跨學科研究,書寫文本亦不足概括所有意義或涵義,如能放在一個較大文化研究層面,便會牽涉到視覺、物質文本,以至歷史與思想史。第二,以一個資深或接近退休期的教授而言,系所現設的課程本來就代表或部分代表他多年研究的成果與動向,如另闢新課,那就可能是兩種心態,一是自尋煩惱,二是像伍子胥心情:「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
慶幸兩者都不是,有情眾生,煩惱夠多了,豈能一尋再覓?倒是日暮路遠有點近似學海無涯之意。一個學者或創作者的成就,不在於他的完成,而在於永不窮盡的追尋與發現。一顆活潑的文心,就是不甘心。課程進度表是按照這書完稿後的一部分大綱設計出來的。所謂大部分是指本書原下半部談外貿瓷,結果由於中國風牽涉太廣,從17世紀直落19世紀,更因19世紀的中國貿易除了出口茶葉、絲綢、香料、瓷器外,還包括大量中國民俗水彩、粉彩、樹膠彩畫,分別繪製在蓪草紙、宣紙、油布、玻璃上,讓中國風從早期故意的誤讀,轉變為向東方學習並認識真正的東方。更令人驚愕的是,西方人除了船堅炮利,醫學、宗教、教育開啟帶動中國民智思想與科技知識外,中國人也在藝術繪畫接受西洋畫法的透視法與暈染作用,以及在植物科學要求的魚禽花鳥科學繪圖製作。這種中西文化的緊密互動,讓一生從事比較文學硏究的我,一時瞠目結舌,興奮莫名。
於是當機立斷,課程上雖然儘量伸展入外貿瓷的民窯特性,以及德國麥森(Meissen)白瓷彩瓷的崛起,歐洲瓷國群雄並列,轉印瓷(transferred wares)大量複製,讓硏究生進入一種宏觀的文化影響比較。外貿瓷的衰落,不是代表航運與科技知識的超越,更指向西方瓷器文化藝術的興起,自給自足,形成每一個歐洲瓷國個別民族傳統的傳承。
我本科是英美文學,但不知不覺已伸展入中西藝術文化,雖是互相牽連,但由於牽扯太大,開始像一個大學生那般從頭學習藝術史主修本科,譬如巴洛克與洛可可本來在歐洲文學也有所涉獵,甚至當年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硏究所修過一門「巴洛克詩歌硏究」,與17世紀的玄學詩人相提並論,更與美國的漢學家認同唐代詩人李商隱為巴洛克詩人。但在藝術史上如何從華鐸與布欣的畫作帶出歐洲的中國風風味,以及他們的誤讀或故意誤導,卻是需要閱覽群書後的個別思維。
……
於是開始發覺,尋求知識是我的解憂良藥,書寫是我的青春祕方。只要一天不停止閱讀書寫,一天都是一個汲取知識的青春少年郎。有時覺得像在歐洲漫遊時碰到的一些手拿地圖與背囊年輕人,更有在博物館專心聆聽講解或觀賞的旅者,這些人與年齡無關,甚至比一些無所事事的中年人或一事無成的偽學者、行政人員更年輕有為。真的,知識就是青春的泉源,也就是我完成《中國風》一書的青春動力。
2013年夏天,我和南加大比較文學系同事狄亞士(Roberto Diaz)教授,他同時也在西葡語文學系任教,合開了一門出外遊學的「無國籍疑難雜症」,有點像「無國籍醫生」夏天到世界各地貧瘠國家進行義診。我們把十二個學生帶往香港澳門邊走邊上課。……我們除了飽覽香港藝術博物館收藏19世紀中國南方蓪草紙畫及油畫真蹟,還有機會追蹤殖民主義國家在各地的建築或街道遺跡,尤其是澳門各大教堂巴洛克或洛可可風格,不只是大三巴的聖保羅大教堂,就連遠在路環的聖方濟各沙勿略小堂(Chapel of Saint Francis Xavier)也深具中國風融西入中的巴洛克面貌。澳門是葡萄牙殖民地保留最完整當年風貌的一個中國巿鎮,回歸前饒富中國南方風味,回歸後卻搖身一變而成極具葡萄牙飲食建築風光的美麗小鎮。有了中國風的認識,我一步步引導學生在博物館觀賞西方畫家留澳作品,包括名重一時的錢納利(George Chinnery)的油畫及素描,還帶他們到白鴿巢公園附近一訪基督徒墓園,瞻仰錢納利的墓碑遺址。
……
這書也是我從東西文學、宗教、哲學與歷史研究一路走來的產品。2000年香港城市大學出版《利瑪竇入華及其他》,原意不僅是基督文明入華,而是本想建立一個「前五四」傳統。這方面與李歐梵的見解可謂「莫逆於心」,他對五四研究的層面極廣,前推晚清,後入鴛鴦蝴蝶,我也一直覺得五四文學運動不應始自1919年,應該前推向洋務運動、西書中譯、鴉片戰爭、甚至明末1600萬曆年間耶穌會士利瑪竇入華,把宗教真理附會科學真理,從而取得中國君主的信任。這研究方向一直做到清末小說和中國新小說的興起,以及西方自然主義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理論在魯迅等人小說的影響。在這一階段同時,我的研究分歧轉向,由於多年對南中國海沉船海撈瓷與外貿瓷的注意,以及西方海上霸權興起與貿易,我希望能藉文物詮釋藝術與歷史。也就是說文物的產生,不只是歷史事實。它為何產生?牽涉到政治、歷史、文化、考古、藝術等因素。
但又不想單從書寫文本入手,想從藝術史的視覺及物質文本來檢視中國風這段歷史話語。歐洲法國路易十四天威鼎盛與亞洲康熙皇朝是一個適合的中西交匯點,歐洲三桅炮船自地中海駛出大西洋,繞過好望角來到印度洋,威逼利誘,到處殖民,正是後來林則徐奏摺描述的「此次士密等前來尋釁…無非恃其船堅炮利,以悍濟貪。」雖然最初達伽馬(Vasco da Gama)打著東來的旗號,只是尋求香料與基督徒。
本書架構分為三面,第一面敘述歐洲中國風起源與藝術傳承,對東方誤解可說是薩依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最早發軔。第二面敘說西方開拓貿易同時,藉兩大古國印度與中國來認識東方,譬如東印度公司是一個官商團體、英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華的禮儀爭論。第三面為中國風末期認知,西方畫家亞歷山大、錢納利及其他畫者如何親身在華體驗生活,繪出真正的中國風味作品。更由於18、19世紀中國畫派(Chinese school)的蓬勃興起,帶給西洋人嶄新的東方視野,至今在英美兩國餘波不絕。這三面支架,構成一個完整三角形中國風時尚。
……
為什麼標題有幡然醒悟四字呢?那是指多年厭惡學院本位主義之餘,研究撰寫中國風時,幡然醒悟於自己的歸屬或無從歸屬。在學院裡,如果被認定是一個文學人(大不了是一個文化人),就不是藝術史人、考古史人或歷史人。當然這是別人認定,我不在乎,我行我素,我是一個文藝復興人,一個飄泊者,沒有家,四海為家,學術的歸宿亦如是。
《中國風》一書完成於先母舊居「逸仙雅居」,那是我精神生活的避風港,沒有遠山積雪,也沒夜曇來訪,許多冷寂良夜,清風不來,明月未照,只有一顆熾熱的心,與檀爐餘燼氤香,躍動閃爍,這就是完成這書的許多平靜、靜穆、寂靜無聲的夜晚,神遊物外,風動帆來,有一點喜悅,一點自豪,一點寧靜。(本文為摘錄)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中國風:貿易風動‧千帆東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06 |
藝術設計 |
$ 320 |
藝術美學/欣賞 |
$ 324 |
藝術美學/欣賞 |
$ 324 |
中文書 |
$ 324 |
藝術總論 |
$ 324 |
總論 |
$ 324 |
美術 |
$ 342 |
藝術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風:貿易風動‧千帆東來
本書為張錯繼《雍容似汝》、《瓷心一片》及《風格定器物》後的最新力作。作者浸淫在文物的汪洋中,研究方向更為開闊,發產出了這條重新理解東西方文物及繪畫交流的新航向。
「中國風」(Chinoiserie)是什麼?它又是以何種形式影響著文化交流?作者在此書中藉著過去研究東西文學、宗教、哲學與歷史的豐厚成果為基底,以繪畫、布料、瓷器、服裝、建築等物質文化的角度出發,配合大量的文本,從中國輸出絲綢而與西方接觸開始,探索在文化藝術方面,西方人如何從被東方文化吸引、誤解東方進而了解東方;而東方人如何從拒絕西方到接受西方。本書佐以精采圖片,帶領讀者一窺藉由貿易而形成的「中國風」藝術風格,是研究中西方藝術交流與文化發展,不可錯過的著作。
作者簡介:
張錯
客籍惠陽人。台灣國立政治大學西語系學士,美國楊百翰大學英文系碩士,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原名張振翱,台北醫學大學特聘講座教授、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東亞系及比較文學系教授。。
曾獲台北《中國時報》文學獎(敘事詩首獎)、國家文藝獎、中興文藝獎。著作四十餘種,詩集即達十七種。近著有《雍容似汝》、《瓷心一片》、《風格定器物》等。
作者序
中國風動‧幡然醒悟
《中國風:貿易風動‧千帆東來》出版後記(摘錄)
2012年秋季我在南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新開一門〈Chinoiserie中國風與外貿瓷研讀〉的文化研究課程,利用視覺文本來詮釋近代東西文化接觸與交流、誤解與了解、海洋與陸地、貿易與殖民的種種細節差異。本來要開一門新課,必須呈送學校課程委員會,更要有關院系加簽准許,以免誤闖人家的既得利益或研究領域。如果誤闖了,就叫「撈過界」,要撤回修改後再送,那是層層關卡、扇扇衙門、外行充內行、有理說不清之事。為了節時省事,我用了系內一個高級文學研究課程及課號...
《中國風:貿易風動‧千帆東來》出版後記(摘錄)
2012年秋季我在南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新開一門〈Chinoiserie中國風與外貿瓷研讀〉的文化研究課程,利用視覺文本來詮釋近代東西文化接觸與交流、誤解與了解、海洋與陸地、貿易與殖民的種種細節差異。本來要開一門新課,必須呈送學校課程委員會,更要有關院系加簽准許,以免誤闖人家的既得利益或研究領域。如果誤闖了,就叫「撈過界」,要撤回修改後再送,那是層層關卡、扇扇衙門、外行充內行、有理說不清之事。為了節時省事,我用了系內一個高級文學研究課程及課號...
»看全部
目錄
【導言】中國風與絲綢
1. 西方海上霸權、殖民主義、東印度公司
2. 西方啟蒙運動、洛可可、中國風
3. 中國風與東方想像
【附錄】:什麼是Sawaragi?
4. 印度花布與壁紙
5. 另一種寫實中國風:錢納利與亞歷山大
6. 從東方想像到東方印象──林官、廷官與《中國服飾》
7. 誰是史貝霖?──廣州外銷畫家身分之謎
【後記】中國風動‧幡然醒悟
1. 西方海上霸權、殖民主義、東印度公司
2. 西方啟蒙運動、洛可可、中國風
3. 中國風與東方想像
【附錄】:什麼是Sawaragi?
4. 印度花布與壁紙
5. 另一種寫實中國風:錢納利與亞歷山大
6. 從東方想像到東方印象──林官、廷官與《中國服飾》
7. 誰是史貝霖?──廣州外銷畫家身分之謎
【後記】中國風動‧幡然醒悟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張錯
- 出版社: 藝術家 出版日期:2014-06-04 ISBN/ISSN:978986282128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92頁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藝術總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