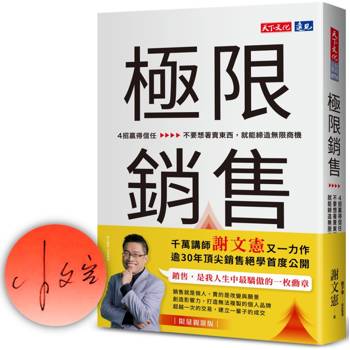謝里法說自己
一手開啟台灣美術傳史的窄門,美術史於是從「我」開始寫起;
曾經是有兩個父親的孤兒,祖父的章回小說是幼年的童話,
以虛擬的故事寫下第一部美術史演義,紫色從此是永遠的代號。
遠看是個政治外衣脫不掉的文化人,
近看是個遊走在台北、巴黎、紐約的浪人,
多少美術前輩在他紐約客廳沙發上留下動人的故事!
於是,這一生的傳奇等於是台灣美術的傳奇。
回台定居的三十年,以策展和裝置的觀念舖陳多樣藝術人生,
近代美術裡他只爭取在眾人之前走出第一步,
今後且看他怎樣完成一個拓荒者的多彩人生!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原色大稻埕:謝里法說自己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95 |
藝術家傳記 |
$ 395 |
藝術家 |
$ 395 |
美術 |
$ 450 |
中文書 |
$ 450 |
藝術家 |
$ 450 |
總論 |
$ 585 |
藝術設計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原色大稻埕:謝里法說自己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謝里法
台北大稻埕永樂町(迪化街)1938年出生。1948年台北市太平國民學校畢業(戰爭期間在金瓜石就讀東國民學校兩年)。1954年省立基隆中學畢業。1959年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系畢業。1964年乘船經香港赴法、進國立巴黎美術學院雕刻班、夜間學作版畫(銅版和絹印)。1968年轉往美國紐約。1970年開始寫文章在國內刊物投稿,介紹歐美現代美術。 版畫作品參加東京國際版畫雙年展、挪威國際版畫雙年展、瑞士國際版畫三年展等,受巴黎國家圖書館、紐約現代美術館收藏。
著作有《紐約藝術世界》、《藝術的冒險》、《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台灣出土人物誌》、《我所看到的上一代》、《重塑台灣的心靈》、《探索台灣美術的歷史視野》、《紫色大稻埕》、《變色的年代》等 。 1996年回國,目前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 國立台灣美術館展出「垃圾美學」、「10+10=21」(策展)、「紫色大稻埕—七十回顧展」。 受聘任總統文化獎、國家文藝獎、全國美展、全省美展、台新獎、台北市獎、大墩美展、台灣國展等評審員。 獲美國台美文教基金會人文成就獎、台灣文藝社文學評論獎、台東縣榮譽縣民。
謝里法
台北大稻埕永樂町(迪化街)1938年出生。1948年台北市太平國民學校畢業(戰爭期間在金瓜石就讀東國民學校兩年)。1954年省立基隆中學畢業。1959年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系畢業。1964年乘船經香港赴法、進國立巴黎美術學院雕刻班、夜間學作版畫(銅版和絹印)。1968年轉往美國紐約。1970年開始寫文章在國內刊物投稿,介紹歐美現代美術。 版畫作品參加東京國際版畫雙年展、挪威國際版畫雙年展、瑞士國際版畫三年展等,受巴黎國家圖書館、紐約現代美術館收藏。
著作有《紐約藝術世界》、《藝術的冒險》、《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台灣出土人物誌》、《我所看到的上一代》、《重塑台灣的心靈》、《探索台灣美術的歷史視野》、《紫色大稻埕》、《變色的年代》等 。 1996年回國,目前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 國立台灣美術館展出「垃圾美學」、「10+10=21」(策展)、「紫色大稻埕—七十回顧展」。 受聘任總統文化獎、國家文藝獎、全國美展、全省美展、台新獎、台北市獎、大墩美展、台灣國展等評審員。 獲美國台美文教基金會人文成就獎、台灣文藝社文學評論獎、台東縣榮譽縣民。
目錄
目錄
謝里法各階段作品簡介 彩1至彩32
自序 8
1 町(出生)/ 犁(大學) 19
台北大稻埕出生 20
牛乳餅‧查某姑 24
和阿公一起行走在永樂町大街上 26
「富士山」和鬱金香 30
阿公的認同 33
那一天日本老師都哭了 39
重回生父母的家 44
「山陽行」發了光復財 48
我們的老師叫「怪手」 53
學校裡鬧「匪諜」 58
中學時代對死亡的聯想 63
偷窺姑丈的保險箱 67
決定投考藝術系 70
大學生不跳舞! 75
我們這一班 78
繪畫的基礎素描課 88
師大藝術系老師們 92
找夢的人 96
孫老師是「台北人」 101
廖老師不懂國畫! 104
孫多慈畫室裡的才女 108
畢業前夕 113
加入「五月畫會」 117
2 礁(教學生活) 123
在礁溪找到第一件教職 124
不來鄉下不知道官有多大 126
五月裡走入畫壇 131
入營受訓 134
「領袖」這東西 136
入營去「作兵」 139
脫下軍服一起裸泳 141
下部隊當排長 143
南亞遠征軍 146
基隆顏家商職任教 150
秦松有個爸名叫秦嶺 153
出國前的「黑」、「白」畫 156
惜別雨港都 161
3 丘(出國、巴黎)165
喝中國水長大的香港人 166
戰火下的西貢 168
國語人與「金陵春夢」 170
啞巴和尚在唸經! 173
佳榭遠東學生宿舍 176
留學生的認同與歸宿 181
60年代的緊張關係 183
民初老留學生 187
巴黎三劍客 191
唱日本國歌慶祝光復節 195
神祕小聚會 198
「臺灣青年」有毒‧師公如是說 200
走在藝術人生的路上 203
對立與辯證 205
1960年代的巴黎「沙龍」 211
天真文化價值觀 214
看見教皇 216
當上遊走西班牙的背包客 220
阿爾塔米拉洞窟繪畫 225
留學生的打工生活 230
「光」的美術史展覽會 233
踏尋梵谷的足跡 237
「共匪」在哪裡? 240
闖開那扇門看見玻璃箱裡有嬰兒 243
沿著塞尚的下坡道走下去 245
在美術館長廊找歷史 248
臺灣出國旅團的前鋒 251
為美術史上的小名家爭一席之地 254
數數美術史有多少三劍客 258
在「人類」裡找原始與現代的距離 262
調色板上的變奏曲 268
阿拉伯區木炭街 273
好甜的「現代感」! 277
為象鼻岩演出「現代舞」 280
香港來的阿平 282
歐洲學生反對的是「戰神」 285
看到不一樣的羅丹 288
蘇朝棟在巴士站送我離開巴黎 292
4 村(紐約) 299
美國/一個熟悉又陌生的國度 300
哈德遜河岸的西貝茲 303
紐約美術界的東方人 306
臺灣來的「雲上の人」 311
「盤古」說我背叛祖宗 313
這才開始寫文章 315
江文也/一個音樂家的出土 318
為「臺灣」、「美術」、「史」牽上了線 322
父與子/郭家的兩代情 324
不是為上一代寫歷史 327
客廳沙發椅上坐過的前輩們 333
再見《媳婦入門》 338
三個女人的故事 340
格林威治村的「橄欖樹」 343
兩個只花錢不賺錢的女人 345
文章裡沒有了意識就沒有意思! 348
「出土人物誌」背後的故事 351
老英雄走了! 355
夏威夷來的廣東人 357
生意人的政治思考 360
宜蘭外海一個小島惹的禍 362
版印「嬰兒」與「玻璃箱」 364
畫家、收藏家與策展人 367
年輕時候的「美齡」和「水龍」 370
5 埕(回國) 373
民進黨旗是我畫的! 374
把自己交給機場的李將軍 378
舊時同學已是今日當權派 381
拜會台中畫壇三佬 385
這才是名畫家! 389
為文建會提三項建議 394
珍重與再見 398
重回巴黎尋找聖者光環 402
6 墩(定居) 411
彰化師大美術系客座教授 412
遊走在臺灣政治的邊緣 419
初識台北畫廊 422
「牛耳」的黃議員 426
「卵生文明」換來一棟房子 430
笑看台中市長民選 434
編撰中臺灣美術年表 438
尋找地方美術的特質 443
10+10=21 447
臺灣美術史從「我」開始寫起 450
「舊瓶裝新酒」老人裝置展 455
「文英」復興運動 459
童年記憶裡的二二八 464
在大地震中誕生的攝影家 467
一百個「臺灣頭」裡唯一的童子 471
初識東海岸美術界 474
轉型後的礦山九份 480
為大稻埕寫小說 483
此生第一個文學獎 486
紫色的回顧展 489
換得一條市長的紫色領帶 494
什麼都不是,就是我的地位 498
左派與右派在時間裡和解 504
7 屯(老年) 509
四十年前版畫意外重現 510
「核」光山上的「素」食年代 512
在壁上讓藝術與民主串聯 515
青睞大稻埕 519
失敗畫家贏得一座美術館 522
達文西割掉我一塊肉 524
謝里法各階段作品簡介 彩1至彩32
自序 8
1 町(出生)/ 犁(大學) 19
台北大稻埕出生 20
牛乳餅‧查某姑 24
和阿公一起行走在永樂町大街上 26
「富士山」和鬱金香 30
阿公的認同 33
那一天日本老師都哭了 39
重回生父母的家 44
「山陽行」發了光復財 48
我們的老師叫「怪手」 53
學校裡鬧「匪諜」 58
中學時代對死亡的聯想 63
偷窺姑丈的保險箱 67
決定投考藝術系 70
大學生不跳舞! 75
我們這一班 78
繪畫的基礎素描課 88
師大藝術系老師們 92
找夢的人 96
孫老師是「台北人」 101
廖老師不懂國畫! 104
孫多慈畫室裡的才女 108
畢業前夕 113
加入「五月畫會」 117
2 礁(教學生活) 123
在礁溪找到第一件教職 124
不來鄉下不知道官有多大 126
五月裡走入畫壇 131
入營受訓 134
「領袖」這東西 136
入營去「作兵」 139
脫下軍服一起裸泳 141
下部隊當排長 143
南亞遠征軍 146
基隆顏家商職任教 150
秦松有個爸名叫秦嶺 153
出國前的「黑」、「白」畫 156
惜別雨港都 161
3 丘(出國、巴黎)165
喝中國水長大的香港人 166
戰火下的西貢 168
國語人與「金陵春夢」 170
啞巴和尚在唸經! 173
佳榭遠東學生宿舍 176
留學生的認同與歸宿 181
60年代的緊張關係 183
民初老留學生 187
巴黎三劍客 191
唱日本國歌慶祝光復節 195
神祕小聚會 198
「臺灣青年」有毒‧師公如是說 200
走在藝術人生的路上 203
對立與辯證 205
1960年代的巴黎「沙龍」 211
天真文化價值觀 214
看見教皇 216
當上遊走西班牙的背包客 220
阿爾塔米拉洞窟繪畫 225
留學生的打工生活 230
「光」的美術史展覽會 233
踏尋梵谷的足跡 237
「共匪」在哪裡? 240
闖開那扇門看見玻璃箱裡有嬰兒 243
沿著塞尚的下坡道走下去 245
在美術館長廊找歷史 248
臺灣出國旅團的前鋒 251
為美術史上的小名家爭一席之地 254
數數美術史有多少三劍客 258
在「人類」裡找原始與現代的距離 262
調色板上的變奏曲 268
阿拉伯區木炭街 273
好甜的「現代感」! 277
為象鼻岩演出「現代舞」 280
香港來的阿平 282
歐洲學生反對的是「戰神」 285
看到不一樣的羅丹 288
蘇朝棟在巴士站送我離開巴黎 292
4 村(紐約) 299
美國/一個熟悉又陌生的國度 300
哈德遜河岸的西貝茲 303
紐約美術界的東方人 306
臺灣來的「雲上の人」 311
「盤古」說我背叛祖宗 313
這才開始寫文章 315
江文也/一個音樂家的出土 318
為「臺灣」、「美術」、「史」牽上了線 322
父與子/郭家的兩代情 324
不是為上一代寫歷史 327
客廳沙發椅上坐過的前輩們 333
再見《媳婦入門》 338
三個女人的故事 340
格林威治村的「橄欖樹」 343
兩個只花錢不賺錢的女人 345
文章裡沒有了意識就沒有意思! 348
「出土人物誌」背後的故事 351
老英雄走了! 355
夏威夷來的廣東人 357
生意人的政治思考 360
宜蘭外海一個小島惹的禍 362
版印「嬰兒」與「玻璃箱」 364
畫家、收藏家與策展人 367
年輕時候的「美齡」和「水龍」 370
5 埕(回國) 373
民進黨旗是我畫的! 374
把自己交給機場的李將軍 378
舊時同學已是今日當權派 381
拜會台中畫壇三佬 385
這才是名畫家! 389
為文建會提三項建議 394
珍重與再見 398
重回巴黎尋找聖者光環 402
6 墩(定居) 411
彰化師大美術系客座教授 412
遊走在臺灣政治的邊緣 419
初識台北畫廊 422
「牛耳」的黃議員 426
「卵生文明」換來一棟房子 430
笑看台中市長民選 434
編撰中臺灣美術年表 438
尋找地方美術的特質 443
10+10=21 447
臺灣美術史從「我」開始寫起 450
「舊瓶裝新酒」老人裝置展 455
「文英」復興運動 459
童年記憶裡的二二八 464
在大地震中誕生的攝影家 467
一百個「臺灣頭」裡唯一的童子 471
初識東海岸美術界 474
轉型後的礦山九份 480
為大稻埕寫小說 483
此生第一個文學獎 486
紫色的回顧展 489
換得一條市長的紫色領帶 494
什麼都不是,就是我的地位 498
左派與右派在時間裡和解 504
7 屯(老年) 509
四十年前版畫意外重現 510
「核」光山上的「素」食年代 512
在壁上讓藝術與民主串聯 515
青睞大稻埕 519
失敗畫家贏得一座美術館 522
達文西割掉我一塊肉 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