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與詩的對話》為嶺南畫派大家歐豪年的親筆獨白。以水墨創作見長的歐豪年,其善書、善詩的藝術才華同為世人共睹,所創作的詩文源自其生活上的體驗和感悟,詩句曉暢,寓意深遠。
本書收錄歐豪年歷年所作之72件水墨精品,結合歐豪年對作品創作時空背景的細數陳述,以及視覺圖像與詩文的對照,綜合闡釋中國水墨畫與文言詩詞、書法之間的互動關係及共通美學,開啟畫作與詩文的深度對談,為讀者呈現詩、書、畫三合一的中國人文美學景觀。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畫與詩的對話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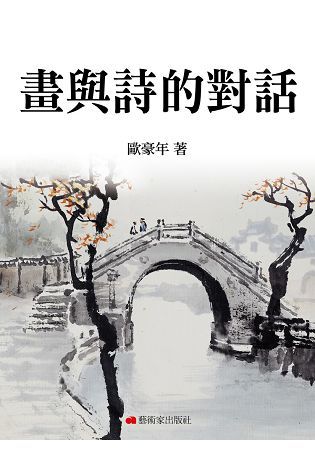 |
畫與詩的對話 出版社:藝術家 出版日期:2017-01-1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160頁 / 16k/ 19 x 26 cm / 普通級/ 全彩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32 |
文學 |
$ 332 |
Literature & Fiction |
$ 374 |
詩集旋風來襲! |
$ 378 |
中文書 |
$ 378 |
繪畫 |
$ 405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畫與詩的對話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歐豪年
作者歐豪年為嶺南畫派當代宗師,其水墨創作兼容古法與新技,融合紮實的寫生功夫,以及對水分與色彩的巧妙運用,構圖新穎獨到,氣勢磅礡灑脫。歐豪年善畫,同時也善書、善詩,其詩詞與書法作品並不遜於繪畫成就,著有《八十得天寬:歐豪年書畫展集》、《歐豪年廿一世紀創作畫集》……等畫集。
歐豪年
作者歐豪年為嶺南畫派當代宗師,其水墨創作兼容古法與新技,融合紮實的寫生功夫,以及對水分與色彩的巧妙運用,構圖新穎獨到,氣勢磅礡灑脫。歐豪年善畫,同時也善書、善詩,其詩詞與書法作品並不遜於繪畫成就,著有《八十得天寬:歐豪年書畫展集》、《歐豪年廿一世紀創作畫集》……等畫集。
目錄
自序 4
畫與詩的對話 10
歐豪年教授年表 152
樂山圖 16
故居仁壽里 19
香港離島寫生 20
柳陰宿鷺 24
膏火伴長吟 27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景色 29
南洋風物 30
柳鷺 32
一鳴天下白 33
山高水長 34
蒼鷹 35
陽明山 36
九份濱海 37
陽明山公園光復樓 38
觀音山 40
觀音山 42
美國白麗峙峽谷 44
大峽谷 45
羅馬廢墟 46
竹林七賢三聯屏 48
群獅出柙 50
獅侶 51
虎視 52
虎踞 53
虎步 53
吼處朗生風 54
五虎五聯屏 56
蒼鷹獨立 58
海鷹 60
鷹揚 61
八駿圖 65
秋澗清猿 67
楓葉坐猿深 67
浴牛之一 72
浴牛之三 74
秋壑 75
觀音山暮靄 78
美人君子 80
牡丹 81
屏風 83
良寬上人慈幼圖 85
竹 87
桃源 88
長鰱 92
春江魚樂 93
溪山清遠 96
屈原 99
東坡題壁 100
筆搖五嶽 101
蘇公論藝 103
寒山子 104
東坡題壁 100
筆搖五嶽 101
蘇公論藝 103
寒山子 104
鍾進士揮毫 106
鍾馗翰戲 107
鍾馗倚醉 108
京都樂姬弄琴 111
楚辭山鬼篇辭意 112
臺灣九九峰遠眺四聯屏 116
華嶽西峰 125
牧興 129
長城登覽 133
長城春訊 134
雁蕩山石筍 136
長江秋意 138
蘇州寒山寺 139
張家界山澗 140
黃山飛來石 141
黃山始信峰 142
黃山四聯屏 144
黃山玉屏峰 146
黃山玉屏雪徑 148
黃山天都峰遠望 149
黃河壺口 150
畫與詩的對話 10
歐豪年教授年表 152
樂山圖 16
故居仁壽里 19
香港離島寫生 20
柳陰宿鷺 24
膏火伴長吟 27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景色 29
南洋風物 30
柳鷺 32
一鳴天下白 33
山高水長 34
蒼鷹 35
陽明山 36
九份濱海 37
陽明山公園光復樓 38
觀音山 40
觀音山 42
美國白麗峙峽谷 44
大峽谷 45
羅馬廢墟 46
竹林七賢三聯屏 48
群獅出柙 50
獅侶 51
虎視 52
虎踞 53
虎步 53
吼處朗生風 54
五虎五聯屏 56
蒼鷹獨立 58
海鷹 60
鷹揚 61
八駿圖 65
秋澗清猿 67
楓葉坐猿深 67
浴牛之一 72
浴牛之三 74
秋壑 75
觀音山暮靄 78
美人君子 80
牡丹 81
屏風 83
良寬上人慈幼圖 85
竹 87
桃源 88
長鰱 92
春江魚樂 93
溪山清遠 96
屈原 99
東坡題壁 100
筆搖五嶽 101
蘇公論藝 103
寒山子 104
東坡題壁 100
筆搖五嶽 101
蘇公論藝 103
寒山子 104
鍾進士揮毫 106
鍾馗翰戲 107
鍾馗倚醉 108
京都樂姬弄琴 111
楚辭山鬼篇辭意 112
臺灣九九峰遠眺四聯屏 116
華嶽西峰 125
牧興 129
長城登覽 133
長城春訊 134
雁蕩山石筍 136
長江秋意 138
蘇州寒山寺 139
張家界山澗 140
黃山飛來石 141
黃山始信峰 142
黃山四聯屏 144
黃山玉屏峰 146
黃山玉屏雪徑 148
黃山天都峰遠望 149
黃河壺口 150
序
自序
我以「畫與詩的對話」為書目,寫的這本獨白,又重興了許多往事追懷,憶自少小就學,作詩作畫是我自投習,古典文學的就讀研習,則以家父堅持,家道亦可支持,即在當年抗日兵馬慌亂時代,仍幸得家父執教,以近似塾學的方式,給我加強教育,且所延師亦能隨家轉赴他地,始得不輟受教的機會。詩三百篇以至經史子集選讀以外,書法則自「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九宮格,晉王羲之聖教序,唐孫過庭書譜序,以至經史格言,唐宋詩文 集的默寫,亦是小時能有所表現的功課。所以我如今說,繪畫既已成為專業,則詩是生活,而書法當為我的遊戲之作。
自古以來的庭訓,讀聖賢書,自都以能幹國家事,為對子弟的期望。可惜我雖亦曾正心誠意研讀國學,卻祇願作山野閒散的人,棄絕功名。在某種標準 而言,則不成材了。即使今日作詩,或者揮灑行草書法,而以我詩作內容,雖非過分的艱澀,猶且每為有些老學友生,看不懂,讀不清時,給我暗地埋怨。也想到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陶淵明,淵明雖曾自言好讀書,不求甚解,但若因強解、誤解而彼此的思想距離更遠,那終將是作者更大的罪過。況且作詩不免有時要用典,無法一一解讀得盡,但能儘量加上一些讀物做旁解,能因作者的坦 率陳述得到讀者會意、理解,便是我天大的滿足與感激了。至於本書的行文風格,則由於這是我數十年間生活感言的讀物,若以所涉時地,雖然也有明顯次序,但卻不願將其分開章節去論述,免如論文的枯燥、拘謹;更免於行文思路因分割而致斷裂。夫子自道,也想像畫與詩是可以對話,讓更多讀者普遍都能 接受。至愛讀者,尚盼能多雅諒。
關於詩的品評,古往今來,雖曾有梁鍾嶸所撰詩品,然所品古代的五言詩,自漢、魏以至梁代之一百餘人。惜全盛的唐詩品評,不在其內。而唐人對古今作詩的權衡品鑑則更有司空圖的詩品,司空圖字表聖,他的詩品一書,二十四則中:
(一)雄渾──之積健為雄。
(二)沖淡──之若飲大和。
(三)纖穠──之窈窕深谷。
(四)沉著──之若為平生。
(五)高古──之太華夜碧。
(六)典雅──之人淡如菊。
(七)洗煉──之古鏡照神。
(八)勁健──之天地與立。
(九)綺麗──之淺者屢深。
(十)自然──之俯拾即是。
(十一)含蓄──之盡得風流。
(十二)豪放──之吞吐大方。
(十三)精神──之妙造自然。
(十四)縝密──之要路幽行。
(十五)疎野──之與率為期。
(十六)清奇──之淡不可收。
(十七)委曲──之似往已迴。
(十八)實境──之妙不自尋。
(十九)悲慨──之壯士拂劍。
(二十)形容──之如寫陽春。
(二一)超詣──之少有道契。
(二二)飄逸──之矯矯不群。
(二三)曠達──之何如樽酒。
(二四)流動──之如轉丸珠。
二十四則中,多有可於詩作聯想相扣相關,今所從事書與詩的對話,也就是個中能有體認,儘試和盤托出是了。
近現代人在普世價值觀上,每喜談到「真、善、美」三字,尤其與美術青年談到審美時,每被問到的,也就容易將「美」與「真」、「善」並提。若從古代詩人去探求,則晉陶淵明熱愛生活的詩是「真」;詩聖杜甫心繫生民疾苦所吟,及其茅屋為風所破,不自怨艾,猶念安得廣廈萬間,盡庇天下寒士的情懷,「善」與人同。至於言「美」,則我生平作詩,熱切以能為畫作的求「美」詮釋。亦自冀望可以「美」字相論。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研究所,我為博碩士班所開的一門課「畫與詩書之美」,為中國水墨畫與文言詩、書法之間,在美感上作申論。所訂講義的開宗明義,即曾首先援引二千餘年前孔子與老子所論,有提及美的,試為銓釋。孔子提倡人格美術,當以他所提論的「以里仁為美」,可以體認。而老子的五千言道德經,玄論切要,其言「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後人對之,多有不解,甚至誤解。實在此語的關鍵,繫在其中「知」字的識別,科學可以強調知性,惟獨求美,則必循於感性。當時老子即已太息,天下滔滔者,皆昧於至道,徒能以知識心,去求美之為美,謂斯惡矣。後來康德論美,猶能主張無念、無心、亦無目的,以期感悟於美,或可與老子持論比擬。西方學者論美雖多,莫衷一是,更難相提並論了。實有感於近代學者們都過度刻意於體系嚴整。要求去作自成一家之言,反而使人不易判讀。
近讀余秋雨先生所著的「極品美學」一書,他在自序中,大意有說:中國歷代對「美」,都在著力於對具體作品中的選擇、品賞、比較,最後成果也不一定是體系嚴整的什麼「學」。故對於西方理論著作,所受德國黑格爾美學理論影響,那些總是先從抽象概念定義出發,先打造一個理論框架的情形,顯然有別。那是中西美學思維方向之別,上述看法、淺見實同。因我平生治學,就一以直指本心,不假途於拼貼成型的解釋,以為符合所謂時代精神。事實上那亦祇屬近代西方人治學的途徑之一而已。其與中國遠古文化,動輒可上溯至二千餘年以上的說法,雖不免有鑿枘,然我寧取大醇而去小疵,不作牽強附會。余秋雨先生更曾於藝術文化,提出儒家的中庸之道,對極端化的防範,不排斥極端,卻能將中國的傳統思想,對藝術文化作潛在的掌控,以至充份融入。再說上述「真、善、美」,今日普世對此價值觀的強調,則更由於曾已頒贈榮譽文學博士給我的,天主教輔仁大學,持為校訓,我更欣然接受,省察不忘。余秋雨先生與我雖猶素昧平生,但由於對其論述的嚮往,我今不期而開懷愜心,亦遂振筆成文。寫出藝術文化中,詩與畫的對話。
我以「畫與詩的對話」為書目,寫的這本獨白,又重興了許多往事追懷,憶自少小就學,作詩作畫是我自投習,古典文學的就讀研習,則以家父堅持,家道亦可支持,即在當年抗日兵馬慌亂時代,仍幸得家父執教,以近似塾學的方式,給我加強教育,且所延師亦能隨家轉赴他地,始得不輟受教的機會。詩三百篇以至經史子集選讀以外,書法則自「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九宮格,晉王羲之聖教序,唐孫過庭書譜序,以至經史格言,唐宋詩文 集的默寫,亦是小時能有所表現的功課。所以我如今說,繪畫既已成為專業,則詩是生活,而書法當為我的遊戲之作。
自古以來的庭訓,讀聖賢書,自都以能幹國家事,為對子弟的期望。可惜我雖亦曾正心誠意研讀國學,卻祇願作山野閒散的人,棄絕功名。在某種標準 而言,則不成材了。即使今日作詩,或者揮灑行草書法,而以我詩作內容,雖非過分的艱澀,猶且每為有些老學友生,看不懂,讀不清時,給我暗地埋怨。也想到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陶淵明,淵明雖曾自言好讀書,不求甚解,但若因強解、誤解而彼此的思想距離更遠,那終將是作者更大的罪過。況且作詩不免有時要用典,無法一一解讀得盡,但能儘量加上一些讀物做旁解,能因作者的坦 率陳述得到讀者會意、理解,便是我天大的滿足與感激了。至於本書的行文風格,則由於這是我數十年間生活感言的讀物,若以所涉時地,雖然也有明顯次序,但卻不願將其分開章節去論述,免如論文的枯燥、拘謹;更免於行文思路因分割而致斷裂。夫子自道,也想像畫與詩是可以對話,讓更多讀者普遍都能 接受。至愛讀者,尚盼能多雅諒。
關於詩的品評,古往今來,雖曾有梁鍾嶸所撰詩品,然所品古代的五言詩,自漢、魏以至梁代之一百餘人。惜全盛的唐詩品評,不在其內。而唐人對古今作詩的權衡品鑑則更有司空圖的詩品,司空圖字表聖,他的詩品一書,二十四則中:
(一)雄渾──之積健為雄。
(二)沖淡──之若飲大和。
(三)纖穠──之窈窕深谷。
(四)沉著──之若為平生。
(五)高古──之太華夜碧。
(六)典雅──之人淡如菊。
(七)洗煉──之古鏡照神。
(八)勁健──之天地與立。
(九)綺麗──之淺者屢深。
(十)自然──之俯拾即是。
(十一)含蓄──之盡得風流。
(十二)豪放──之吞吐大方。
(十三)精神──之妙造自然。
(十四)縝密──之要路幽行。
(十五)疎野──之與率為期。
(十六)清奇──之淡不可收。
(十七)委曲──之似往已迴。
(十八)實境──之妙不自尋。
(十九)悲慨──之壯士拂劍。
(二十)形容──之如寫陽春。
(二一)超詣──之少有道契。
(二二)飄逸──之矯矯不群。
(二三)曠達──之何如樽酒。
(二四)流動──之如轉丸珠。
二十四則中,多有可於詩作聯想相扣相關,今所從事書與詩的對話,也就是個中能有體認,儘試和盤托出是了。
近現代人在普世價值觀上,每喜談到「真、善、美」三字,尤其與美術青年談到審美時,每被問到的,也就容易將「美」與「真」、「善」並提。若從古代詩人去探求,則晉陶淵明熱愛生活的詩是「真」;詩聖杜甫心繫生民疾苦所吟,及其茅屋為風所破,不自怨艾,猶念安得廣廈萬間,盡庇天下寒士的情懷,「善」與人同。至於言「美」,則我生平作詩,熱切以能為畫作的求「美」詮釋。亦自冀望可以「美」字相論。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研究所,我為博碩士班所開的一門課「畫與詩書之美」,為中國水墨畫與文言詩、書法之間,在美感上作申論。所訂講義的開宗明義,即曾首先援引二千餘年前孔子與老子所論,有提及美的,試為銓釋。孔子提倡人格美術,當以他所提論的「以里仁為美」,可以體認。而老子的五千言道德經,玄論切要,其言「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後人對之,多有不解,甚至誤解。實在此語的關鍵,繫在其中「知」字的識別,科學可以強調知性,惟獨求美,則必循於感性。當時老子即已太息,天下滔滔者,皆昧於至道,徒能以知識心,去求美之為美,謂斯惡矣。後來康德論美,猶能主張無念、無心、亦無目的,以期感悟於美,或可與老子持論比擬。西方學者論美雖多,莫衷一是,更難相提並論了。實有感於近代學者們都過度刻意於體系嚴整。要求去作自成一家之言,反而使人不易判讀。
近讀余秋雨先生所著的「極品美學」一書,他在自序中,大意有說:中國歷代對「美」,都在著力於對具體作品中的選擇、品賞、比較,最後成果也不一定是體系嚴整的什麼「學」。故對於西方理論著作,所受德國黑格爾美學理論影響,那些總是先從抽象概念定義出發,先打造一個理論框架的情形,顯然有別。那是中西美學思維方向之別,上述看法、淺見實同。因我平生治學,就一以直指本心,不假途於拼貼成型的解釋,以為符合所謂時代精神。事實上那亦祇屬近代西方人治學的途徑之一而已。其與中國遠古文化,動輒可上溯至二千餘年以上的說法,雖不免有鑿枘,然我寧取大醇而去小疵,不作牽強附會。余秋雨先生更曾於藝術文化,提出儒家的中庸之道,對極端化的防範,不排斥極端,卻能將中國的傳統思想,對藝術文化作潛在的掌控,以至充份融入。再說上述「真、善、美」,今日普世對此價值觀的強調,則更由於曾已頒贈榮譽文學博士給我的,天主教輔仁大學,持為校訓,我更欣然接受,省察不忘。余秋雨先生與我雖猶素昧平生,但由於對其論述的嚮往,我今不期而開懷愜心,亦遂振筆成文。寫出藝術文化中,詩與畫的對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