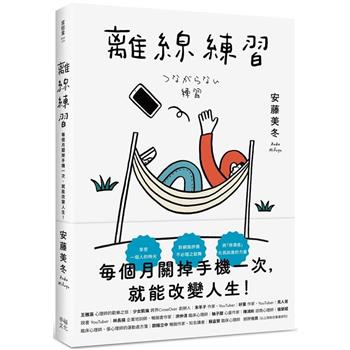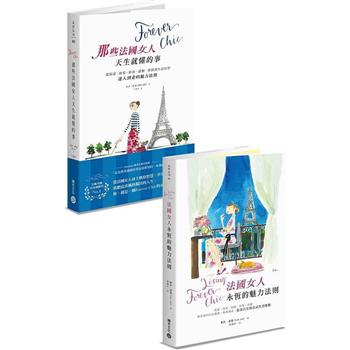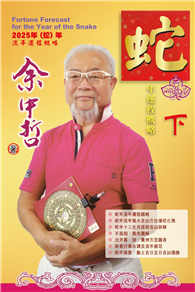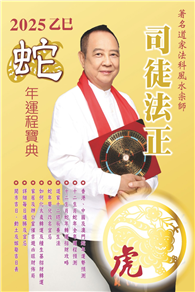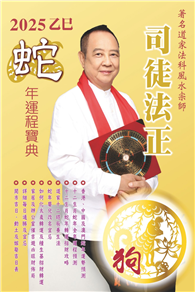自序
以學徒精神自勉
由於從小父母都在外地生活、工作,所以我的童年以至青少年時期,大多都在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四位老人家的照顧與庇蔭下長大。我後來不時聽到「隔代教養有某某某缺點」之類的說法,但自己回想起來,卻似乎受益與溫厚之感,占據了大部分的記憶。
我在國小的時候,外公剛好公務員屆退,不用上班以後,除了出門散步、買菜,他幾乎整天都待在書房寫毛筆字。每到周三下午或周末,他常會抓著我一起練字。外公習慣喝熱茶,即便六七月份燠熱難耐,他也要沖上一大壺滾燙的烏龍,然後才邊喝茶邊開始磨墨。外公又非常節省,前一天沒用完的餘墨從不洗掉,所以打開硯臺時,都會聞到淡淡的膠的臭味。隨著新墨慢慢磨出來,墨香混著微臭又混合了茶香,加上夏天那種不知如何形容的悶濕氣息,便是附著在我心底特別深刻的屬於童年的味道。作為我的書法啟蒙老師,他總教我不要貪多貪快,每天專心練幾個字,一個字多練幾遍,然後對著字帖,反覆檢查自己與顏真卿的差異。
讀美術系之後,我上過學院體系的專業書法課,也聽過許多書法創作與表現的講座,但我平時習書,儘管面對的典範早已不限於顏字,但用的始終都是外公的「土法」。
至於我爺爺,原是高中國文老師,他每天也都很早起,在我印象裡,清晨脆亮的鳥鳴,總在曙光未露或漸露時,伴隨著爺爺在家門口做晨操與鄰居老人們互道早安的招呼聲一起出現。等到我急忙出門趕公車上學,他常已用過早點,看完當天的《中央日報》,然後回房間翻開二十五史或四書之類的硬殼書,繼續閱讀並做他的筆記了。高三那年寒假,我爺爺肺癌復發,八十五歲的他經過幾次化療,身體愈顯衰弱,但即便到了生命的最末十幾天,他在榮總病房內,一旁不時出現急救或病床推進推出等混亂場面,他卻還是打起精神繼續與那些典籍對話,然後勉力寫下眉批與心得。
近些年來,每當我想起外公寫字與爺爺讀書的畫面,內心都會特別懷念與感動,他們不是書法家、文學家或史學家,他們熱愛書法與文史,不斷向典範學習,
並沒有想要創造或達成任何了不起志業的企圖,所以那種勤懇不倦極為純粹,如學徒般的身影則很動人。當然,我不是在否定文藝實踐的具體成果與功績,因為那也是我自身所追求的,但每當我觀看真正精采的好作品時,往往最震撼心魂的並非藝術家想要表達什麼,而是他們即便有再高的成就,也仍未丟失一名學徒的心態與精神,並留下學習時反覆觀察、思索、探求的痕跡。面對塞尚中晚年的靜物、風景,或是馬諦斯許多素描、剪紙,以及余承堯的山水⋯⋯,這種感受都特別強烈。
收錄在這本文集中的文字,是我這七、八年來研究與書寫的部分整理。文章來自三個大面向,一是策畫展覽的手記,二是因各種機緣或邀稿所寫的評論,另外則是關於民間藝術研究與田野考察的專文。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文章,也不論敘述的主題與脈絡有何差異,我都是用一雙學徒的眼睛去看,並以身為藝術學徒的心態,將所思所感點點滴滴記錄下來。在整理文稿的過程中,我也讀到一些自以為是或盛氣凌人的段落,多出自較早幾年的文章。我知道假使是如今的自己肯定不會那像寫,但我並未刪減或修潤,因為幼稚也有幼稚的可貴,這也是做學徒教會我的一件事。
三年前外公辭世,告別式後不久,外婆與母親開始清理他的遺物,她們問我有沒有一定要留的東西,我說任何外公練字的紙片都不能丟,我全部都要。最後她們找出一疊泛黃脆弱的毛邊紙,上面滿是外公用很慢的中鋒臨寫的楷書,我找了一個乾淨的紙夾,如獲至寶般仔細收好。我知道,那將永遠是最珍貴的提醒。
講了老人家的這些身教,算是交代為這本文集取名的初衷。最後,我想要特別感謝林惺嶽老師,他一方面在理論方法上是啟發、影響我最深的恩師;同時,若非他實踐繪畫與研究書寫時的自持、刻苦與巨大的紀律,我可能早早已被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績所惑,而忘記自己是多麼的渺小。
二○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