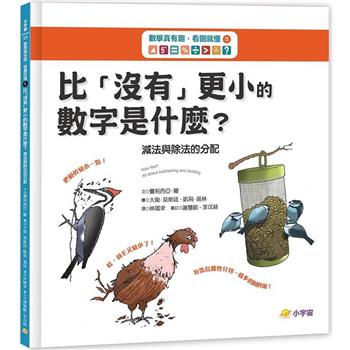她,是流雲山莊的少主;他,是大魏王朝的太子,
一雙龍鳳玉玨、一段家傳祖訓,牽起兩人間的情緣……
記得爹爹曾經對她說,若有人手持蒼龍血玉前來求助,
她就一定得幫助他,除非那是個十惡不赦之人,
當時,她萬萬沒想到,
多年後,前來求助的人,竟會是當今太子!?
而且,他不僅身中劇毒,生命垂危,
還將各方殺手引來她這個與世隔絕的流雲山莊!
不過,因為祖上有交代,
她既不能送走這尊「瘟神」,也無法不幫他收拾善後,
所以,她只得兩肋插刀,全力相助──
ㄟ……可這忙幫得似乎有點過了頭,
最後她竟連人都被整個打包帶回了皇宮……
作者簡介
閒庭晚雪
踏浪聽濤成長的嶺南女子,酷愛唐詩宋詞。
生活中渴望純粹簡單,睡夢裡嚮往駿馬西風。
代表作:《神醫皇后》、《寂寞才說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