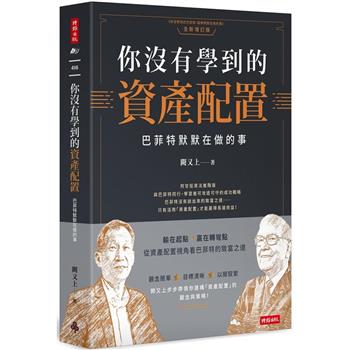所謂有情人終成眷屬,
這話完全不適用在如初跟戚繼光身上,
原本兩人以為堅定情意就能廝守一生,
不料卻遇到戚家長輩反對的難題!
原來戚家人早已替戚繼光訂下親事,
堅持要他娶她們「內定的媳婦」--白凝若。
之後,無論戚繼光與如初怎麼苦求,
戚家長輩依舊堅持這婚約,完全不改變心意。
她們料準依戚繼光孝順的個性,
最後一定會妥協!
只是,情緣難斷的如初與戚繼光,
真的會像戚家長輩所希望的那樣黯然分手,
還是……選擇為愛做最後的反撲呢?
作者簡介:
柳暗花溟
天津人,生活經歷簡單平凡,類似於溫室裡的花朵那一類植物,唯一的愛好是白日作夢。不過內心深處有邪惡因子,時時頭腦脫線,喜歡唬弄別人,以用自己的筆迷惑讀者為能事,並樂此不疲,目前此症狀發展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章節試閱
縱然千般不捨、萬般不願,戚繼光第二天一早還是忍痛離開了如初,先回魯橋鎮再做打算。不過,一想到虛大師和如初在一起,他將照顧她的病情、排解她的憂愁,最後還要和她一起先到海防衛去,他的心裡就七上八下的。
這種情緒如此強烈,他完全掩飾不住,被趙三紅看了出來。
「你不相信如初?」趙三紅勸道:「虛大師確實是人中龍鳳,但他畢竟是出家人嘛!再說,如初也不是這樣朝三暮四的人。」
「我當然相信她。」戚繼光毫不猶豫地點頭,「我怎麼會懷疑她的人品,我只是……不相信我自己。」
「什麼意思?」趙三紅被他說愣了。
戚繼光長嘆一聲,「我何德何能,可以遇到如初,還能得到她芳心首肯,願意嫁給我這個一文不名的窮小子。可現在,不過是想娶她而已,卻讓她遭受那麼多的折磨,每念及此,我不知要如何對她再好一些,我總覺得……我配不上她,所以……我才會緊張虛大師。」
聽他這麼說,趙三紅能體會他的心,卻不知道要怎樣幫他,只搔了搔頭道:「要不,我回去陪著如初?」
戚繼光苦澀一笑,搖頭道:「你還是跟我演好這齣釜底抽薪的戲碼吧!這一次,不管做什麼無理無德之事,只要對我奶奶和母親身體無大礙,我都說得出、做得到。長痛不如短痛,我想好了,既然我無法做到不傷人,那就傷個徹底,至少快刀斬亂麻,能讓被傷者有恢復的機會,不然對大家都沒好處。」
「好吧。」趙三紅嘆了口氣,「你能豁出聲名,我就全力幫你,如初也會明白你這份心的。」
戚繼光感激地點頭,再沒多說什麼,策馬疾奔而去。
而留在客棧的如初,因為心結解開,有帥而有趣的師兄不斷寬慰,身體恢復得相當快,本來病勢沉重,似乎要客死異鄉似的,可第三天就活蹦亂跳了。
她把最近發生的事一說,虛海道:「這件事不能急,但也不能拖,最為難的當然是小光、最受氣的也是小光。不過,他要想抱得美人歸,賣點力氣也是應當的,佛曰:想得到好東西,總要付出代價。」
如初啼笑皆非,不知道佛祖還說過這樣的話。
只聽虛海又道:「聽師兄一句,在這件事上,千萬別站在他身邊,要站在他身後,不是躲著,是從後方用力,前台讓他去唱,不然妳過了門,也不會有好日子的。妳想,妳和他肩並肩這樣做有什麼意思?難道是聯合起來和長輩們唱對台戲?」
「我本來是想跟他同甘苦、共患難,不想讓他獨自辛苦,而我坐享其成的。」如初有點沮喪,聽虛海一說,她也覺得自己笨。
她的想法是好的,她的心意也是真實的,但現實中卻造成了反效果,這是她之前絕沒有想到的。
所謂疏不間親,小光和家裡的人再怎麼鬧,他奶奶和母親也會原諒他。而她就不同了,就算嫁進戚家門,在生下寶寶前還是外姓人,平時盡力做好所有事,婆媳關係也不一定能改善,何況現在她只是個不相干的狐狸精呢?
假如一開始她就不自作聰明,就算最後戚家長輩還是討厭她,但厭惡程度會有所不同。唉,只有以後慢慢彌補了。
「師兄,你是方外人,怎麼連世俗中的事情也看得那麼透澈呢?」她甩甩頭,拋掉煩惱笑問。
「阿彌陀佛,就是看破世情而已。」虛海目光悠遠,一臉虛無狀,「師妹,注意『看破』二字。」
如初噗哧一聲笑出來,「那師兄又所為何來呢?」
「為妳而來。」他說得簡單直接,卻嚇了如初一跳,不明就裡地望著他。
於是,他又露出那拈花微笑的神情。那是他的皮相,完全不會露破綻的,不管心裡有多少火在燒,表面上仍然可以淡然若水,「我想……就算困難重重,師妹終是會嫁給小光的,因為他是個性情堅定、百折不撓的人,否則就不值師妹以心相許。既然妳要成親,身為師兄的,當然要準備賀禮。」
「師兄是為送賀禮來的?」這回答讓如初很意外,「可師兄不是常說錢財乃身外之物,你應該是沒有錢……難道你之前說要辦點私事再來找我,是去為我『化』禮物?」
「非也。」虛海搖搖頭,「禮物自然是我最珍貴的東西,如何能化來?我辦的私事其實是公事,我辭掉僧官的職位,再回少林辭去戒律院首座之職,然後拿了度牒……」
「師兄拿度牒是要去雲遊嗎?」如初插話道,心中有些不捨得。
有這個腹黑、多智的師兄在身邊,她感覺非常安全。現在的虛海對她而言,就和胡大海一樣是她娘家的人、是她的依賴和靠山,更因為虛海知道她真實的身分與來歷,那種感覺更加特別的親切。
「拿度牒,是要免除徭役。」虛海雲淡風輕地說出高僧不該說的話,看起來一點心理負擔都沒有,「師妹有什麼資產可以放在小僧名下,不用繳稅。」
他說得認真,卻把如初逗得咯咯直笑。世上哪有這樣的和尚啊,居然逃稅!
「那你到底要送我什麼禮物?」為了避免再聽到什麼驚世駭俗的話,如初話題一轉。
「天機不可洩露。妳成親那天,小僧自會告訴妳。」虛海神祕一笑,令如初總感覺他又有什麼壞主意。
不過,還沒等她逼問,虛海卻說出另一個與他們的談話八竿子打不著,卻十分重要的消息:「我在京城時遇到了胡宗憲,他被皇上欽點為浙江巡按監察御史,雖然不是多大的官,但是他直接參與平定沿海倭患事宜。他跟我提起小光,認定他是個百年難見的人才,說一旦有機會,會想辦法讓小光到倭患最嚴重的地方去,一展他的才華。」
如初聞言一愣,想起那個在她被俺答擄走時,寧願充任小兵也要參與追擊行動,以此巴結嚴世蕃的人。他果然因此而升官了啊!
話說回來,小光終於可以站到歷史的舞台上了嗎?那她的位子又在哪裡?還有,師兄到底要做什麼呢?
「你怎麼沒告訴小光這事?」如初回了神後問。
「他一直像守著寶貝似的守著妳,我哪有時間跟他說話?」虛海端起茶抿了一口,然後皺了皺眉,大概是覺得茶不好,「再者,他胸中本有遠大抱負,現在對他說,他難免會心浮氣躁,只怕連眼下海防衛的事也做不好。師妹,妳最好什麼也不提,一切等水到渠成方為上策。」
如初點了點頭,她雖然覺得情人之間不要有任何祕密,但經歷了最近一些事,她心智成熟不少,明白很多事沒有絕對的對與錯,有時候緩一緩、退一步,甚至輸一局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既然現在她的身體完全好了,就該按計畫和虛海一起先到登州海防衛去「微服私訪」,為小光之後成為民族英雄之路墊墊場。人家都說一個好男人背後肯定有一個好女人,那她就先做背後的好女人吧!
三天後,她和虛海到達了目的地。
其實,她本不必花這麼多時間的,不過她先繞道到有慶善號分號的大鎮上轉了一圈,寫信通知父親自己一切安好,然後支了點銀子出來,還和此分號的掌櫃、夥計聯絡了下感情,提防萬一出什麼事,娘家這邊能支援。
「穿越最重要的是什麼?是有一個好爹!」她再度感嘆。
「非常同意。」虛海應道,想起了自己那個爹來。
如初把身世祕密全都告訴他,他感覺神奇的同時也有些慚愧,因為他的祕密並沒有完全告訴如初。也許,以後找個機會告訴她吧。
「其實這邊的海防衛也沒有多荒涼嘛!雖然確實沒有天津衛繁華熱鬧,但小光說得也太誇張了。」望著眼前名為「富春」的小鎮,如初評論道。
富春說是「小鎮」,其實並不小,人口也多,遠勝於魯橋鎮。不過,大概是山東半島有倭患的緣故,富春鎮距離軍隊駐紮的海防衛所比較遠,走路大約要一天多,不像天津衛所就在海河碼頭附近,戚繼光所謂的荒涼可能是指這個。
在富春鎮和海防衛之間,還有數個由屯軍駐守的堡壘,漁民聚居的村鎮交互錯落著,其背後則是大片人口相對稠密的腹地,說起來也算是交通樞紐,是方圓幾百里最熱鬧的所在。
不過,鎮上分化嚴重,貧富極為不均,鎮西酒樓商肆林立,富庶繁華,不管想買什麼東西都有賣,包括買醉、買笑、買倒楣(特指賭博);鎮東則是貧民窟,據打聽鎮東的百姓多是附近礦山的貧苦礦工,一大家子人能吃飽飯就不錯了。
如初走過鎮東時,經常看到衣衫襤褸的孩子和形如枯槁的老人,連狗都是瘦骨嶙峋的,心裡覺得很是難受。
她來到大明兩年,沒真正看到窮苦的農民,直到此時此刻才見識到。
「富春鎮是誰管呀?」她很是惱火地問,覺得地方官如果任由吏下百姓如此,肯定是個該殺的。
「這邊還是海防衛的地界,應該是衛裡派人管轄,出了鎮往西就是當地官府的下屬轄區了。」虛海緩緩地答,「看來小光的擔子不輕呀!依我看,這邊的吏治腐敗到必須肅整的地步了。」
「我要為他當好馬前卒,把所有的事都看得清楚明白,好讓他下手治理。」如初一揮拳,因為有正經事做,心頭那絲為婚姻事而生的擔憂倒淡了,「我們先找個客棧住下來,觀察觀察情況如何?現在你是我哥,就讓我會鈔,不必化緣了吧?」臨了,她挪揄了一句。
他們此行是易了容的,如初和八重依舊是男裝,虛海則冒充俗世中人,成為一位風姿俊逸的翩翩公子。對外,他們宣稱是親兄弟,來自金陵,一個月前帶小書僮八重出來遊學,路經此處。
由於如初俊俏、虛海妖美,這一對「兄弟」一路不知擄走了多少少女心,如今到民風相對開放的富春鎮依然如此,走到哪兒都惹人注目。
如初對此有些煩惱,因為這限制了她暗訪的可能,但如果要是高調當幌子,確實是再合適不過了。
「小僧從師妹處化緣也是修行。」虛海一本正經地道,「就找個紅塵幻象最虛無的場所,然後酒肉穿腸過,再去最污濁之地散些財,保證能打聽到不少好消息。」
不出虛海所料,兩天下來,他們「兄弟」兩人住最好的客棧、上最好的酒樓,偶爾到賭場中小賭怡怡情,還真打聽到很多事情。
原來海防衛的財政來源除了所封屯田和些許漁產外,就沒別的收入,但衛所中的高級軍官卻都在富春鎮上有私人的生意,等級五品以上的,居然還在附近的礦山有類似於股權的分紅。
聽虛海講解,如初才知道這個時代本來不允許私人採礦的,朝廷把礦山的坑道封了起來,由當地官府看管。可是礦產利潤極為豐厚,部分「奸民」鋌而走險,私下開礦,就像現在的私人小煤礦,而朝廷屢禁不止,稅也無法徵收,各礦主之間還因為盜礦還經常發生械鬥事件,死傷嚴重,官府根本管不了。
後來就有大臣上書,朝廷開放了採礦權,名為「包採」。各地官府或者私人可以申請開礦,每年要繳納一定的銀子,浙江是一年四萬多兩,福建是一年兩萬多兩,山東和福建差不多。不過,朝廷不放心把礦權全部下放,在各地都派了礦監。
說來奇怪,這些礦監全由太監擔任。太監任要職,說來也是明朝的特色了。而目前,聽說派到山東的礦監病死任上,朝廷派的新礦監還沒有到。
「好買賣。」如初私下對虛海說,興奮得兩眼冒藍光,「要是海防衛能把這筆生意包過來,那不就是一條生財之路嗎?衛裡能自給自足,士兵就不會因為生活所迫而逃跑,小光也有錢賄賂上峰,組建新軍了。」
「哪有妳想的那麼容易!」虛海笑道,「先不說這包採權不好拿到手,就說妳吧,能把賄賂兩字說得這麼理直氣壯,倒也奇特。」
「目的永遠證明手段是正確的。要想保家衛國,有時候不得不裝出小人的樣子,甚至自侮自污。」如初嘿嘿一笑,「這叫適應環境,小光做不出來,我不一樣,我的良心可是很有彈性的。」
既然存了這份心思,如初就注意起包採的事情來。不過,還沒等她弄出個眉目,富春鎮就出了一件大事。
半夜三更時,如初正睡得香,忽然聽到街上傳來喧嘩和哭叫聲,那聲音之悲涼淒厲,令她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從心底寒了上來。
「八重,妳不用起來。」儘管客棧最好的房間保暖措施極佳,可是半夜鑽出熱被窩也是件辛苦的事,所以如初自己迅速穿衣下床。
打開窗子一看,見街上停了幾輛板車,車上蓋著草席,席下似乎有人,有幾個老人和女人邊哭叫著邊砸對街醫館的門,幾個瘦小的孩子圍著板車哭泣不止。
在如此寒冷冬夜出來,多半是家裡男人出了事,一家子老老小小,頂著寒風前來求醫,心中那悽惶怎麼是語言能形容得了的?偏偏那個名為濟世堂的醫館沒有半點濟世之心,裡面的人也是鐵石心腸,人家砸了半天門,連如初這種睡得很沉的人都醒了,他們還是不露面。
「怎麼了?小姐,外面哭得怪嚇人的。」八重白著小臉問。
「可能是窮人得了急病,沒良心的大夫不肯治,我下去看一下。」如初道,但心裡明白這不可能是普通的病,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多人同時求醫,而且非常急的樣子?
「外頭冷,小姐加件斗篷,不然我跟您下去吧?」八重一掀被子就要下床。
如初連忙攔住:「妳下去有什麼用?再凍著可怎麼辦?我叫師兄一起去,他的醫術很高的。對面那家醫館不幫人看病,就讓咱們的聖僧高手幫忙。」說完,幫八重掖了掖被子後,就跑出了房間。
沒想到她一衝出門差點撞到虛海,想來他也是被吵醒,要出客棧看看。之後,兩人下了樓,見兩個店夥計正打開一道門縫往外瞧。
虛海攔著冒冒失失要往外衝的如初,然後問夥計:「外面怎麼回事?」
「回爺的話,是附近礦上的人傷了,抬到濟世堂求醫。」一個年紀較長的夥計恭恭敬敬地答,因為這幾天如初出手闊綽,對夥計們也不苛求打罵,所以他們對這對「兄弟」很有好感。
「礦難嗎?」如初瞪大了眼睛。
年紀較小的夥計擺了擺手,道:「不是的,聽他們嚷嚷是刀棒傷,肯定是最大的那兩群礦黨又打起來了。」
又?看來師兄講的不錯,盜礦者之間為了爭奪資源會毆鬥,這確實是安定社會的隱患,真正受到傷害的不是礦主,而是最底層的礦工。不過,為什麼說「最大的那兩群礦黨」?難道是當地黑社會?
「把門打開,我們出去瞧瞧。」她說著向前一步。
那個年紀大的夥計立即攔道:「不行啊,小爺。外面天寒地凍的,濟世堂又不肯開門,您沒瞧見這條街上的店家都在裝死嗎?萬一咱們這兒開了口,那些人把病人抬到客棧裡可怎麼得了?」
如初一聽,擰起眉頭道:「你也知道外面天寒地凍!平時瞧你挺善良的,怎麼這時如此冷漠無情?外頭的人病的病、老的老,又有女人跟孩子,倘若我們真的不管,難道任由他們凍死?心裡連一點善念也不存,當心將來得報應!」
夥計聽她說得重了,都嚇了一跳,年紀小的趕緊解釋:「小爺,不是我們沒惻隱之心,實在是有難處。倘若這時開門,他們肯定一古腦全衝進來,掌櫃的非辭掉我們不可!若是弄壞了客棧裡的東西,說不定還要我們賠錢。我們哥倆也是有家要養的,哪能冒這險?」
如初也覺得自己有些性急,冤枉了好人,於是克制著情緒溫言道:「沒事,你們掌櫃的要發難,自有小爺我承擔,就算這些人拆了這客棧,小爺我也賠得起。開門吧,一會兒到我那兒領賞,絕不虧待你們。」
那兩個夥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時還是無法決定。
最後,那個年長的夥計道:「濟世堂的人不開門,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怕這些人交不出診金、藥費;二是怕他們傷重死掉,壞了他們名聲,畢竟富春鎮就數這家醫館最有名。我們知道小爺心善,可是這些傷者若是死在店裡,就太不吉利了。」
「真若如此,小爺我就買下這客棧,絕不讓你們掌櫃的吃虧。」如初見這兩個夥計還是不開門,知道他們怕擔責任,所以自己動手。這樣一來,就算事後掌櫃的怪罪,也是她這客人所為,與他人無關。
兩個夥計看她這樣,勸也不是,不勸也不是,一味的擔心。
一邊的虛海安慰道:「兩位不必如此擔憂。在下不才,倒是懂些醫理,倘若不是必死無疑之症,料想是能救得的。兩位先聽我的,你們趕緊把店中桌椅、板凳全搬到一邊去,再把燈火全點亮,然後一人速去報告掌櫃,說是客人私開店門,另一人把廚房的人找來,燒些熱水、熱湯,待會肯定派得上用場。對了,把其他夥計全叫來幫我的忙,事後……」他看了一眼如初的纖細身影,「定有重賞。」
聽這位慈眉善目的爺的意思,他們又能行善,又能拿大筆賞賜,何樂而不為呢?於是,依言而行,動作俐落,很快就把事辦好了。
與此同時,如初也已經帶著那群人進入店中安頓。不過,還沒等她關上店門,就又有一群人抬著傷患趕來求醫,他們同樣是在濟世堂吃了閉門羹,一回頭見客棧中燈火明亮,似乎有人在救治傷者,立即也抬了人進來。
頓時,客棧大堂內擠了幾十人,大人哭、孩子叫、傷者呻吟,忙亂成一團。
虛海態度沉著,忙而不亂,一邊叫惶急中趕來的掌櫃先安撫其他客人,也跟他說明會賠償損失;一邊指揮夥計把傷患抬到大堂左側,家屬隔離在另一側,然後依傷者的傷勢程度逐一診治,如初就緊跟在他身邊幫忙。
兩人正忙著時,突然聽到一個男人拉著嗓門叫道:「這位大夫,你怎麼不先診治我們的人?」
另一個男人冷笑道:「憑什麼你們先?」
話音一落,兩批人對峙了起來。
如初嚇了一跳,剛才只注意老弱病殘,沒發現有不少身體強健的青壯年男子跟進了客棧中,看樣子像是黑社會要鬥毆似的。
她一愣之後轉而大怒,氣呼呼地跳到兩群人之間,大聲罵道:「沒病的人給我滾出去!不然就別怪小爺我不客氣了。況且,我哥並不是大夫,他不過是一片善念,要用比濟世堂名醫還要高明的本事來救死扶傷,你們是來鬧什麼場!分了我哥的神,到時出意外誰要負責?醫者父母心,我哥要按照受傷的程度來治,輪得到你們攪和、多嘴嗎?我不管你們之間有什麼恩怨是非,現在這情況是小爺我說了算!要嘛,安安靜靜待在這兒看診;要嘛,立即給我滾出去!」
一番話說得兩群人對她怒目而視,但她凜然不懼,一一瞪了回去。
半晌,那個高大如黑塔的男人先帶著他的人,不服氣地坐到門邊去。而那個看來堅毅狠辣的瘦高個,則帶著自己人閃到樓梯邊。
如初逼視著兩方人馬,以眼神威脅他們不許輕舉妄動,否則傷患們的小命不保。感覺雙方都鎮定下來,她才回到虛海身邊幫忙。
「我把傷者分了類,也初步診了脈,但我沒有施治的東西和草藥,必須立即弄點來。」很快地,虛海提筆在紙上寫了草藥的名字遞給如初,低聲道:「草藥多多益善,但妳不要自己去,三更半夜的,我不放心。」
不就是需要醫療用具和藥品,這好辦!
如初看了一下,就先回到樓上去,正好八重因樓下的鬧烘烘而起床,於是她立即叫八重拿銀票出來,之後又跑到樓下,對著那個粗豪的壯漢和精明強悍的瘦高個勾了勾手指。
那兩人本來是死對頭,這時卻不禁互相看了一眼,然後走了過去。
「請問兩位英雄名姓?」如初問。
「陳大成。」瘦高個答。
「王如龍。」壯漢答。
如初態度稍放得溫和些,抱拳道:「陳兄、王兄,還請幫個忙。我哥這邊需要點東西,可是我又走不開,可以煩請兩位跑一趟嗎?」
「可是要草藥?」陳大成性格比較穩重,立即猜出如初之意,「這怎麼能說是幫忙!本就是我們欠了兩位兄弟的恩情,跑腿的事就交給我吧。」
「有勞陳兄。不過,還需施針行藥所用之物,反正是大夫們出診要用的,有什麼就拿什麼。」如初一邊說一邊拿出銀票,「只怕兩位還有不少受輕傷的手下吧!我哥的意思是救人救到底,索性一次多買點草藥,免得來回折騰倒耽誤時間。」
陳大成接過藥單,卻沒拿銀票,而是略施一禮道:「兩位兄弟仗義援助,陳某已經感恩不盡,銀子的事……還是我自己想辦法吧。」說著,轉身就要走。
如初早就打量過他和那個王如龍,雖然這兩位看似首領的傢伙衣著整齊,但應不是富貴之人,況且三更半夜的,到哪兒去籌措銀子?
於是,她攔道:「我看陳兄是個英雄,做事何必這麼婆婆媽媽?我們兄弟既然存了善念,就不在乎這些身外之物,陳兄又何必介懷?這時候哪有時間計較這些細枝末節?」
「我去買。」一邊的王如龍走上前,伸手奪過陳大成手中的藥單,又拿了如初手中的銀票,「大恩不言謝,我王如龍行事向來爽快,現在我拿不出這麼多銀子,但倘若小兄弟以後有用得到我的地方,只管跟我說一聲,我和我的弟兄就算上刀山、下火海也絕不推辭!」
如初連忙點頭。
她救治這些傷重卻無錢醫治的窮苦人完全是出於善念,不希望這些男人死了,留下孤兒寡婦,孤苦伶仃,更不想看到白髮人送黑髮人的人間慘劇。不過,後來王如龍和陳大成的出現,讓她生了一點私念,想藉機籠絡人心。
這兩個人一定是私礦的礦主,也是這些窮苦人的首領。而她知道小光是想從窮苦人中募集兵,因為他覺得城市中多市井油滑之輩,不如底層的農民純樸、能吃苦。現在既然有這樣的機緣,她就算是幫小光鋪鋪路,即使後來對募兵沒有大好處,幫他增加點名望也好。
「小兄弟如此磊落,倒顯得我小人了。」陳大成傲然一笑,「姓王的那傢伙平時雖然混帳,但這番話倒說得有理。實不瞞小兄弟,這回我們雙方鬧得大了些,受傷的弟兄也多,出來尋醫的多是重傷者,還有不少斷胳膊、斷腿,流著血的等救治。不知待會兒可否請貴兄到我那去,再次出手相助?」
如初沒回話,而是回頭看了看虛海,見他微微點頭才道:「四海之內皆兄弟,當然是義不容辭。」
陳大成點頭道:「那就有勞你們了。只是富春鎮就這幾間藥鋪、醫館,如今傷者眾多,只怕草藥未必夠用,不如我連夜到其他鎮上搜羅些,免得貴兄醫起人來綁手綁腳。」
「好,那我讓我哥再寫張藥單子。」說完,如初把另一張銀票塞到陳大成手裡。
陳大成微微一笑,「我雖沒有過目不忘的本事,但記幾味藥是沒問題的。」說完一抱拳,快步離開。
看來他是識字的,和王如龍比起來,性子應是有其細膩的一面,將來小光必定用得到此人。不過,這次是什麼樣的鬥毆呀,居然讓鎮上的草藥不夠用?目送陳大成身影消失,如初在心裡盤算了一番。
不久後,王如龍就帶著藥單上所列的東西回來了,辦事相當有效率,也不知是用什麼兇惡法子。想必剛才不肯伸出援手的醫館、藥局,一看到有銀子可賺,也就不會太刁難。
有了針藥等物,虛海就立即施展神醫聖手。
因為這些傷者全是因鬥毆而起的外傷,並非疑難雜症,所以只花半夜的工夫就全處理好了。幾個傷勢特別重、不宜搬動的,如初還出高價訂了客房安頓他們,讓兩方礦主欠她的人情再加上一分。
清晨時分,陳大成也回來了,虛海和如初依約到他們的地盤去治療輕傷者,雖然陳大成和王如龍的「總部」都在富春鎮,但因為附近好幾個鎮都有人牽連進去,所以他們奔波了一整天才算全部了結這件事。
不過,如初也因而打聽到這次集體械鬥的真相,不禁嘆為觀止。
總共有三千多人參加了這場可怕的鬥毆……不,應該算得上是戰鬥了,怪不得官府不敢管,畢竟衙門裡的官兵只怕也沒這麼多人,也怪不得各鎮沒有醫館願意替他們治傷,生怕治了這派的人就得罪了那派。
但,儘管聚集的人多,但他們並不是當地的黑幫,如此拚命,不過是為了掙幾個銀子。他們還要上下打點貪官、向朝廷繳納重稅,每天辛苦勞作,就是想讓一家子有口飯吃。
對於來自現代的如初而言,她實在不理解這些人的思維,既然能如此團結地打架,為什麼不一起抗爭呢?既然連命也捨得豁出去,為什麼還要怕貪官污吏?還為了某個礦道、山頭,打得你死我活?
「難道妳要他們造反嗎?這些百姓全是老實人,只要有一絲活命的機會,他們是不會輕易抗爭。那些無恥貪官利用的就是這一點,吸乾他們身上所有的血,卻留口活命的氣。」虛海嘆了口氣。
那個坐在京城西苑、高高在上、只顧著修仙問道的人,知道這一切嗎?倘若不是因為那個「二龍不相見」的魔咒、假如這天下為他所有,他一定不會讓百姓如此苦的。可惜……他現在唯一能保護的,就只有身邊的人了。
如初一想也是,記得以前上歷史課,老師總講到農民起義的侷限性什麼的,看來封建時代的人真的缺乏自由思想,也沒有那個環境和機制讓他們爭取正當權益。而她是穿越者,知道自己沒本事,也不應該改變歷史,只能做點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縱然千般不捨、萬般不願,戚繼光第二天一早還是忍痛離開了如初,先回魯橋鎮再做打算。不過,一想到虛大師和如初在一起,他將照顧她的病情、排解她的憂愁,最後還要和她一起先到海防衛去,他的心裡就七上八下的。
這種情緒如此強烈,他完全掩飾不住,被趙三紅看了出來。
「你不相信如初?」趙三紅勸道:「虛大師確實是人中龍鳳,但他畢竟是出家人嘛!再說,如初也不是這樣朝三暮四的人。」
「我當然相信她。」戚繼光毫不猶豫地點頭,「我怎麼會懷疑她的人品,我只是……不相信我自己。」
「什麼意思?」趙三紅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