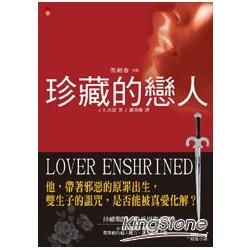他,帶著邪惡的原罪出生,
雙生子的詛咒,是否能被真愛化解?
持續戰鬥,只為捍衛愛情──
永不退燒的黑劍會系列,
罌粟般的魅人魔力,讓人不禁上癮……
紐約卡德威爾市暗夜裡的一角,吸血鬼與獵殺者仍然持續對峙。黑劍會是吸血鬼貴族中最具戰鬥力的一群,他們的存在,是為了捍衛自己的族群。菲尤里是黑劍會中,帶著詛咒原罪出生的雙生子之一,為了解救自己的胞兄,他曾經在黑暗世界裡孤軍奮戰。而這一次,為了延續種族的血脈,他再次義無反顧地獻身……
對黑劍會誓死忠誠的菲尤裡,為了種族而犧牲自己,肩負起傳承黑劍會血脈的任務。身為聖澤侍女的普萊姆,他必須延續種族的香火,成為下一代黑劍會戰士們的父親。
他那被選中的伴侶──聖澤侍女卡米亞,被高尚、充滿使命感,可內心卻傷痕累累的他所吸引,除了和他一起善盡種族的義務之外,更渴望得到他的心。可是,被責任所束縛的菲尤裡,卻不許自己感到一絲喜悅與快樂。當與賴失寧組織間的戰爭變得更加險惡,黑劍會的主屋籠罩在悲劇的陰影中,菲尤裡必須在責任與愛情間做出選擇……
作者簡介
J. R .沃德 J.R.Ward
目前與全力支持她的丈夫,還有寵物黃金獵犬住在美國南方。
從法律學校畢業後,她便進入波士頓的醫療機構上班,隨後又在醫療研究中心服務許多年。
寫作一直是她的最愛,一整天待在電腦前寫作,旁邊又有心愛的狗陪伴,再來上一壺咖啡,就是最完美的一天。
譯者簡介
羅秀純
外貿人才養成班畢業,曾任職外商公司擔任總經理秘書。後因喜愛寫作,投入文學創作,至今十餘年,曾出版數十本愛情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