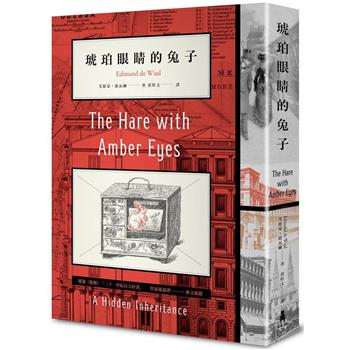第三十二章 原來如此
「你為什麼躲著我?」
夙羽微低著頭,顧雲看不清他的臉,只聽見他有些口齒不清地回道:「我沒有……」
夙羽一開口,濃烈的酒味醺得顧雲眉頭緊緊地皺在一起。他肯定喝了不少,始終低著頭不再理她。顧雲實在不解,她什麼時候這麼遭人討厭了?於是好奇地問道:「我得罪你了?」
顧雲不過是隨口一問,夙羽卻像只刺蝟似的,每一根刺都繃得直直的,沙啞的聲音幾乎是在嘶吼:「我說了沒有!妳以後可不可以不要在我面前出現?」
夙羽這一吼,更是激起了顧雲的好奇心,「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就是不想見到妳!妳走!」一邊說著,夙羽竟然還動手推她。
胸口的傷已經好了大半,被這麼推幾下並不是很疼,不過顧雲顯然已經開始不耐煩了,「你發什麼酒瘋!?」推開他還搭在肩上的手,顧雲決定不再和一個爛醉如泥的人廢話。
顧雲轉過身,手腕上忽然一痛,那力道大得驚人,顧雲疼得倒吸了一口涼氣,回頭一看,只見夙羽死死地拽著她的手,一點鬆開的意思都沒有。顧雲暗罵,這死小子想捏碎她的手啊!
顧雲正在考慮要不要給他一拳醒醒酒的時候,夙羽倏地抬起頭,映入眼簾的這張臉嚇了顧雲一跳,已經握成拳的手僵在那裡。
酒喝多了,臉色紅得發黑,一向光潔的臉上滿是剛剛長出來的鬍渣,充血的雙眼晦暗無神,好像是在盯著她,實則飄忽得厲害,濃重的氣息帶著酒味撲面而來,顧雲臉色也隨之暗了下來。
夙羽在搞什麼鬼,原來俊秀挺拔的一個人,才幾天不見,怎麼就搞成這樣了?
顧雲想抽回手,扶他回他的院落休息,誰知看起來已經醉得一塌糊塗的人,抓她的手還抓得那麼緊,任憑顧雲怎麼拉,他就是不鬆手,最後,夙羽乾脆將她的手抓到胸前,緊緊地貼在胸口的位置。
顧雲一驚,還沒來得及反應,夙羽又瘋了般地摔開他的手,驚慌地往後退,嘴裡低喊著:「妳是大哥的,妳是他的!」
本來走路就已經不穩了,才退了幾步,夙羽就一個踉蹌摔在地上,身體幾乎是直接砸下去的,嘴裡嘟囔著什麼,聽不清楚。
顧雲從來不和醉漢打交道,以前隊裡聚餐,一群人拚酒,她一般不會醉,快結束的時候,她會直接走人,絕對不去收拾殘局。
看著癱在地上的男人,她很無奈,準備去叫巡夜的將士把他扛回去,走過他身邊的時候,聽見夙羽一直在說什麼冰煉「……妳……」之類的。
她一直知道冰煉身上有祕密,夙家幾個老頭不肯說,她可以從夙羽身上下手,半蹲下身子,顧雲仔細聽他說些什麼。
「為什麼冰煉要選妳?為什麼是妳!?冰煉——」
斷斷續續地聽了很久,顧雲還是沒太明白,趁著他醉得糊塗,顧雲低聲問道:「冰煉選擇我,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夙羽閉著眼睛,嘴裡嘟囔了幾句,顧雲聽不清楚,失望地正要離開,夙羽又開始發瘋地坐了起來,充血的眼盯著顧雲,不再像剛才那樣恍惚,而是直直地盯著她,眼中複雜難解的光芒,讓顧雲都有些心驚。
久久,夙羽終於開口:「冰煉選擇了妳,妳就是大哥的妻子,妳是大哥的女人,我不能……不能……」喜歡妳!
最後三個字來不及說,他的衣領已經被顧雲一把抓住,顧雲緊盯著他,語氣急躁地問道:「你說什麼?冰煉選擇誰,誰就是夙凌的妻子?」
夙羽忽然笑了起來,可惜笑得比哭還難看。
顧雲仍是不肯放開他,逼問道:「你說清楚!?你今天不說清楚,我是不會讓你走的!」
夙羽佈滿血絲的眼回視顧雲,一邊笑著,一邊說道:「千百年來,夙家的長媳都是冰煉選的,只要是它選中的人,沒有人可以反對。不管那個女人長得是美是醜,聰明還是愚鈍,只要是它選的,夙家子孫就必須認同。妳是冰煉選的,我連爭的機會都沒有。妳現在懂了吧?」
似乎是為了宣洩,夙羽每一句都吼得很大聲,顧雲想聽不見都難,夙羽最後一句的表白她根本沒來得及去注意,前面的話如同一記重錘,狠狠地擊在她的心上。
是美是醜,聰明還是愚鈍,只要是它選的,夙家子孫就必須認同!夙凌也是這麼想的嗎?
抓著夙羽衣襟的手不自覺地鬆開,顧雲喃喃自語道:「你的意思是說,是誰並不重要,如果不是冰煉選我,夙凌他根本不會注意我這個人?」
顧雲一鬆手,夙羽啪地一聲又摔在地上,大笑地說道:「圍繞在大哥身邊才貌兼備的女人多得是!他不缺女人,不缺!」
是啊,她記得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是多麼地不可一世,甚至吝嗇正眼看她。與他在凌雲閣對打的時候,他看見她拿著冰煉的眼神,充滿了驚訝和憤怒,原來他是在抗議冰煉的選擇,後來他匆匆離開,是因為心有不甘嗎?
顧雲一直想知道冰煉身後的祕密,現在知道了,為何她會這麼難受?心悶悶的,幾乎喘不過氣來。
夙任遠遠地就聽見夙羽在大吼,夙羽與青末一個躺著,一個半跪,互相拉搡著,心下大驚,吼道:「夙羽!」
三步併作兩步衝過去,用力把醉得一塌糊塗的夙羽拖過來,盯著顧雲陰晴不定的臉,忙解釋道:「他醉了,妳別理他!」該死!羽到底喝了多少?
顧雲直直地盯著夙任,語氣急切地問道:「冰煉選擇的人,就是夙家的女主人。你一開始對我這麼客氣、夙家的長輩後來對我那麼好,甚至夙凌會對我另眼相看,都是因為冰煉選擇了我,是不是?」
夙任心一沉。羽果然還是說了。他思索著應該怎麼回答才好,「其實——」
看得出他的遲疑,顧雲一字一句地說道:「我要聽實話。」
太過敏銳的人,也不好啊!低嘆一聲,夙任回道:「一開始的時候確實是因為冰煉,但是後來大家都是真心喜歡妳的。」
原來是真的——顧雲的臉色忽然有些發白,沒再說什麼,轉身就走。
「青末!」夙羽整個人掛在他身上,他又不能追上去。看著她清瘦的背影中透著少有的冷漠,夙任的眼皮不知怎地跳個不停。
扶起地上喝得爛醉的夙羽,夙任罵道:「臭小子,你這回闖大禍了!」大哥要是知道了,絕對扒了他一層皮!
顧雲走回倚天苑的路上,腦子裡不斷重播著與夙凌的每一次交集,從厭惡、憤怒、漠視,到後來的認同、關心,甚至是喜歡,彷彿都與冰煉有關。
若不是冰煉,在剿山賊的時候,別說接收她的意見,他或許根本不會聽一個異國女子多說一句話;若不是冰煉,他應該也不可能讓她這個女人來訓練他夙家軍中的精銳之兵吧?若不是冰煉,那天他是不是也不會說出那句「我願意」?
心裡悶悶的,顧雲走進屋內,一眼便看見了懸掛在牆上的冰煉。輕輕將它取下,握在手心,微涼的氣息以前她覺得很舒服,今晚不知道為什麼,這股涼氣似乎竄進了心裡,心也跟著冷了。
輕撫著瑩白的劍身,顧雲低聲問道:「一切都是因為你嗎?」
清冷的聲音第一次如此迷茫,問出這句話的時候,心倏地一痛,這種不同於刀傷的疼痛,讓她竟有些站不穩,她緊緊地握著冰煉,冷聲問道:「你為什麼要選我?」
顧雲冷笑,她還以為自己有多特別,以為他是真心地喜歡她這個人,原來不過是冰煉選擇了她而已。在夙凌眼中,她是誰並不重要吧?難怪他能接受一張殘破的臉、難怪他忍耐她的囂張,難怪將軍府所有人都對她這麼好!
原來如此……不過如此——為什麼要選她!?她不需要靠一把劍來讓自己獲得別人的喜歡,她不要!
啪地一聲,顧雲將手中的冰煉扔回木盒中,轉身離開。
一直安靜地躺在木盒裡的冰煉,似乎感應到了什麼,從盒中一躍而起,攔在顧雲面前,似乎在向她示好。潔白的劍身在月光的照射下,美得讓人移不開眼。
可惜這時候的顧雲,沒有了欣賞它的心情,她冷漠地說道:「我根本就不屬於這裡,你不應該選我!」
她要回去!她要回到她原來的時代!
越過冰煉,顧雲繼續往外走,冰煉不死心地還要再跟,顧雲頭也不回地低吼道:「不要跟著我!」她現在腦子很亂,她只想一個人靜一靜!
冰煉被留在屋裡,在顧雲踏出院門的那一刻,渾身上下劇烈地搖晃著。
它的主人不要它了!炫目的白光照亮了寬敞的房間,白霧般的寒氣瞬間席捲了整個倚天苑。
顧雲深夜出現在將軍府門口,把守門的將士嚇了一跳,問道:「青姑娘,這麼晚了,您還要出門?」
「嗯,隨便走走。」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或許真的只是隨便走走。現在只有離開這座目前讓她窒息、讓她心痛的府邸,或許才能冷靜地想一想。
顧雲臉色不太好,一副心事重重、精神恍惚的樣子,守將不敢幫她開門,顧雲乾脆自己動手,將軍交代過可以讓她自由出入將軍府,守將也不敢攔她,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她出了府門。
年紀稍小的小將覺得還是不太妥當,低聲問道:「將軍還沒回來,要不要去稟報統領?」
年紀看起來稍長的將士想了想,回道:「還是去吧!」
小將點點頭,朝府內快跑而去。
誰也沒注意到,一道暗黑的身影緊隨著顧雲身後離去。
深夜的街道,沒有街燈,月光照不到巷子裡,純黑的駿馬與馬背上的人幾乎融入夜色,只聽見馬蹄聲由遠及近,並不急促。夙凌手握著韁繩,腦子裡還在想著今日送到的東海戰報。
東面領海時常有海盜作亂,但是因為穹岳貨物基本不走海路,皇上也沒有與附近島國互通的打算,故與海盜少有交集,但是近月以來,海盜竟然多次登岸,在領海小鎮上燒殺擄掠,我軍水師薄弱,多次追擊都讓其逃脫,他和兵部大臣商議了一晚上,決定擬寫奏摺請皇上加派兵力駐守東海。
夙凌還在思索著要調派哪一支隊伍前往東海,腰間的赤血忽然一熱,發出怪異的白光,在漆黑的夜色中顯得耀目而詭異,同時劍身異常劇烈地抖動起來,隔著衣物竟還是讓他覺得灼熱。
赤血少有如此激烈的表現,那道白光更是讓夙凌心驚不已。
冰煉發生了什麼事?想到那日夙任說的話,夙凌本就提起來的心倏地一緊。聚靈島的人當真如此厲害,連冰煉和影衛都護不了她?
握緊韁繩,夙凌夾緊馬腹,駿馬彷彿也感應到了主人的急切,長嘶一聲,暗黑的身影如利劍般飛馳而出,穿行於巷道之中。
急促的馬蹄聲,引起了門口守將的注意,抬眼看去,遠處一道黑影極快地疾馳而來,不一會兒已經到了眼前,馬上的人猛地一提韁繩,駿馬長嘶一聲,停在將軍府門前。
看清馬上的人,守將立刻迎了上去,「將軍!」將軍臉色凝重,守將正猶豫著怎麼和他說青姑娘出府的事情,夙凌已經俐落下馬,將韁繩丟到他手中,急匆匆地往府內跑去。
夙凌剛進大門,與同樣形色匆忙的韓束遇上。
韓束長舒了一口氣,嘆道:「將軍,您總算回來了。」
夙凌擔心自己猜想的事情成真,口氣有些急躁:「出什麼事了?」
韓束表情怪異地說道:「倚天苑出事了,您快去看看吧。」
果然出事了!夙凌腦中自動憶起一劍穿心那一幕,身上一冷,臉色變得很難看。
韓束奇怪地看著夙凌呼吸不暢的樣子,急道:「將軍,您怎麼了?」
韓束響亮的聲音將夙凌的神智拉回,只見韓束除了表情有些古怪之外,並無異樣,以他的性格,若是青末在府中遭襲,他不應該是這樣的神情,夙凌壓下慌亂不安的情緒,一邊朝倚天苑的方向疾步行去,一邊問道:「到底怎麼回事?」
緊跟著夙凌的腳步,韓束眉頭糾結在一起,滿臉茫然地回道:「倚天苑附近不知道為什麼,忽然被一股寒氣包圍,冰冷異常。我本來想進去看看,可是走到院子的時候,整個人都快凍僵了,不得不先出來。不知道青姑娘在不在房裡?要是在就麻煩了!」
寒氣?冰煉雖冷,卻不至於讓人走到院子就受不了的程度,夙凌也不明所以,不過聽到不是夜襲,提著的心放下了一半,只是腳步絲毫沒有停滯。
年紀稍長的守將拴好馬回來,兩人早已沒了影。這時,前去報信的小將小跑著趕回來,沒等他站穩,年紀稍長的守將急道:「你剛才看見將軍了嗎?」
小將搖頭回道:「沒有。」
「夙統領呢?」
小將挫敗地回道:「也沒找到,他不在自己的院子裡。」他還去書房找過了,也沒看見統領。他明明沒有出門,怎麼就不見人了呢?
夜風瑟瑟的晚上,守將急出了一頭汗,「我剛才好像聽到韓前鋒說,倚天苑出事了,青姑娘不就是住那兒嗎?」
「現在怎麼辦?」小將也跟著緊張起來。早知道是這個情況,剛才無論如何也不能讓青姑娘出府!
拳頭緊握,年紀稍長的守將心一橫,說道:「你在這兒守著,我去倚天苑稟報將軍青姑娘出府的事情。」知情不報,罪更重!
「嗯!」小將嚇出了一身冷汗,連忙點頭。
年紀稍長的守將拔腿就往倚天苑衝過去,越往裡走,只覺得一股透心的寒氣直逼而來,竟不自覺地抖了起來。
韓束和夙凌趕到倚天苑的時候,也被眼前的景象驚得一時間動彈不得。
只見一人多高的院牆上,結著一層薄冰,瓦片上結著一條條兩寸有餘的冰柱,茂密的樹葉在夜風的吹拂下生硬地擺動著,本來應該是葉片摩挲的沙沙聲,此刻因為樹葉也結了冰,發出一陣陣小石頭敲擊般的怪聲。整個倚天苑籠罩在寒冰之中,月色下發出瑩瑩流光。
倚天苑外,夜巡的將士看著這樣的奇觀,全都目瞪口呆地僵在院前,一個勁兒地哆嗦著。
夙凌最先回過神來,朝著院門走去。
韓束直直地瞪著院牆上的冰柱,忍不住怪叫道:「我的天!剛才我進去的時候還沒結冰柱呢!這才十一月,怎麼會有這種怪事?」
穹岳位處南方,京城更是選在溫暖舒爽的好地方,一年下來,唯有新年那幾日會飄些雪花,幾時見過這種場面?
夙凌走到門外,院門忽然從裡邊打開,一股極寒之氣立刻湧出,所有站在門邊的人都不自覺地打了個寒顫。
一道高壯的身影一邊拍著身上的碎冰,一邊咒罵著走出來,「冷死老子了!」
從門外看去,屋內透出炫目的白光,將院子裡照得一片敞亮,草地上還結了半尺厚的冰,窗櫺屋簷上全是冰凌,站在院外,已經能感受到入骨的冰寒,若是置身其中,那滋味可想而知。
夙凌急道:「晏叔,她在裡面嗎?」
夙晏趕緊關上院門,一邊搓著僵硬的手指,一邊哆哆嗦嗦地回道:「那丫頭不在。冰煉不知道發什麼瘋,離它一丈以內的東西,全被它凍成了冰塊,白光炫目得刺眼。」沒想到冰煉的能力居然這麼強,若不是他有四十多年的內功護體,怕是進得去出不來了!
「她不在?」那她去哪兒了?夙凌一把推開院門,要進去一探究竟。冰煉會這麼不對勁,一定是知道她發生了什麼事。
院門一開,湧出的寒氣竟然比剛才更加刺骨,夙晏縮了縮脖子,一把拉住夙凌的衣袖,急道:「凌,你別進去,冰煉今晚很不對勁!」
多年來,冰煉雖然一直都寒涼,但是夙家人碰觸它,它都會收斂寒氣,即使依舊冰冷,卻不會凍傷他們,可是今晚他進去,冰煉非但沒有收斂寒氣,反而在他靠近的時候,寒氣更盛,若不是他身手敏捷地躍開,一定會被凍在裡面。
夙凌皺眉,心中有一種不好的預感滋生。
她一定是出事了,不然冰煉不會如此。
握緊手中的赤血,夙凌回道:「我有赤血,沒事!」越是如此,他越要進去。
看了一眼他手中的暗紅長劍,夙晏放心了一點,終於放開了手。
夙凌踏入院中,反手將院門關上,屋內的冰煉似乎感應到他們的到來,本就耀眼的白光愈發炫目。此時,始終安靜的赤血也開始不安地抖動起來,一股暖流由掌心湧入,替他擋了不少寒氣,助他順利走近那座幾乎被冰封的小屋。
夙凌用力推開門,只見偌大的房間沒有打鬥過的痕跡,冰煉正懸於半空,正如夙晏所說,它身邊一丈有餘的東西都被它凝凍成冰,變成中空的大圓柱。而在那炫目的白光堅冰反射下,更是刺得人睜不開眼。
夙凌強忍住凌厲如刀的寒風,跨入屋內,焦急地問道:「冰煉,她人呢?」
他不問還好,一問之下,立刻觸怒了冰煉,隔著一丈多厚的寒冰,冰煉忽然朝著他襲來,隨著它的移動,寒冰也隨之移動,就在瞬間,堅冰攜著極寒之氣和毫不留情的力道直逼而來。
夙凌大驚,後躍一步,手中的赤血一劍橫劈而出,猩紅的劍氣撞上冷冽的堅冰,轟地一聲巨響,堅冰赫然被一分為二。
可惜夙凌和赤血也沒佔到便宜,胸口的悶痛提醒他,剛才那一劍反噬的力量讓他差點受了內傷,而赤血在剛才那一劍之後,到現在還在抖動!
夙凌鷹眸微斂,還想再進去,手中的赤血忽然橫在他身前,不讓他再往前多走一步。
隔著碎裂的堅冰,冰煉似乎也不服氣,瘋狂釋放它的寒氣,碎冰居然又一點一點地凝結起來。
看來冰煉是不打算和他甘休了,夙凌思索了一會兒,不再往前走,轉身退出院外。
門才拉開,他立刻被一隻大手拽了出來。
夙凌出來的時候,不僅渾身上下都是冰屑,就連頭髮和眉毛上都結了冰花,呼吸間,白白的霧氣升騰,可見在裡面也是凍得夠嗆。
看他這副狼狽的樣子就知道,赤血也沒能幫上什麼忙。夙晏趕緊幫他把身上的冰拍下來,焦急地問道:「怎麼樣?」
夙凌黑著一張臉,回答道:「冰煉在暴怒,我也不能靠近它。」
夙晏莫名其妙地問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她不見了,冰煉又莫名其妙地發瘋,夙凌被現在的狀況逼得心火直冒。
此時,夙全和夙任也來到了倚天苑前,看到眼前的景象,就連總是笑咪咪的夙全也是一臉嚴肅。
「青末知道冰煉選妻的事情了。」就在夙凌一頭霧水,心焦憂慮的時候,夙任低沉的聲音忽然響起,道出了問題的癥結點。
她知道了?
「誰和她說的?」夙凌寒眸怒視著夙晏。
夙晏趕緊後退一步,急道:「不是我!」
夙任低嘆一聲,解釋道:「羽今晚喝醉了,正好和青末遇上,他心裡難受,就口不擇言地說了。我看她聽完之後,臉色有些難看地回倚天苑了,本來想送羽回房之後就去找你,誰知——」是他疏忽了。一個如此驕傲的女人,怎麼可能受得了自己不過是一把劍的附屬物?
夙凌心一沉。她走了?
似乎是為了印證他的猜測,守將急忙上前一步,說道:「回稟將軍,青姑娘在半個時辰前出府去了。」
「她去哪兒了?」
夙凌的怒吼嚇得守將臉上發白,哆哆嗦嗦地回道:「她她……她說隨便走走,我們也沒敢問。」
「混帳!你們為什麼不問她去哪兒了?為什麼不跟著她!?」
夙凌煩躁的怒吼聲,不僅嚇傻了站在一旁的守將,就連在場的所有人都被他暴怒的樣子驚到了。
關心則亂,夙凌顯然已經亂了方寸,夙任趕緊為他分析道:「大哥,她有影衛保護,沒事的。等族長回來,把影衛召回來,就能知道她在哪裡了。」
影衛只保護夙家人,也只接受族長的號令,族長不在,他們要知道她的行蹤確實不易,但是有影衛在,她應該不會有什麼危險。
夙任很淡定,夙凌卻沒有這麼好的修為,畢竟失蹤的是自己的女人。
「你在府裡等族長回來。有青末的消息,立刻派人攔住她。無論如何,一定要給我找到她!」丟下一句話,夙凌也不管他們的反應,轉身就往府外疾奔而去,只留下一群被他的怒火掃到的男人們,心有餘悸地站在那裡。
盯著那道旋風般離去的高大身影,韓束心下了然。將軍如此慌亂的樣子,他還是第一次見,青末在他心中的位置已不言而喻。他轉頭看向同樣面色凝重的夙任,問道:「現在怎麼辦?」
「她沒有騎馬,走不遠,我在這裡等族長,你安排將士分成小隊,把京城翻一遍也要找到她!」找不到她,三弟就慘了,就算大哥肯放過他,他自己也能把自己逼死。
韓束點頭回道:「好,我這就去。」
「韓束。」夙任忽然又叫住了他,思索了一會兒,才交代道:「小心謹慎些,別落人話柄。」
韓束拍拍胸口,回道:「放心。」
韓束話音才落,一陣咯吱咯吱的脆響在安靜的夜晚陡然響起,眾人沿著聲響的方向看去,只見牆上的冰居然如蔓藤般,開始緩緩地向地面蔓延,瑩亮透明的冰凌很美,但是這樣沿著地面一路吞噬而來的樣子,卻讓人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眼看著寒冰就要攀上腳背,夙晏如夢初醒般地大吼道:「後退!」
圍在倚天苑外的人趕緊退後,盯著地上還在逐漸延伸的冰凌,夙任的臉色也開始有些發白,對著韓束低叫道:「快去啊!」
「哦!」回過神來,韓束飛也似地往校場後的營地跑去。
寒冰還在瘋狂地往四面八方蔓延,夜巡將士們個個心驚不已。這青姑娘不回來,將軍府會不會被冰凍起來?
將軍府內亂作一團,顧雲卻絲毫不知情。
顧雲沿著青石板小巷慢慢地走著,抬眼看去,頭頂上只有幾塊雲霧遮蓋下的暗淡星辰,就連月光都不明朗,巷道的前方亦是一片漆黑,似乎看不見前路,她就這樣一步步地走著,心由一開始的憤怒,到後來的失望,再到此刻的迷茫,或許在這樣寂靜的夜裡,只有她的腳步聲和心跳聲清晰可聞。
她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因為她也不知道要去哪裡?第一次,她不知道自己想怎麼樣。
她十七歲入伍,十九歲入選武警特警部隊,偵察、野戰、圍捕、解救人質、反恐怖、反劫機……她已經不記得自己執行過多少次任務,直到二十四歲執行反恐任務時,右肺被50AE口徑沙鷹手槍擊中,半邊肺葉切除,她不得不退役。
退役後,申請調入市局刑偵大隊,如願進入了警界,之後次次考核都全部優秀,破案率極高,各種任務也都完成得很出色。
然而,到了這樣男權至上的世界裡,她以為可以靠自己的實力獲得認可。結果才知道,原來一切不過是她的自以為是,她其實就是一把劍的附屬品,在他們眼中,她是誰或許根本不重要。
她現在只想知道,那個時常對她吼,卻總是會答應她的要求;急躁得沒有耐心,卻會默默地陪伴她喝藥;總是黑著一張臉,卻會彆扭地說出「我願意」的男人,是否看中的也不過是那把劍?他到底是喜歡她,還是習慣性地認可夙家神劍的眼光?
腳步變得有些沉重,顧雲背靠著冰冷的石牆,緩緩地坐在路邊的牆角處,將自己隱藏到黑暗中,頭輕輕地搭在膝蓋上,緩緩地閉上眼睛。
她一直以為她不在乎,但現在她的心為什麼會酸澀得難以忍受?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一代軍師(4完):不只是傳說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一代軍師(4完):不只是傳說 出版社:耕林 出版日期:2011-09-2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9 |
二手中文書 |
$ 193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一代軍師(4完):不只是傳說
千年的傳說不只是傳說,
它帶來了是詛咒的解藥,還有夙家的命定新娘……
傳說有一天,族徽會為夙家帶來一個人,
她將解開所有的封印,結束上天對夙家的懲罰。
如果她不是穿越而來、如果她沒有親眼目睹赤血冰煉的神奇,
身為刑警的她,絕對會認為這是不科學的迷信行為,
可是,在她身上發生的一切,
已經證明了「世界上沒有不可能的事」,
而且,這傳說還流傳了千年,
那不就表示──千年前的古早人就預言了她的穿越!
呃……這夙家不只家底雄厚、神劍選妻就罷了,
還可以拓展選妻範圍,到未來把夙凌的新娘打包回古代!?
嗚嗚嗚……天啊,她到底嫁進了什麼樣的異能家族?
現在後悔還來不來得及啊……
作者簡介:
淺綠
又名蝸牛綠。文筆清新,簡練精悍,故事情節引人入勝,字裡行間流露真情。她為人樂觀,堅信如果面前有陰影,那是因為我們背後有陽光。喜歡文字這種簡單而純粹的表達方式,深愛細水長流的情感表達。凡事隨心而至,寫文如是,人亦如是。現為瀟湘書院知名寫手,曾創作《陌香》、《商君》等,為萬千讀者喜愛。
章節試閱
第三十二章 原來如此
「你為什麼躲著我?」
夙羽微低著頭,顧雲看不清他的臉,只聽見他有些口齒不清地回道:「我沒有……」
夙羽一開口,濃烈的酒味醺得顧雲眉頭緊緊地皺在一起。他肯定喝了不少,始終低著頭不再理她。顧雲實在不解,她什麼時候這麼遭人討厭了?於是好奇地問道:「我得罪你了?」
顧雲不過是隨口一問,夙羽卻像只刺蝟似的,每一根刺都繃得直直的,沙啞的聲音幾乎是在嘶吼:「我說了沒有!妳以後可不可以不要在我面前出現?」
夙羽這一吼,更是激起了顧雲的好奇心,「為什麼?」
「沒有為什...
「你為什麼躲著我?」
夙羽微低著頭,顧雲看不清他的臉,只聽見他有些口齒不清地回道:「我沒有……」
夙羽一開口,濃烈的酒味醺得顧雲眉頭緊緊地皺在一起。他肯定喝了不少,始終低著頭不再理她。顧雲實在不解,她什麼時候這麼遭人討厭了?於是好奇地問道:「我得罪你了?」
顧雲不過是隨口一問,夙羽卻像只刺蝟似的,每一根刺都繃得直直的,沙啞的聲音幾乎是在嘶吼:「我說了沒有!妳以後可不可以不要在我面前出現?」
夙羽這一吼,更是激起了顧雲的好奇心,「為什麼?」
「沒有為什...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出版社: 耕林 出版日期:2011-09-26 ISBN/ISSN:978986286126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2013/04/12
2013/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