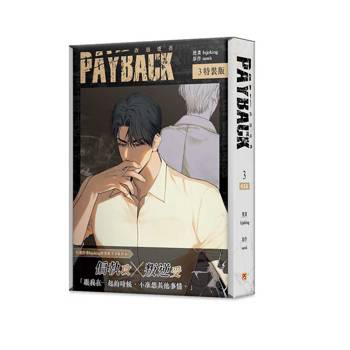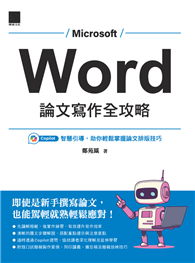桃花綠了春風,滄海桑田,人世變遷,轉眼便是六年。
僻靜的荒野,綠草蔥翠,楊柳依依,春風微微拂過,吹開一地繁花。溪水叮咚敲打著拍子,樹梢上鳥兒輕快的歌唱,為這一地的輕柔憑添無盡風情。
溪水中,梨花雨落,點點嫩白飄灑在河水裡,蜿蜒而去,煞是好看。
一白玉般的手臂從溪水裡破水而出,緊接著一纖細身影跟著穿出,灑落一溪水滴,濺起點點漣漪。
黑髮被攏到耳邊,如瓷般無瑕的白玉臉孔露出,眉心間一點櫻花胎記,粉嫩粉嫩的,柳葉眉下一黑如夜空的眸子,眼波流轉間帶起無盡溫柔,一點朱砂唇,小巧的瓜子臉,靈氣逼人,清麗無邊。
雲輕斜斜靠在溪水中的石頭上,這裡基本無人來,倒是不用擔心有人看見的問題。
抬頭望了望天空,天很藍,雲輕微微勾勒了一下嘴角。明天婆婆就會回來了,一個月沒見了,好想婆婆。
雲輕,也就是當年離開丁家的丁叮,離家之時帶她走的婆婆,就送了她一個名字——雲輕,雲淡風輕,從此後前緣盡消,不再留戀。
雲輕輕柔的一笑,朝溪邊走去,這麼幾年來,婆婆帶著她走南闖北,七國除了最強大的秦國和最邊緣的韓國沒去,走走停停的居然走過了楚國、趙國、燕國、魏國等四國。
而天下局勢也幾乎在這走走停停間,了然於胸。
今七國並立,以秦為最強,齊楚兩國次之,若按十分來算,秦獨佔三分,齊楚兩國占之四分,其他三分為韓、趙、燕、魏四國所瓜分,合縱連橫把戲層出不窮,戰火紛飛,誰都想一統天下,誰卻也都沒那個能耐一統天下,平白苦的也只是老百姓罷了。
只是亂世能保的也不過自己罷了,多想不過是徒增無奈。
雲輕浮出水面,正欲取衣,前面林中突然一片快馬奔馳之聲傳來。情況不對!雲輕立刻探身,一把抓過衣服,斜靠在溪邊的大石頭後,整個潛入水中去。
雲輕剛鑽入水中,林子前,一馬當先而出,一血衣男子迅猛遠去,身後一馬三人跟著奔馳出來,馬上三人一身狼狽,血濺身衣,鬢髮凌亂,不過臉色倒甚是沉穩。
嗖嗖。
幾聲利箭破空聲傳來,後一匹馬上,最後那人見逃之不過,手中劍光湧動,斜身躍起,與馬上前面那兩人一個前撲,在箭雨中穿了出去,而那老馬悲鳴一聲長嘶,轟然倒地,腹部、腿腳全部中箭。
馬蹄狂亂,十幾個黑布覆面,只露出一雙眼睛來的黑衣人,風馳電掣的追了上來,什麼話也沒說,揮舞著長劍就朝那三人追殺過去。
匡!當!
長劍碰撞的聲音響起,那三人中兩年輕人,護衛著中間那看起來文質彬彬的男子,竭力抵抗著,一片劍光飛閃,幾乎看不見圍攻的人影,鮮血如雪花一般飛濺出來,一地翠綠的顏色醞釀上鮮紅,居然妖豔的晃眼。
沒有人說話,只有滿天的劍光、砍殺和抵抗,目的相當明確。
一刀砍下,三人中飛起一片血光,一人背後被狠狠的劈了一刀,卻聲都沒出,咬牙死撐,無一人慘呼驚回跑遠的當前一人。
雲輕這麼多年來走南闖北,見過很多這樣的場面,這些黑衣人是殺手,是給他錢就可以買命的殺手,這麼多殺手,這三人是惹了什麼事了?
臉上神色不動,雲輕只是輕輕的伸手,摸向那大石頭上十寸長的古琴。那是她隨身的琴。
正在此時,馬蹄聲突然從林子的另一邊穿出,那當先而去的血衣男子,重新折返,穿林而出,一手拉韁,一手橫向握著一把利劍,黑髮幾乎飛在半空中,濃黑的眉如利劍一般斜插入鬢,那雙帶著點琥珀色的眼眸,凌厲的驚人,高挺的鼻子下緊緊抿著的唇,薄而寡淡,深如雕刻般的臉頰,混合著上面的血水,孕育出絕對的肅殺和兇狠。
「你快走。」那被圍困三人中書生模樣的人,焦急的朝掉頭趕回來的血衣人大聲吼道。
馬蹄未停,來人縱馬飛躍而來,並不理會他的話,一刀橫空而過,迎面對上他的殺手,劍在外,卻如定格一般,停在了半空,血色飛速四濺,而那來人停也不停,一提馬韁,手中長劍臨空一劃,快如閃電的刺向另一個人胸口。
血花四濺,馬蹄長嘶,雲輕只看見一個黑色的死神,拿著鐮刀在收刮生命的稻草,那劍幾乎快的她看不見,鐵硬的殺氣幾乎讓人窒息。
幾個照面間,那剛才三人對付不了的十幾個殺手,居然倒下三分之二多,而那血色男子,身上、背上連吃兩刀,卻哼都沒哼一聲,殺氣越發的凌厲。
剩下兩人一看情況不對,一聲呼哨,分兩邊縱馬而逃,具是挑那男子無法追擊的死角。
來人一聲暴喝:「想走?」
手下馬繩一提,腳在馬背上一點,身形臨空一個翻飛,斜斜朝向他身後跑去的那黑衣人馬頭落去,手中長劍橫於當胸,眉眼中殺氣一閃,一聲長嘯,橫空擊出。
一片血光,那黑衣人連人帶馬依舊衝過他身邊,卻在下一刻,血色如利劍而出,身形驟然一折,轟然倒地,馬和人連一聲都沒叫出。
那男子一擊得手後,眉眼一沉,手中長劍高高拋起,一個換手握住,揚手就朝那幾乎快跑的沒影的黑衣人投擲而去。
劍光閃動如流星追月,呼嘯而去。
一擲而出,該男子根本不再看那逃竄的人,轉身看著那自從他來,就在一旁歇息的三人,喘著氣沉聲道:「如何?」
「還好。」為首的那文弱書生模樣男子點頭答道。
而這個時候,遠處突然傳來一聲慘呼,緊接著咚的一聲重物著地,只餘馬蹄狂奔而出,那逃跑的人終究沒有逃脫。
雲輕見此不由得輕輕揚了揚眉,好厲害,然後一邊縮回手來,幾乎沒有聲響,然而……
「什麼人?」那血衣男人刷的一下轉過頭來,腳尖一挑,挑起地上的一把利劍,伸手一抓,快步就朝雲輕所在的地方走來。
雲輕見此,手腕一動,穿衣站了起來。
那男人一見溪水旁雲輕站了起來,眉眼中肅殺之色不收,血紅著雙眼,一片狠辣,什麼話也不說,手中利劍一舉,當頭就朝雲輕砍來,快的不給雲輕任何說話的機會。
雲輕見此也不躲避,只淡然的站在水中,幾乎像沒看見那人要殺自己一般,連眼都沒有眨。
而這個時候,旁邊草叢中一道黑光一動,迅猛無比的朝那男子面門射去,快的根本看不清楚是什麼東西。
黑光快,那男子也快,一見有變,手中長劍一翻,不及取雲輕的命,反手就是橫向一砍,朝那黑光臨空砍去,居然又快又準。
那黑光眼看著要撞上那刀劍,居然臨空一翻,不朝面門而去,一個翻滾斜斜向下,靈巧的從血衣男子胯下一翻而過,從他背後飛速竄出,又竄到雲輕的肩膀上,停下不動。
血衣男子再快,也沒快過牠,當下飛速的往後一退,眉眼中一片殺氣,瞪著雲輕肩膀上的東西。
一隻小小黑色的貂兒蹲在雲輕的肩膀上,巴掌大小,皮毛光滑的幾如油脂一般,此時瞪著兩個黑眼睛,惡狠狠的盯著那血衣男子,毛都炸起了。
雲輕見此溫柔的摸了摸小貂兒,不理睬剛要殺她的男子,緩步上了岸,理了理自已的衣服。
那血衣男子一看,眉眼一沉,反手就是一劍欲向雲輕砍去,卻手到一半,陡然發現無力,身體一陣麻木,幾乎動彈不得,腳下一軟朝後便倒。
「公子。」那一邊受傷不輕的三人,同時一聲驚呼,齊齊撲了過來。
本來蒼白的唇,此時已經佈滿一層黑色,早就傷痕累累的身體,飛速的轉換上一層灰白,快的讓人幾乎以為眼花,不過血衣男子眼中卻無一絲懼怕,只狠狠的盯著雲輕和她身上的貂兒。
「毒,這是毒。」那文弱書生模樣的人驚聲叫道。
「姑娘,手下留情。」文弱書生旁邊一鐵色衣裳的男子,一個轉身就朝雲輕低下頭來。
那些殺手刀劍上沒有毒,那麼只有一個可能,就是在這個女人手中中了毒,那貂兒有毒。貂喜食毒蛇,自然口爪帶毒,他們沒有帶解毒的藥,若耽擱時間,定然不治。
雲輕撫摸著貂兒,看了一眼血衣男子,淡淡的道:「他剛才可沒對我留情。」邊說邊抬腳就走,全然不加理會。
「姑娘,是我家公子的不對,只因我們的行蹤不能洩露給外人知道,姑娘,本非冒犯……」
「那我就該死嗎?」雲輕淡淡的打斷了那文弱書生的話。
文弱書生頓時語結,雲輕見此抬腳就走。
「妳沒死。」血衣男子咬牙切齒的話語,突然冒了出來,聲音沙啞,中氣不足,卻該死的低沉和肯定。
雲輕聞言轉過頭來,溫和的點點頭道:「所以,我也不能殺了你?」
沒有回答,但是那凌厲的眼,就這樣狠狠的瞪著雲輕,彷彿他的意思就是如此。
雲輕也沒說話,就那麼淡淡的看著血衣男子。
一淡然溫和,一兇狠冷酷,兩道眼光在空中交鋒著、對峙著,不知道在交涉著什麼。
旁邊的三人見此雖然莫名其妙,但是也不敢吭聲。
半晌,血衣男子的唇更黑了,呼出的氣都帶起一絲腥臭味,垂在身旁的五指緊握成拳頭,幾乎能聽見手指的咯吱作響。
殺氣,不因為中毒而減弱的殺氣,越發醞釀的渲染了整個溪邊上空。
雲輕彷若未見一般,依舊一派的淡然和幽雅。
「抱歉。」已經轉至醬黑色的唇,緊咬著,從牙縫中迸出這兩個字,冷淡卻擲地有聲。
旁邊那三個男子齊齊一愣,顯然沒有想到他們公子會說出這兩個字。這兩個字在他們公子心裡是不存在的,他的字典裡沒有這個詞語。
雲輕聞言嗯了一聲,點了點頭,返身走過來,俯下身去,開始察看血衣男子中毒的地方。
旁邊三人見此,對視一眼,這算什麼,原則問題?
雲輕一眼掃之,中毒的地方居然在那男子的大腿內側,距離隱私地方實在是不遠,幾條血痕劃過,正是貂兒的爪子印記。
雲輕見此,側頭看著貂兒搖頭,輕點了一下貂兒的腦袋,溫柔的笑道:「你這調皮的小傢伙。」
小貂兒親密極了的蹭蹭雲輕的臉。
「妳不怕我殺了妳?」血衣男子瞇眼看著雲輕。
雲輕劃開血衣男子的褲子,露出很隱密的地方,目不斜視的一邊伸手用小銀刀挑開血痕,放血,取出特地為貂兒的毒配置的解藥,一邊道:「只要你有這個本事。」
血衣男子眉眼中殺氣一閃,眼光深處暗潮洶湧,深深看了雲輕一眼,眼前一個昏暈,下意識的反手就抓住雲輕的手臂,狠得幾乎要扣進雲輕的肉裡去,雲輕不由得微微皺了皺眉。
「公子?」那三人頓時大叫。
「只是暫時昏過去了,貂兒很毒,而且他身上的傷太多了。」雲輕邊解毒,邊查看了一下血衣男子的傷。很多,前胸、後背、胳膊、腿幾乎都有,若是沒有這些能夠影響他行動的傷,估計貂兒可能傷不到他。
「多謝姑娘。」書生模樣男子點頭道。
雲輕一邊為血衣男子餵藥,一邊道:「舉手之勞而已。」
另一鐵色衣服的年輕男子,聞言看了一眼周圍後,沉聲道:「此處不能久留,我們必須馬上離開。」
「他毒還沒清。」雲輕頭也沒抬的輕聲道。
書生模樣的人皺了皺眉後,朝雲輕道:「能不能煩請姑娘一路,我們必須離開。」
雲輕聞言還沒答話,那書生模樣的人趕緊接著道:「只求姑娘能待到公子醒來就好,那時候姑娘要走,我們絕不阻攔。」
雲輕見這人已經把話說到這個份上,這血衣男子的毒也真不是一時片刻能解的,貂兒的毒可厲害著,再看看那人抓自己抓得死緊的手,想掙開也不容易,當下微微沉吟了一瞬間,便輕微的點了點頭。反正她也要離開這,一起走也無所謂。
見雲輕點頭答應,那三個男子頓時大喜,也不顧自己身上的傷勢,快速的拉過馬匹,讓雲輕和血衣男子同騎,他們步行跟隨。
雲輕見他們所走的正是自己要走的方向——她和婆婆所住的地方,當下便默不作聲的一邊為血衣男子解毒,一邊催馬前行。
身後,清風掠過,腥腥血氣醞釀開來,緩緩滲透至溪水中,泛起一溪暈紅,真乃多事之春啊!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獸妃(1):宿世冤家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50 |
二手中文書 |
$ 165 |
古代小說 |
$ 174 |
言情小說 |
$ 193 |
中文書 |
$ 198 |
古代小說 |
$ 19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獸妃(1):宿世冤家
【隨書附贈:拉頁海報】
他霸道冷情;她冷淡無慾,
他,武功絕世高超;她,能夠以音馭獸,
當一個無敵的大男人,碰上一個不甩人的大女人,
瞬間巨大冰塊化成燎原大火,一整個火花四射到不行!
一個爹爹不愛,姥姥不疼,
在眾人眼中除了浪費糧食之外,沒有任何用處的女孩,
其實是萬世難得其一,能以音馭獸的天才!?
丁家,武林世家出身,能夠以音色殺人而稱雄七國。
偏偏這一代出了個庸才女,竟然到了七歲,連樂譜都不識,加之身子骨弱,連武功都不能練,被當作下人使喚也就算了,甚至還被家人陷害,險些命喪自己母親刀下,逼得她遠離丁家。
原本以為從此以後,海闊天空,沒想到,她竟然又遇上了一個不講理的妖孽男,先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想殺了她,她為了防身讓自己養的貂去咬了他一口,他竟然又趁她不備還她一毒,用以逼迫她必須留在他身邊,以換取解藥。
這該死的男人,可惡得讓她不只想讓她叫貂兒咬,她都想咬他了!
偏偏,遇上危險之際,他卻又挺身護住她,就連她的琴音莫名其妙引來了一群食人猛獸包圍,他也沒拋下她,甚至盡全力護她周全。
這男人,到底是存了什麼心呀!?
作者簡介:
周玉
女,瀟湘網路作者。
這筆名我取的隨意,順手拈來,簡簡單單。
我喜歡風的變化萬千,自在逍遙,因此,有讀者說我筆下的文字,也同樣的變幻莫測,詭譎兇險中風雲乍起。
有人說女子當如風,文字當如雲,千萬種風情,以筆化作文中的美好和感動,我心嚮往之。
希望能瀟灑如風的追逐著自己的人生。同時也願給大家帶來更多不同的故事。
章節試閱
桃花綠了春風,滄海桑田,人世變遷,轉眼便是六年。
僻靜的荒野,綠草蔥翠,楊柳依依,春風微微拂過,吹開一地繁花。溪水叮咚敲打著拍子,樹梢上鳥兒輕快的歌唱,為這一地的輕柔憑添無盡風情。
溪水中,梨花雨落,點點嫩白飄灑在河水裡,蜿蜒而去,煞是好看。
一白玉般的手臂從溪水裡破水而出,緊接著一纖細身影跟著穿出,灑落一溪水滴,濺起點點漣漪。
黑髮被攏到耳邊,如瓷般無瑕的白玉臉孔露出,眉心間一點櫻花胎記,粉嫩粉嫩的,柳葉眉下一黑如夜空的眸子,眼波流轉間帶起無盡溫柔,一點朱砂唇,小巧的瓜子臉,靈...
僻靜的荒野,綠草蔥翠,楊柳依依,春風微微拂過,吹開一地繁花。溪水叮咚敲打著拍子,樹梢上鳥兒輕快的歌唱,為這一地的輕柔憑添無盡風情。
溪水中,梨花雨落,點點嫩白飄灑在河水裡,蜿蜒而去,煞是好看。
一白玉般的手臂從溪水裡破水而出,緊接著一纖細身影跟著穿出,灑落一溪水滴,濺起點點漣漪。
黑髮被攏到耳邊,如瓷般無瑕的白玉臉孔露出,眉心間一點櫻花胎記,粉嫩粉嫩的,柳葉眉下一黑如夜空的眸子,眼波流轉間帶起無盡溫柔,一點朱砂唇,小巧的瓜子臉,靈...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周玉
- 出版社: 耕林 出版日期:2012-06-27 ISBN/ISSN:978986286220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