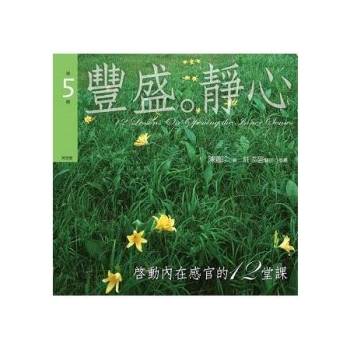窗外,清冷的月光依舊靜靜地灑落在緊閉著的窗戶上,房間裡有點兒冷。章桐伸手摸了摸床邊的暖氣片,果然,細細的指尖很快就傳來了熟悉的冰冷感覺。
暖氣停了。現在是凌晨一點半剛過,離天亮還要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需要去等待。
她費力地探身搆到了書桌上的幾張七寸相片,在徹骨寒意把自己完全吞併之前,重新又縮回到了被窩裡。
這是自己臨睡前還沒有來得及完成的工作。
相片中,是一朵已經乾枯的雛菊,土黃色乾癟的花瓣被草草地揉成了一團,壓得扁扁的,毫無生命氣息的枝幹,如同是用鐵絲在很短的時間內笨拙地彎曲製成的一般,醜陋而又怪異。
如果只是看相片,它和假花一般無二,但是章桐卻很清楚,相片中的這朵雛菊,是一朵曾經在溫暖陽光下充滿了生命的雛菊,就像那對眼球的主人一樣。
兇手的用意已經非常明確。可是自己到底該怎麼辦?
眼球的主人是不可能存活的了,而這對眼球離開人體的時間很顯然已經超過了七十二個小時,通過DNA尋找相關證據的可能性也就幾乎不存在,而且即使能夠提取到完整的DNA樣本,如果死者沒有進行過相應的備案登記的話,那麼結果還是為零,而這個,恰恰正是章桐最不願意去面對的一幕。
或許是盯著看的時間太久,相片中的雛菊突然讓章桐幾乎喘不過氣來,她不得不把相片翻了個面,反面朝上,微微閉上了雙眼,靠著床頭,似乎看不到它,自己的心裡至少能感覺好受一些。
十三年前,要是自己沒有記錯的話,曾經見過一朵幾乎和這個一模一樣的雛菊,而和它一同出現的,則是一具同樣沒有了生命氣息的年輕女孩那殘缺不全的屍體。
當時的一切,給章桐的印象並不是非常深刻,唯一讓她感到不寒而慄的,是耳邊傳來的那一聲聲撕心裂肺般痛苦的哀嚎。
那天,烏雲密佈,灰濛濛的天空下著很大的雨,圍觀的人群卻似乎一點都沒有因為那糟糕的天氣而受到任何影響,他們小聲議論紛紛,目光中盡是惋惜和驚愕。
突然,不遠處警用封鎖帶外,一輛警燈閃爍的警車飛馳而來,急剎車停下後,卻不等停穩熄火,一個男人就不顧一切地拉開車門跳下車,發了瘋一般悲泣著,向案發現場直直地衝了過來。
這突發的一幕,讓守候在封鎖帶周圍的員警嚇了一跳,最終,刑警隊的人不得不動用了手銬,幾個人合力,才把這個傷透了心的男人,給死死地銬在了那輛由他親自開來的警車車門邊上。
可是,儘管如此,遠遠看去,被雨水澆得濕透的男人,依舊幾次三番地在做著無用的掙扎,伴隨著陣陣哀嚎聲傳來,一邊的員警們只是默默地把頭轉開,似乎都不忍心去看這一幕讓人痛苦的場景。
這麼悲傷,肯定是聞訊趕來的死者親人。
「他是誰?」章桐抬頭問身邊站著的自己的同事。
同事只是面無表情地嘆了口氣,搖搖頭。遇到這樣的事,誰的心裡都不會好受的。
頭頂沉重的防雨布在大雨中劈啪作響,快結束屍表初步檢查的章桐,低頭看看死者殘缺的面龐上那異樣平靜的表情,又抬頭朝自己身後看去,那輛橫在路口的警車卻早就已經開走了。潛意識中,章桐的心頭突然油然而生一種悲涼的感覺。
事後才知道,死去的女孩是這個男人的親生女兒,也是他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親人。而這個男人,名字叫歐陽景洪,是一名緝毒警。
每個員警都有親人,而親人的意外逝去對誰來說,都是一次足以致命的打擊。
因為案發現場被一場大雨給沖刷得乾乾淨淨,死者歐陽青的身上又一絲不掛,所以,儘管在發現屍體後,盡可能多地做了補救措施,但是有用的破案證據卻仍然是少得可憐。
章桐記得很清楚,當這個案子最終被按照懸案定義而被封存起來的時候,和薄薄的卷宗放在一起的,就只有這麼一朵乾枯的雛菊了。
雛菊是在女孩本來應該是眼睛的地方被發現的,拿起雛菊,就是空蕩蕩的兩個眼眶。即使是外行人都看得出來,摘除眼球的手術進行得非常糟糕,很多眼部組織都被破壞了,橫切面參差不齊,深的地方甚至於已經觸及到了腦部組織。
章桐不明白,如此殘忍的摘除眼球,甚至可以用「挖」來形容,但是為何女孩體內沒有任何麻醉劑的殘留物,而臉上卻一點都沒有痛苦的表情顯露出來?
當然了,不同種類的麻醉劑在人體內停留的時間都是不一樣的,沒有發現殘留物可以解釋為屍體被發現時,殘留物早就已經分解消失。可是,還有那雛菊,又到底意味著什麼?
案件被宣佈終止調查後沒多久,歐陽景洪也在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
聽說他的工作出了差錯,導致槍枝意外走火,和他搭檔的同事因此而喪命,最終,這個曾經意志堅強、功績無數的男人,卻因為怠忽職守最終致人死亡而身敗名裂、進了監獄。
宣佈判決結果的那一天,警局顯得格外平靜,就連平時最嘈雜的報案大廳裡,也是靜悄悄的。
在大家同情而又惋惜的目光注視下,曾經和歐陽景洪親如手足的緝毒組組長馬雲,毅然遞交了辭職報告,然後流著淚,頭也不回地離開了警局。
每個人的心情都很糟糕。
十三年過去了,案件依然沒有答案。死者歐陽青失蹤的眼球也再沒有被人找到過。
雖然在公開場合,沒有人再提起過這個案子,但是大家心裡其實都是明白的——「他」,一直都在,從來都未曾離開!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女法醫之死亡承諾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198 |
華文推理/犯罪小說 |
$ 198 |
推理/犯罪小說 |
$ 198 |
推理/驚悚小說 |
$ 220 |
中文書 |
$ 220 |
推理小說 |
$ 22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女法醫之死亡承諾
一個神祕的盒子,一對乾癟的眼球,一朵枯黃的雛菊,
看似毫不相關的三個物件,
竟讓一件十三年前的懸案,再次重新啟動調查。
法醫章桐收到一件神祕人寄來的包裹,
裡面裝有的三個物件,直指十三年前發生的一件至今未破的命案。
緊接著,陸續發現失去眼球的遺體,
時隔多年,是十三年前的兇手再次行兇?
抑或是有知情的「模仿犯」出現?
兇手殘忍地挖走眼球,究竟有何目的?
因十三年前命案而失去女兒的緝毒警探,
突然冒出貌似已過世的劉春曉檢察官的男子,
坐享名利的知名女雕塑家,
看似八竿子打不著的三個人,
竟然成了這個案件的最關鍵人物!
法醫章桐,面對一具具失去眼球的屍體,
面對毫無頭緒的重案組警員,
誓言要從死者身上尋出破案的曙光!
作者簡介:
戴西
原名李琪,女,作家協會會員,曾經從事法醫工作十餘年,碩士研究生畢業,喜歡看懸疑偵探小說。
章節試閱
窗外,清冷的月光依舊靜靜地灑落在緊閉著的窗戶上,房間裡有點兒冷。章桐伸手摸了摸床邊的暖氣片,果然,細細的指尖很快就傳來了熟悉的冰冷感覺。
暖氣停了。現在是凌晨一點半剛過,離天亮還要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需要去等待。
她費力地探身搆到了書桌上的幾張七寸相片,在徹骨寒意把自己完全吞併之前,重新又縮回到了被窩裡。
這是自己臨睡前還沒有來得及完成的工作。
相片中,是一朵已經乾枯的雛菊,土黃色乾癟的花瓣被草草地揉成了一團,壓得扁扁的,毫無生命氣息的枝幹,如同是用鐵絲在很短的時間內笨拙地彎曲製...
暖氣停了。現在是凌晨一點半剛過,離天亮還要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需要去等待。
她費力地探身搆到了書桌上的幾張七寸相片,在徹骨寒意把自己完全吞併之前,重新又縮回到了被窩裡。
這是自己臨睡前還沒有來得及完成的工作。
相片中,是一朵已經乾枯的雛菊,土黃色乾癟的花瓣被草草地揉成了一團,壓得扁扁的,毫無生命氣息的枝幹,如同是用鐵絲在很短的時間內笨拙地彎曲製...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戴西
- 出版社: 耕林 出版日期:2014-11-25 ISBN/ISSN:978986286549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開數:25K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推理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