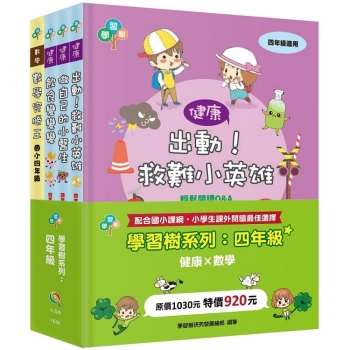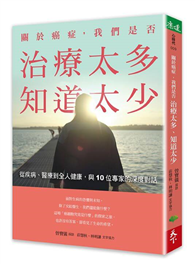我想告訴他,不管陰曹地府再淒冷,我都會在那裡等著他。
我想告訴他,若是有來生,就一起投胎,生生世世在一起。
但是,我卻什麼都說不出來。
眼前等待我的,是死亡……
死裡逃生,卻得知他背棄了她,
震驚心碎之餘,她努力查明事情真相,
竟發現,原來他這樣傷害她,是為了要保全她,
而曾經對她許下的諾言,他也一刻都沒有忘記過——
以身試毒,他拚盡全力一搏,只為讓她脫離險境;
三刀六洞,他在自己身上劃下駭人傷口,只為替她爭取名分;
獨排眾議,他願拋棄大好江山,來交換讓她留在他的身邊……
這一生,她多麼慶幸擁有了這樣一個他,
可是眼前危機重重,
讓她不得不違背他們的誓言,
為了守護他的一切,
她選擇離開他的身邊,
即使要出賣自己的靈魂,甚至是生命——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舞傾城4:分離之舞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舞傾城4:分離之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