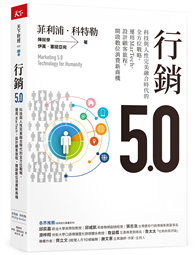大學女學生離奇中毒、古老宗廟的三具焦屍、古墓遺址兇案驚魂……
測謊神探&懸疑文大神寫手攜手,
案情一步步展開,人性的陰暗面一層層掀起,
同時掀起的,還有……兩人那說不出口的「奸情」!
測謊神探&懸疑文大神寫手攜手,
案情一步步展開,人性的陰暗面一層層掀起,
同時掀起的,還有……兩人那說不出口的「奸情」!
◎隨書附贈:人物書籤卡一組
她這是走了什麼倒楣運,
難得乖乖跑去圖書館閉關一天,
她的室友就這麼湊巧在這一天被毒害,
而她,因為「消失」了一整天,
就這麼被認定為「畏罪潛逃」,直接被當成了「第一嫌疑人」!?
雖然這些探員總會對罪犯說:你有權保持沉默!
她、才、不、幹!
身為懸疑文的超級大神寫手,
沒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走路,
她可是要積極為自己分析辯護才行!
偏偏那幾個探員,硬是認定她「動機充足」且「有機可乘」,
無論她怎麼說破嘴都沒用,
沒想到,一個一級帥哥探員一出現,不過兩三句分析,
竟然就讓她的嫌疑去了七八分?
嘖嘖,當個像他這樣的探員好像很有趣耶,
她是不是該好好考慮來巴著他不放呢?
人物介紹
岑戈
身分:一級探員
個性:沉穩,心思縝密
擅長:運用心理戰術、識破罪犯的心理活動
興趣:揪出趙蘇漾心裡的小九九
常用武器:一雙識破人心的眼
趙蘇漾
身分:見習探員
個性:直率,粗線條
擅長:發揮無限想像力,將案情「故事化」
興趣:當岑戈的小跟屁蟲去辦案
常用武器:一張口齒伶俐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