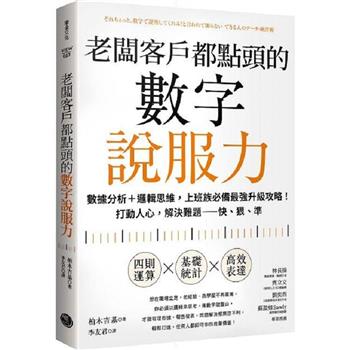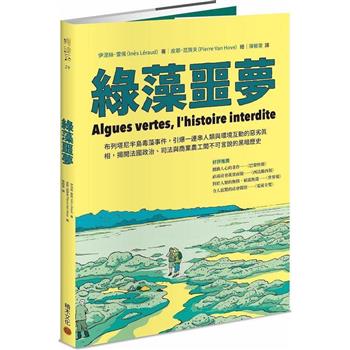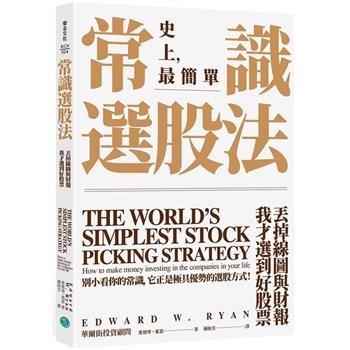回到房間,龔克洗了把臉,脫掉外套躺在床上,拿起身旁的卷宗。
案情最早要追溯到二十年前,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一場暴雨之後,兩個收車準備下班的公車司機在解手時,意外撿到了個帶封條的盒子。
自以為撿到寶貝的司機打開盒子,卻意外發現裡面裝著的是一男性生殖器,生殖器呈壽司狀被切成數段,他們隨後報警。
接到報警電話,警方立即出動。在接下來的近十五個小時內,臨水市陸續在多處地點發現了被切割下來的人體器官。其中包括一隻左耳、兩顆眼珠、十指,以及沿著腳踝骨剁下來的雙腳。
後來,法醫通過對這些殘骸的皮下組織、骨骼,以及可以提取出來的生物數據進行比對分析,最後確認它們是來自同一男性。根據傷情判斷,法醫得出該名男子應該已經遇害。
可離奇的是,無論警方再如何嚴密搜尋,被害者身體的其餘部分,卻一直沒有下落。
更讓人費解的是,市警局對本市失蹤人口,以及外來流動人員的排查中,也是少有斬獲,一個月過去了,前來認屍的人都逐一搖頭離去。
那些屍塊,就像隨著一陣大雨,一同憑空降臨在了臨水市,再難尋得來處。
警政單位把此案列為頭號重案,要求限期破案,臨水市警方為此成立了精英匯聚的「八二五」分屍案專案組,那段時間,全市所有警力,幾乎都投入到這起案件當中。
可無論他們是圍繞著各個拋屍現場擴大搜尋範圍,還是排除掉了無數嫌疑人,面對一起連被害人是誰都確認不了的案子,就算施公再世,也是束手無策。
隨著時間的逐漸推移,八二五專案組在無任何案情突破的情形下,無奈宣佈解散,同樣的無奈,恐怕也留在當年那群為八二五耗盡心血的專案組探員心裡,再也揮之不去。
二十年時光荏苒而過,當年的專案組探員多半已經退休或調職,八二五好像一個被遺忘在世界角落的小小塵埃一樣,鮮少被人提及。直到二○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一起近乎相同的案件再次在臨水市發生。
同樣是切口整齊地被割下的左耳一隻、兩顆眼珠、十指,沿著腳踝骨剁下來的雙腳,以及被切割成數段的男性生殖器,並在和上次相同的地點被陸續發現。
唯一的不同大概是,上次是只木盒子,這次真成了裝壽司的塑膠盒。但也和上次一樣,塑膠盒被拿紙條交叉封了,上面寫著兩個字——天譴。
「你是有多恨男人?」目光從卷宗上的字跡移開,龔克眼神迷離,像在對虛空中那個看不見的兇手說。
突然,耳邊傳來尖叫聲,聽聲音像是夏圖的,可卻是從隔壁二○五號房,葉南笙的房間裡傳出來的。
龔克立刻下床穿鞋,開門,兩步路就走到了葉南笙的房間。
房門被鎖扣夾住,並沒關緊。
龔克推開門,看到的是葉南笙手拿著菜刀和夏圖扭成一團……
「早說妳是在做現場模擬啊……」夏圖喘口粗氣坐在床沿上,她十指交叉,掌心對扣,一下下活動著手腕,「真沒看出來,那麼瘦,力氣倒不小!」
葉南笙同樣也氣喘吁吁的,她挨著牆角坐在地板上,臉色給了龔克和之前那晚一樣的慘白詭異感。她休息的時間比夏圖要久,半天過去才出聲說:「老穆說,人死前,按已知自己要死,和未知自己要死的兩種情況,心臟和神經系統會給肌肉兩種截然不同的反射結果,反應在屍體上也會有相應的區別,如果能找到其中的規律,對判定死者是意外死亡,還是被殺,甚至兇手是否是其熟人,都能提供出重要的參考依據……」
「這麼神?果真泰斗!」夏圖吹聲口哨,卻沒忘記教育葉南笙,「那妳也不該親身實驗吧,妳自己看不到,就妳剛剛那眼神,真像有第三個人舉刀在砍妳的手一樣。」
一想到像被什麼東西附身一樣的葉南笙,夏圖強忍住寒顫。
「刀呢?」葉南笙像沒聽到夏圖的話,自顧自地低頭找菜刀。她眼神迷離,不住地喃喃:「那是我和廚房借的,要還的。」
夏圖翻個白眼,考慮著一會兒去網路搜索下,看是不是所有泰斗的徒弟關注點都如此神奇。
她們似乎都沒注意到,房間裡還站著第三個人。
不過正如關楚評價的那樣,在某些時刻,龔克的存在感極低,他像個不屬於這人間的生物,只在某些時刻發出不能讓人忽視的光芒,而絕大多數時候,他就像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物,只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個,引不起別人注意。
好比現在。
如果他一直保持著沉默,真不知道夏圖她們要什麼時候才能注意到他的存在。
「玩刀很危險。」出來的急,龔克的襯衫領鬆著,袖口挽起一截至手肘,小臂是和手背一樣的蒼白顏色。剛剛的搶奪過程,讓他額頭掛了層薄汗,再配上右手握著的菜刀,這形象和他不苟言笑的臉形成了鮮明對比。
不知道是龔克這種殺雞的造型太過滑稽,還是他明顯不大擅長的教育式言論,總之,夏圖笑場了,連葉南笙的嘴角也彎彎的。
他是真不擅長同人打交道,尤其是女人,所以龔克直接轉身出門,「我去還刀。」
七點不到,陽光招待所的走廊裡一片寂靜,腳步過處,有年頭的木質地板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
廚房在一樓東側靠裡位置,龔克穿過明亮的大廳,進了走廊。
大廳裡,有幾個人坐在吧旁聊天,斷續有笑聲像是尾隨在他身後。
招待所是橫向設置結構,走廊很長,約十五米左右的樣子,龔克走了幾步路,頭頂突然嘶一聲,緊接著四周便陷入了漆黑。
隱約中,似乎能聽到櫃檯經理安撫客人的說話聲,和招呼檢查電路開關的聲音,可這種種聲音都掩蓋不了他身後的吱吱地板聲。
一隻手搭上了龔克的肩膀。
「你怎麼會知道我名字的?」
幽幽的,帶了點狀況外、無情緒的聲音響起,來人是葉南笙。
「跳樓很危險。」龔克想也沒想地回答。
然後在久久的沉默之後,帶著極度揣測的聲音再次響起。
「你住九○二?」
恭喜你答對了!龔克想起關楚總愛說的這句話,這讓他多少感到有些欣慰。即便再不在乎存在感的人,也是不願一直被當成空氣的。
他點了點頭,後來想起來她現在看不到,又「嗯」了一聲。
「九○二住的不是個老太太嗎?還是那帶著七歲小孩的一家三口?要不就是那個搞行為藝術的雜毛小子?」葉南笙扳著手指,細數她記憶中的那些鄰居。
但無論是誰,她都覺得不是龔克。
龔克不想告訴葉南笙,那些鄰居都是在一年前,甚至在更遙遠的過去,而且據說那些人的入住時間,基本上都在一個月之內。
「溺水危險。」想起剛剛在房間內的情景,出於安全考量,他出聲提醒。
第一次在案發現場見到葉南笙,龔克就把她同那個筆名為「南聲」的《真相》雜誌寫手畫上了等號,他看得出來,這個女人對法醫事業有著很大熱情,甚至狂熱。
「去年就試過了。」她的回答依舊簡約。
「捆綁勒死也危險。」
「上個月勒過了。」
你來我往,黑暗中,兩人從容對答。
「觸電不要試……」
「唔,這個真沒試過,回去可以提上日程……」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死者之證(1):女法醫的活體實驗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88 |
靈異/推理 |
$ 188 |
驚悚恐怖 |
$ 220 |
中文書 |
$ 220 |
驚悚/懸疑小說 |
$ 225 |
文學作品 |
$ 225 |
推理/驚悚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死者之證(1):女法醫的活體實驗
喜歡推理懸疑小說的讀者們:「很抱歉!珊姍來遲了!」
犯罪推理輕小說新秀
懸疑推薦驚豔指數★★★★★
每一個死者,都是至關重要的「破案證據」,
每一個案件,都有出人意料的「破案關鍵」。
搞怪女法醫V.S面癱男犯罪心理學家
驚人的死亡真相,想像不到的破案過程,
兩人衝撞出異想不到的「激情火花」!
「溺水危險。」他說。
「去年就試過了。」她答。
「捆綁勒死也危險。」他說。
「上個月勒過了。」她答。
「觸電不要試……」他說。
「唔,這個真沒試過,回去可以提上日程……」她答。
她,搞怪無比的女法醫,
非常具有「研究精神」──總拿自己當實驗品測試各種死法!
她對分析「死者」的各種狀態,有著異於常人的執著,
而以往對於法醫相關之外的事情,總是反應慢八百拍的她,
這次竟對一個「面癱男」產生了無與倫比的「興趣」!?
他,冷度破表的犯罪心理學家,
總是面無表情,卻也總是能一言道破驚人的事實!
他總能平靜分析各色人種,一語道出關鍵,
唯有「她」,一個擁有「無法預測」想法的女法醫,讓他「非常不冷靜」……
兩人攜手偵破各項驚悚案件的同時,
兩個別人眼中的「怪人」之間,
也有了令人驚悚的「發展」!?
TOP
章節試閱
回到房間,龔克洗了把臉,脫掉外套躺在床上,拿起身旁的卷宗。
案情最早要追溯到二十年前,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一場暴雨之後,兩個收車準備下班的公車司機在解手時,意外撿到了個帶封條的盒子。
自以為撿到寶貝的司機打開盒子,卻意外發現裡面裝著的是一男性生殖器,生殖器呈壽司狀被切成數段,他們隨後報警。
接到報警電話,警方立即出動。在接下來的近十五個小時內,臨水市陸續在多處地點發現了被切割下來的人體器官。其中包括一隻左耳、兩顆眼珠、十指,以及沿著腳踝骨剁下來的雙腳。
後來,法醫通過對這些殘骸的皮下組織、骨...
案情最早要追溯到二十年前,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一場暴雨之後,兩個收車準備下班的公車司機在解手時,意外撿到了個帶封條的盒子。
自以為撿到寶貝的司機打開盒子,卻意外發現裡面裝著的是一男性生殖器,生殖器呈壽司狀被切成數段,他們隨後報警。
接到報警電話,警方立即出動。在接下來的近十五個小時內,臨水市陸續在多處地點發現了被切割下來的人體器官。其中包括一隻左耳、兩顆眼珠、十指,以及沿著腳踝骨剁下來的雙腳。
後來,法醫通過對這些殘骸的皮下組織、骨...
»看全部
TOP
目錄
楔子 天譴
Chapter 01神探
chapter02九○二先生
chapter03超級神探
chapter04屍體復活
chapter05驚人真相
chapter06心底的傷
chapter07吸血鬼的詛咒
chapter08真人密室逃脫
chapter09葬禮上的新生
chapter10死局
番外 陸北航日記
Chapter 01神探
chapter02九○二先生
chapter03超級神探
chapter04屍體復活
chapter05驚人真相
chapter06心底的傷
chapter07吸血鬼的詛咒
chapter08真人密室逃脫
chapter09葬禮上的新生
chapter10死局
番外 陸北航日記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蕭珊
- 出版社: 耕林 出版日期:2017-09-15 ISBN/ISSN:978986286729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72頁 開數:25K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驚悚/懸疑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