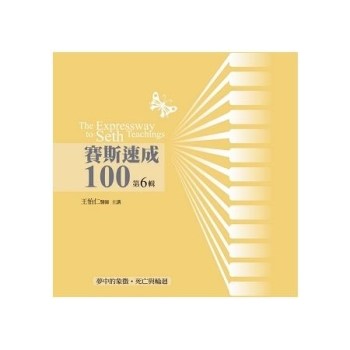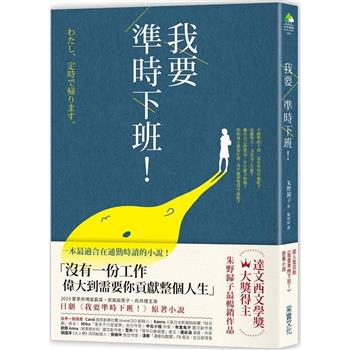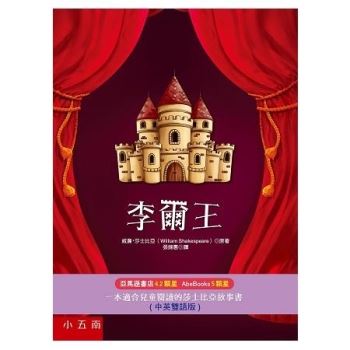什麼樣的工作能窺見他人的人生跑馬燈?
什麼樣的工作死亡是一種日常?
答案是──禮儀師
什麼樣的工作死亡是一種日常?
答案是──禮儀師
「木村老師給我的,不僅僅是入殮的技術,更多的是那告別的精神跟態度。其實面對死亡、面對生活,我們有很多種方式。透過自己的工作日常,付諸更多的努力,無非就是想一起把生命鏡頭下的遺憾縮小。」──台灣和光里創辦人‧唯一日本認證送行者 許伊妃 溫暖推薦
「這是一份了解往生者『度過什麼樣的人生』的工作」
「也是一份協助在世者『如何活下去』的工作」
嬰兒猝死、高中生車禍、同事的逝世……
禮儀師目睹了許多人生的最後告別,聽聞過許多往生者的「人生歷練」。
他們所見證的,絕不單單只是人「如何死去」這件事。
日本最溫暖的禮儀師木村光希
向你/妳娓娓道來「送行者」不為人知的一面……
✑由同學入殮的男高中生
「接下來我將進行入殮儀式,替壯太換穿壽衣,可以請你們協助我,在這最後一刻,為壯太出一分力嗎?」大概是沒料到我的提議,每個人露出驚訝的表情,
卻依舊堅定地回答我:「當然……當然!我願意!」
✑最後的寶寶更衣
媽媽輕撫著凛凛的身體,開始喃喃道歉。眼淚撲簌簌地流下,口中一遍又一遍地重述「對不起」。原因不明的嬰兒猝死症,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嬰兒身上,並非任何一人的過錯,這位母親是否終有一天也能由衷說出感謝呢?
✑昨天才通過電話的工作夥伴……
「最後可以請你幫他換上這套衣服嗎?」攤開一看,內裡繡著中本的名字,
像是主人驕傲地宣示他的所有權。「為什麼……為什麼我得幫這個人入殮……」
我心中充滿無處宣洩的悲痛。
▍本書簡介 ▍
木村光希自大學時代起,即跟在從事入殮工作的父親(為電影《送行者》的技術指導)身邊學習,迄今已為數千位亡者送行。看過享盡天年的喜壽,也看過突如其來的死亡。
書中以他在工作上接觸過的個案為例,談看盡各種死亡的送行者,對生命、死亡、人生的想法,以及禮儀師存在的意義。
本書中要探討的,並不是人的「死亡方式」,而是「生存之道」。
▍本書特色 ▍
☺日本知名禮儀師木村光希的十年送行體悟
☺透過死亡來談論該如何好好生活
☺透過執業以來所遇到的種種事件,分享送行者對生命、死亡、人生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