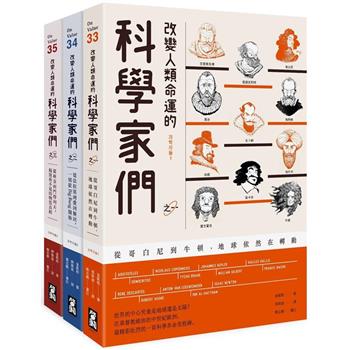一/幫個忙而已
本事件從台北市廈門街某條巷子某棟公寓一樓說起,再平凡不過的星期三正午十二點,塑料遮雨棚被白金日光擊得靈魂出竅,深淺不一的光暈趴達趴達黏在書桌上,趙芳慧闔起影印筆記,捉住手機往柔軟的床倒去,當她用大拇指飛快按下愛的簡訊的時候,鐵鎖彈簧被旋開的聲線竄起,從客廳一路劈開空氣直達人在臥房的趙芳慧的耳中。
「爸,有我的信嗎?」她扭頭往門外問。
「嘸啦,都是帳單。」趙佑土在藤椅上坐下,手指忽然不自覺鬆開,花花綠綠的信件如魚兒般游到茶几上。正如他所言,全是帳單,水費、電費、電話費、瓦斯費,林林總總有完沒完。每封信都擺扭著身子彈跳,呼喚著先來宰它,趙佑土只能嘆口氣,眉宇皺紋先宰了一隻蚊子。
這時趙芳慧從房間走出來,還沒把手上的杯子斟滿水,就先噴口水數落著趙佑土:「不是早跟你說,這些帳單可以用自動扣款的嗎?」
趙佑土憨厚笑笑:「我想說自己繳比較踏實。」
「踏什麼實,你就是這樣不懂得變通,媽才會跟人跑掉。」
「阿慧,那件事就別提——」
趙佑土還沒說完,趙芳慧已經站在茶几旁,撈起了三、四封信:「這個、這個、還有這個,我來繳。」
「妳哪有錢?」趙佑土急忙站起身要攔,但女兒動作更快,收齊在掌心便調頭走開:「我有打工薪資啦,搞不好賺的比你搬磚頭還多勒。」
忽然趙芳慧的手機短促一響,她喜上眉梢,拿起來一看,果然是親愛的回傳的簡訊——我也想妳噢!再加上一顆紅冬冬閃爍的愛心,趙芳慧滿臉都是笑意了。
「怎麼妳的電話一直響,是誰啊?」趙佑土好奇地問。
「還有誰?」趙芳慧闔上手機:「就是那個阿盛啊。」
***
阿盛跟趙氏父女的相遇是在四個月前的一場大雨中,天雷打得猛,饒是頭好壯壯的高樓大廈也得低頭,膽子小的小客車早嚇得哇哇哭了。當時趙氏父女擠著一把傘過馬路,兩聲轟雷忽然近得像在對面巷內,直到一名年輕小夥子把一襲黑衣的壯漢拖到街上後,他們才跟周圍的路人一起意會過來,原來那兩聲不是落雷,而是兩記把壯漢肚皮挖出血洞的槍響。
「這個人剛剛被槍擊了,快叫救護車!」年輕人朝圍觀的人大喊,卻沒人敢動,這時黑衣壯漢突然拉住年輕人的衣襟,狼狽摔倒在地,「小子,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來我是黑道,就你敢救我,我記住……」黑衣壯漢沒有太多力氣說更多話,昏了過去,倒是周遭原本沉默的人牆,議論紛紛了起來。
「果然是黑道!」
「好恐怖,死掉了嗎?」
「怎麼會在這裡發生槍擊案,我就住這裡耶。」
年輕人使勁搖著黑衣壯漢的肩膀,但他卻像斷線傀儡般動也不動,「喂!醒醒,你們快點叫救護車啊,他中了兩槍欸!」
大雨滂沱落下,彷彿打算淹沒那被人群圍起來的孤島,當趙佑土回過神、趕緊要拿出手機撥打119之際──趙芳慧竟從他手中搶過傘,衝入了孤獨無援的圓。
「拿好傘遮雨,再淋下去他會先失溫!」趙芳慧掏出手帕,按住黑衣壯漢汩汩流血的創口:「你也一起壓住,別讓血流出來!」
年輕人愣了一下,連忙伸手動作。期間他們除了止血外,也不停拍打黑衣壯漢的臉龐,試圖喚醒他的意識,但直到抵達醫院,他都沒有反應。
醫院的冷氣很冷,渾身濕透的趙氏父女跟年輕人更是冷斃了,簡直要把身上的雞皮疙瘩都抖下來。
「他會有救嗎?」趙芳慧問。
「不知道……」年輕人望著急診室的紅燈。
趙佑土拍拍他的肩膀:「少年仔,你很勇敢耶。」
「應該的。謝謝你們願意幫忙打電話。」
這時好幾名黑衣人從外邊魚貫而入,臉上橫肉像是絞到極限的筋。
「X的,竟然敢暗算我們頭子。」「現在情況如何?」「快去查出來是誰幹的!」
他們邊走邊低聲咒罵,瘸腿病人都嚇得往旁邊跳開。平凡如趙氏父女跟年輕人,自然直接被這群黑衣人忽略,完全不曉得把黑衣老大送來醫院的就是他們。
「這樣也好,我們也沒必要再涉入了。」年輕人說道。
「嗯,阿慧,我們走吧。」趙佑土拿起濕淋淋的雨傘。
「等一下!那個,這個,啊對了,這條手帕。」年輕人喚住趙芳慧,忽然臉紅了起來:「我洗乾淨以後再還給妳好嗎?」
臉紅像是會傳染似的,本來還冷得直發抖的趙芳慧,突然意會過來現在是什麼情況,耳根子燒得燙吱吱。
***
「喔,那個阿盛,不錯不錯。」趙佑土點點頭。
趙芳慧眉毛一挑,連應都不應,彷彿理所當然,其實她又驕傲又樂,「我要回房間了。」還沒走到門口,她的大拇指就在手機鍵盤上蜻蜓點水。
望著女兒雀躍的背影,趙佑土停頓半刻,望向牆上掛的一張父女合影,照片裡的他還沒有大肚腩,小芳慧的個頭只有丁點高,坐在他肩頭上開心比YA。背景是阿里山的日出,雲霧嬝娜,彷彿時光在那一瞬間停格。忽然,他想起按下快門的那個人,下意識地摸摸左手無名指上的金戒,都多少年了噢,或許再過不久,阿慧也要離開他的身邊了。
趙佑土重新坐回藤椅上,從茶几的小抽屜裡拿出一本小簿子,甫一翻閱,皺得像秋天枯葉的紙張伸展開來,紋路全是密密麻麻的數字,每一個減號都畫得極其不捨。趙佑土挑塊空白,斟酌片刻後寫下「阿慧的結婚基金」,然後把「存款」那一串號碼改寫到這個新增的欄位下,這才滿意地點點頭,再往前翻幾頁,他準備從雜項中擠出阿拉伯數字來餵那些帳單,目光卻忽然落在「茂德」二字上頭,思緒跟著飄遠——
日正當中,工地揚滿塵土,他們像螞蟻一樣在巨大鋼筋中穿走,直到工頭喊吃飯了,大家才停下手邊工作,領餐盒到陰影下大快朵頤。但趙佑土啃雞腿啃到一半,發現茂德窩在不遠處的牆角打盹,於是他朝他喊:「茂德,你怎麼沒吃飯?」
茂德微微睜開眼,靦腆笑了笑,又繼續睡覺。
「他要留起來啦。」另一名工人低聲對趙佑土說道:「你不知道?他老婆吃不了苦跟人跑了,把五歲的小女兒丟給他一個人養,現在他都把便當留到晚上才吃,這樣才省飯錢。」
「有這款代誌?」
那名工人嘆口氣:「大家都很想幫他,但是我們這種搬鐵條的臨時工,實在是湊不出幾個錢。」
趙佑土愣得停下筷子,十五年前的畫面如蜂般螫來,他彷彿在茂德身上看見彼時的自己,那個女人轉身走,房間裡的小芳慧倔強地不哭,小手緊緊牽住他的厚掌。
「他會很艱苦。」趙佑土有點感傷。
「誰不艱苦。」工人繼續低頭扒著自己的飯。
拉回思緒,小簿子上「茂德」兩字底下寫著三萬元,那是趙佑土預計借給他救急的錢,他本來打算明天上工時偷塞給他,可是現在他卻猶豫了。
趙佑土悄悄回頭望向女兒的房間,確定她不會突然走出來,這才躡手躡腳地從口袋裡拿出一份手術同意書,那是今天上午去醫院檢查完後,醫生交給他的。
「趙先生,請看,這是你腦部的X光。」醫生將底片吸到透光的燈箱上,趙佑土覺得這顆看了五十餘年的頭顱好陌生。接著醫生指向一團白白中的一團黑黑,對他說道:「很明顯地,當你從鷹架上摔下來的時候,因撞擊頭部而形成這塊瘀血。一般來說,瘀血會自行吸收,但兩個禮拜過去了,這塊瘀血卻越來越大,現在已經即將壓迫到腁胝體了,坦白說這是極為罕見的狀況。如果不開刀取出的話,甚至會影響你的日常生活。」
「影響日常生活?」
「是的,腁胝體是左腦與右腦的連結,如果受損或異常,可能會發生你想舉左手卻舉右手、往前走卻後退的情況。」
「那我上工不就很危險!」趙佑土擔憂地說:「可是一定要開刀嗎?不能吃藥?」
「抱歉,只能動手術了,而且越快越好。」
「那這樣要多少錢?」
「一般來說,前後大概要八萬多塊吧。」
八萬元,對普遍家庭來說還不算多大的負擔,但在趙家,可以繳趙芳慧三個學期的學費,或者省吃儉用,維持七、八個月的雜項開銷。趙佑土對醫生說要考慮一下,把手術同意書暫時帶回來。在「茂德」旁,他寫下「手術」兩字,然後筆尖不停在半空盤旋,再也無法降落,他掙扎得皺紋都要打結了。
「啊!」
忽然,趙芳慧尖叫一聲,從房間裡衝出來,趙佑土連忙把手術同意書塞回口袋:「阿慧,安怎啊?」
趙芳慧沒有回他,一邊抹著脖子好像沾了什麼髒東西,衝進浴室後拿著塑膠盆出來,趙佑土立刻懂了:「天花板又滲水了?」
他跟著女兒的憤怒腳步走進房間,趙芳慧把椅子拉開、盆子一放,豆大的水珠滴滴答答落下。
「爸!一定又是樓上澆盆栽澆太多水啦。」
「傷腦筋,我去拿抹布。」
想不到趙芳慧更火了:「抹布我拿就好,你去跟樓上那個死研究生講啦,每次我去講他都沒聽進去,而且還色瞇瞇地看我。」
「阿慧,妳怎麼可以這樣說人家,他只是眼睛比較小——」
「爸!」
「好好好,我去講。」
趙佑土摸摸鼻子,他可不敢跟被惹了潔癖的趙芳慧多講幾句,回身走出房間,打開客廳大門便拾階而上,這樓梯間窄到不行,兩邊牆壁彷彿要把人給合掌壓扁。走到一樓與二樓的夾層轉彎處時,趙佑土喘了口氣,感覺自己真的有些上了年紀。再往上爬,他來到二樓家門前,按下電鈴。
片刻,內層大門被打開,一臉不悅的陳彥昭皺起眉頭:「幹嘛?」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攪禍的圖書 |
 |
攪禍 作者:白色七號 出版社: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2-2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3 |
驚悚/懸疑小說 |
$ 43 |
驚悚/懸疑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攪禍
繼《追神傳》、《路吞之屋》和《神鬼二分之一》後,睽違新作
白色七號◎著/ Cash◎封面繪圖
誰也沒想到只是一個漏水,
竟把我們的命運都攪在一起了……
「你在說什麼?」張義果才詢問完,馬上感覺到冰箱將手壓得更緊,另一端的陳彥昭也吃痛低嗚,原來是黃德能使勁想把手抽出來,才會反向迫壓到他們。「我得回去!我知道藥在哪裡!」黃德能發了狂似的按住冰箱,玻璃裂痕如蜘蛛絲般擴張,從黃德能的手臂裡吸了血,隨著紋路暈染開來,「你瘋了嗎?快住手!」
「好痛啊!我的手!我的手!」張義果與陳彥昭痛得大叫,許向國也驚訝地放開了手,空氣被三人的吼叫沸騰起來,宛如一頭即將突破網子的惡獸。但黃德能根本不介意自己的手傷,更何況是陳張二人的喝阻,他疼得眼角飆出眼淚,牙關卻咬得比鱷魚還猛,最後爆吼一聲,一拳砸向玻璃,玻璃爆裂,血珠噴紅了電冰箱一隅,窗戶開出一口崎嶇的牙齒,齒尖還咬著幾塊皮屑……
心跳加快 指數 ★★★★☆
後遺症 指數 ★★★★☆
催淚 指數 ★★★☆☆
閒嗑牙 指數 ★★★★★
作者簡介:
白色七號
在漫畫堆裡長大,廣告設計系出身,還意外當了一天的街頭插畫家。上了大學後一頭栽入寫作的世界,目前就讀台灣藝術大學戲劇系,創意是作品的王牌,創作是一生的實踐,創傷要記得擦藥。
個人Blog:http://www.wretch.cc/blog/white07
◆在明日已出版作品
《追神傳》2008.8
《路吞之屋》2009.4
《神鬼二分之一》2010.8
《攪禍》2012.2
章節試閱
一/幫個忙而已
本事件從台北市廈門街某條巷子某棟公寓一樓說起,再平凡不過的星期三正午十二點,塑料遮雨棚被白金日光擊得靈魂出竅,深淺不一的光暈趴達趴達黏在書桌上,趙芳慧闔起影印筆記,捉住手機往柔軟的床倒去,當她用大拇指飛快按下愛的簡訊的時候,鐵鎖彈簧被旋開的聲線竄起,從客廳一路劈開空氣直達人在臥房的趙芳慧的耳中。
「爸,有我的信嗎?」她扭頭往門外問。
「嘸啦,都是帳單。」趙佑土在藤椅上坐下,手指忽然不自覺鬆開,花花綠綠的信件如魚兒般游到茶几上。正如他所言,全是帳單,水費、電費、電話費、瓦斯費,林林...
本事件從台北市廈門街某條巷子某棟公寓一樓說起,再平凡不過的星期三正午十二點,塑料遮雨棚被白金日光擊得靈魂出竅,深淺不一的光暈趴達趴達黏在書桌上,趙芳慧闔起影印筆記,捉住手機往柔軟的床倒去,當她用大拇指飛快按下愛的簡訊的時候,鐵鎖彈簧被旋開的聲線竄起,從客廳一路劈開空氣直達人在臥房的趙芳慧的耳中。
「爸,有我的信嗎?」她扭頭往門外問。
「嘸啦,都是帳單。」趙佑土在藤椅上坐下,手指忽然不自覺鬆開,花花綠綠的信件如魚兒般游到茶几上。正如他所言,全是帳單,水費、電費、電話費、瓦斯費,林林...
»看全部
作者序
老式公寓的樓梯間是一個十分特別的場域,與鄰居不期而遇,不外乎就是幾個狀況:彼此點頭,親切一點還會微笑;說聲你好,禮貌一點會問你要去哪;聊聊天氣,熱心一點會提醒帶傘;發個牢騷,八卦一點會直說哪樓又招惹哪樓。
這裡不是正式的社交場所,卻無法避免與人親密近身;你很難無視迎面或尾隨你的鄰居,偏偏又不適合停下來與他好好聊一陣。通常不是你趕著回家,就是對方急著出門,不是你高高在上,就是對方抬頭抬得脖子痠,這個上上下下的空間,常搞得人不上不下。
造成種種尷尬的原因,我認為就是來自距離。都市公寓的居住型態,強制...
這裡不是正式的社交場所,卻無法避免與人親密近身;你很難無視迎面或尾隨你的鄰居,偏偏又不適合停下來與他好好聊一陣。通常不是你趕著回家,就是對方急著出門,不是你高高在上,就是對方抬頭抬得脖子痠,這個上上下下的空間,常搞得人不上不下。
造成種種尷尬的原因,我認為就是來自距離。都市公寓的居住型態,強制...
»看全部
目錄
一/幫個忙而已
二/兩個補償我的我
三/那個我深愛的臭婊子
四/正是重要的時刻
五/死鬼,叫你接電話就快接
六/數三就直接來
七/行與不行
八/你是誰?
九/都是冰箱害的
十/你知道那些事嗎?
十一/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了
十二/對了,其實……
十三/小心
十四/好像那是別人的事
十五/可是那又怎麼樣呢?
二/兩個補償我的我
三/那個我深愛的臭婊子
四/正是重要的時刻
五/死鬼,叫你接電話就快接
六/數三就直接來
七/行與不行
八/你是誰?
九/都是冰箱害的
十/你知道那些事嗎?
十一/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了
十二/對了,其實……
十三/小心
十四/好像那是別人的事
十五/可是那又怎麼樣呢?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白色七號
- 出版社: 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2-23 ISBN/ISSN:978986290507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8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驚悚/懸疑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