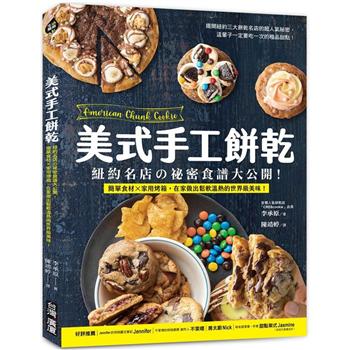一、 巨獸
西元一六五二年,歲次壬辰,正好距今三百六十年,合六甲子。
龍年開春,拖著火紅赤尾的彗星出現在極南面的海平面上,漢人稱之為「赤龍之尾」,荷蘭南非總督贊.范里貝克為其命名為「C/1652 Y1」。
巨獸般的熱蘭遮城蹲伏在沙丘上,睥睨台灣海峽。
彷彿地獄底層的惡龍,有著三層式疊合而上的厚實堡體;紅磚塗上灰泥的外牆,有如經火焰燒灼的龍鱗,紅黑斑駁;上面還有一層如發霉般薄薄的細粉,醜惡不堪。
牠粗壯的四肢是由四角稜堡所構成,指爪是黝黑的銅製火炮,伸向八方。巨獸牢牢掌握著福爾摩沙(Formosa),也恫嚇著黑水溝上來往的商船。渡海而來的漢人舟上遠望,恰如惡龍口中吐出火紅彗星,燃燒著台江內海。
台江內海古稱「大員灣」,是「台灣」一名的由來。靠外海處有七塊沙丘圍繞,狀似巨鯨浮海,由南向北,分別稱為「一鯤鯓」、「二鯤鯓」……以至於「七鯤鯓」。莊子《逍遙遊》曰:「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荷語意為「海中之地」的熱蘭遮(Zeelandia)即建築於一鯤鯓上,四面環海,易守難攻。自首任福爾摩沙長官建城以來近三十年,一向是殖民地具體運作的樞紐和權力壓迫的象徵。荷蘭王威所及最遠的一塊領土,在望樓上灼灼的目光監視下,任何風吹草動都無所遁形。面向市街的巨口,貪婪地吞噬著源源不絕的財富,以及台灣人的夢想與希望。
古老的傳說中,只要赤龍現於南海,必起兵災——
一位胖壯中年漢子貌似發呆,躲在熱蘭遮的巨大陰影下歇涼,瞇眼仰望城牆上執火鎗巡邏的荷蘭士兵。
「呿……鄉下人。」由於背光陰影的緣故,荷蘭士兵看不清他的樣貌,竟辨不出大名鼎鼎的五官懷一(Gouqua Faet)——漢人墾戶的大結首、殖民地的甲斐丹(China captain)。荷兵看他未帶武器,料無威脅,隨即向城下啐了一口,面無表情地走開。
這一年五官懷一正沖太歲,台灣人算四十九歲。他全名「郭懷一」,依閩南例小名「五官」,在荷蘭文獻上多以「Faet」記載;早年隨海賊首領鄭芝龍(一官)自日本平戶來台拓墾,於金門料羅灣大敗荷軍,成為漢人農民的首領。
五官身高七尺二,背厚膀寬;圓凸凸肥壯的鮪魚肚幾乎要繃破略嫌短窄的青布衫。他腿短臀肥,黑布褲腳打了綁腿,下盤沉穩,似是練家子;但穿著草鞋的腳底,滿是泥土和龜裂的厚皮,十足說明了是個務農的莊稼人;更妙的是,居然在腰帶上纏了破書、葫蘆、算盤等亂七八糟的應用雜物。
「呵呵,這隻膨肚短命的吃錢官!」五官輕輕撫摸這糯米、黑糖、蚵灰所加固的城牆,似要安撫這頭沉默的巨獸。再用力一拍,砰的悶響。他低頭一看,手掌泛紅,熱蘭遮城未曾動搖半分。灰泥撲簌簌剝落,露出內層暗紅色的磚塊。無可奈何,伸手捻了捻粗濃的鼻毛,呆望著天上疏雲幾絲。
此時,遠處傳來男聲呼喊——
「五官甲螺!街上出事情囉——」
猿臂蜂腰、身形剽悍的年輕人快步跑近,瞬間就到眼前。
「呵呵,免緊張、免緊張!龍官,急事緩辦。」
五官解下腰間的葫蘆,遞給年輕人。「來,龍官,稍歇喘,慢慢講……恁爸不是跟你說過,練內功最忌心急,才不到幾步路,你就跑得臉紅氣喘,沒路用咧你。」
龍官接過葫蘆,望著五官笑咪咪的雙眼和肥厚的雙下巴。心想大概是跌倒撞到了頭,才會讓這原本連狠霸霸的紅毛人聽見就要發抖的五官懷一,變成今日這一副傻乎乎的模樣。他啜了口水,說道:「黑頭仔,赤崁頭人蔡益可在街上與紅毛兵衝突,恐怕會相打,你敢要去喬一下?」(台語中「喬」意為「調整、協調」。)
「嘿,熱蘭遮城下是紅毛人的地頭。可仔敢在這和紅毛兵衝突,算他有角色,讓他衝!」
「可是,紅毛兵帶刀帶槍,我怕對蔡益可不利——」
「免驚,咱漢人移墾日多,紅毛人評議會為避免激起民變,要求軍隊不得擅自動槍殘殺漢人。只要不動槍,可仔應該猶能應付……他手腳還不錯。」烈日炎炎,五官肥大的身軀猛冒著汗,實在不想離開陰涼的城下,只好猛搧涼。
「甲螺,走啦!既然來到熱蘭遮了,走幾步路去看看蔡益可的生意如何也不錯啦,大家都兄弟,相挺一下不過分啦!」龍官看著五官冒出鼻孔外的濃密黑毛,懷疑他年輕時幹海賊、縱橫台海的霸氣哪去了?「荷蘭人還帶了一個矮矮的黑人,腰配一支鳥首金刀,眼神真狠毒。蔡益可不知能否對付?聽說過年前巴達維亞送來了一批爪哇奴兵,身手神祕,深淺不知。」
五官捻捻鼻毛,猛地拔下兩根來,隨手一彈。「日頭赤炎炎……好啦好啦,去看看。」
走出城牆陰影時,金黃的陽光灑在兩人身上,卻在他們身前拉出了長長的陰影,指向熱蘭遮城下的大員街道。
龍官心中騷動不安,感到背後巨大的壓力。他不自禁回頭一看——
巨獸熱蘭遮昂首矗立在湛藍的天色中。
赤龍之尾若隱若現,五官的心思飄往十餘年前那一夜,自漚汪大河到山寨邊的狹長平野上,篝火有若繁星。夜空染成猩紅的豬肝色,月暈朦朧,烏雲漸合。雜木林間,暗黑人影祟動,隱約傳來激昂的戰歌。
聽著平埔族勇士出獵前的戰歌,五官覺得毛骨悚然。他抱著赤裸的雙臂,撫了雞皮疙瘩。
明明是盛夏六月的悶熱夜晚,腳底板卻升起一陣涼意。木寨倚坡而建,五官可將周遭的拓墾地盡收眼下。他心想,大河邊炙焰的篝火旁,大概就圍繞著紅毛人的火鎗隊吧?
荷蘭人這番有備而來,勢在必得。
篝火旁的帆布帳棚中,尼德蘭聯邦東印度公司所指派的福爾摩沙長官特勞牛斯,正坐在行軍椅上搧涼,對著首席牧師兼智囊說道:「尤努斯,我知道你籌劃已久,加強了對新港社的思想控制,才終於把溪南最強大的平埔族原住民勢力納入掌握,這是大功一件啊!」
尤努斯手握十字架,看著帳外荷軍的篝火。「長官,上回在金門被一官黨殺得丟盔棄甲,艦隊司令普特斯曼還因而去職;許多荷蘭軍士的親友都在大海戰中傷亡,這次一定要向漢人報這一箭之仇——」
「嗯,這一來,等於斬斷了漢寨的左手。普特斯曼司令是我的老長官,我不會讓他失望。」
「長官您努力修復與海賊王鄭一官的關係——送錢貿易、援助醫藥、提供軍火——使他更能專注與韃靼人的對抗,捨棄笨港。這一來,相當於斬斷了漢寨的右手。」
「漢寨左右手皆斷,孤立無援,的確是將台灣全島納入轄下的好時機。這次帶了熱蘭遮城四百名火鎗隊出征,分乘三百艘舢舨偷渡越過漚汪,在此建立了陣地。陣中全員均配備歐洲最新穎的毛瑟槍,並從戰船上卸裝二十門大小火炮隨隊……」特勞牛斯屈指點算了一下兵力,問道:「你那邊帶來多少番人?」
「一千四百頭噬血的台灣黑熊。」建起了這支黑暗大軍,尤努斯頗為自豪。
「太好了!我們兩股勢力像巨螯一般鉗住了笨港十寨,不知道他們那邊實力如何?」
「浪花軍的主力將士,都在三年前料羅灣大海戰中消耗殆盡;笨港的漢人武士大約只剩下一百五十名左右;而混居的平埔族人雖有近三千之數,卻多為無法上陣的老弱婦孺。此刻大概雞犬不寧,嚇得睡不著吧?他們的『甲螺』五官懷一,縱是有天大本領,也無計可施。」甲螺是日語中「首領」的意思,尤努斯少年時與海賊黨多次交手落敗,籌劃復仇已久。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血花熱蘭遮:愛と勇氣(3)的圖書 |
 |
血花熱蘭遮:愛と勇氣(3) 作者:施百俊 出版社: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6-14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44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武俠/歷史小說 |
$ 246 |
武俠小說 |
$ 246 |
武俠小說 |
電子書 |
$ 280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血花熱蘭遮:愛と勇氣(3)
特色
施百俊◎著
愛と勇氣3
二○一二文化部電視劇本創作獎得主 原著小說
比《賽德克巴萊》還早三百年的熱血革命!
自由至上,寧死不讓!
宇文正、甘耀明、喬靖夫、譚劍、陳夏民 仗義推薦!
內容簡介
比《賽德克巴萊》還早三百年的熱血革命!
自由至上,寧死不讓!
福爾摩沙版《七武士》,台灣最大農民起義!
古老的傳說中,赤龍現於南海,必起兵災:
赤色的巨獸熱蘭遮城蹲伏在沙丘上,彷彿地獄底層的惡龍:紅磚塗上灰泥的外牆,如經火焰燒灼的龍鱗,紅黑斑駁。牠粗壯的四肢由四角稜堡所構成,指爪是伸向八方的黝黑火炮:牢牢掌握著福爾摩沙,也恫嚇著黑水溝上來往的商船。
夜空自這日染上血色,浪花、五官懷一、柳生十兵衛、龍官……眾人再度集結,血戰已無法停止——
大海嘯來臨時,你能用雙手擋住它嗎?百姓的怒吼,已經停不了了……
作者簡介:
施百俊 BJ http://www.bjshih.idv.tw
台客武俠創始人,期望以傳奇的形式將台灣歷史上的英雄人物全都寫出來。
重要獲獎紀錄:
二○一二《浪花》、《血花熱蘭遮》獲文化部電視劇本創作獎、《小貓:林少貓傳奇》繪本獲選國家出版獎。
二○一一《小貓》獲選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台灣館優良出版品。
二○一○《浪花群英傳》獲温世仁武俠小說百萬大賞首獎、《流民本色》獲行政院新聞局第一屆優秀電視劇本獎、《小貓》入圍台北國際書展「年度之書」大獎。
明日工作室出版:《祕劍》、《浪花》、《本色》、《小貓》、《小貓:林少貓傳奇》、《走出二二八:以愛相會》
章節試閱
一、 巨獸
西元一六五二年,歲次壬辰,正好距今三百六十年,合六甲子。
龍年開春,拖著火紅赤尾的彗星出現在極南面的海平面上,漢人稱之為「赤龍之尾」,荷蘭南非總督贊.范里貝克為其命名為「C/1652 Y1」。
巨獸般的熱蘭遮城蹲伏在沙丘上,睥睨台灣海峽。
彷彿地獄底層的惡龍,有著三層式疊合而上的厚實堡體;紅磚塗上灰泥的外牆,有如經火焰燒灼的龍鱗,紅黑斑駁;上面還有一層如發霉般薄薄的細粉,醜惡不堪。
牠粗壯的四肢是由四角稜堡所構成,指爪是黝黑的銅製火炮,伸向八方。巨獸牢牢掌握著福爾摩沙(Formosa),也恫嚇著黑水溝上來...
西元一六五二年,歲次壬辰,正好距今三百六十年,合六甲子。
龍年開春,拖著火紅赤尾的彗星出現在極南面的海平面上,漢人稱之為「赤龍之尾」,荷蘭南非總督贊.范里貝克為其命名為「C/1652 Y1」。
巨獸般的熱蘭遮城蹲伏在沙丘上,睥睨台灣海峽。
彷彿地獄底層的惡龍,有著三層式疊合而上的厚實堡體;紅磚塗上灰泥的外牆,有如經火焰燒灼的龍鱗,紅黑斑駁;上面還有一層如發霉般薄薄的細粉,醜惡不堪。
牠粗壯的四肢是由四角稜堡所構成,指爪是黝黑的銅製火炮,伸向八方。巨獸牢牢掌握著福爾摩沙(Formosa),也恫嚇著黑水溝上來...
»看全部
作者序
作者自序
《血花熱蘭遮》是台客武俠系列第一部先有劇本後成小說的作品。寫作當下,正巧是全球歷經金融風暴,熱血之士舉起「正義」的大旗,呼喊著「公平」的口號,而將社會推向左傾的2012年——我們訴求政府干預市場,因為它「太自由」引發商人的貪婪;我們訴求政府加「富人稅」,彌平貧富差距……
我想到正好六甲子之前,台灣爆發了史上最大一場農民革命,郭懷一領導手執竹槍、鋤頭的上萬漢人農民,對抗擁有全球最強武力的荷蘭殖民政府。起義的原因就是荷蘭人加徵各種稅收:從田賦田租、人頭稅血稅無所不收,繳不起就殺人。另一方面,漢人貪婪...
《血花熱蘭遮》是台客武俠系列第一部先有劇本後成小說的作品。寫作當下,正巧是全球歷經金融風暴,熱血之士舉起「正義」的大旗,呼喊著「公平」的口號,而將社會推向左傾的2012年——我們訴求政府干預市場,因為它「太自由」引發商人的貪婪;我們訴求政府加「富人稅」,彌平貧富差距……
我想到正好六甲子之前,台灣爆發了史上最大一場農民革命,郭懷一領導手執竹槍、鋤頭的上萬漢人農民,對抗擁有全球最強武力的荷蘭殖民政府。起義的原因就是荷蘭人加徵各種稅收:從田賦田租、人頭稅血稅無所不收,繳不起就殺人。另一方面,漢人貪婪...
»看全部
目錄
作者簡介
自序
一、巨獸
二、獵人與農夫
三、浪花再現
四、聚義
五、秋月
六、錯著
七、背叛
八、失空斬
九、聖王殯天
後記
附錄:《血花熱蘭遮》劇本大綱
自序
一、巨獸
二、獵人與農夫
三、浪花再現
四、聚義
五、秋月
六、錯著
七、背叛
八、失空斬
九、聖王殯天
後記
附錄:《血花熱蘭遮》劇本大綱
商品資料
- 作者: 施百俊
- 出版社: 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6-14 ISBN/ISSN:978986290554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64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武俠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