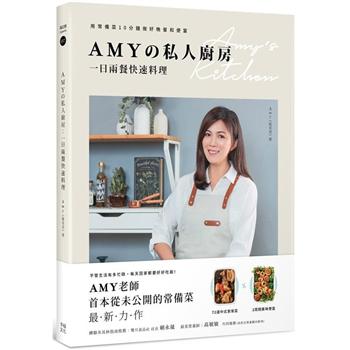# 1《按摩師》
桃園,被遺落在城市外的小巷子,小巷子裡的老舊按摩店,門口懸掛的招牌,有氣無力地閃爍著,就像這附近的居民一樣,大家每天也都只是在過日子而已。
我是一位按摩師傅,也是這家按摩店裡唯一的按摩師傅。
我高中畢業後就在這家按摩店工作,一路從學徒做起,二十幾年來,按摩過幾千隻腳,有不少我光摸腳就認得出是誰的熟客,甚至能猜出他昨晚吃了什麼、今天心情好不好、最近性生活美不美滿之類的生活瑣事。
透過與他們的肌膚筋骨接觸,某些時候我真的以為,自己是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朋友,時不時與他漫談閒聊、分享彼此的心事──但漸漸發現,這顯然只是個美麗的誤會,當一間間外掛時尚裝潢、內建辣妹美容師的護膚業興起之後,那些熟客每個都變得不太熟,什麼按摩技術、經驗技巧,在青春的肉體面前根本不堪一擊,店裡的生意一落千丈,按摩師紛紛出走,找尋其他能夠餬口的工作,到最後只剩下我和老闆兩個人,相依為命地守著這家店。
我不是念舊,只是對我來說,按摩就是我的人生,而人往往無法選擇自己的人生,所以生活是舒適或辛苦都沒關係,日子還過得去就好。
我的年紀已經不小了,老闆則更加年邁,我們坐在客廳邊看電視,邊等待幾乎不存在的客人,老闆頭歪歪地雙手交叉在胸前,畢竟年紀大了,一不注意就會打起瞌睡。
我用手撐著下巴,百無聊賴地看著電視新聞。
這幾天最火紅的新聞,剛好就發生在桃園,一名清潔隊員在清掃山區馬路時,發現了好幾包裝有屍塊的大黑垃圾袋,裡頭的屍塊亂七八糟的,有手、有腳、有頭,而且不只是一個人的屍塊,警方拼湊起來發現,被害者是一男一女,更玄的是,竟然找不到他們之間有任何關聯性,於是,全案朝向變態的隨機殺人分屍魔方向偵辦。
「媽的,這社會真的有病……」
我喃喃自語,但這在鬼島上,應該也只能算見怪不怪,生存在這種病態的社會裡,那傢伙想必患了什麼身不由己的疾病,活脫脫的一條可憐蟲。
人生嘛,還不就是混口飯吃。
我聳肩,默默寄予他可有可無的同情。
外頭的雨下得很大,就像颱風夜那樣的糟糕天氣。
──今晚大概不會有客人了吧!
我心想,看著門上懸掛的時鐘,距離十點的打烊時間只剩下二十分鐘,我還在思考要不要叫醒老闆,說服他今天提早收工時,門外突然傳來了聲響。
打盹的老闆驚醒,我也立刻打開了門。
「我要按摩。」
門口一名高大的男子沉著嗓子說。
竟然是客人──還是個奇怪的客人。
明明是八月,正值夏天,他還穿著長袖毛衣,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風,晚上九點多了,卻戴個墨鏡,而他頂著的大光頭,以及臉上未遮掩的累累刀疤,更讓我直覺這傢伙並非善類。
不過,所謂「有奶就是娘、有錢便是爺」,服務業的精神正在這裡,我依然拉開了笑臉,熱情地招呼他。
「請問是要腳底按摩,還是肩頸按摩?或是要全身按摩呢?」
「全身。」他不假思索。
「好的,來!裡面請!」老闆見到客人上門,整個精神都來了,彷彿年輕十歲一樣,充滿活力。
「加把勁啊!我等你關門。」老闆低聲跟我說道,我比了個「沒問題」的手勢。
昏黃的按摩室內,他脫掉鞋子,換成浴袍式的按摩衣後,我讓他躺上按摩床,幫他蓋了小毯子,我雙手塗滿精油,從他的左腳掌開始按摩。
「力道如果太大或太小,再麻煩跟我說喔!」我提醒他,他鼻子哼了聲當作回應。
我按摩的雙手,卻傳來了異樣的感覺。
是小玲。
小玲是一個在外商公司上班、快三十歲的小姐,大概每兩個月就會來光顧一次,她總是抱怨上班很累、腳很痠,要我多用點力,每次按摩一節四十分鐘下來,總是按到我滿頭大汗,讓我對於「錢歹賺」這件事,有著莫名深刻的體認。
──但我怎麼會在這個光頭刀疤佬的左腳上感受到小玲呢?
懷著詫異而困惑的心理,我就著昏黃的燈光,多看了他的左腳掌一眼,不舒服的感覺頓時油然而生。
小小的腳掌,微微透著青筋的白嫩肌膚,從我二十幾年的按摩經驗看來,可以斷定那是一隻年輕女人的腳。
而透過精油,我與那隻腳的筋脈、肌膚、骨骼,作了柔軟綿密的接觸,我完全無法否認它該是小玲的腳掌,卻極度詭譎地接在這個光頭怪男腿上的扭曲事實。
腿?
我心念一動,摸上了他的小腿,竟然沒有扎手的腿毛,粉嫩光滑的程度,依然是不可思議地像極了女生的小腿。
或者說,像極了小玲的小腿。
──應該是錯覺吧!可能我今天實在是太累了吧!
我嘴角自嘲地撇了撇,到底是說什麼也不甘心,自己20幾年的經驗,竟然會發生這麼大的失誤。
誰說光頭男就不能擁有漂亮美腿的?我決定不再胡思亂想,定下心來繼續幫他按摩左掌,輕重適當的力道,似乎相當合他的意,不過才幾分鐘的時間,他的呼吸已沉,甚至發出了低低的鼾聲。
客人安穩的酣睡,總是讓按摩師有種成就感,我微微一笑,輕輕放下他的左腳,改扶起他的右腳掌。
然後我差點嚇到放開了雙手。
我的心臟劇烈地砰砰跳著。
──現在我手中的、他的右腳掌,跟剛剛放下的左腳掌,絕對不是同一個人的。
剛剛那隻像極小玲的左腳掌,是那麼白嫩纖細,而我手裡這隻,卻寬厚肥壯、毛孔粗大、膚色黑沉、過長的腳指甲藏汙納垢,是標準的中年男子腳掌。
不需要二十幾年按摩經驗,任何人都能用肉眼察覺,這個光頭佬非常不對勁。
──這傢伙的雙腿上,竟然裝著不同人的腳掌!
我驚嚇地幾乎合不攏嘴,按摩二十幾年來,第一次遇到這樣讓人頭皮發麻的事情,正當心亂如麻,不知如何是好時,他原本穩定的鼾聲,突然頓了一下。
我的心也跟著震了一下,連忙又繼續手邊的按摩工作。
抹油、揉捏、指壓、骨滾……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似地繼續按摩著,而他的鼾聲總算又低沉地繼續。
像是解除警報似地,我鬆口氣,看著牆上的時鐘,按摩時間只剩下二十幾分鐘,我決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埋著頭撐完這節就對了。
於是,我對那兩隻壓根不同的腳視若無睹,我也不再去想這隻右腳,是不是很像中壢水電工阿海的腳,總之,什麼都不管地繼續我的按摩,一切都很順利──直到我看見了那環縫線。
在他的右腿膝蓋上方五公分的地方,有一圈相當粗糙的縫線,就像拿縫衣針似地,將一條腿與身體下部隨便縫了起來,縫線的交界處更是膚色、粗細分明,可以斷定是一男一女身體部位的縫合。
我想起了剛剛才看的新聞,桃園山區發生的分屍命案。
六神無主的我,悄悄掀開他的浴袍按摩衣,裡頭的身體充斥著粗製濫造的縫線,簡單的大概情形就是:他的身體由一男一女的肢體胡亂拼湊而成。
我不知怎麼描述自己的震驚,但當他鼾聲又停頓的瞬間,我立刻又扶起了他的右腿,準備繼續按摩。
可能是因為恐懼而造成力道失控,又或者是因為其他無法解釋的力量,總之我的手中突然多了一隻右腿。
具體的說,我將他的右腿「拆」下來了。
沿著縫線分裂,斷口處滴滴答答地淌著鮮血。
我的腦袋只有一大片的空白。
他的鼾聲竟然還在繼續。
待會他醒來,會怎麼報復我?
我這個想法才出現沒多久,手裡竟然又多出了他的一雙左右前臂。
我不知該怎麼解釋,拆下他雙手的瞬間,我大概是抱持著這樣的想法:「就算他醒來要報仇,失去雙手也不可能有辦法攻擊我吧!」
我微微喘著氣,感覺像氣管長刺一樣地呼吸困難。
眼前的場景是,他依然躺在按摩床上,他的兩隻前臂、一隻右腳,被我拆下丟在地上,整張床溢滿了鮮血,戴著墨鏡的他卻依然打呼酣睡,表情一副等待繼續按摩的平和模樣。
我僵在原地,不知一切該如何收尾。
──他這樣會不會死?我變成殺人兇手了嗎?這樣算犯了傷害罪嗎?好像真的是我拆了他的手腳耶?我會被關嗎?我要賠他多少錢?我哪裡有錢可以賠他啊!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恐懼罐頭的圖書 |
 |
恐懼罐頭 作者:不帶劍 出版社: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1-0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87 |
驚悚/懸疑小說 |
$ 87 |
驚悚/懸疑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恐懼罐頭
按摩師:光從觸感,我就可以知道這個人的身體狀況,但我一碰到這位客人,卻發現——
植物:我的手指長出了綠芽,連醫生都找不到原因,只知道它即將一點一滴悉干我的生命……
飢餓:那隻圓圓胖胖的藍色機器貓,是我們兒時共同的回憶,他的道具之中,最夢幻的就是拿起話筒一切都會實現的「如果電話亭」——
每個罐頭提供口味不一的恐懼,這只是其中的幾個。今天,你想吃哪一個?
作者簡介:
不帶劍
1987年出生於彰化鹿港。
文學與法律熱愛者,最得意的是成為人夫與人父。
創作領域橫跨純愛、奇幻、武俠、靈異與社會百態,
從來不覺得自己的文字受到限制。
而他都是這樣面對詢問:
「成功不是等待即至的未來,
而是需要不斷努力的現在。」
章節試閱
# 1《按摩師》
桃園,被遺落在城市外的小巷子,小巷子裡的老舊按摩店,門口懸掛的招牌,有氣無力地閃爍著,就像這附近的居民一樣,大家每天也都只是在過日子而已。
我是一位按摩師傅,也是這家按摩店裡唯一的按摩師傅。
我高中畢業後就在這家按摩店工作,一路從學徒做起,二十幾年來,按摩過幾千隻腳,有不少我光摸腳就認得出是誰的熟客,甚至能猜出他昨晚吃了什麼、今天心情好不好、最近性生活美不美滿之類的生活瑣事。
透過與他們的肌膚筋骨接觸,某些時候我真的以為,自己是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朋友,時不時與他漫談閒聊、分享彼此...
桃園,被遺落在城市外的小巷子,小巷子裡的老舊按摩店,門口懸掛的招牌,有氣無力地閃爍著,就像這附近的居民一樣,大家每天也都只是在過日子而已。
我是一位按摩師傅,也是這家按摩店裡唯一的按摩師傅。
我高中畢業後就在這家按摩店工作,一路從學徒做起,二十幾年來,按摩過幾千隻腳,有不少我光摸腳就認得出是誰的熟客,甚至能猜出他昨晚吃了什麼、今天心情好不好、最近性生活美不美滿之類的生活瑣事。
透過與他們的肌膚筋骨接觸,某些時候我真的以為,自己是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朋友,時不時與他漫談閒聊、分享彼此...
»看全部
作者序
作者自序
獨享恐懼
恐懼其實是一件很私密的事。
也許在人前你不願意承認,但在夜深人靜一人獨處的時候,在胡思亂想心底鬼影幢幢的時候,你總會想起那麼一個故事,一個短短的,卻深深的烙在你腦海的故事。你忘記是多久之前聽過或者看過這個故事,但當中的角色與情節卻拚命地鮮明起來,與你周遭的環境氛圍漸漸地搭配、吻合──然後你害怕了,恐懼就這樣一聲不響地來到你面前。
是啊,我們都習慣稱呼這樣的故事叫作鬼故事,而它的重要特徵就是:短潔有力,剛剛好就是一個恐懼的力道。
《恐懼罐頭》正是如此發想下的產物,它...
獨享恐懼
恐懼其實是一件很私密的事。
也許在人前你不願意承認,但在夜深人靜一人獨處的時候,在胡思亂想心底鬼影幢幢的時候,你總會想起那麼一個故事,一個短短的,卻深深的烙在你腦海的故事。你忘記是多久之前聽過或者看過這個故事,但當中的角色與情節卻拚命地鮮明起來,與你周遭的環境氛圍漸漸地搭配、吻合──然後你害怕了,恐懼就這樣一聲不響地來到你面前。
是啊,我們都習慣稱呼這樣的故事叫作鬼故事,而它的重要特徵就是:短潔有力,剛剛好就是一個恐懼的力道。
《恐懼罐頭》正是如此發想下的產物,它...
»看全部
目錄
# 1《按摩師》
# 2《禿頭》
# 3《植物》
# 4《租屋》
# 5《女醫生》
# 6《飢餓》
# 7《捉迷藏》
# 2《禿頭》
# 3《植物》
# 4《租屋》
# 5《女醫生》
# 6《飢餓》
# 7《捉迷藏》
商品資料
- 作者: 不帶劍
- 出版社: 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1-03 ISBN/ISSN:978986290642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4頁 開數:32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驚悚/懸疑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