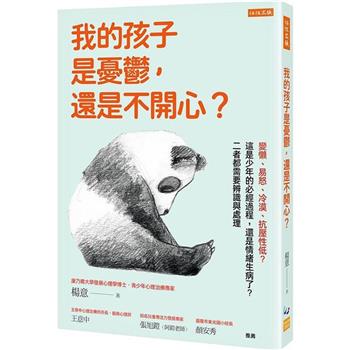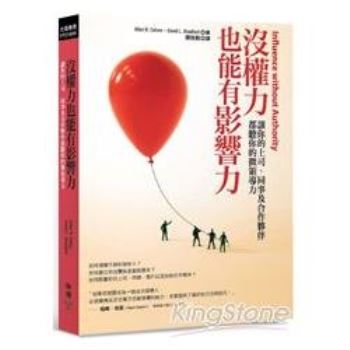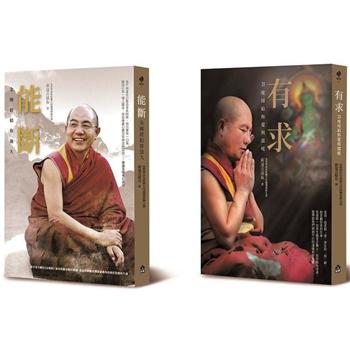推薦序
芝慧的「雙鄉記」
《雙鄉記》是長成於日治時代的台灣菁英葉盛吉的傳記,以日文寫成、在日本出版,後來亦翻譯為中文版面世,是一部使後人得以窺見跨越時代、語言、政權的台灣人心靈之複雜深微的記錄。
葉盛吉出生於台南,仙台第二高等學校畢業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在日治時期,這樣的台灣菁英求學歷程極為自然——殖民統治下,台灣人的國籍亦登記為日本,葉盛吉前往日本甚至不能稱為「留學」,因為是「國內」移動。然而,以日文為思考書寫語文、也透過日文進入開闊世界的葉盛吉,其自我認同並未被「日本」所定義。當戰爭結束、台灣「光復」後,選擇回歸母島台灣的葉盛吉,在白色恐怖中死去。他搖動擺盪於日本、台灣、中國之間的國族認同意識,在民主化的今日看來,仍是台灣人未解的難題。 一九九八年,芝慧與我相識於東京;如今想來,隨父母而來的她與將進入研究所的我,當時都站在人生的轉折點。那是九○年代末,電視衛星頻道開播,日劇、日本電影帶來乾淨、簡潔、明亮的城市生活想像、今日幾乎已成為死語的「哈日」風潮席捲台灣都會區;我們都不是因著追隨、吸附於這高漲如熱氣球的日本夢而來到異地。
日文對我們來說,不是可以與偶像歌曲、影音世界連結的符號,更不是前輩台灣人如葉盛吉般,在生長環境中隨時間而浸附於身的母語,而必須透過教科書才能逐漸認知到日語:一種與中文漢字看似相近、思維組織方式卻千差萬別的陌生存在。而時代雖已不復葉盛吉一九三○ ~ 五○年代的波瀾萬丈,但台灣的國際地位與政治主體依舊曖昧未定;只是一開始我們都那麼年輕,尚未意識到從「舊殖民地」來到「舊帝國」求學本身可能具有的「溯源」意涵,以及「留學」行為中所顯現的兩地學術權力位階。
於是,我們總相約在東京各處:新宿(芝慧鍾愛伊勢丹)、澀谷、惠比壽(我的寄宿地)、銀座,逛街購物看時髦繽紛的街頭人物,或找尋當期雜誌報導的甜點美食店家,與此平行前進的是競爭激烈而壓力沉重的校園生活。從「我可以試穿嗎?」都得比手劃腳才能與店員溝通,到可以用日文進行論文寫作、發表、學位審查答辯;從只能跟同操「國語」的族類一同行動,到與異國戀情的開展與消散;七年過去,當語言不再是最主要的障礙與隔閡,對「日本」的覺知卻未必能如濃霧散清,更多時候可能是強烈的迷惘。 如果那謙和婉轉、行事如儀的組織文化是日本,那麼監禁殘殺無辜過路人、沉迷於機械式無機質遊戲如小鋼珠或偶像團體的又是什麼?台灣資訊節目、旅遊導覽中由名嘴、職業旅者所演出的潔淨有禮、多情婉轉的日本,彷彿是東亞地區現代化後的理想型態,然而交纏著高度競爭、因而壓抑猥闇的實際面,也只有在怎麼記也記不完的大量情緒詞彙中、透過日復一日的真實生活經驗才能體悟。
芝慧開始半開玩笑的稱我「先生」,大概是我開始教書以後的事;一直以來,她以日文發音叫我「□□□□」,名字後不加「□□」,則是延續台灣中文口語的使用習慣。離開學生身分後的工作性質,讓我們獲得了重新觀看台灣、並轉化傳遞「日本」經驗的機會。在閱讀書稿的過程中,我多次按下自己提筆修改的職業病衝動——中文語境中透出「違和感」的文字運用,不正與芝慧的「雙鄉記」互為呼應,因此可以成為獨特風格?能進入日本政治核心:「國會」工作的經驗至為稀有,而這樣的經驗在芝慧回到台灣、並決定在政界一角邁出步伐之際更顯難得。讀者應可隨著芝慧那驚訝、讚嘆、不解、困惑的視線,對照由台灣媒體或書物所提供的形象知識,在紙上遊覽一次日本與台灣的「雙鄉記」。
張文薰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