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解台灣「牛」諺語
今逢農曆除夕。我曾呼籲「與國際社會同步過年」(改過陽曆年),但人微言輕,「蚊子叮牛角」,無人理會。只好與眾隨俗,也來湊熱鬧一番。今逢牛年,想起台灣俗諺中有許多用牛來比喻的話,列舉數則,加以現代新解,供春節茶飯餘話——
「牛稠內觸牛母」:牛稠是牛舍之意。本句原意是指公牛對外軟弱無能,卻只會在牛舍內欺負母牛。這句形容「內倨外恭」的話,用來形容馬英九集團真是恰好不過!平常拿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教訓台灣人,碰到小小共產黨員來了,「國旗」就收得無影無蹤,拿國旗還反遭教訓;平常「中華民國」喊得震天響,到北京朝「共」時,個個像龜孫子,不敢哼半聲。對外無能,對內欺負台灣人最內行。
「嘴念阿彌陀,身藏宰牛刀」:比喻說一套、做一套。觀諸馬政府,這種事例最多,如嘴說「台灣前途由台灣住民決定」,實際上卻連和中國海協會簽署協定的內容都不讓台灣人民知道;嘴說「愛台灣」、「尊重人權」,卻鼓勵警察禁止唱片行播放〈台灣之歌〉、染指公視的內容……。
「老鼠入牛角,穩觸觸」:老鼠鑽入牛角,死路一條,穩被抓。自馬英九的黨國復辟後,又把台灣帶入「一中」死巷,處處迎合一中需求,為一中鋪路。胡錦濤若懂台語,也該咧嘴而笑曰:「老鼠入牛角,穩觸觸。」
「牛牽到北京嘛是牛」:比喻魯鈍不堪造就,或本性難移之意。依後者之意來看,國民黨復辟之後,「台灣」又改回「中華」,民主紀念館又改回中正紀念堂,可知其「去台灣化」的「一中」意識形態,以及依戀獨裁者的「反民主」情結,依然難改;再例如:政客與知識份子的不同在於,前者以個人名利權位為依歸,後者以天下蒼生、國家社會為己任。政客再怎麼擁有高學歷,還是政客。
「做人著磨,做牛著拖」、「若欲做牛,毋驚無犁通拖」:農業時代的牛,難逃拖犁耕田的命運,前句有宿命意味,表示人與牛一樣,都必須勞碌認命;後句意義則更積極,比喻如果有心扮演某角色、承擔某責任,就不怕無份內之事可做。台灣人民若有心獨立建國,不怕無著力之處。
「軟索牽牛」:牽牛不必硬拉,以免牛脾氣一發,僵著不走,徒費力氣。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也是一樣,空喊口號,不一定有效,說不定嚇跑更多人。如何講求方法,迂迴輾轉,因勢利導,可能更重要。
「驚某大丈夫,打某豬狗牛」:此話在勸人疼愛妻子,切勿動粗施暴,否則就無異畜生。記得胡適說:「怕太太是民主政治的表現。」不過,若政治人物太過於怕太太,以至於任其干政亂紀,需索無度,最後弊案叢生,致使四十年來的民主運動成果毀於一旦,那胡適的話就要修訂了。
與牛有關的台灣俗諺還很多,例如「一隻牛剝雙層皮」、「豬母牽到牛墟去」、「細漢偷挽匏,大漢偷牽牛」、「牛角噴無風」、「生牛不識虎」、「無牛駛馬」,不勝枚舉,篇幅所限,無法一一新解。
吾友施並錫教授常以台灣牛比喻台灣人。如今台灣牛有麻木消沉之態,讓我想起蘇格拉底的自我期許:「雅典像一頭無精打采的牛,我將扮演『牛虻』的角色,狠狠地咬牠一口,讓牠驚醒過來。」
行文至此,忽然覺得對牛有點歹勢。蓋牛過去對台灣農業開發功不可沒,吾人理應感念才對。本文如有對牛不敬之處,尚祈眾牛多多包涵。
原載於二○○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自由時報》「李筱峰專欄」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烏鴉不快樂的圖書 |
 |
烏鴉不快樂 作者:李筱峰 出版社: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09-0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90 |
二手中文書 |
$ 253 |
政治 |
$ 272 |
社會人文 |
$ 282 |
中文書 |
$ 282 |
Others |
$ 288 |
政治/法律/軍事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烏鴉不快樂
◎本書特色
1、一個自比烏鴉的知識份子,最懇切的政治觀察。
2、二○一二年台灣最關鍵的大選之前,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台灣人,都要看的一本政治評論。
作者簡介:
李筱峰
一九五二年生於台灣台南麻豆。
經歷:
《八十年代》《亞洲人》雜誌執行主編;
報社記者、編輯、主筆;
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授。
現任: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專任教授;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董事。
著作:
史論──《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灣革命僧──林秋梧》、《台灣民主運動40年》、《解讀二二八》、《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唐山看台灣──228事件前後中國知識分子的見證》、《台灣近現代史論集》、《台灣人應該認識的蔣介石》、《60分鐘快讀台灣史》、《台灣史100件大事》、《台灣,我的選擇》、《與馬英九論台灣史》、《台灣歷史閱覽》、《進出歷史》、《台灣史》 (與林呈蓉合著)、《台灣近代名人誌》一~五冊 (與張炎憲等合著)、《二二八回憶集》(與張炎憲合編)、《快讀台灣歷史人物》(與莊天賜等合著)
政論集──《恐龍的傳人》、《叛徒的告白》、《政治小檔案》、《我們不做空心人》、《眉批台灣》、《台灣要衝決網羅》、《吾輩是狗》、《統獨十四辯》、《聖誕老公公不見了》、《台灣怎麼論?》、《李筱峰專欄》、《李筱峰專欄續集》、《我的覺醒》、《黨國復辟前後》、《一個新台灣人的死與生》 (與張杏梅合編)
其他──《我生印記》
章節試閱
新解台灣「牛」諺語
今逢農曆除夕。我曾呼籲「與國際社會同步過年」(改過陽曆年),但人微言輕,「蚊子叮牛角」,無人理會。只好與眾隨俗,也來湊熱鬧一番。今逢牛年,想起台灣俗諺中有許多用牛來比喻的話,列舉數則,加以現代新解,供春節茶飯餘話——
「牛稠內觸牛母」:牛稠是牛舍之意。本句原意是指公牛對外軟弱無能,卻只會在牛舍內欺負母牛。這句形容「內倨外恭」的話,用來形容馬英九集團真是恰好不過!平常拿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教訓台灣人,碰到小小共產黨員來了,「國旗」就收得無影無蹤,拿國旗還反遭教訓;平常...
今逢農曆除夕。我曾呼籲「與國際社會同步過年」(改過陽曆年),但人微言輕,「蚊子叮牛角」,無人理會。只好與眾隨俗,也來湊熱鬧一番。今逢牛年,想起台灣俗諺中有許多用牛來比喻的話,列舉數則,加以現代新解,供春節茶飯餘話——
「牛稠內觸牛母」:牛稠是牛舍之意。本句原意是指公牛對外軟弱無能,卻只會在牛舍內欺負母牛。這句形容「內倨外恭」的話,用來形容馬英九集團真是恰好不過!平常拿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教訓台灣人,碰到小小共產黨員來了,「國旗」就收得無影無蹤,拿國旗還反遭教訓;平常...
»看全部
作者序
李筱峰最後一本政論集
自從高中時代因狂熱閱讀課外書籍以來,我從一個法西斯狂徒覺醒過來,開始成為一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追尋者。進而開始奮筆疾書,諤諤直言。……好不容易熬過了凜冽的軍事戒嚴時代,以為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將有一片清明景象。
然而,……積重難返的社會大眾,依舊難改其深層結構的奴性;七十年前心理學家佛洛姆所指陳的「逃避自由」的心態,依舊在受虐性格極深的台灣人身上揮之不去;「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依然在台灣人民身上集體發作。
不過,再怎麼失望,都還不敢絕望。我決定少寫政論,不是要完全歸隱山林...
自從高中時代因狂熱閱讀課外書籍以來,我從一個法西斯狂徒覺醒過來,開始成為一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追尋者。進而開始奮筆疾書,諤諤直言。……好不容易熬過了凜冽的軍事戒嚴時代,以為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將有一片清明景象。
然而,……積重難返的社會大眾,依舊難改其深層結構的奴性;七十年前心理學家佛洛姆所指陳的「逃避自由」的心態,依舊在受虐性格極深的台灣人身上揮之不去;「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依然在台灣人民身上集體發作。
不過,再怎麼失望,都還不敢絕望。我決定少寫政論,不是要完全歸隱山林...
»看全部
目錄
自序 我此生最後一本政論集
國民黨整肅台派人士有新方
新解台灣「牛」諺語
愛錢的台灣人
唐山客的寶島美感
吳淑珍說出了我的心情
二二八事件中看到的中國說謊文化
二二八事件中看到台灣人的憨直
支那狂犬范蘭欽
「高級外省人」所不認識的人
假如我是陳致中
惡僧高誦帝國經
蔣經國的叛徒要追思蔣經國
週年啟示錄
給「反動巨星」上上課
鄭成功加入國民黨?
台灣民主政治的大恩人——紀念傅正先生逝世十八週年
白痴與花痴——馬英九支持者的成分分析
耍賴的文化
台灣人應...
國民黨整肅台派人士有新方
新解台灣「牛」諺語
愛錢的台灣人
唐山客的寶島美感
吳淑珍說出了我的心情
二二八事件中看到的中國說謊文化
二二八事件中看到台灣人的憨直
支那狂犬范蘭欽
「高級外省人」所不認識的人
假如我是陳致中
惡僧高誦帝國經
蔣經國的叛徒要追思蔣經國
週年啟示錄
給「反動巨星」上上課
鄭成功加入國民黨?
台灣民主政治的大恩人——紀念傅正先生逝世十八週年
白痴與花痴——馬英九支持者的成分分析
耍賴的文化
台灣人應...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李筱峰
- 出版社: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09-06 ISBN/ISSN:978986294009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政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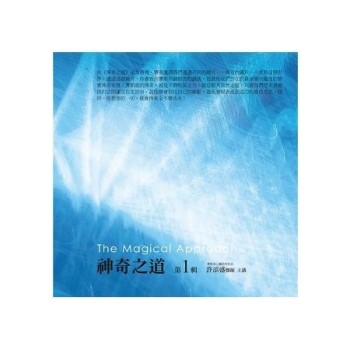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