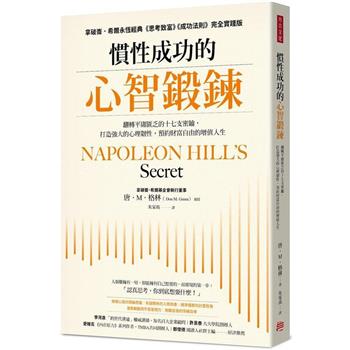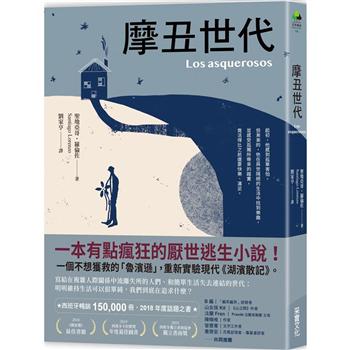編者的話
要翻譯一本百年前的書,尤其那是一個東西文化碰觸最劇烈的年代,地名、人名都已久遠,下筆的思維模式也和今日大不相同,要譯到這個時代的人看得懂並非易事;而且要翻譯一個人的日記更難,特別是執筆者並不知道他的私密手稿要公諸於世,在遣詞用語、時間點的掌握、事情的交代和人物的暱稱,都是相當隨興的。馬偕牧師的日記,就是這兩種困難的總和。
但也並不能因這些困難而放棄翻譯,不僅今日教會以他為信仰和宣教的範本,他在醫療教育上的貢獻,與台灣社會發展不可分割,他台灣行腳的珍貴記錄,更是今日研究百餘年前台灣不可或缺的史料,浪漫的一生也成為小學課本人物,坊間他的著作、評傳和小說充斥,說馬偕已成台灣的顯學,實不為過。這本日記是研究他、瞭解他、效法他的最完整根據,他的翻譯出版正是今日社會所深深期待的。
由於日記蒐集跨海回台的過程冗長、複雜,由手寫稿轉成打字稿再出英文版已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加上2012年為馬偕博士來台140週年這個有意義的時間點須掌握,為壓縮翻譯的時間,由六位譯者分段譯出,若不加修正、統整而直接出版,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因此在出版前的編輯過程中,有不少的困難必須克服:
一、首先真的要佩服馬偕牧師,日記雖是個人隱私的手稿,字體龍飛鳳舞,但筆法流暢,其個人也為了參考方便,日記上都有下標(文中會用粗體字呈現),甚至附註(如秀才、舉人、進士,他以學士、碩士、博士比喻);而且他有意無意都把不少台語直接用羅馬拼音記述(如頭人thau–lang,文中羅馬拼音字會用斜體字呈現),減輕不少日記翻譯的困難。此事也可看出馬偕牧師的行事風格和嚴謹的為學態度。日記中牽扯到不少他的好友、門生,雖有暱稱、小名,但藉著羅馬拼音讓我們方便推敲,尤其是台灣教會史在過去已有很多先輩的努力,教會資料的保存還算完整,讓我們盡量予以還原。
二、在華基督教宣教士我們也以漢文姓氏譯出。另外日記中出現的外國人,包括商人、領事、海關客卿和晚期劉銘傳所聘的顧問和技術洋員,我們都已盡量以官方的譯名,如英國領事Herbert James Allen,應譯為阿倫(見1875.4.25),但官方卻是「阿赫伯」;偕醫館的醫生Dr. B. S. Rinnie,教會過去都譯為「瀝尼」,官方則譯為「禮德」,我們也都還原。台灣茶葉史上的重要人物、馬偕好友,寶順洋行的John Dodd,過去教會都譯為「道先生」,這是與台語較接近的音譯,但近代民間都以「陶德」譯之,我們也循此通俗譯名。比較困擾的是英文名字相同者太多,自己的日記當然不用註明,但要翻譯,除非有把握,否則不能貿然區分,只能勞煩讀者自己注意了,尤其是馬偕回國那四年的地名、人名,若翻成漢文,意義不大,就直接用原文了。
三、雖馬偕牧師日記中的地名都以羅馬拼音稱之,但因台灣改朝換代、社會變遷劇烈,地名隨著政權一改再改,因此老地名若不註明現今地名,無法讓讀者讀來身歷其境,我們也都盡量找出,如:艋舺、水返腳、三角湧,一般人都知道,但「洲裡」是今日的「蘆洲」、「棕櫚島」是基隆的「和平島」,可能就較少人知道了。「三重埔」一般人會誤以為是今日新北市的「三重」,實際上是台北市的「南港」,兩者相去甚遠。後期常提及的圓窟仔教會,若知道是在今日林口東側某地,讀者就能理解這是馬偕從五股、新莊到南崁行腳的中繼點。當然,限於編者所學和時間有限,部分地名未標示或錯誤,也請日後專家不吝指正了。另外要強調的是,馬偕用的是百餘年前的台語拼音,和今日研究可能不盡相同,如今天的大溪,他記的是「大姑陷」而非「大科崁」,相信研究同好會很有興趣的。
四、誠然,如上所言,「馬偕日記」的記述是較隨興的,我們在日記原文的判讀上遇到頗多困難。首先遇到的困難是日記原稿沒有分段落,標點符號不清,大小寫的隨興書寫更增加上下文、斷句判讀的難度。常常一段話寫了一半就沒有下文,或是留下許多空白,後來沒有再填寫進去。例如:洗禮人數……,之後就留下空白。
馬偕手稿的英文字母「T」、「L」、「F」大寫常造成編譯者的誤判,而英文的草體「n」與「u」也很容易混淆。例如:1884年2月20日禮拜三:「早上去看劉和(Lau-ho)的墓,『我們若能忍耐,也必和祂一同作王。』提摩太後書2章12節的字樣在他的墓(碑)上。」若把劉和(Lau-Ho)誤看成陳和(Tan-Ho),那就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了。因為就在十天前的2月10日禮拜日,馬偕記著:「和順仔以及陳和去八里坌。」
馬偕常以暱稱呼其學生,例如:「九」(Kau),陳九或是柯玖?陳九是1882年之前所謂「逍遙學院」時期的學生,柯玖(柯維思)則是牛津學堂第二年入學的學生,我們必須從出現的時間點判斷是陳九或柯玖。當然晚期出現的可以確定是柯玖,因為柯玖是馬偕鍾愛的學生,跟隨馬偕身邊,擅長攝影,現存許多馬偕相關影像應多出於柯玖所拍攝。1893年第二次返國述職只帶著柯玖隨行,後來也成為馬偕的二女婿(1899.3.9)。另外一個名字也容易混淆的是「和」,究竟是陳和或連和?需要瞭解馬偕在台灣傳教的背景才能做判斷。
林昌華牧師有一文:〈馬偕研究的史料問題〉,文中有提及馬偕日記原稿的判讀問題,在此不再贅述,有興趣的讀者可上賴永祥長老網站參考。www.laijohn.com/articles/Lim,CHoa/Mackay/sources.htm
五、馬偕牧師晚年因喉癌疾患,日記只記到1901年2月11日即停筆不能再寫。那麼,直到馬偕逝世的6月2日,這一段近四個月時間的情形呢?馬偕的愛徒柯玖於馬偕死後曾寫一封信,向加拿大長老教會海外宣教委員會幹事偕彼得牧師(R. Peter MacKay)報告馬偕臥病、臨終以及葬禮的各項情節,正好彌補了這段空缺。馬偕次女偕以利(Bella MacKay,柯維思夫人)於馬偕死後,也曾寫信給友人,將父親病情的起落逐日記錄,一直到過世、安葬,都詳細做了報告。後來這信函,就以「馬偕博士的最後一段日子」(Dr. Mackay’s Illness and Death)為題,刊登於《加拿大長老會會誌》(Presbyterian Record, Dec. 1901)。偕以利的報告與柯維思的信,內容相去無幾。編者以為柯維思的報告更為細膩且富有感情,旅居加拿大的陳俊宏長老曾發表:〈柯維思的馬偕臨終記錄〉,即是將柯玖的信翻譯成漢文。讀者也可上賴永祥長老網站參考。www.laijohn.com/Mackay/MGL/death-report/Koa,Usu/tr/Tan,Chong.htm
六、馬偕牧師在台宣教前後二十九年(1872-1901),這期間僅兩次返國述職(1880.1.1-1881.12.19;1893.9.6-1895.11.19)。返國述職期間,馬偕廣受歡迎,被邀請到各地講道、演講與報告台灣的宣教處境與需要,「馬偕熱」蔚成風潮,尤其第二次回國,當選加拿大長老教會總會議長(1894.6.13-1895.6.12),肩負重任,更是奔波於加拿大東部各省的市鎮與教會。北到愛德華王子島(Prince Edward Island),東達新蘇格蘭省(Nova Scotia)東南的海港哈利發克斯(Halifax),西及曼尼托巴省(Banitoba)省會溫尼貝格(Winnipeg)西邊的大草原鎮(Portage La Prairie)。到美國紐約尋訪牙醫學院(1881.5.25),返回普林斯頓神學院演講(1881.4.4)與參加同學會(1895.5.6),也曾走訪愛爾蘭、蘇格蘭的祖籍故鄉(1894.9-10),與堂兄弟們歡聚。令人驚訝的是,這些地名,經過一個半世紀以來幾乎不變,至今我們還是可以從Google衛星地圖搜尋得到這些地方。
七、既然是私人日記,都會有它獨特的習慣,讀者閱讀時必須理解。如他日記並非全部逐日記載,很多是事後追記或一日內記多日事情。也有不少地方直接在日記上畫圖,我們將在文中予以說明。當然難免也有詞義不清的,譯者也盡量以馬偕心思加以揣摩,必要時再加附註,以減輕私人日記的形式讓讀者易明。
八、也因為是私人日記,難免筆無遮攔,赤裸反映出他個人的看法,如他和助理黎約翰牧師夫婦之間,因宣教工作方式的摩擦,以及對他工作態度的批評相當直接,這是要讀者諒解的。另外,畢竟馬偕是外國人,難免有當時西方人的優越感,對台灣社會宗教、風俗和官僚,有較嚴厲的批判。此外,他的生活圈也是以當時的漢人為核心,會稱原住民為「生番」、噶瑪蘭族為「平埔番」,這也是讀者要去諒解的。
九、馬偕牧師日記中除了獨子偕叡廉外,對家人著墨不多,但我們實在要注目馬偕夫人張聰明女士,馬偕牧師兩次回國,張聰明都隨行在側,所到之處多有張聰明的陪伴,有時也向婦女宣道會的聚會發表演講(1880.6.29)。馬偕夫人在19世紀末已然繞行地球一周,走訪過印度、以色列聖地,更走過半個加拿大,這是多麼有福的女子啊!若非有過人的膽識與聰明智慧,當東西文化碰觸的時代,誰能擔負起這個重責大任?
最後,日記出版後,讀者必會跟我們一樣,驚訝於馬偕牧師的博學多能、精力充沛而且膽識過人、隨遇而安,這些都豐富的反應在這包羅萬象的日記上。它的出版,對台灣人文歷史、自然生態的助益,自不在話下。但我們必須強調的是,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翻譯出版馬偕牧師日記的目的,乃在緬懷這位偉大的宣教師,效法他的信心、瞭解他宣教成功的要素、感受他那蓽路藍縷、流淚撒種的艱辛和歡呼收割的報償。讓台灣教會深信百年前能讓馬偕牧師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的上帝,是永不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