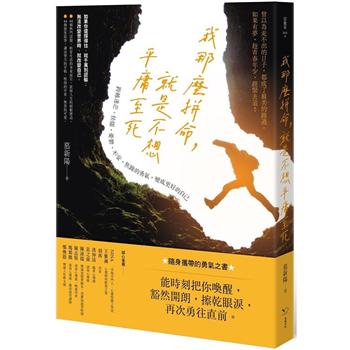【本書特色】
◎以史料奠基,再現臺灣文學之聲
◎本書研究了1910到1970年代約60多年間的第一手文獻,這是臺灣社會多重轉折的時代,從為期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到戰後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與長期戒嚴。這些前輩文人走過激烈動盪的年代,有人甚至付出犧牲自由與生命的慘痛代價。其事蹟與作品在歷史時空中縱橫交錯,點燃希望的微光,讓我們深刻體悟到,他們在黑暗中有所堅持、在挫敗中不放棄希望的曲折心路歷程,而我們,更沒有理由對未來感到悲觀。
◎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廖振富近年來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從這七篇文章中仔細體會傅錫祺、蔡惠如、林獻堂、葉榮鐘、朱點人、莊垂勝、林莊生等臺灣前輩文人,他們面對時代變遷時的思索與生活,以及內心世界的失落與堅持、苦悶與奮鬥、糾結與反思。
【專業推薦】
◎「通過這本書,我們得以看到這些前輩文人,如何以他們的行動與作品來回應缺乏自主性的殖民社會?如何在臺灣社會的多重矛盾與煎熬之中,展現作為知識份子的理念和實踐。」─向陽
◎「詩的歷史,就是記憶的創造,就是意志的泉源,像臺灣人這樣,連單純地活著都得要拼命的,夾縫中的弱小民族的,朝向希望的意志。」─吳叡人
【內容簡介】
文學作品是當代社會的反映。
從日治到戰後,短短幾十年間,臺灣的政治環境以及社會氣氛產生了非常巨大的變化。出生於臺灣,走過這些時代轉折的前輩文人,他們如何在劇變的環境中思索與自處?發展出什麼樣的人際關係?面對劇烈變化的現實環境,他們又發出了什麼樣的文學之聲?
現任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廖振富從前輩文人的照片、書信,以及社團文件、地圖等當代史料著手,建構出1910到1970年代臺灣文化人的關係網絡,以及文學社群的形成與凝聚,並討論時代變化中臺灣文學的發展狀況。由此回顧臺灣前輩文人如何以文學呼應時代變局,並從其作品中認識他們的涵養與視野,以及想要脫困、突圍的韌性和勇氣。
◎日治時期三大詩社,以古典詩創作為主的櫟社,是日治時期臺灣中部最活躍的文學社團。本書收錄了多項櫟社相關文獻,包括(1)1912年的櫟社題名錄(2)社員黃旭東,1911年11月在青島行醫時對辛亥革命後中國的第一手觀察報導(3)1912年1月、1930年3月,反映連橫與櫟社互動情誼,從親密到決裂的兩張明信片(4)1918年12月,蔡惠如為發起「臺灣文社」奔走募款,與傅錫祺聯絡之信函(5)1924年,蔡惠如因意外受傷,回信答謝社友之慰問(6)1947年1月,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夕,櫟社為謀復興,推舉林獻堂接任社長,並吸收新社員的會議紀錄。透過這些史料,不但可具體認識櫟社從日治到戰後數十年間的興衰起伏軌跡,也能看出面臨臺灣近百年來多重時代轉折,櫟社社員如何回應?其理想與堅持何在?也能藉此體會社員文學涵養與寬闊視野,乃至成員立場的差異與紛爭的具體細節,從而思索背後所隱藏的文化與政治意涵。
◎除此之外,作者又從「詩集印刷與文學傳播」、「鐵路交通與文人社群往來」兩大面向,觀察日治時期傳統文人如何透過新興文學傳播網路的運作,以凝聚文學社群意識,從而建構綿密的聯繫網。在現代化巨輪的主導下,各種技術的進步連帶影響了文化、精神的發展。印刷與出版普及,鐵路交通使詩人身體快速移動,人際連結因而更加緊密,而當時盛行的詩會,尤其像「全島詩人大會」如此大規模的文學活動,更是建立在上述物質條件的基礎之上,始有實踐的可能。
◎出身臺中清水的世家公子蔡惠如,跨越商業、政治、文化界的人生經歷,以及長年在日本、中國、臺灣三地奔走往來,使他對世界局勢發展與時代思潮的掌握相當敏銳,在1920年代一躍成為臺灣抗日民族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他的作品中所蘊含的啟蒙意識與進步思想,更見證了時代改變的浪潮。若不以成敗論英雄,他的一生,猶如一道劃過臺灣夜空的流星,如此短暫,也如此絢爛。
作者簡介:
廖振富
1959年生於臺中霧峰,1977年畢業於臺中一中,1981年畢業於臺灣師大國文系,1996年臺灣師大文學博士。先後任教於嘉義師專、臺中科技大學、臺灣師大、中興大學。曾任中興大學文學院副院長、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現任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著有《臺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晩清到二二八》、《櫟社研究新論》、《新修霧峰鄉志.文化教育篇》、《蔡惠如資料彙編與研究》、《林癡仙集》、《林幼春集》、《在臺日人漢詩文集》、《時代見證與文化觀照:莊垂勝、林莊生父子收藏書信選》、《臺中文學史》(與楊翠合著)、《追尋時代:領航者林獻堂》等書。
章節試閱
時代轉折的見證,臺灣文學史的新發現
─傅錫祺家藏櫟社史料的學術價值
「臺灣文學研究」成為獨立的學科,時間相當短淺,臺灣文學史料的挖掘、整理與建構,乃是臺灣文學研究朝向深刻學術化不可或缺的奠基工作。近十多年來,在臺灣文學的學術範疇,不論原住民文學、母語文學、民間文學、古典文學、日治時期新文學、當代作家文學等諸多領域,不少學者、作家及其家屬、文史工作者、研究生紛紛投入這股挖掘臺灣文學史料的潮流中,提供不同程度的貢獻,出版各類專書或論文,使臺灣文學的研究不斷有新發現,產生新論述,逐步建構更堅實的研究成果。目前臺灣文學史料的挖掘、整理工作仍如火如荼展開之中,而國立臺灣文學館發行《臺灣文學史料集刊》,提供交流分享的平臺,也可說是以國家資源回應這股新興學術潮流的產物。
筆者專業研究以臺灣古典文學為主,從事櫟社研究多年,並關注近百餘年來臺灣新舊世代知識份子的思想傳承、文學活動與創作,社會與政治關懷。2007 年8 月筆者從臺灣師大轉到中興大學臺灣文學所任教,偶然得知興大臺文所在職專班學生羅瑰琳(現任臺中市潭子國小教師)為櫟社社長傅錫祺之外曾孫女,筆者經由她的引介,進而結識其母親傅紅蓮女士,透過傅女士之協助,並取得其家族之信任,陸續將其家中珍藏大批櫟社書信、手稿及其他原始文獻提供筆者參考。其資料之豐富、份量之龐大,令筆者大為驚訝。根據這批資料顯示,傅錫祺雖然在1917 年才接任社長,但其實從1906 年櫟社組織化開始,他便擔任櫟社活動的主要聯絡中心,與資料之保管者,因而可以斷言:櫟社相關資料與原始文獻,絕大部分都保存於傅錫祺家中,若能陸續整理,將可提供不少值得研究的新資料。
由於這批資料份量龐大,整理、解讀相當複雜費時,以下筆者初步選錄數件珍貴史料,說明其背景及其學術價值,提供學界及有興趣的讀者參考。包括(1)1912 年的櫟社題名錄(2)社員黃旭東,1911 年11 月在青島行醫時對辛亥革命後中國的第一手觀察報導(3)1912 年1 月、1930 年3 月,反映連橫與櫟社互動情誼,從親密到決裂的兩張明信片(4)1918年12 月,蔡惠如為發起「臺灣文社」奔走募款,與傅錫祺聯絡之信函(5)1924 年,蔡惠如因意外受傷,回信答謝社友之慰問(6)1947 年1 月,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夕,櫟社為謀復興,推舉林獻堂接任社長,並吸收新社員的會議紀錄等。
透過這些史料,不但可具體認識櫟社從日治到戰後數十年間的興衰起伏軌跡,也能看出面臨臺灣近百年來多重時代轉折,櫟社社員如何回應?其理想與堅持何在?也能藉此體會社員文學涵養與寬闊視野,乃至成員立場的差異與紛爭的具體細節,從而思索背後所隱藏的文化與政治意涵。這些史料既是時代多重轉折的珍貴見證,也將為臺灣文史學界提供不少新發現。
一、櫟社社友題名錄:櫟社創社初期的一手史料(1912 年)
後圖所示「櫟社社友題名錄」,從字體判斷是傅錫祺的筆跡,題名錄下方註明「以齒為序」,亦即按照年齡大小依序排列,時間是明治45 年(1912),名單上共有二十一人,姓名下方有兩行小字,第一行是本名、字號、地址,第二行是出生年月日(陰曆)。這份資料是考察社員年齡的重要依據,相當珍貴。年齡最長的是生於慶應3 年(1867)的陳基六,其次是張麗俊、王學潛,都生於明治元年(1868)年,其次依序從1871 年出生的賴紹堯,一直到1882 年出生的陳賈,櫟社第一代核心社員,大體上都是在日本領臺之前已完成接受傳統的漢學教育。
從居住地考察,櫟社社員基本上都是定居臺灣中部,但當時記載的地名,不但與現今頗有差異,日治時期也曾多次更名。如陳瑚、陳貫兩兄弟住苗栗房裡,屬於現在的苑裡,陳基六、蔡惠如住牛罵頭,即臺中清水,而林家的林仲衡、林幼春、林獻堂的地址都寫霧峰舊名「阿罩霧」等,林子瑾居住的「臺中廳臺中街新庄仔」,是現在的臺中市區後火車站大智路附近。至於社員中唯一非出身中部的是臺南人連橫(雅棠),因櫟社創辦人林俊堂邀請而加入該社,1909 年時他受雇於霧峰林家的合昌商會,寓居林家所擁有的「瑞軒」(在現在臺中公園附近,1912 年左右因建公園而拆除)。
名單中較具知名度的人物包括:林俊堂、林幼春、賴紹堯三人是櫟社最初的創辦人,林獻堂、林幼春、蔡惠如等人則在1920 年代積極投入臺灣民族運動,櫟社被認定具有強烈的抗日色彩,也肇因於此。傅錫祺在1917 年接替此年去世的賴紹堯擔任櫟社社長,一直到1946 年去世為止,是維繫櫟社運作的靈魂人物之一。林子瑾則是1919 年櫟社創辦臺灣文社的重要人物,臺灣文社發行的《臺灣文藝叢誌》以其臺中住宅為發行地址。而這份1912 年的櫟社社員名單,出身鹿港者計有鄭玉田(汝南)、陳懷澄(槐庭)、莊嵩(太岳)三人,足以反映鹿港向來文風鼎盛的事實。
二、黃旭東致傅錫祺函:辛亥革命後的青島見聞(1911 年11 月)
由於櫟社成員之社會身份,皆屬於當時社會之知識菁英,其中有不少社員曾有豐富的境外旅遊經驗,如林獻堂1927 年至1928 年的歐美之行,著有《環球遊記》,已成為當今學界的熱門研究對象。而在筆者目前所見櫟社信函中,有多件屬於社員旅居日本與中國之見聞,相當具有研究價值,以下試舉一例說明之。
社員黃旭東(1883 ─ 1913)畢業於臺北醫學校,曾在臺中中央醫院任職,櫟社外團組織「中央金曜會」之例行活動,便是在其任職之醫院舉行。不過,由於他早在1913 年於旅居日本期間意外病故,其事跡並不被後人熟知。而這批信件中,有數封黃旭東旅居中國大連行醫時寫給傅錫祺的信,都是以工整之毛筆小楷書寫。其中一封是1911 年11 月所寫,信紙多達十張,內容約數千字。根據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可知,他大約1911 年8 月下旬離臺赴大連。1911 年11 月23 日黃旭東寫信給傅錫祺報告近況,當時恰好是辛亥革命爆發不久,大連屬於日本勢力範圍,黃乃得以處在風暴之外,旁觀中國時局之劇烈變遷。信中談到他在大連行醫對大連的觀察,以及與梁啟超、湯覺頓兩人晤談的經過,乃至梁啟超對革命的態度等,摘述片段如下:
近頃革命風潮澎湃全清,大連一地雖不受其影響,而避難來者日有所聞。當盛大臣避難往青島時,亦在此地停船數時間,但不接客耳。約十數日前,任公由日來連,越日往旅順,再越宿赴奉天,在奉天住兩三日,即赴營口,其時擬再回奉天或往北京。後因湯荷庵自北京來連,電促任公來連談話,故任公行程改換來連,二宿即同荷庵乘嘉義丸回神戶矣。
當任公初到時,弟本擬往訪,後思任公際此革命大亂之際,想亦無心與閒人聚談,故不果往。再來之際,因思荷庵亦在,故於夜間挾刺往,則荷庵歡顏出迎,大謂奇遇。弟告以故,始恍然明白,謂彼常來往北京、天津、日本間,每到此地多獨宿旅邸,未有友人聚話,
並謂此後來往,有弟在此,可以免寂寞之感矣。
少頃,任公出,亦訝弟南人何以來此?聽彼二人之言,謂此回革命,與彼常時持論不同,固眾所周知者。現時革命乃種族革命,彼主張者乃政治革命,蓋謂種族革命,須大動戈矛,終招外國干涉,則不利莫大於是,政治革命則不然。且此回之亂,因政府不從其平時一黨所主張,虛傳立憲,毋有實行之期,故種族革命一黨,得以藉此肆其所欲為,是以此回之亂,政府亦甚惶恐,已頒十九條新憲法之文,蓋從此息戰,實行憲法,則革命此舉不為無益,但恐革命軍不悟,兵連禍結,則國力消耗,雖有英傑亦難為力耳。
梁啟超與湯覺頓(湯覺頓即信中所提之「荷庵」)兩人,在1911 年4 月曾應林獻堂之邀訪問臺灣,並與櫟社成員在臺中聚會賦詩。黃旭東因為這次機緣,乃有機會在大連與梁、湯兩人敘舊,交換對革命與時局的看法,梁啟超自言擔心激烈動亂與外國干涉,並不贊成革命黨所謂「種族革命」的作為。黃旭東隨後在信中還批評袁世凱,利用革命成功、清廷尚未終結之際,從中取利以遂行掌權之野心。接著,他還談到大連一地之社會狀況:
大連本一漁村,名為青泥窪,露國租借後經營成市,名為グル二―,及改隸日本,改名大連。現時商業甚盛,滿鐵本社設在此處。而此處清人惟商人及勞慟者,多由山東、天津、北京、上海、湖北等處來者,其中山東人十居八九,多獨身者。商人略有上等、中等者,而勞慟者則較吾臺乞丐相似,蓬頭垢面、破衣纏身,無屋可住,且政府設有收容所數處,以收容此等勞慟者。其屋約可六尺高,上蓋草蓆,傍以木板為壁,四壁屋上皆可透光,較吾臺乞丐之屋更不堪甚多。弟曾往觀,訝其冬季不知如何聊生耳。
上文可說是一段相當精采的大連見聞報導。此信的研究價值,在於可多方面考察臺灣人與梁啟超的互動,對晚清、民國政權更送之際的態度,對袁世凱的批判,以及大連被日本佔領後的治理情形與社會面貌等,如下階級的勞動者如乞丐,為數甚多,居住環境簡陋而惡劣。
三、陳懷澄致連橫明信片(1912 年1 月):斷髮風潮漸起
傅錫祺家藏書信,數量最多者仍屬櫟社成員之信函。目前初步清查,幾乎櫟社第一代、第二代社員,與傅錫祺曾有往來書信者至少有三十多人。其中數量尤多者,包括陳槐庭、賴紹堯、陳瑚、陳貫、林癡仙,乃至第二代的莊垂勝、葉榮鐘、林陳琅、張賴玉廉,從上百件到數十件不等。這類信件內容廣泛,從詩社活動、私人事務、友情分享、婚喪慶弔、時局批判、人事臧否,內容無所不包。以下舉陳懷澄與連橫相關之明信片二例,加以說明。
連橫於1908 年移居臺中,1909 年加入櫟社,1912 年赴中國旅遊,1930 年因發表附和總督府鴉片政策之言論而被櫟社除籍。筆者曾發表〈論連橫與櫟社之互動與決裂─兼論櫟社「抗日」屬性之再評估〉,詳論連橫與櫟社之互動經過。根據這批書信資料可知他與賴紹堯、林癡仙交情匪淺,在臺中時期寄居林家專祠。筆者又根據〈傅錫祺日記〉的相關記載判斷,連橫約1911 年7月,透過傅錫祺介紹進入臺灣新聞社任職,1912 年1 月因準備赴中國旅遊而去職7,連橫擬央請陳懷澄接任,陳懷澄因而寫這張明信片推辭。明信片正面如下:
臺中街林家專祠內
連雅堂先生
惠披
鹿港陳懷澄覆
郵戳日期是明治45 年(1912,大正元年)1 月6 日,內容是:
接示,蒙委匡助錫兄,敢不唯命是聽,奈不譯文,以是裹足。日前痴兄經來書勸往,亦以此意答之。抱歉實甚!現汝南歸家,何不懇於獻、階二兄,請其暫派汝南往助,獻、階二兄必首肯。此舉甚善,兄以為然否?大駕何日發韌耶?仙兄斷髮,弟之辮尾,自此休矣!哈哈!頃抱感風病。匆匆此覆。即侯雅堂兄健安
一月六日 弟懷澄頓首
時代轉折的見證,臺灣文學史的新發現
─傅錫祺家藏櫟社史料的學術價值
「臺灣文學研究」成為獨立的學科,時間相當短淺,臺灣文學史料的挖掘、整理與建構,乃是臺灣文學研究朝向深刻學術化不可或缺的奠基工作。近十多年來,在臺灣文學的學術範疇,不論原住民文學、母語文學、民間文學、古典文學、日治時期新文學、當代作家文學等諸多領域,不少學者、作家及其家屬、文史工作者、研究生紛紛投入這股挖掘臺灣文學史料的潮流中,提供不同程度的貢獻,出版各類專書或論文,使臺灣文學的研究不斷有新發現,產生新論述,逐步建構更堅實的研究成...
推薦序
推薦序
鉤沉史料,重建宿昔
向陽
從事臺灣古典文學研究卓然有成的廖振富教授,從1990年初期,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班階段,就已潛心於臺灣文學研究,1996年他以論文《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獲得博士學位,開展了此後他在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的輿圖,相關研究成果也備受學界重視與推崇。他的研究方向,大抵以博士階段的成果為基礎,開枝散葉,為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開拓了新的領域,尤其是他所致力的日治時期臺灣新、舊知識份子的文學行誼與思想的研究,更是特具創見。他以嚴謹的治學態度,篤實的治學方法,挖掘一手史料,進行細密分析與探討,且能以嶄新的視野,提出有力的論點,讓史料與論述可以互相詮釋,從而廓清了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子在啟蒙年代中的思維,提供給研究者據以對話的清晰圖式。
這二十年來,廖振富教授所撰相關論述甚多,其中備受矚目者,如《櫟社研究新論》(臺北:國立編譯館出版,2006年)、《臺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臺北:國立編譯館出版,2007年),都是獲得國立編譯館審查獎勵出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獎勵臺灣文獻書刊出版」優選獎勵的重要論述;他也曾參與國立臺灣文學館《全臺詩》的編撰,另又為臺文館所出《臺灣古典作家精選集》系列編選《林幼春集》、《林癡仙集》、《在臺日人漢詩文集》等三冊,2013年由臺大出版中心出版的《蔡惠如資料彙編與研究》,更是研究蔡惠如與臺灣文化啟蒙運動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近兩年來,他更與楊翠教授合力完成《臺中文學史》(臺中:臺中市文化局,2015年),並有《追尋時代:領航者林獻堂》(臺北:遠景,2016年)之出,可見他研究之勤、著述之豐。
廖振富教授這本新著《以文學發聲:走過時代轉折的臺灣前輩文人》,正是以他二十年累積的扎實研究和學術論述為基礎,透過新出土文獻的取得與一手資料的掌握,參照日治時期臺灣社會情境與歷史脈絡,以及處身於殖民地的臺灣知識份子的苦悶、轉折、掙扎與奮鬥的內在世界的佳構。通過這本書,我們得以按圖索驥,看到這些走過時代轉折的前輩文人,如何以他們的行動與作品來回應缺乏自主性的殖民社會?如何在傳統與現代、救亡和啟蒙、殖民與自主、政治與文化的多重矛盾與煎熬之中,展現他們作為知識份子的理念和實踐。
本書共收錄七篇擲地有聲的專論,廖振富教授是研究臺灣古典詩社「櫟社」的權威。本書由傅錫祺家藏櫟社文獻開章,以他獲得傅錫祺家屬信任,所取得的大批櫟社書信、手稿及原始文獻的珍貴史料,進行論述,一方面既讓被歷史塵埃所掩的櫟社史料出土,提供給學界參考引用,展現了研究者的無私態度;另一方面也更清楚地呈現櫟社從日治到戰後的興衰起伏,見證了臺灣文人在歷史轉折過程的心路歷程。本書由此發端,從而也有揭開全書各篇所述論旨序幕的用意吧。
也正因為掌握了新出土的文獻,包括〈傅錫祺日記〉、書信、名簿等,以及林莊生等提供的史料,本書的論證因而更加可稽可信。在〈印刷、鐵路交通與文學社群─日治前期新興文學傳播網路的形成〉文中,我們看到著者細密稽考這些文獻,重建以櫟社為中心的日治時期臺灣傳統詩社圖譜,探究其蛻變過程,並見證其與時代緊密連結的軌跡。尤其可貴的是,這篇論述從「詩集印刷與文學傳播」和「鐵路交通與文學社群往來」的新視角切入,一開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與現代文化研究交融的取徑,為臺灣文學傳播研究開拓了融古於新的研究領域,而不止於文獻、史料的稽考。廖教授探討一個古典詩社如何在現代印刷技術與交通建設引進之後形成的文學傳播網路,更新了過去學界對古典詩社「保守、落後、封建」的刻板印象,也擴大並豐富了我們對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史/文化史的認知和視野。
廖振富教授以這兩篇論述作為全書的開頭,或許也有鋪陳歷史脈絡的深沉用意在。接下來五篇,他分別探討蔡惠如的生平與作品,朱點人、莊垂勝與岸田秋彥三人之間深刻的跨國情誼,莊垂勝詩中的時代與自我,葉榮鐘的散文創作及其文學史意義,最後收攏於林莊生致葉榮鐘信函中表露的海外臺籍知識份子的現實關照。透過這五篇同樣都建立在新出土文獻的基礎上,細密分析、印證的論述,讓我們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得以對這一群走過時代轉折的臺灣前輩文人擁有更深刻的、更親切,但也更加痛惜的認識。
從日治時期到戰後,臺灣前輩文人面對的,不只是單純的「朝代」變革和移轉,也還有隨著新舊殖民者而來的認同困惑與矛盾,以及作為文學人/文化人對於臺灣命運和前景的期待與憂心。從已經成為歷史的事實來看,這些前輩文人的種種奮鬥,無論是主張或行動,隨著他們的離去,似乎都已成灰;但是,他們的理念和實踐精神,透過本書的鉤沉與鑑照,則彰然若新,典範常在,足為今日的我們所效式。重建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家(無分新舊)在政治變動與社會變遷的大轉折過程中的真實圖像,允為本書具有重大意義的所在。
推薦序
那個時代─ 吳叡人
「在黑暗時代裡詩人何為?」
─德國詩人賀德林
(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
哲學家康德說,所有哲學工作最終都想回答三個基本問題:「我們能知道甚麼?我們應該做甚麼?我們可以希望些甚麼?」作為一個臺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面對「臺灣」這個臨界的、邊緣的場所(topos)─以及它所負載的那令人困惑、不快、乃至沉重到令人窒息的時空經驗,我常會忍不住地將這組康德哲學的問題予以歷史化,轉化成這樣具體、素樸的疑問:「關於臺灣,我們能知道些甚麼?我們應該做些甚麼?我們到底可以懷抱甚麼希望?」活在臺灣是一件拼命的事,作為一個臺灣人首先必須先和歷史搏鬥,存活下來了,我們才會有哲學。在夾縫中,在黑暗中,在稀薄的空氣中,我們首先想知道的不是形上學的命題,而是我們自己的身體與容顏,因為我們想呼吸,想要手舞足蹈,想掙扎,想移動到有光的所在,想要活下去,我們想知道該怎麼做才能活下去,而我們又可以懷抱多少希望。
還有,當我們絕望時,我們的身體與容顏又如何扭曲。
作為一個臺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我總是忍不住地想要去揣摩、想像,想像那個時代到底是甚麼樣子,活過那個時代的他們到底在期待些甚麼,在希望些甚麼,又到底被容許希望些甚麼?他們懷抱希望時的姿態是甚麼?徬徨動搖時的神情是甚麼?絕望時的姿態又是甚麼?我曾經嘗試在他們留下來的關於政治的手稿中─大多是斷簡殘篇─尋找蛛絲馬跡,然而這些壓抑、隱晦而曖昧的訊息固然顯露了他們行動的軌跡,他們作為英雄、敗者和叛徒的軌跡,卻看不清他們作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希望、徬徨、絕望的神情,他們掙扎的姿態。這是政治史與政治思想史這類理性知識的限度,我們必須仰賴另一種知識,某種能夠碰觸歷史行動者的靈魂與鼓動的心的知識,來擴張我們對那個時代與那些前輩的想像邊界。換言之,我們必須超越思想史,進入精神史的層次,而為了進入精神史,我們不可避免地必須行經文學史的場域。
廖振富教授這冊《以文學發聲:走過時代轉折的台灣前輩文人》,就是一部引領我們走進臺灣精神史深處的文學史勞作。他在過往櫟社研究的堅實基礎上,辛勤發掘新史料,拉長時間軸,以工筆細緻而細膩地重建了從日治到戰後國民黨統治時期臺灣中部三個世代知識份子的精神歷程。閱讀這冊精神史,這群臺灣知識分子在那個漫長的黑暗時代裡希望、絕望與徬徨交替與重疊的姿態與神情,清晰而生動地浮現在我們的心頭,讓我們彷彿與這些被歷史翻弄,但又不甘於被歷史翻弄的前輩們一起走過了這段困頓的荊棘之路。
櫟社第一代「吾學非世用,是為棄材,心若死灰,是為朽木」的自況是這段精神史的複雜原型─,正如同櫟木辯證的「無用之用」,這群棄民也在絕望之中留存希望,遁世而暗藏用世之心,以傳統追求現代─因為古典漢詩是他們用以言志,甚至行動的主要媒介。在其後不同時期的歷史條件下,這個辯證、複雜、重層的精神面貌的各個不同面向與不同層次被分別凸顯,形成了這個中部知識社群精神史跌宕起伏的縱軸。在蔡惠如「一生最愛多才智,恨無鴻鵠高飛翔。腳力翻雲,蹉跌尋常事」這段文字之中,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時代臺灣知識分子的豪氣干雲,躍然紙上。莊垂勝在太平洋戰爭時寫下「等閒莫道非時用,古幹凌空一核生」,表達了不改其志,延續傳統的志節,一系列的田園詩則隱晦表達了對日本戰爭動員的堅決抵抗。然而同一作者卻在二二八事件遇險後,對祖國幻滅,真正歸隱田園。閱讀他的晚年傑作「一爐湯正沸,山月度窗來」時,我不由聯想起吉田兼好的《徒然草》第五段那句深刻的話語:
「…以無罪之身而思一望配所之月」
於是我這個完全的古典詩素人會忍不住突發奇想:莊垂勝的《徒然吟草》(還有陳虛谷晚年的「來去無人知,但見花開落」),難道不是在向兼好的「無常觀」致意嗎?對祖國幻滅之後,這群知識分子的精神史之路終於已經走到了「無念無想」的諦觀境地了嗎?
當然歷史並未停留在這個時點,台中知識分子也沒有因此全面終老隱遁,新的時間醞釀著新的不滿與勇氣,於是我們會再看到與莊垂勝同世代的葉榮鐘在六零年代以散文與述史再起,精神史的軌跡從谷底經歷了一次憤怒的跳躍與復甦,我們甚至還讀到了詩人少奇晚年的金剛怒目:
「迎狼送虎一番新,浪說同胞骨肉親。軟騙強施雖有異,後先媲美是愚民。」
最終,是台中知識分子社群的第三代─莊垂勝的長子林莊生,溫柔地承接了他父祖輩的所有絕望中的希望,遁世中的用世,抵抗意志的萌生與摧折,無常的諦觀,憤怒的反擊,安靜細膩地梳理這一切交錯重疊的身影與姿態,然後把這些故事再娓娓道來,寫成幾冊書,彷彿像栽種幾株百年後的大樹,有用之用的大樹,用來懷念,用來記憶,然後轉身,走向一個新的時代─或者說走回了終於體現了台中知識人百年前的初心,「天心自古從民意」的時代,從那裏,找到了下一階段台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起點。
在黑暗時代裡,希望的根據是甚麼?希望的第一個根據,是記憶。從記憶中產生了意志,即使毫無根據也要懷抱希望,也要活下去的意志,朝向希望的意志。黑暗時代裡詩人何為?詩人見證黑暗,賦予意義。詩史作者紀錄詩人的見證,賦予詩的見證以新的意義,也就是記憶。詩的歷史,就是記憶的創造,就是意志的泉源,像臺灣人這樣,連單純地活著都得要拼命的,夾縫中的弱小民族的,朝向希望的意志。
(2017.10.19 草山)
推薦序
鉤沉史料,重建宿昔
向陽
從事臺灣古典文學研究卓然有成的廖振富教授,從1990年初期,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班階段,就已潛心於臺灣文學研究,1996年他以論文《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獲得博士學位,開展了此後他在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的輿圖,相關研究成果也備受學界重視與推崇。他的研究方向,大抵以博士階段的成果為基礎,開枝散葉,為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開拓了新的領域,尤其是他所致力的日治時期臺灣新、舊知識份子的文學行誼與思想的研究,更是特具創見。他以嚴謹的治學態度,篤實的治學方法,挖掘...
作者序
在出版市場萎縮的當今,玉山社願意出版這本學術氣味濃厚、主題嚴肅的專書,我既深懷感謝,也略感不安,一方面擔心銷路有限,增加出版社的困存壓力﹔另一方面也不免懷疑,有多少讀者對這種書有興趣?
值得慶幸的是,在本書校對過程中,重新瀏覽這些文章,細細體會臺灣前輩文人走過的艱困時代,以及他們內心世界的失落與堅持、苦悶與奮鬥、糾結與反思,個人仍深受震動。如果能讓更多當代人認識前輩文人的思想與作品,並作為當代社會的鑑照,本書或許仍有出版的價值吧!
本書出版緣起,是2015年初玉山社發行人魏淑貞女士的邀稿。當時她約我見面,討論重新出版林莊生《懷樹又懷人》事宜,進而表示希望也能出版我的著作,她的賞識真是讓我受寵若驚。不過這兩年多的時間,個人因工作變動需適應摸索,其間又應台中市文化局之邀,抽空撰寫《追尋時代:領航者林獻堂》新書,以致拖延至今,非常感謝魏淑貞女士的鼓勵與包容。而負責編輯本書的邱芊樺小姐,以無比耐心協助內容的排版修訂,也提供不少專業意見,乃至於書名的擬定,經多次討論後,我欣然接受編輯群的建議,以《以文學發聲:走過時代轉折的臺灣前輩文人》,取代先前構思的《脫困與突圍:近代台灣文化人的文學視野與時代反思》。
本書收錄7篇論文,較早的兩篇分別討論葉榮鐘散文與莊垂勝的漢詩,分別在收錄在2007年出版的兩本學術會議論文集,距今恰好10年。論蔡惠如一篇,是為臺大出版社主編《蔡惠如資料彙編與研究》一書而寫,曾發表於2013年的《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7期。其餘四篇側重新出土文獻史料的解析,都是應任職於臺灣文學館的許素蘭老師邀稿,在2012─2016年間,陸續發表在他主編的《臺灣文學史料集刊》,因此許素蘭老師可說是催生本書的主要貢獻者之一。去年9月起我有幸成為他的同事,更是奇妙的因緣,容我致上誠摯的謝意。而同樣任職於臺灣文學館的許惠玟研究員,全力支持相關文物的典藏與研究,也是催生本書的另一幕後功臣。
回想20多年來走上台灣文學研究的旅程,完全是出自「尋找生命根源」的初心,雖然甘苦備嘗,但鑽研越深,越發現堂廡之大。由於研究機緣,我獲得研究對象家屬的信任,陸續接觸豐富的一手資料。而透過「會說話的文獻」,百餘年來台灣前輩文人的音容笑貌,及其幽微心境,也就更清晰地浮現眼前。藉此機會,我也要分別感謝多年來提供我珍貴資料的後代家屬,包括林幼春長孫林中堅先生、傅錫祺家屬傅紅蓮女士及羅琬琳、莊垂勝長子林莊生先生及其夫人郭孋容女士、葉榮鐘次子葉蔚南先生。若非他們的信賴與無私,我無法展開這些研究。
本書收錄極多信函、手稿、照片等珍貴圖像,堪稱一大特色,從日治時期櫟社詩人以小楷寫的明信片,到戰後初期朱點人寄往日本名古屋的信,以迄1970年代林莊生從美國寄回臺灣的航空信,書信本身就是時代演變的軌跡與見證。
書中引用的第一手文獻,最早大約是1910年代的櫟社史料,延伸到戰後,距今最近的是1974年林莊生寫給葉榮鐘的信函,前後約60多年間。這是台灣多重轉折的時代,從為期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到戰後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與長期戒嚴,這些前輩文人走過激烈動盪的年代,有人甚至付出犧牲自由與生命的慘痛代價。其事蹟與作品在歷史時空中縱橫交錯,點燃希望的微光,讓我們深刻體悟:他們在黑暗中有所堅持、在挫敗中不放棄希望的曲折心路歷程,做為後輩的我們,更沒有理由對未來感到悲觀。
本書從櫟社新出土文獻出發,進而拓展到蔡惠如、朱點人、莊垂勝、葉榮鐘,及日籍學者岸田秋彥等人的個案分析。就討論的文本而言,書信是最大宗,尤其傅錫祺家屬珍藏大量的櫟社詩人往來信札,以及莊垂勝與林莊生父子的相關書信,這些不同時空背景下的文人對話,讓我們能對歷史情境與時代氛圍,產生「今昔相融」的一體感,堪稱難以取代的珍貴文本。另外,本書也將莊垂勝的古典詩與葉榮鐘的白話散文,放在時代座標中進行詳細解讀,足以見證文類不分新舊,都是作者思想行誼與生命人格的映現。
為了替自己壯膽,我特別邀請向陽老師與吳叡人兩位老師為本書寫序,這是我的頭一遭,主要是出自對他們的敬重。而他們雖然都熱情澎湃,活力充沛,卻因工作量極大而長期過度勞累。向陽老師在10月17日出席臺灣文化日的記者會之後,隨即熬夜寫序﹔吳叡人老師則在剛結束兩度出國行程,身體微恙之際,接受我的緊急請託,都讓我內心深感不安。巧合的是,10月15日我們三人曾共同出席在國家圖書館舉行的「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文學家論壇」座談會(由臺灣文學學會主辦),此一機緣想來頗具象徵意義。當天由向陽老師主持,吳叡人老師壓軸的慷慨發言,尤其讓在場聆聽者同感振奮,也與本書關切的台灣前途與臺灣文化發展,有巧妙的呼應。
2016年9月起,我到國立臺灣文學館任職,沐浴在南臺灣的自在與活力中,同時也展開四處行走的生涯。轉換跑道實踐理想之餘,還能持續筆耕,其動力雖然是來自自我鞭策的初衷,更是因為內人的長期付出,為我構築了家庭的堅固城堡始能臻此,道謝永不嫌晚,是為誌。
廖振富寫於臺南 國立臺灣文學館
2017年10月19日
在出版市場萎縮的當今,玉山社願意出版這本學術氣味濃厚、主題嚴肅的專書,我既深懷感謝,也略感不安,一方面擔心銷路有限,增加出版社的困存壓力﹔另一方面也不免懷疑,有多少讀者對這種書有興趣?
值得慶幸的是,在本書校對過程中,重新瀏覽這些文章,細細體會臺灣前輩文人走過的艱困時代,以及他們內心世界的失落與堅持、苦悶與奮鬥、糾結與反思,個人仍深受震動。如果能讓更多當代人認識前輩文人的思想與作品,並作為當代社會的鑑照,本書或許仍有出版的價值吧!
本書出版緣起,是2015年初玉山社發行人魏淑貞女士的邀稿。當時她約我...
目錄
推薦序 鉤沉史料,重建宿昔 向陽
推薦序 那個時代─ 吳叡人
自序
時代轉折的見證,臺灣文學史料的新發現─傅錫祺家藏櫟社文獻的學術價值
印刷、鐵路交通與文學社群─日治前期新興文學傳播網路的形成
從「富家公子」到「啟蒙先鋒」─蔡惠如生平與作品新論
動亂時代的跨國情誼─從朱點人致莊垂勝、岸田秋彥信函談起
從反殖思想到戰後的退隱意識─莊垂勝詩中的時代與自我
建構在地文化的旗手─論葉榮鐘60 年代的散文創作及其文學史意義
一個海外臺籍知識份子的現實關照─林莊生致葉榮鐘信函初探(1961─1976)
推薦序 鉤沉史料,重建宿昔 向陽
推薦序 那個時代─ 吳叡人
自序
時代轉折的見證,臺灣文學史料的新發現─傅錫祺家藏櫟社文獻的學術價值
印刷、鐵路交通與文學社群─日治前期新興文學傳播網路的形成
從「富家公子」到「啟蒙先鋒」─蔡惠如生平與作品新論
動亂時代的跨國情誼─從朱點人致莊垂勝、岸田秋彥信函談起
從反殖思想到戰後的退隱意識─莊垂勝詩中的時代與自我
建構在地文化的旗手─論葉榮鐘60 年代的散文創作及其文學史意義
一個海外臺籍知識份子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