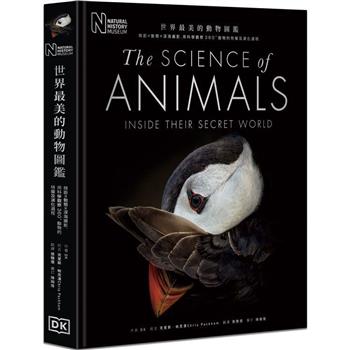導論:紅磚與白石交疊而成的西洋建築史
古羅馬建築師維特魯威在《建築十書》中所述的三原則:「堅固、適用、美觀」(firmitas,utilitas,venustas),千百年來被西方建築師奉為圭臬,而石頭的堅固和富雕琢性,正是達成這些目標的理想建材。凡是意欲名留青史的建築師,莫不努力爭取設計能使用石材建造的作品傳世;而服務神權和王權的永恆象徵建物也必為石造,所以說西方建築史是一部石頭打造的史書並不為過。建築師設計、建造石造作品需要努力爭取,乃因石材的特點之一即為昂貴的開採及運輸成本。19世紀末,日本政權來到臺灣,因都市計劃等理由拆除清代臺北府城的城牆,也並未浪費棄置,而是將開採自臺北盆地各處的城牆石轉用於其他建設,如圍牆、建築基座、下水道等,可見石材的珍貴與得來不易。
歐洲在16世紀宗教改革後,新教流行地區的天主教教義遭到挑戰與質疑的社會風氣,連帶影響以往教會集中資源榮耀上帝的的行為。新教教義認為,聖經而非教會才是基督信仰的最高權威,並鼓勵所有信徒皆祭司,也就是非聖職人員的信徒,在禮儀上積極共同參與,同心合一來敬拜神。如此一來教會主導儀式的重要性大減,而需要聚集信眾財力,耗費百年方能建成的石造大教堂,也就更難有機會產生。19世紀的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則認為,新教鼓勵個人財富積累,標榜世俗的成功可以做為個人超度的標誌。而私人商家為了快速取得可營業生財的使用空間,比起石材取得門檻更低的磚造建築,便在新教國家如北歐、英國、德國和法蘭德斯地區的商業城市中展開流行。
人類使用磚的歷史非常古老,目前已知可上溯西元7000年前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而在西方建築史中,同時具有結構與外觀功能,在材料生產、工法與建築形式關係上具現代意義而延續至今的磚造建築,則是從12世紀起,因為地域缺乏石材,而於中歐平原(North European Plain)開始流行。
位於該區域內的漢薩同盟(Hanse),即有許多以磚代替石頭建造,卻也能納入整個歐洲建築風格趨勢的公共建築。到了16世紀,因應興起的市場經濟貿易活動,磚造建築則以能夠快速取得建材的特性,被更廣泛的運用於世俗的商業建築。
從一些早期的案例觀察磚石兩種材料的混構,可找出至少兩種不同需求的起因。其一是結構需求:如5世紀時修築的君士坦丁堡城牆(Wallsof Constantinople),外表採用石灰岩塊,城牆核心則是以石灰及碎磚壓成的灰泥。並以大約7至11條,厚約40公分的磚帶貫穿聯繫,透過不同材質間抗剪強度差異的摩擦力來鞏固結構,增強城牆對地震的抵抗力。
其二則是純粹美感的考量,如13世紀建於保加利亞內塞伯爾,屬於拜占庭晚期風格的潘特克拉特教堂(Church of Christ Pantocrator, Nesebar),在以石砌為主的構造體中,圖樣繁複的磚橫帶排列便為無結構作用的裝飾性質。
磚材雖較石材易於生產取得,材質的物理特性卻不如石頭堅固。因每塊磚的單位體積小,所承受的抗壓強度大,但抗拉、抗彎和抗剪強度卻都較低。尤其是在建築物的轉角與門窗開口處,由於應力集中更容易造成破壞,而為了強化磚構造,人類逐漸學會在容易產生裂損的部位使用石材增加結構強度。
其實即便是全石造的建築,也會在脆弱處使用更為堅硬的石材,如法國布列塔尼半島和義大利山城石造的風土建築,為了抗震而在轉角或側牆中脊以及開窗處使用較大塊的石材。爾後逐漸演變成西洋建築的語彙。而磚和石的色彩對比大,搭配起來會形成令人印象深刻的「框邊」視覺效果,也由色彩的差異,從外部即可辨別樓層分隔或空間開口。
西洋建築為製造整體作品的雕塑立體感,以及強調入口和壁體的主從關係,常以凹凸量體排列分割與組合表現立面,此一情形至文藝復興後期的矯飾主義更為明顯。過於龐大的建築量體,則有可能因為瑣碎的分割而造成視覺渙散,砌石堆疊的水平方向感便產生統整量體的捆綁效果。而模仿砌石建築的磚石混合構造也承襲此種美學,且能夠降低石造成本,滿足建築師對於熟悉形式的襲用,符合宗教改革後中產階級興起的大量營造需求。
到了1877年,日本正值脫亞入歐的明治維新時期,擁有英國建築師伯吉斯(William Burges)事務所工作資歷的孔德(Josiah Conder),受到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RIBA)推薦,和日本政府簽訂五年工作約,受託擔任工部省營繕局建設顧問,以及工部大學校,也就是後來的東京帝國大學工學部造家學科教師,開啟日本建築界有系統學習西方建築體系的大門。
日本第一代建築師辰野金吾即為孔德首屆學生之一,大學畢業後取得優秀畢業成績的獎學金,以老師故鄉英國做為遊學目的地,1880年進入孔德在倫敦大學的研究室,並繼續循著孔德的腳步,進入伯吉斯的事務所實習。當時英國正值維多利亞時代鼎盛之際,建築活動為了襯托國力和貿易的壯盛,進入歷史主義的最高潮,並且因為近代營造技術的突破,各種風格樣式的語彙不再受到結構需求侷限,成為建築師隨意運用的素材。
辰野金吾躬逢其盛,結束英國遊學後,又在法國和義大利待了一年,造訪歐洲建築名作,進行細部和平面的素描練習,如同歐洲年輕人的壯遊(Grand Tour)一般,徹底浸淫在世界大戰前,歐洲發展至頂峰的理性、科技、文明和帝國光輝,並將經驗帶回日本,再由辰野的學生赴臺任職時帶來臺灣。在日本建築現代化的歷程中,辰野金吾運用磚石混構手法的作品最為著名,如東京車站、大阪公會堂、日本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九州分支店等皆為名作,並因其廣泛的影響力及其後輩的繼承而被稱為「辰野式」,對臺灣近代建築風貌產生深遠影響。
然而臺灣卻早在大航海時代,經由荷蘭東印度公司傳入製磚技術,使得紅磚成為建築地景上的特色;1882年馬偕在淡水興建理學堂大書院,即藉由紅磚模仿西方空間形式與滿足使用需求,並創造與臺灣民居氛圍相近的近代校園空間。日本時代系統性引入西洋建築形式,地方匠師營造體系也無縫接軌使用原已熟悉的材料與技術,滿足新時代流行的風格。
進入日本時代,1901年落成的第二代磚造臺北車站,做為島都的門戶意象,來訪者進出城皆可看見這座由野村一郎和福田東吾設計的精品,與車站對面由松崎萬長設計,於1908年的落成臺灣鐵道飯店,共譜壯盛華麗的建築饗宴,後站則有同為磚造的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菸草工場。紅磚與白石相間交錯所表現出的商業氣氛,以及帶飾水平流動的視覺效果,與川流不息的車站、旅館、工廠等人來人往和運輸物流非常契合。
除了臺北,由森山松之助設計的臺南郵便局、總督府專賣局等作品,皆可見到紅白相間帶飾被大量運用。而使用此種風格最為頻繁的近藤十郎,也在臺灣日日新報社、新起街市場、基隆郵便局、臺北醫院等作品中展現。爾後風格鮮明的辰野式被持續傳播,在非由總督府技師營造的各地公共建築甚至民宅建物中開枝散葉,如臺灣銀行嘉義支店、高雄劇場等。
而臺灣因較為缺乏石材,多以灰泥、洗石子與面磚等材料代替石材顏色及質感,與紅磚交錯排列於建築皮層。如臺灣日日新報社初落成時只有兩層樓,後增建至第三層,但原外牆帶飾卻在增建後消失,可見帶飾的設計由於無關構造可任意增減。
原本即以紅磚為主要建材的傳統合院,在外牆加入灰白色仿石材帶飾後,便可完成外觀的西洋現代化。如桃園楊梅道東堂玉明屋、屏東萬巒五溝水劉氏觀海山房和臺南後壁菁寮黃宅等。鄉間民宅雖然多是基地寬廣的矮建築,但也有附庸風雅,可登高望遠將景色盡收眼底的高層樓房,如嘉義大林陳瑞祥宅、嘉義民雄陳實華宅,在這兩棟住宅作品中也皆能看到辰野式紅白相間的蹤影。
嘉義聞人許世賢的夫家:溪東張早宅,以及溪西曾長宅,兩案相距不遠,皆為三開間兩層樓房,中有泥塑山牆,由於兩家關係密切,推測可能為同一匠師的作品。此外醫院建築也時常轉化材質與顏色,將原本應為與灰白帶飾交錯的紅磚,更換為象徵醫院文明與衛生的白色磁磚,如臺北大稻埕仁安醫院、艋舺朝北醫院、宜蘭羅東嘉普醫院及臺南下營文貴醫院等。
日本時代由官方營繕體系將西洋建築系統性移植到臺灣,初期公共工程多由具有成熟組織的營造包商承攬,對於本就相當熟悉磚造的臺灣匠師營造體系來說,西洋建築風格是日本傳來具有文明開化意味的象徵,其形式和表現等知識門檻掌握在官方建築設計者手中。大量運用於官方建設的西洋建築特徵,代表的是官方優勢文明所闡釋的正統符碼,本島仕紳依樣畫葫蘆,則等同於品味受到主流認同。
而長久以來的樣式模仿,除了民間仕紳透過營造彰顯自身品味,匠師也沒有放棄原創及融合不同文化表現的機會,在西洋建築內加入臺灣屋主偏好的傳統吉祥語彙。在鄉里間也時有所聞「這棟樓仔厝和總督府是同款建築師蓋的」的鄉野傳言,讓地方人士津津樂道, 雖然可能並非事實,但也反映了民間認可官方建築品質的嚮往心情。
多年來西洋建築成為帝國主義留在臺灣的獨特印記,至今也象徵著對於美好生活的憧憬。綜觀數十年來的演變,此種因政權強勢導入,卻在本地展現特有風貌的文化交流結果,既是西洋建築變化萬千、適應能力極強的特質反映,也體現臺灣複雜且豐富的文化涵構,以及強韌又具包容性的生命力。
經過日本人再現於臺灣的西方建築,與歐洲原版建築的異同之處,至今仍是全球化與在地化等題目樂於探討的議題。本書試圖顛覆文化單向傳播造成的交流,模糊同時期的地域分野,組合起歐洲與臺灣的近代化建築與街景,透過建築風格形式的比較和對話,定位臺灣建築在世界脈絡中的角色。也試圖思考今日看待這些帝國主義時代文化資產的視角與當年建造時有何不同?或許能夠發現自己與這塊土地上前輩對於理想國度的憧憬仍相去不遠。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福爾摩沙的西洋建築想像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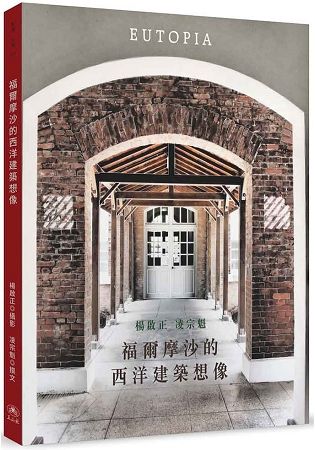 |
福爾摩沙的西洋建築想像 作者:楊啟正、凌宗魁 出版社: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8-0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福爾摩沙的西洋建築想像
日本時代,人們逐漸對西化、現代化產生了嚮往與追尋。在官方的主導下,西洋建築形式逐漸在臺灣發展。政府官舍、火車站、郵便局、銀行、洋式街屋……,充滿異國風情的紅磚、石柱、尖塔和雕飾成為日常風景,不僅改變了市容景觀,也象徵令人憧憬的理想生活。細究這些建築,除了原本固有的形式,還有許多展現出在地性格的細節。
從荷蘭時代開始,臺灣的建築匠師開始模仿西方的建築技法和空間運用。到了日本時代,地方匠師的營造體系已經能用熟悉的材料與技術,打造出符合新時代流行的風格。這些出現於臺灣的西洋建築,與歐洲原版建築的比較,一直都是全球化與在地化研究樂於探討的議題。
透過相機和文字,建築專業出身的兩位作者試圖顛覆文化單向傳播造成的交流。模糊同時期的地域區別,將歐洲與臺灣的近代化建築與街景組合起來,經由風格形式的比較和對話,進一步思考,我們在今日看待這些西洋建築的角度,與當年建造時有什麼不同,並且定位臺灣建築在世界脈絡中的角色。
本書特色:
◎從日本時代開始,逐漸在臺灣各地建起的西洋建築,大幅改變了生活景觀。
◎富有權威感、具有嚴謹外觀的公共建築;街屋商店中繁榮、活潑的建築表現;西洋宗教建築所帶來的信仰感受……透過這些照片,可以看到臺灣歷史中文化傳播的足跡,以及臺灣社會所憧憬和嚮往的理想生活。
◎這些西洋建築,不僅是有形的物質資產,也是臺灣對於現代化的想像與實踐。
◎透過臺灣與比利時兩地建築物的對照,除了從相同之處看到臺灣與世界的關聯,也能從相異的地方看到在地的特色與轉化。
◎回顧這些建築在建造之時的理念和時代意義,也有助於進一步思考,對於當代的我們來說,這些建築除了文資價值以外,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意義與價值?
◎全書150多張全彩照片,以功能將建築區分為六類,帶領讀者一遊臺灣與比利時的西洋建築風光。
作者簡介:
楊啟正‧攝影
臺南人,現居高雄市。
東海大學建築系、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畢業,比利時魯汶大學都市與策略規劃學碩士、人類居住環境學碩士,主要學術研究方向為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空間體系構成,著有《The Modernization, Reorganization & Control of the Taiwanese City: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Tainan City (1895-1945)》、《A Research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atial Planning in Tainan City during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1895-1915)》等專論。
FB專頁:facebook.com/MAP1MAP
凌宗魁‧撰文
現職為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古蹟菜鳥學徒,不想被稱為文化恐怖份子,只想和大家分享有趣的歷史空間故事,相信建築與空間形貌反映所處社會的健康情形、人民信仰、價值觀和精神狀態。期許自己和臺灣人一起努力成長,發現自身原有的美好環境品質,立足於對過去的理解放眼未來,透過建築認識島嶼在每個時代與世界的各種連結,對歷史保持開闊眼界與包容態度,對前途未明的土地環境懷抱永不放棄的希望。
TOP
章節試閱
導論:紅磚與白石交疊而成的西洋建築史
古羅馬建築師維特魯威在《建築十書》中所述的三原則:「堅固、適用、美觀」(firmitas,utilitas,venustas),千百年來被西方建築師奉為圭臬,而石頭的堅固和富雕琢性,正是達成這些目標的理想建材。凡是意欲名留青史的建築師,莫不努力爭取設計能使用石材建造的作品傳世;而服務神權和王權的永恆象徵建物也必為石造,所以說西方建築史是一部石頭打造的史書並不為過。建築師設計、建造石造作品需要努力爭取,乃因石材的特點之一即為昂貴的開採及運輸成本。19世紀末,日本政權來到臺灣,因都市計劃等...
古羅馬建築師維特魯威在《建築十書》中所述的三原則:「堅固、適用、美觀」(firmitas,utilitas,venustas),千百年來被西方建築師奉為圭臬,而石頭的堅固和富雕琢性,正是達成這些目標的理想建材。凡是意欲名留青史的建築師,莫不努力爭取設計能使用石材建造的作品傳世;而服務神權和王權的永恆象徵建物也必為石造,所以說西方建築史是一部石頭打造的史書並不為過。建築師設計、建造石造作品需要努力爭取,乃因石材的特點之一即為昂貴的開採及運輸成本。19世紀末,日本政權來到臺灣,因都市計劃等...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臺灣的城市,不好看,晚上倒還可以。
很多人這樣覺得。
然而,
真是如此嗎?
仔細尋找,
便可以發現,
自19世紀末以至於1950、1960年代,
曾經有著無數華美而精彩的建築作品,
以西洋趣味之姿,
散布在臺灣各地的都市、城鎮、鄉間。
即便許多精品已消逝在時間洪流中,
不可復返,
令人惋惜,
然而正因為如此,
許許多多當下依然靜立在一隅的逸品,
更顯彌足珍貴。
這些帶著歐洲表情或點綴的建築物,
過去是乘載著人們對於理想國度嚮往的具體表徵,
現在則是值得珍視而亟待守護的重要資產。
謹以此書,
紀念那個年代,...
很多人這樣覺得。
然而,
真是如此嗎?
仔細尋找,
便可以發現,
自19世紀末以至於1950、1960年代,
曾經有著無數華美而精彩的建築作品,
以西洋趣味之姿,
散布在臺灣各地的都市、城鎮、鄉間。
即便許多精品已消逝在時間洪流中,
不可復返,
令人惋惜,
然而正因為如此,
許許多多當下依然靜立在一隅的逸品,
更顯彌足珍貴。
這些帶著歐洲表情或點綴的建築物,
過去是乘載著人們對於理想國度嚮往的具體表徵,
現在則是值得珍視而亟待守護的重要資產。
謹以此書,
紀念那個年代,...
»看全部
TOP
目錄
序言
導論──紅磚與白石交疊而成的西洋建築史
公共建築──國家力量的具體展現
宅邸莊園──人生成就的終極積累
宗教機構──以宗教儀式宣示文明開化
街屋商店──具體而微的風格戰場
醫療慈善──邁向康復的集合村落
產業遺跡──人類文明進程的註腳
後記
導論──紅磚與白石交疊而成的西洋建築史
公共建築──國家力量的具體展現
宅邸莊園──人生成就的終極積累
宗教機構──以宗教儀式宣示文明開化
街屋商店──具體而微的風格戰場
醫療慈善──邁向康復的集合村落
產業遺跡──人類文明進程的註腳
後記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楊啟正、凌宗魁
- 出版社: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8-05 ISBN/ISSN:978986294206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60頁 開數:19cm×24cm
- 類別: 中文書> 建築設計> 各式建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