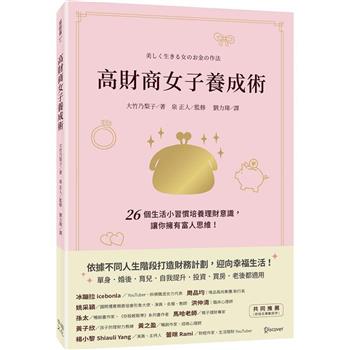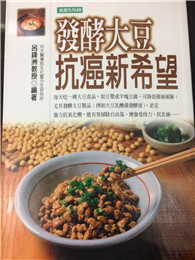無常和不斷變動
是所有事物的本質,
包括詩。
是所有事物的本質,
包括詩。
詩人以詩的幽光燭火,
去照亮整著灰濁,甚至黑暗的社會現實,
以詩的形式載體,傳遞給世間一絲溫暖與情意。
詩人寫詩,必起源於對現實人間的浪漫情懷,
且認肯文學不死的決心,才能投注畢生的熱情於詩的創作上。
但,它不是耽溺甜美的「大二女生讀物」,
而是能夠揭示現實中「事」與「物」的內在本質。
曾貴海面對混濁的社會現象,以詩的「思考的纖維」,
探觸到現實的角落,敏銳地揭露人生存在的真諦。
因此,在漫漫寫作歷程中,從《波濤從來沒有停止過》的最前、最後詩作相互呼應,
推知曾貴海在此詩選,仍本著他對自然萬物的關照吟咏、內在心緒的感悟騷動;
以及他一貫對社會現實、族群等面向,幅射而出的深切凝視與省思。
「曾貴海第二階段中短詩選集的出版,證實詩人不斷前行的續航力與創造力。」--阮美慧 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本書特色
詩人寫詩,必起源於對現實人間的浪漫情懷,且認肯文學不死的決心,才能投注畢生的熱情於詩的創作上。
能夠揭示現實中「事」與「物」的內在本質。曾貴海面對混濁的社會現象,以詩的「思考的纖維」,探觸到現實的角落,敏銳地揭露人生存在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