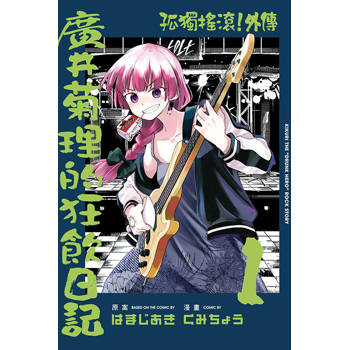本書特色
本書收錄七篇獨立論文,充分表達作者對台灣少年司法的懇求、論證、期盼。作者先以簡單的文字闡述表達對司法實務界的懇求,從心理與道德決斷這兩件事情形構出對於少年司法的想像,企圖在建構與解構中反覆驗證,中間提出台灣新少年司法與矯治制度的經驗與展望報告,最後以實務操作要點的建議作結尾,並加入處理少年事件守密原則,作為本書的補充。適合正在研究或是研習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研究者與學生閱讀。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少年事件處理法論文集:一部以贖罪心理與道德決斷形塑出來的法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23 |
法政學群 |
$ 447 |
政治/法律/軍事 |
$ 447 |
社會人文 |
$ 460 |
中文書 |
$ 461 |
高等教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少年事件處理法論文集:一部以贖罪心理與道德決斷形塑出來的法律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李茂生
學歷:
日本一橋大學法學博士
現職: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專任教授
研究領域:
少年事件處理法、監獄學、刑法解釋學、犯罪學及刑事政策
著作:
《法律與生活》、《權力、主體與刑事法》
翻譯:
《犯罪與刑罰》貝加利亞(Cesare Beccaria)著
李茂生
學歷:
日本一橋大學法學博士
現職: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專任教授
研究領域:
少年事件處理法、監獄學、刑法解釋學、犯罪學及刑事政策
著作:
《法律與生活》、《權力、主體與刑事法》
翻譯:
《犯罪與刑罰》貝加利亞(Cesare Beccaria)著
目錄
序言 i
導言 001
第一章 推動少年司法的心理深層動機──愛、憐憫與贖罪間的交錯 005
第二章 後現代犯罪學的啟示與少年事件處理法 023
第三章 新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立法基本策略──後現代法秩序序說 095
第四章 少年犯罪的預防與矯治制度的批判──一個系統論的考察 189
第五章 台灣新少年司法與矯治制度實施十年的經驗與展望 291
第六章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的檢討與展望──以刑事司法與福利行政兩系統的交錯為論點 321
第七章 處理少年事件守密原則之探討 357
導言 001
第一章 推動少年司法的心理深層動機──愛、憐憫與贖罪間的交錯 005
第二章 後現代犯罪學的啟示與少年事件處理法 023
第三章 新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立法基本策略──後現代法秩序序說 095
第四章 少年犯罪的預防與矯治制度的批判──一個系統論的考察 189
第五章 台灣新少年司法與矯治制度實施十年的經驗與展望 291
第六章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的檢討與展望──以刑事司法與福利行政兩系統的交錯為論點 321
第七章 處理少年事件守密原則之探討 357
序
序言
民國九十一年年初某個寒冷又下著小雨的星期天,小黑用著牠還能夠動的三條腿,一瘸一瘸地走到了新店一個小山坡上的社區。瘦瘦的身軀、淋溼的皮毛,在牠身體的左側還可以看到已經結疤的暗紅色傷痕。社區警衛偶而會將吃剩的便當給牠,而且警衛室的旁邊還有一個小池塘可以喝水,於是牠就住了下來。
我太太看牠可憐,於是開始間歇地弄些狗豆豆加雞肝給牠補身體。個把個月後,小黑的腿傷好了,細細的腿雖然還是有點瘸,但是已經可以用牠的三條半隻腿開始奔跑。我太太每晚遛狗的時候,都會帶一些食物出去,只要有看到小黑,總會分一點給牠。小黑警戒心很高,不喜歡靠近人,移動牠的食物時還會對人齜牙咧嘴地嗚嗚叫。不過牠對於第一次給牠食物的警衛,倒還頗親近的,只要那位先生值班,牠都會靜靜地躺在警衛室巡邏車的旁邊。
暑假到了,小黑日益活潑。晚上十一點警衛用巡邏車開始繞行社區的時候,如果有看到小黑尾隨在車子後面奮力地「巡邏」,我和我太太都會會心一笑,今晚又是那位警衛在值班。
開學的第一天九月十六日晚上,中秋節快到了,我太太準備了一些雞胸肉,想要讓社區內的流浪犬們補一補,小黃、賤狗大家都吃了,但是找來找去就是找不到小黑。我看到當晚的警衛就是那位經常餵食小黑的先生,於是走過去詢問小黑的蹤影。不料那名警衛回答說,昨晚深夜就把小黑圈起來,丟到中興路上了。他說,小黑不僅是會追摩托車,還會去咬騎摩托車的人,而且只要他去巡邏,小黑一定會跟,結果巡邏車所到之處,社區內其他家犬都會跟著狂吠,吵到社區安寧,大家抱怨連連,所以不得已只好把小黑弄離開這個社區。他還說,反正小黑是隻流浪狗,在社區流浪或是在市區流浪,都是一樣。
我當場愣在那裡,心想不一樣,不一樣。假若牠沒有產生過對人的任何信賴,那或許是一樣,當牠的腸子被蛔蟲漲破而死亡時,心中一定是充滿了恨意,這也就算了,但是小黑的情形絕對不一樣。一頭沒被人關愛過的狗,只因為人們一時的心軟,施捨牠一些食物,於是從對人的不信賴慢慢地開始發展出對人的依賴,甚至於想用盡全力來報答人們的關懷,正當此際牠竟然被最信賴的人背叛,而且被強制地驅離牠已經視為是自己家園的地盤,再度地面對沒有食物沒有水的生活。不知牠可不可以撐過這一次的災難,不知牠還會不會再度信賴人類。想到這裡,除了唾棄人類的自私外,我和我太太不禁一陣鼻酸。阿弟在身邊一直不肯安靜下來,催我快點帶牠到籃球場玩球,我低下身來狠狠地打了一下阿弟的頭,對著這隻曾經是成功國宅的流浪狗,但現在卻生活在天堂的可卡,呢喃了一句:臭弟你可真幸福。而手上拎著的中秋節禮物,晃蕩著、晃蕩著,不知怎麼地好像是飄散出陣陣諷刺的味道。
我的專攻不是少年事件處理法,只不過回國後不久就玩票性質地寫了一篇少年事件處理法的文章,而且也因為機緣而參與了新少年事件處理法的訂定工作,十年下來不僅是累積了一些的文章,甚且還自大地干預了實務的運作。回想起來,我不禁冒了一身冷汗,環視這個悲哀的社會,我的所作所為豈不就像是那位警衛。向少年提供了人際關係中的信賴契機後,再無情地將他拋擲到冷漠的社會,讓他再度地嘗受到人際的冷酷。
或許我應該更加深切地去體認矯正學校裡某位老師的心情,當她將少年送出學校的瞬間,看著少年的背影,想著日前奮力聯絡社會資源時的無奈與因為過度熱心而遭到政風調查時的憤怒,她心中的絞痛,應該是難以言喻。或許我也應該更深入地去理解某位少年司法人員,當他打完電話給更生保護會後,口吐穢言時的心情。或許我更應該公布,將矯正學校出校生編入資優班,逼他再度中輟的國中校名,或那位在研討會上揚言要盡有生之年的餘力把矯正學校搞垮的學者姓名,讓大家來唾棄這群教育人員。但是我太懦弱、太鄉愿了,連這些事情都沒有做到。這個社會真的是有夠冷酷,而我就是加深少年對這種冷酷的體認的一份子,給他們一點的希望,然後殘酷地利用社會現實來讓他們產生再度被拋棄的感覺。
有一位三年來只要我出國就會到我家照顧阿妹、阿白、阿弟的研究生家僮寫了一本碩士論文,名為修復性司法。他在結論時談論到我國曾經有過一個發展修復性司法的契機,這就是新少年事件處理法,不過因為理論過於深奧隱諱,所以始終無法將概念擴展到整個的刑事司法以及社會。我真的是錯了,學問上的傾向使得我不知不覺地就把新少年事件處理法當成是自己的東西,開始操弄自己的腦袋瓜,並且把昨天的自己當成敵人,不斷自娛地嘗試自我超越,不斷地在象牙塔中封閉自己,而忽略了到底社會中會有多少人想去花時間、精力來認識這種艱深的理論並產生反應。
九月十七日抽空拜訪高雄少年法院,晚間回到台北後,莊秋桃院長滔滔不絕地講述著少年法院同仁努力成果的身影一直不斷地困擾著我。我與她只見過兩次面,當然她沒看過我的文章,頂多只是看了一篇新聞報導而已。她不懂「我的」少年事件處理法,但是她努力地將「大家的」少年事件處理法,透過他們團隊的詮釋,傳遞到周邊的社會。玩弄自己學問的我,羞愧之餘,也開始反省到自己的自私。
今晚,在還有三篇本來就不應該答應的稿約惡夢般地在背後追趕的壓力下,我開始改寫以前的論文。如果可以完成,我會集結成冊,丟到社會中。不,只要完成一部分,我也會不畏羞愧地將未完成的作品投入冷漠的國度。在司法院沒有預算繼續新設專業的少年法院,在法務部沒有經費而決定中止輔育院的改制,甚至於扭曲現有矯正學校教學傾向,企圖將學校改成黑手訓練所的此刻,我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來破除自己的象牙塔了。
縱或是未完成的作品,應該也可以激起一點漣漪。企盼社會中會有人感受到這一點的漣漪,而願意向受過司法以及矯正處遇的犯罪少年伸出援手。給他一點的鼓勵、一點關懷,一句話或一個拍肩膀的動作,就能夠讓已經有一點信賴人際關係契機的少年,努力地、有尊嚴地活下去。就像是小黑一樣,雖然遭到創傷與背叛,但是往後只要機緣湊巧,可以斷續地獲得一丁點的關懷,應該就可以喚起牠的回憶,繼續有尊嚴地生存下去,而且對於那一丁點的關照,牠會用盡全力來回報。
或許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精神,並不是那些難解的用語與敘述,而在於二○○二年九月十六日晚間那一絲絲的鼻酸上。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
李茂生
2002年9月21日4:23AM
民國九十一年年初某個寒冷又下著小雨的星期天,小黑用著牠還能夠動的三條腿,一瘸一瘸地走到了新店一個小山坡上的社區。瘦瘦的身軀、淋溼的皮毛,在牠身體的左側還可以看到已經結疤的暗紅色傷痕。社區警衛偶而會將吃剩的便當給牠,而且警衛室的旁邊還有一個小池塘可以喝水,於是牠就住了下來。
我太太看牠可憐,於是開始間歇地弄些狗豆豆加雞肝給牠補身體。個把個月後,小黑的腿傷好了,細細的腿雖然還是有點瘸,但是已經可以用牠的三條半隻腿開始奔跑。我太太每晚遛狗的時候,都會帶一些食物出去,只要有看到小黑,總會分一點給牠。小黑警戒心很高,不喜歡靠近人,移動牠的食物時還會對人齜牙咧嘴地嗚嗚叫。不過牠對於第一次給牠食物的警衛,倒還頗親近的,只要那位先生值班,牠都會靜靜地躺在警衛室巡邏車的旁邊。
暑假到了,小黑日益活潑。晚上十一點警衛用巡邏車開始繞行社區的時候,如果有看到小黑尾隨在車子後面奮力地「巡邏」,我和我太太都會會心一笑,今晚又是那位警衛在值班。
開學的第一天九月十六日晚上,中秋節快到了,我太太準備了一些雞胸肉,想要讓社區內的流浪犬們補一補,小黃、賤狗大家都吃了,但是找來找去就是找不到小黑。我看到當晚的警衛就是那位經常餵食小黑的先生,於是走過去詢問小黑的蹤影。不料那名警衛回答說,昨晚深夜就把小黑圈起來,丟到中興路上了。他說,小黑不僅是會追摩托車,還會去咬騎摩托車的人,而且只要他去巡邏,小黑一定會跟,結果巡邏車所到之處,社區內其他家犬都會跟著狂吠,吵到社區安寧,大家抱怨連連,所以不得已只好把小黑弄離開這個社區。他還說,反正小黑是隻流浪狗,在社區流浪或是在市區流浪,都是一樣。
我當場愣在那裡,心想不一樣,不一樣。假若牠沒有產生過對人的任何信賴,那或許是一樣,當牠的腸子被蛔蟲漲破而死亡時,心中一定是充滿了恨意,這也就算了,但是小黑的情形絕對不一樣。一頭沒被人關愛過的狗,只因為人們一時的心軟,施捨牠一些食物,於是從對人的不信賴慢慢地開始發展出對人的依賴,甚至於想用盡全力來報答人們的關懷,正當此際牠竟然被最信賴的人背叛,而且被強制地驅離牠已經視為是自己家園的地盤,再度地面對沒有食物沒有水的生活。不知牠可不可以撐過這一次的災難,不知牠還會不會再度信賴人類。想到這裡,除了唾棄人類的自私外,我和我太太不禁一陣鼻酸。阿弟在身邊一直不肯安靜下來,催我快點帶牠到籃球場玩球,我低下身來狠狠地打了一下阿弟的頭,對著這隻曾經是成功國宅的流浪狗,但現在卻生活在天堂的可卡,呢喃了一句:臭弟你可真幸福。而手上拎著的中秋節禮物,晃蕩著、晃蕩著,不知怎麼地好像是飄散出陣陣諷刺的味道。
我的專攻不是少年事件處理法,只不過回國後不久就玩票性質地寫了一篇少年事件處理法的文章,而且也因為機緣而參與了新少年事件處理法的訂定工作,十年下來不僅是累積了一些的文章,甚且還自大地干預了實務的運作。回想起來,我不禁冒了一身冷汗,環視這個悲哀的社會,我的所作所為豈不就像是那位警衛。向少年提供了人際關係中的信賴契機後,再無情地將他拋擲到冷漠的社會,讓他再度地嘗受到人際的冷酷。
或許我應該更加深切地去體認矯正學校裡某位老師的心情,當她將少年送出學校的瞬間,看著少年的背影,想著日前奮力聯絡社會資源時的無奈與因為過度熱心而遭到政風調查時的憤怒,她心中的絞痛,應該是難以言喻。或許我也應該更深入地去理解某位少年司法人員,當他打完電話給更生保護會後,口吐穢言時的心情。或許我更應該公布,將矯正學校出校生編入資優班,逼他再度中輟的國中校名,或那位在研討會上揚言要盡有生之年的餘力把矯正學校搞垮的學者姓名,讓大家來唾棄這群教育人員。但是我太懦弱、太鄉愿了,連這些事情都沒有做到。這個社會真的是有夠冷酷,而我就是加深少年對這種冷酷的體認的一份子,給他們一點的希望,然後殘酷地利用社會現實來讓他們產生再度被拋棄的感覺。
有一位三年來只要我出國就會到我家照顧阿妹、阿白、阿弟的研究生家僮寫了一本碩士論文,名為修復性司法。他在結論時談論到我國曾經有過一個發展修復性司法的契機,這就是新少年事件處理法,不過因為理論過於深奧隱諱,所以始終無法將概念擴展到整個的刑事司法以及社會。我真的是錯了,學問上的傾向使得我不知不覺地就把新少年事件處理法當成是自己的東西,開始操弄自己的腦袋瓜,並且把昨天的自己當成敵人,不斷自娛地嘗試自我超越,不斷地在象牙塔中封閉自己,而忽略了到底社會中會有多少人想去花時間、精力來認識這種艱深的理論並產生反應。
九月十七日抽空拜訪高雄少年法院,晚間回到台北後,莊秋桃院長滔滔不絕地講述著少年法院同仁努力成果的身影一直不斷地困擾著我。我與她只見過兩次面,當然她沒看過我的文章,頂多只是看了一篇新聞報導而已。她不懂「我的」少年事件處理法,但是她努力地將「大家的」少年事件處理法,透過他們團隊的詮釋,傳遞到周邊的社會。玩弄自己學問的我,羞愧之餘,也開始反省到自己的自私。
今晚,在還有三篇本來就不應該答應的稿約惡夢般地在背後追趕的壓力下,我開始改寫以前的論文。如果可以完成,我會集結成冊,丟到社會中。不,只要完成一部分,我也會不畏羞愧地將未完成的作品投入冷漠的國度。在司法院沒有預算繼續新設專業的少年法院,在法務部沒有經費而決定中止輔育院的改制,甚至於扭曲現有矯正學校教學傾向,企圖將學校改成黑手訓練所的此刻,我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來破除自己的象牙塔了。
縱或是未完成的作品,應該也可以激起一點漣漪。企盼社會中會有人感受到這一點的漣漪,而願意向受過司法以及矯正處遇的犯罪少年伸出援手。給他一點的鼓勵、一點關懷,一句話或一個拍肩膀的動作,就能夠讓已經有一點信賴人際關係契機的少年,努力地、有尊嚴地活下去。就像是小黑一樣,雖然遭到創傷與背叛,但是往後只要機緣湊巧,可以斷續地獲得一丁點的關懷,應該就可以喚起牠的回憶,繼續有尊嚴地生存下去,而且對於那一丁點的關照,牠會用盡全力來回報。
或許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精神,並不是那些難解的用語與敘述,而在於二○○二年九月十六日晚間那一絲絲的鼻酸上。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
李茂生
2002年9月21日4:23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