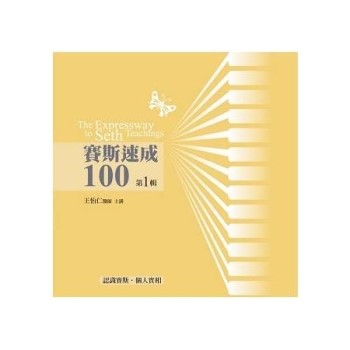序
夜舞復活後,方子淇最喜歡幹的事,就是跑到笑瞇瞇的鄭直同學身邊,問大家:「我跟鄭直看起來誰更正直?」
大家拚酒的拚酒,幹架的幹架,低頭擦著飛鏢的JFEE抬頭掃了兩人一眼,懶懶回答:「大概是你。」
子淇同學再跑到謝鄂同學身邊繼續問:「那我跟謝鄂看起來,誰更邪惡呢?」
這次答案倒是肯定的,眾人異口同聲回答:「當然還是你。」
得到滿意的答案,方子淇滿足地跑回范子郗身邊比手劃腳,向他炫耀自己比『正直』更正直比『邪惡』更邪惡。
黃昏的山道,夕陽餘暉層林漾彩。熾艷的晚霞拖著明朗天空往黑暗漫步滑舞,自美好回過神時,黑暗已取代光明。
謝鄂坐在欄杆上對著夕陽,餘暉脈脈,拂照在他有點淺的髮色上漾出金澤。
鄭直提了罐啤酒走到他身邊坐下,自己喝了口,勾住他的脖子笑嘻嘻將酒往他嘴裡灌。
「這樣的天氣,讓我想起……」謝鄂就著這姿勢喝了大半罐,直到鄭直盡興不再灌他,這才從鄭直手中接過酒瓶端正地拿在手上。
「真巧,我也想起……」鄭直胳膊繼續架在謝鄂肩上,眉開眼笑地瞄著。
兩人對看了眼,異口不同聲:「我們第一次見面就在傍晚(陽臺上的小花需要澆水了。)。」
一模一樣的十一個字,字字不同音,話音落下的同時,兩人一臉黑線。
鄭直抱怨道:「你都跟我混這麼久,為什麼還是一點默契都沒有?」
「真是抱歉,我沒想到你突然會想到陽臺上的小花。」
「想到小花又怎麼樣,好歹我也有為它澆過水。」
「……」
「你想說什麼,雖然水澆多了點,但它還活著不是嘛。」
「……你說得是。」
「所以囉,我想到小花很正常,對不對?」
謝鄂一臉為難地看著他,不確定要不要表達反對的意見。
眼見兩人還要糾纏下去,方子淇從子郗身邊探頭說了聲:「鄭哥,你們沒默契正常啦,畢竟你們本質就完全不同。」
「什麼本質(哪裡正常)?」兩人再次展示自己的無默契。
方子淇聳了聳肩:「不就是正邪不兩立嗎?」
「是鄭謝不兩立!」非常難得地,這次兩人終於發出字數與內容完全一樣的反對聲。
第一章 鄭直是個混蛋
每個人的名字,或多或少都寄託著最初時家長對他們的期待。要嘛翻遍字典雜書;要嘛問全周圍親友,再麻煩點就是找算命的按五行互補起個上上大吉的名字。總之,從孩子出生到正式在戶籍上記下名字,就是個兵荒馬亂爭論不休的過程。
不過,寄託了家長這麼多心血而出現的名字,有時也會出現意外的悲劇。
鄭直同學的名字起得非常順利。他家是警察世家,從爺爺到父親都是警界中流砥柱,七親八戚也全是法律相關行業的。公正嚴謹,端方清白,沒有差錯的話,會一直保持這端方清白的傳統直到世界末日。
所以大家日後想來最不明白的就是,這麼正直的遺傳基因到底哪個地方拐了個不小的彎兒?
鄭直同學從很小很小還沒來得及進行任何學前教育時,就展現他欺男霸女欺街霸市的優良風格。再大點,鄭家的鐵門更是多次被上門告狀的人砸壞。人數多到什麼程度?如果當天上門告狀的只有兩三人的話,鄭爸爸就要擔心鄭直同學是不是生病了,才這麼精神不濟。
如果說鄭直這樣不正直的人生中,曾帶給別人什麼好處,那個人一定是他弟弟。鄭家二公子出生時,鄭直小朋友不正直指數正達到顛峰,被他老爸拿了把太極劍追得雞飛狗跳。聽聞二兒子出生,鄭爸爸看著已經跑遠的前車之鑒,果斷放棄了結婚時為二公子準備好的鄭義之名──開玩笑,有個不正直的,至少還不犯法。要再來個不正義的,他拿什麼面子去對九泉下端方清白的公伯祖先。
鄭直每每說起這事,總一定要敲鄭漠一頓飯。鄭漠摸著癟癟的錢包,心碎哭訴:「我寧可當初英勇就『義』!」
謝鄂同學那邊又是另一回事。謝同學是他媽媽四十歲時生下的,頭上三個哥哥兩個姐姐,最大的哥哥比他大十三歲,最小的姐姐也比他大了六歲。可以說,謝同學出生前,他父母已經不打算再要小孩,他是個在誤打誤撞的情況下意外來到世上的生命。
雖然是意外,卻不等於不受歡迎。自古皇帝疼么兒,最小的孩子本便是最受寵的。謝媽媽老蚌生珠,對么兒疼愛不提,謝爸爸想到老婆高齡孕婦一路養胎直到平安生產的艱辛,也是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裡怕化了。幾個哥哥姐姐從半大人到半小孩都有,對這突然出現的弟弟,基本都是抱著標準以上的好奇。謝小朋友從出生就是萬眾注焦的目標,為了給他起個好名字,大哥翻字典二哥抓鬮,大姐看荷馬二姐誦楚辭。小弟陪著爸媽聽算命先生怎麼說,這個不好聽那個不好看,否決了一大堆。眼見百日就要到了大家意見還不能統一,大姐以她未來一家之主的氣勢『啪』地一聲將詩經摔在桌上:「就這個吧!」
那是首《棠棣》。
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美好的祝願。
於是,謝鄂小朋友的名字就在他大姐一捶定音下決定了。
從小被當寶貝寵的謝鄂同學,以辜負他『邪惡』名字的端正態度過著純良的人生,直到十七歲那年,他轉學到楊基高校。
--------
謝鄂轉學到楊基第一天,受到大家熱烈的歡迎。
第一節下課後,從別的教室跑來看他的同學一批又一批。以至晚一點來的人根本不用問哪個是『邪惡』,只要看到人群重重包圍,就知道中間那個男孩就是大家在找的目標。從顏色稍淺的清爽頭髮到線條柔和的側面輪廓,乾淨整齊得不像男生的穿著以及從頭保持到尾的笑容,打量完後大家紛紛搖頭。刻薄點的說笑得真傻;善良點的說看起來很純良;憂心忡忡的說謝同學你要多小心啊;興災樂禍的說哎呀有好戲看了。
謝鄂因為自己的名字,被人圍觀已經習慣,每次換了新學校後,總免不了這種騷動。但楊基的騷動似乎有點不正常,大家參觀完後,總要加上一句:你多保重。
保重?保重什麼?謝鄂想問卻沒來得及。上課鈴響,圍觀的人潮像退潮一樣散下去,講台上老師拿著課本皺著眉。
謝鄂同學只能用最無辜和最無奈的眼神回看他。
一個上午都被人用各色同情的目光觀賞,謝鄂保持風度掛著微笑,心下的不解卻如貓撓毛團越撓越大團。眼見要午休了,大家在收拾桌面。他第一時間拉住旁邊合上課本的同學,眼睛飛快瞄了下書本上的名字:「成同學,你好。」
成聶吃了一驚,險些抽回手。乾笑兩聲:「謝同學你好,謝同學再見。」
「等等,我有問題想問一下。」眼見成聶想跑,謝鄂忙加重手上力道不讓他抽身:「就一個問題。」
「過幾天你要沒事,幾個問題都行,現在你就饒了我吧。」成聶眼見周圍同學不管有帶便當的還是沒帶便當的都跑光了,不由苦下臉。
「為什麼?」謝鄂固執地抓著不放。
「萬一被人看到,以為我和你是一夥,我說不定就慘了。」
「和我一夥不好嗎?」謝鄂有些受傷地垂下眼,溫和的臉上第一次失去了笑容而顯得黯然。
成聶心裡突然升起了點點罪惡感,對於看起來純良的事物,人們總會多些不忍與寬容:「也……也不是那麼不好。」
「那是為什麼?」
「你錄音機啊!」
謝鄂專注地看著他,充滿了求教的信任。
被這種目光看久了,心中會浮起很多的罪惡感──就像看一隻被人拋棄的小貓或者是一隻等著餵食的小狗?拒絕了會良心不安背後發麻的。
成聶覺得自己還是很有良心的人,為此感動地歎了口氣:「你先放開我,我就告訴你。」
「好。」謝鄂連猶豫都沒有,馬上放開手。
這麼快?轉了轉被握得生痛的手腕,再看謝鄂不知像小貓多還是像小狗多的眼神,本來想藉機溜走的腳步變得有些困難。腳尖在地面磨了磨,不自在地咳了幾聲,索性一屁股坐回椅子上嘀咕道:「我說你這邪惡的名字根本就是起錯了。」
「對不起,大家都這樣說。」謝鄂有些歉意。很多人都說過,類似本來期待見到一個邪惡大魔王結果是隻純良兔子的心情實在讓人洩氣。
「楊基這裡也有個跟你一樣,大家說名字起錯的人。」
「跟我一樣的人?」
「他叫鄭直。」
「正直?他很壞?」
「他壞不壞不是重點,重點是,他是楊基的地下老大。現在你明白了吧?」
「……不明白。」謝鄂搖頭。
「你白癡啊!」成聶受不了地拍了下他的額頭:「他叫正直你叫邪惡,從名字上聽你們就是天敵,大家都在傳說,邪惡將壓倒正直……」
「應該是邪不勝正。」謝鄂指正。
「多謝指正。」成聶用力戳著他的額頭:「不過誰管你們正邪哪個贏,重要的是,鄭直是老大,所以,他一定會給你點顏色看。誰讓你什麼名字不好起,偏偏起了個跟他犯沖犯忌的。」
「名字不是我能選擇的。」謝鄂歎了口氣。如果他能選擇,如果他有時光機,他一定會回到那個一捶定音的時刻,改變這個從小到大給自己惹了無數麻煩的名字:「謝謝你的說明,如果會給你帶來麻煩,我一定會幫你解釋,證明你我之間不是一夥沒有關係。」
同學!什麼叫越描越黑你懂不懂!?
成聶瞪了謝鄂半天,洩氣地搖搖頭,「隨便你,我走了。」
--------
謝鄂轉學第一天,在校園裡意外平安地度過了。傳說中是他天敵的那人好像有事沒來學校,所以大家頂多過來觀望觀望。
──老大沒下令,小弟們也不敢冒然生事。撥了大哥的頭籌,難說是禍是福。
放學後,謝鄂慢吞吞收拾書包,掛了一天的燦爛笑容漸漸有點黯淡。
很少被人這樣明顯的排斥著……
不過,才只是第一天,慢慢會沒事的。
他對自己點了點頭。
還有,那位鄭直到底是怎麼樣的人?為什麼一提到他大家都禁聲不談?要在楊基這樣一所學校當上老大,他的體格一定很出眾,不知像輕量級的還是重量級的?萬一他真要揍自己……
討厭暴力的謝鄂思考得很嚴肅──要不要準備防狼電棒?或者哨子?還是辣椒水?
「你是今天新來的轉校生?」
謝鄂抬頭,一個身形高大魁梧,完全符合他想像中楊基地下老大的光頭男孩帶著五六個同伴擋在他前面。校服鬆垮地套著,下擺露出一截白襯衫也不知沾了什麼,色彩詭異。眉毛比眼睛粗,正斜著瞇瞇眼睨視自己。
再看看周圍,好像是個巷子,不大也不深,可是看到這架式,本來要進巷子的人都轉身退出去。
「你就是鄭直同學?」謝鄂試探地問。
光頭與其他幾人對看了眼,粗眉皺得更深:「大爺手上不便,缺了點錢,你識相地就好好孝敬大爺,這樣才能在楊基待下去。」
「果然是勒索。」謝鄂歎氣:「這麼明目張膽,不怕進警察局?」
「嘿,要論關係,從上到下哪個派部的不稱我們老大一聲大少,誰敢對他動手。」旁邊的小弟得意洋洋,往前邁了兩三步,順腳踢開路邊一塊擋道的石頭。石頭骨碌碌滾開兩三米,撞倒了不知是誰擱在路邊的紙箱,紙箱一歪,紙箱上的竹竿掉了下來,乒乒乓乓一連串聲響,動靜大得巷頭巷尾都有人探頭看過來。
不太想跟這些人動手,謝鄂有些苦惱地思考要不要趁亂跑到大街上去喊救命。
「你這笨蛋,搞什麼鬼!」同樣被動靜嚇到的光頭揍了同伴一記響頭。
「老……老大。」光頭身後脫染成紅髮的小弟驚叫了聲:「你看……」
掉開的竹竿後面還有箱子,箱子上坐了個男孩,正懶洋洋地看著大家。
城市裡的光線並不好,夕陽照進小巷,光波在空氣中折過幾折,只剩黯淡的殘影。謝鄂轉向黑暗而急劇收縮的瞳孔中,只看到男孩頭髮顏色非常地黑,純粹的鴉色。
他後來才想到,那是因為男孩皮膚特別白,才襯得頭髮特別黑,左耳上掛著個鮮紅的流蘇墜子。黑、紅、白三色都是極為純粹的色彩,一時間,除了這三種顏色外,再沒有其他印象。
「是……是你!」光頭口吃。
「是我。」男孩搖了搖頭:「真是不幸。」
「我們走!」光頭被針扎到一樣馬上轉身跑走,理也不理待在一旁的謝鄂。
這男孩是誰?居然能讓楊基地下老大一句廢話都不敢多說就跑了?謝鄂張大嘴。
男孩轉頭打量他:「他剛才在勒索你?」
「呃,是的。」
「我救了你?」
「非常感謝……」謝鄂還想說,被男孩打斷。
「說謝沒用,要用行動報答我才行。」他招招手,示意謝鄂過來。
這個人……應該不是壞人吧?謝鄂有些忐忑。
能嚇走惡人的,只有比他更惡的人,可是眼前這比大多數學生都更乾淨清爽的俊美少年……怎麼看也不像惡人。
小心地走過去,保持著隨時可以逃之迢迢的姿勢:「你也要錢?」
「我不要錢。」男孩修長的手指抓住謝鄂的手,掌心很冰涼:「我只要你。」
??????!!!!!!!!
謝鄂心中升起了一整排的問號和驚歎號。
「──陪我去吃蛋糕。我低血糖,頭暈,走不動。」男孩有氣無力地說。
!!!!!!!!!!!!!!!!!
謝鄂同學扯下前面掛著問號,心中再次升起了一整排的驚歎號。
--------
「謝謝你的蛋糕,真是美味。」桌面上擺了六七種不同口味的甜點,從藍莓芝士到櫻桃慕斯到牛奶布丁杯都有,男孩揮舞叉子以一種奇妙的速度將蛋糕從桌面轉移到嘴裡。
明明動作不算很快,可是蛋糕為什麼消失得這麼快?謝鄂捧了杯冰綠茶,摸不透其中竅門。
「你不吃呀?很好吃~」男孩拿著叉子指指桌上的流淌著濃香醬汁的核桃巧克力。
看起來就非常黏牙甜膩的甜品讓謝鄂第一時間搖頭:「我不喜歡吃甜食。」
「這年頭,喜歡吃甜的男人是不是比恐龍還稀有?」男孩哀歎搖頭,耳朵上鮮紅的流蘇耳墜隨著他的動作一晃一晃,晃得人難以專心。
「不會那麼少的。」謝鄂想了想:「我想總有蘇門答臘虎的數量多吧。」
「蘇門答臘虎?」
「嗯,目前野生的大概還有二十隻。」
男孩被慕斯嗆到,直瞪謝鄂,謝鄂無辜地回看他。
看男孩吃完最後一口香蕉派,謝鄂也放下杯子,正要叫服務生買單,男孩手一舉:「小姐,再給我一份超大的抹茶紅豆冰。」
他解釋說:「你剛才讓我嗆了下,有口蛋糕沒吃到。」
謝鄂看著桌上滿滿的空盤子,再看看旁邊柱子上綿綿冰的廣告照片,也扶著額頭舉手:「小姐,給我續杯水。」
等待綿綿冰製作過程,嘴巴閒下來的男孩終於有興趣問對方名字:「看你校服,你是楊基新來的轉校生吧?我以前沒見過你。」說到這,頓了頓,想到還沒自我介紹。
「對了,我叫鄭直。」
這次換謝鄂被水嗆到。
--------
在謝鄂嗆咳的同時,抹茶紅豆冰送上來,於是鄭直暫時忘了追問謝鄂的名字,繼續埋頭苦吃。
謝鄂連灌好幾口水鎮壓還處於敏感狀態的氣管,緩過氣來才有空打量鄭直。
這位……就是傳說中惡人裡的惡人,楊基的地下老大,害自己被同學圍觀了一天,還差點被人勒索的罪魁禍首?
謝鄂看著吃得眉開眼笑心滿意足的鄭直,深深有種自己被人欺騙的感覺。那耳朵上晃來晃去的鮮紅耳墜,簡直像在拚命搖尾巴的小狗。
小狗吃完紅豆冰,抬起頭,一點紅豆糖漬沾在潔白的臉頰上,自身卻完全沒有察覺。
看不過眼的謝鄂從口袋裡掏出疊得整整齊齊的手帕,習慣性地為他擦去。
「嗯?」冒然的舉止讓兩人都怔了下。
謝鄂額上沁出細細的冷汗。
壞了,眼前這人是楊基地下老大,不該覺得他像小狗就真的拿他當小狗看。
「你臉上沾了紅豆漬。」
鄭直眨了下眼,流蘇墜子又開始搖晃了。
「哎呀,你可真是好人~為了表示感謝,我請你吃拉麵吧!」
還……還要吃啊?!買完單被鄭直拖著跌跌撞撞出了蛋糕店的謝鄂忍不住上下打量男孩,看他到底把剛才吃的東西都吞進哪個異次元。
------
「雞蛋仔,來碗牛肉拉麵。」衝進店裡嚷嚷的鄭直叫完,看見有人結帳離開,忙將被他拉扯得眼花的謝鄂再扯過去往座位上一塞,自己竄回櫃檯前:「還要五串烤牛舌,五串烤香菇,五串梅子醬燒雞肉,兩串烤白果……對了,你要什麼?」
他回頭朝謝鄂大聲問。
謝鄂才坐下就聽他又點了一連串食物,不由呆木,被他問話才手忙腳亂地拿起菜卡:「……牛肉拉麵就好。」
「再加一碗牛肉拉麵。」
廚房的遮簾掀開,戴著工作帽的工讀生有著尖長的額頭和圓圓的眼晴,看起來像枚倒置的雞蛋。他拿起本子一邊嫻熟地記單一邊問:「鄭哥,你今天點得不多,在外面吃過了?」
「我在外面吃過了還來你這捧場,你感動不?」鄭直有些無賴地趴在櫃檯上笑。
「感動感動,你要能把之前欠的債一起還了,我更感動。」
「這話什麼意思,我會賴你不成?」鄭直捶了他的肩膀一記,從櫃檯後面拎了兩盤小菜:「這算送我們了?」
「鄭哥……」雞蛋仔苦下臉,又不敢反對,歎了口氣,邊記邊說:「是是,這兩盤我請你。」
鄭直點的拉麵很快就送上來,他大方向謝鄂推薦:「這家拉麵很好吃~這個不是甜的,你總該喜歡。」
謝鄂嘗了幾口,湯汁濃醇甘辣,麵也壓得很有彈性,充滿嚼勁。肉塊燉得極有火候,挾起時碎而不散,入口酥爛綿軟又入味,異常鮮美,當下也大點其頭:「好吃!」
「是吧。」鄭直笑瞇了眼,像隻滿足的大貓,一邊吃一邊從碗裡小心挑出蔥花。
「你不喜歡吃?」謝鄂不明白他既然不喜歡剛才幹嘛要灑上。
「就是不喜歡吃。」鄭直笑嘻嘻將挑出的蔥花往謝鄂碗裡倒去,還將調羹筷子順便往他湯裡洗一下,洗掉上面沾的蔥花:「你喜歡那就給你吃。」
我……我也不喜歡啊!謝鄂的臉小白了下,看碗裡厚厚的兩層蔥花,再看看一臉若無其事的鄭直,鬱悶地用筷子小心撥開。
鄭直唏哩嘩啦扒完拉麵,開始吃剛送過來的烤牛舌和香菇。謝鄂努力撇開湯上浮著的蔥花,慢吞吞地喝著湯,看著鄭直的目光像在看怪獸──他的胃到底有幾次元?
「烤牛舌也很美味,你要不要嘗嘗?」鄭直慇勤地遞了串烤牛舌給他,禮儀周到怕他拒絕一般直接肉送到他嘴邊就要塞進他嘴裡,嚇得謝鄂忙伸手擋下:「我自己來就好。」
牛舌烤得柔軟甘醇,上面的調醬辛辣微酸,隱隱有檸檬的香氣。謝鄂吃得不住點頭。
「要不要再點幾串?」鄭直歪頭看著他。
「不不,我吃飽了。」拉麵加牛舌,已經八分飽了。小哥教育的養生之道,飯不可吃至十分飽。
「去,才這麼點,再吃再吃。」鄭直一把按下他:「雞蛋仔,再加五串烤牛舌,十串烤板筋,五串青瓜……」
有點……誤上賊船的感覺。
謝鄂撫著胃歎氣。
不是有點誤上賊船,而是真的上了賊船。謝鄂在心底更正自己。
好不容易把桌面上的東西都消化掉,茶都來不及喝一口,雞蛋仔已經眼疾腳快地跑過來:「鄭哥吃飽了要買單是吧,這就來。」
「雞蛋仔,鄭哥現在手頭不便,先記下。」
「鄭哥,你已經記了十次帳了,該清了。」雞蛋仔笑得有點僵。
「該清,當然該清。不過鄭哥今天忘了帶錢包,別小氣,再記一次吧。」
「鄭哥,我們拉麵店小利潤又薄,經不起你這麼欠啊。」
「好兄弟就不該這麼計較。」
眼見兩人還要推託下去,不習慣吃白食的謝鄂不自在地咳了聲:「我來付好了。」
「這怎麼好意思。」鄭直雙手抱胸笑嘻嘻地說著,雞蛋仔則飛快將帳單塞到謝鄂手上:「承惠承惠。」
謝鄂掃了眼,四位數的金額晃得他眼花:「怎麼這麼多。」
「這是鄭哥記了十次帳的總額。」雞蛋仔露出八顆牙齒的職業微笑:「這位同學,現金不足的話沒關係,本店有POS機可提供貴賓刷卡。」
──這是賊船!
謝鄂下了定義。
--------
結了帳出來,進店前天際僅餘的一抹亮光也被黑暗取代。鄭直伸了個懶腰:「啊,吃飽了。」
終於吃飽了嗎……已經無力吐槽的謝鄂將收據塞進錢包,想回去。
鄭直回過身來,眼神亮晶晶的:「吃飽了就該有夜生活。為了表示感謝,我請你去泡吧。」
謝鄂現在一聽個請字就頭皮發麻,飛快地搖頭:「不用不用。」
「沒事,這次真的是我請,去我朋友店裡泡吧不收錢。」鄭直不容分說拖著他走到街口,伸手招下一輛計程車,將人塞了進去:「勞駕,藏地BAR。」
「我……剛才那家拉麵店不也是你朋友的……」謝鄂完全不信眼前這個笑得彷彿很天真的傢伙。
「NONONO,雞蛋仔只是我學弟,在那裡打工而已。」鄭直大力拍著謝鄂肩膀,哈哈大笑:「放心,這次真的不會讓你出半分錢的。」
----------
從傍晚認識鄭直以來,謝鄂就一直處在後悔的狀態,現在也不例外。
他覺得自己比較希望去能讓他花錢的地方,而不是待在這個免費的地方。
藏地BAR跟它的名字一樣,藏在地下二層,排氣不好,室內煙霧縈繞,濛濛的乾冰包捲著菸、酒、香水、汗水以及種種可言不可言的氣味。進來不到一分鐘謝鄂就覺得暈頭轉向呼吸困難。而周圍閃爍不停的光線和震耳欲聾的音響,還有打扮得恍如群魔亂舞的男女,都讓他頭痛欲裂。
鄭直在這裡卻混得如魚得水,一進來便不停有人向他打招呼,隨後就被人拉入舞池中,從爵士舞到貼面舞,高《身兆》的身形像條滑魚一樣不斷游移在人群之間,煽動著共舞者的慾望。
謝鄂被扔在一旁,待了幾分鐘後,見鄭直在舞池裡好像沒空顧及到自己,正想趁這機會離開藏地,卻被人拍了下肩膀:「你是小鄭帶來的吧?」
謝鄂回過頭,是位二十來歲的女性,渾身上下洋溢著飽滿得幾乎要流淌出汁液的性感氣息,深灰的眼影媚意橫斜,雙手抱在胸前,將原本就很偉大的胸懷烘托得更是觸目驚心。
謝鄂小退一步,離開女人荷爾蒙的捕獵範圍,小心回答:「我跟他今天才認識。」
「瞧這小臉嚇得,我會吃了你不成?」女人覺得有趣,又逼近一步:「叫我Anne姐。」
「很高興認識妳,Anne姐。」謝鄂笑得有點勉強:「我有事要先走了,再見。」
「別這麼快就走。小鄭很少帶人過來,大家都很好奇。」Anne姐伸手拉住他的手,冰涼細膩的指端摩挲著他的掌心指縫,蜿蔓而上,他有種自己被蛇纏上的驚悚感,差點摔開她的手。
「對不起,我跟他真的不熟。」
「這地方哪個人跟別人是熟的?不用太熟。」Anne姐趴在他耳畔輕笑,濃郁的香水味讓他狠狠打了個噴嚏。
「對不起,我……」
「我什麼我。」一支瘦削有力的胳膊從後面勾過來,鄭直不知什麼時候從舞池裡脫身,手上端了一罐啤酒,笑嘻嘻往謝鄂嘴裡灌:「來,Anne姐請你的,喝一口。」
「等等……」謝鄂慌忙躲避著:「我還未成年……」
「不是這麼挫吧,來來。」鄭直抬手勾住他的脖子單手捏住他下巴,繼續將酒往他嘴裡灌。
掙扎中,有幾滴酒液濺上嘴唇,冰冷苦澀,而大部分酒液則順著下巴線條流進校服領口。謝鄂又驚又怒,用力推開鄭直:「鄭直!」
「哈哈哈哈~」鄭直鬆開手不再繼續灌他,給自己喝了一口,放肆地笑著。五顏六色的鐳射光照不明他的臉,只照出耳上血紅的墜子一晃一晃,宛如催眠。「果然是好孩子。」
「我喜歡好孩子。」Anne姐雙手抱胸在旁笑吟吟地贊成。
伸手抹了把臉上和脖子上的酒液,謝鄂沉下臉:「我先回去了。」
「你衣服都溼了,不用在這裡換一件嗎?」鄭直勾了勾他的校服外套,又勾了勾他的領帶,瞇眼嘖了聲:「都溼了。」
很正常又很下流的對話,聽懂的人都曖昧地笑了起來。
謝鄂僵硬地拉回自己領帶:「不用了,再見。」
「好吧,再見。」鄭直將下巴墊在他溼透的頸窩,側著頭笑道:「謝鄂同學,明天見。」
「你……」溼熱的氣息含著淡淡的酒氣,噴在耳垂上又熱又癢,以至謝鄂慢了一拍才反應過來。「你晚上是故意的!」
鄭直揮揮手,繼續放肆地笑著。
「我難得給人請客的機會,不客氣~」
----------
走出藏地BAR,夜風一吹,溼答答的領子帶了些冷意,也讓謝鄂在酒吧裡被薰得暈沉的神智為之一清。
深吸口充滿汔車廢氣和塵埃的城市空氣,從來沒有這麼懷念過。
晃了晃腦袋,拍拍臉,謝鄂確定了一件事。
鄭直就是個混蛋。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正邪不兩立(上冊)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正邪不兩立(上冊)
老天究竟是哪裡搞錯了呢?
出身員警世家的鄭直同學,
跟「正直」二字沾不上一點邊,
從小展現的就是街頭小霸王的性格。
另一個意外來到的謝鄂同學,
過著辜負「邪惡」之名的人生,
純良、端正到像個會走動的教科書。
當「邪惡」遇上「正直」,人人都在猜,
究竟是正不勝邪?或者邪不勝正呢?
意外的是--單純的小白兔竟然敢捋虎鬚!
章節試閱
序
夜舞復活後,方子淇最喜歡幹的事,就是跑到笑瞇瞇的鄭直同學身邊,問大家:「我跟鄭直看起來誰更正直?」
大家拚酒的拚酒,幹架的幹架,低頭擦著飛鏢的JFEE抬頭掃了兩人一眼,懶懶回答:「大概是你。」
子淇同學再跑到謝鄂同學身邊繼續問:「那我跟謝鄂看起來,誰更邪惡呢?」
這次答案倒是肯定的,眾人異口同聲回答:「當然還是你。」
得到滿意的答案,方子淇滿足地跑回范子郗身邊比手劃腳,向他炫耀自己比『正直』更正直比『邪惡』更邪惡。
黃昏的山道,夕陽餘暉層林漾彩。熾艷的晚霞拖著明朗天空往黑暗漫步滑舞,自美好回過神...
夜舞復活後,方子淇最喜歡幹的事,就是跑到笑瞇瞇的鄭直同學身邊,問大家:「我跟鄭直看起來誰更正直?」
大家拚酒的拚酒,幹架的幹架,低頭擦著飛鏢的JFEE抬頭掃了兩人一眼,懶懶回答:「大概是你。」
子淇同學再跑到謝鄂同學身邊繼續問:「那我跟謝鄂看起來,誰更邪惡呢?」
這次答案倒是肯定的,眾人異口同聲回答:「當然還是你。」
得到滿意的答案,方子淇滿足地跑回范子郗身邊比手劃腳,向他炫耀自己比『正直』更正直比『邪惡』更邪惡。
黃昏的山道,夕陽餘暉層林漾彩。熾艷的晚霞拖著明朗天空往黑暗漫步滑舞,自美好回過神...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清靜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08-23 ISBN/ISSN:978986296038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